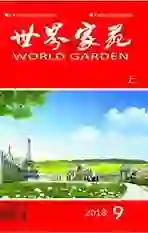从《广艺舟双楫》浅论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2018-09-18宋婷婷
宋婷婷
摘 要: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一部在中国书法史上极有理论特色的著作。书中集中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他在政治上的观念对书学影响甚大,并在其书学思想及实践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康有为书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以退为进的原则,着眼于书法艺术的表现性特征,确立了以变为核心的基本内容。欲用多变的体势,取代陈旧保守的书风,意在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倡导,进行书风的改良。因而提出了“尊卑抑帖,重魏卑唐”的根本主张。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学思想;变;碑;帖
康有为的书论主要见于《广艺舟双楫》,这是晚清碑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本书学著作。全书虽然是在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但它是有计划、有体系、一气呵成地写就的,这一点,与包世臣将平日零碎的信札、论文辑录成《艺舟双楫》完全不同。康氏通过自己大量收集评骘汉魏六朝碑刻的经验,于前人之说颇多匡正,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新见,遂写成这部六万余字的论书名著。全书除去《自叙》一篇之外,共六卷二十七章,卷一、卷二论书体源流,卷三、卷四评骘历代碑版,卷五、卷六讨论笔墨技巧与学书经验。全书虽涉及之面极广,然要在通过尊卑抑帖而体现了他的变法求新的思想。
一、求变思想
贯穿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思想可一言以蔽之曰:变。康有为以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他于书中第一章《原书》中就指出:“变者,天也。”以为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规律,它是出于自然,不可更易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各种书体发展的认识之中。他说:“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人由于天生的灵智,不仅能创造文字,而且一定会发展文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康氏甚至举西洋文字发展的例字来说明这一道理,英、法、德、俄的文字各异,“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篆、籀、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康氏对西洋文字的演变过程虽然说得未必正确,然其主张发展变化的观点于此可见。
他以为文字之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人情趋简的规律,因为人心无不厌恶繁难而喜欢简便,所以人类的各种器具都表现出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书体由篆到隶,由隶变为真、草,由真、草变为行书,正是这样。由此,康氏肯定了后起之书较为便捷容易的特点。他说:“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致速,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这种进化的发展观在当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他的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的体现。康氏以此来分析考察中国书学,遂得出书法必将有所新变的结论,他说:“综而论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 书法艺术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因时而易,变法、创新的历史。只有变,才有创造,才有新意,才有价值,才能传之久远,留之后人,确立自己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这一点,书法与政治上的变法有相同的规律。在政治上,往往“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胜,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蔡襄)笃守旧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也开新之胜旧之证也 。”只有开新创造,才有希望,而他根据历史的经验预言书法必变,其言外之意正是说他自己所致力的就是一次书法的新变尝试,这种尝试具体地说便是他尊卑抑帖的主张。
康氏以这种“变”的书学思想来评价历代之书,故颇能看出发展的脉络,对于书史的理解就有不少精到的看法,为前人所未道。
二、尊卑抑帖思想
《广艺舟双楫》在书论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备了碑学的理论,它比阮元和包世臣的主张更为系统和完善,他修正了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以为“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故其论书不言南北而分碑帖,又于碑中分朝论之,重在南北朝时期的碑刻而鄙薄唐以后之碑。康氏对前代书法的评价可以概括成两句话:尊卑抑帖,重魏卑唐。
康氏之所以尊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康氏主变的观念来看,书体无时不在趋新,书法发展到清代后期,绵延千余年的帖学已为陈腐之物,故有识之士宜趋新求变,邓石如、包世臣等人找到了北碑作为改革帖学的武器,实际上正是古人的复古为通变的途径,也与康有为在政治上提倡“托古改制”的方法相类似。他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伊秉绶)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邓石如),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八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可见他以为碑学是一种兴起于晚近的意在变革陈腐之帖学的新风尚,故他反以效法晋、唐及宋、明人的帖学为“古学”,而以宗尚北魏、两汉碑版者为今学,他说:“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在新旧今古的抉择中康氏自然提倡新生的事物,故其力崇碑学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二)康氏以为纸帛易坏,故晋人之遗墨已难以见到,当时所传的晋人书帖不过是宋以后人双钩临摹的赝品,故羲、献的面目精神已不复可得,帖学大壞,至清而极,物极必反,故碑学之兴起,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三)康氏以为碑学之兴起与清代中后期的金石学之盛行与大批六朝碑版的出土有关。由于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一时研究金石碑版、搜讨摹拓碑刻之风大盛,如著名的学者孙星衍、林侗、武亿、王昶等都致力于金石之学,《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志》、《金石萃编》等著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于是导致了书法风气上的转学碑刻,康氏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故康氏之尊碑也是当时的学风使然。
康氏重南北朝之碑而鄙薄唐人之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从书法发展史上来看,南北朝之碑处于真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时期,它能兼备篆、隶之古朴醇厚,又不乏流宕飘逸之气,唐人之法即出于此,故学者宜取法乎上,舍唐而取南、北朝之碑,他于《购碑》中说:“购碑当知握要,亦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然而,在南、北朝碑中他尤重北魏之碑,这是因为北魏特定的历史环境所给于他得天独厚的优势:“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北魏社会的相对繁荣导致了书法艺术的繁荣,故北魏的楷书能包蕴众体,罗列万象,康氏称观北魏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二)从书法艺术的风格上看,南北朝之碑最富于各自的风格特征,包含了书法艺术各种不同的审美意趣。康有为认为,书法如同自然界山川的千姿百态一样,有的雄奇秀美,有的峻峭淡宕,各不相同,故他作《体系》、《导源》二章,将南、北朝个别分别标以不同的风格,并披枝见本,因流溯源,追溯到蔡邕、钟繇、卫恒等人之书,并将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乃至后来的苏东坡、赵孟頫、文征明、邓石如等历代书法家从属于南、北朝碑所体现的书法风格之下。这种见解未必客观,后来也屡遭人疵议,然康氏欲以南、北朝碑来统领各种书风的态度由此可见。
(三)康氏以为唐人之书本身失之呆板,加上名家之碑又多经摹拓翻刻,面目全非,故未可爱宝,《广艺舟双楫》中有《卑唐》一章即申述他的此种观点,其言曰:“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讲之尤甚。……而颜、柳迭秦,澌灭尽矣!”他以南北朝碑刻与唐人之書相比,则前者穷极变化,奇伟婉丽,后者呆若算子,缺乏变化。因而以为若欲学书,切不可由唐人入手。他又说:“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也以六朝碑刻与唐人碑刻相比,以为前者完好而后者失真,其间高下自见。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六朝之碑胜于唐以后书远甚,是习书者应取得途径。
康有为基于倡变、求新的价值取向,而力主碑学,反对帖学。他抑帖、反帖,正是因为他认为帖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滋生了一种保守、僵化、封闭的倾向。他说,帖学“昧于学古”,取法浅近,迎合时好,“徒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陈陈相因,涂涂如附”。这种批评,虽然尖锐,但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自晋代王羲之裁古铸今、变法“出新意”取得成功后,唐人便将其尊为“尽善尽美”的典型。王羲之的书法不仅成了唐人评价书法艺术价值高低的标准,也成了书法创造的起点。不学王书,便无立身之本。宋人则将颜真卿视为学王能变的楷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无不以学颜作根基。而元代则更以崇王复古为旗帜。及明、清之际,赵孟頫、董其昌两位学王书有成者,则交替风靡一时,成为楷模。在康有为看来,帖学书风的这种近取“俗字”、迎合时俗的做法,失去了古代书法风气纵向开拓的力度和深刻,已变为一种横向移植、缺少个性和创造的承袭与复归,陷入一代不如一代的困境,以至于使“今人日习院体”,而“不复自知”,弱化了艺术的创造性和表现力,甚至将书法艺术堕化为经世致用谋取功利的工具和手段,导致了大量的经生字、干禄书,和千人一面、万人同体、以“乌”“方”“光”为美的“馆阁体”,缺少“新理异态”,愈来愈趋于保守、封闭、僵化,而难以自拔。为此,康有为对兴起于清代咸、同之际的碑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碑学的成就,大加褒扬。他极力倡导碑学,提出书法要“本汉”、“宝南”、“备魏”、“取隋”。也即认为书法要以汉代为根本,汉代的书法气体高古,而且变化最多,汉人能尽变古人之书而自创新体,草书、飞白书、行书都由汉人首创,故汉之书法盛极一时。他还指出,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自吴碑《葛府君》、钟繇《力命表》诸帖始,至二王变化殆尽,并创立了法则。原因是汉代极讲书法,钟、王诸人皆取法汉魏间缪篆、隶法中的精品而加以变化,方取得极高的成就。王羲之说“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如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后人学王羲之字,《兰亭》、《圣教》烂熟,然而不知道王羲之字“结胎得力”的原因,所以只能平直如算筹而已。因此,学者要在楷书体上获得成功,一定要本原于汉,舍此则无蹊径可寻。其次,要博涉魏、晋、南北朝诸碑,观这些碑,使人“ 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道上”,凡后世之所有之体势无不备,凡后之所有意态无不有。若能“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二王之不可及处,不仅是因为其书法自身的雄奇超妙,而更在于他们取法古人,并能博涉诸家等等。
康有为对碑学的赞美和倡导,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康有为如此尊碑抑帖,倡导“学古”,并非是为了“复古”,或以古为美。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是它的土壤。”康有为倡导碑学与“学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和心态。他要使帖学披枝而见本,因流而溯源,寻找书法艺术发展的“武库”和“土壤 ”,并以此为根基、为前提,广开视野,探讨和寻找医治帖学保守、僵化、停滞、缺少新意的药方,开拓艺术创造的新境界 。“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久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则可使欧(阳询)虞(世南)抗行,褚(遂良)薛(稷)扶毂,鞭笞颜(真卿)柳(公权),而狎畜苏(东坡)黄(庭坚)矣,尚何赵(孟頫)董(其昌)之是云?”如此“复古”,虽导源于古人,实为别开新体,犹唐代人的律诗,虽源于古体,但音韵与其迥异;亦犹宋代人的四、六诗句,虽出于骈文,而“引缀绝珠”。由此可见,康有为所极力倡导的碑学,“复古”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和中介,而变革、创新,才是其根本要求和目的。他始终为书法的倡变、求新而鼓吹、呼吁,为超越帖学的束缚,批判帖学的保守、停滞、弱化的弊端寻找理论根据;以变和新,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我们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肯定他倡碑抑帖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这就是他尊卑抑帖,重魏卑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书论的核心所在。
康有为书学思想不仅仅体现于此,我仅就其中两点进行了浅要论述,因学识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总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对历代书法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检讨,其理论虽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个人好恶之感,然内容丰富,颇具新见,不失为书论史中之殿军。
参考文献
[1]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 [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2]刘恒.中国书法史(七卷本).[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4]刘文华.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与实践.[J].中国书法,1988.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