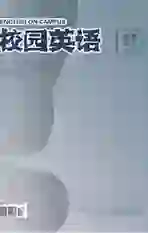英汉语法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基于小称范畴的考察
2018-06-30刘陈姣
【摘要】小称作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表达了人类的主观化情感。本文旨在对比英汉小称范畴的语法化进程,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出发,确定小称范畴语法化的来源,即汉语中的“Z变韵”其实是来自于“子”这个语素,特别是一些合口呼的字,在Z变韵时都加上了前高特征,这一特征应该是“-子”早期读音的反映和转化。从而证明汉语并不构成例外,和人类其他语言存在共性,非常符合语法化的特点。
【关键词】小称范畴;语法化;英汉对比
【作者简介】刘陈姣(1994.02- ),女,研究生,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7YCX057)。
一、前言
本文以作者母语一手语言材料为基础,以变音理论为视角,旨在探讨英汉小称语法化进程及其伴随的“音系化”进程的共性和差异。
Crystal(1997:116)曾作出关于“小称”的普通语言学定义:小称——形态学上用于表示“小”的词缀,经常引申为表示“可爱”的意思。比如意大利语的-ino, 葡萄牙语的-zinho,英语中的-let。Spencer(1991:197)也指出,世界上很多语言都存在广泛使用的、高度能产的小称标记,汉语普通话和广大方言的情况也一样,存在大量的“小称”语法形式。我们认为,小称是用各种语法手段或形态标记对相对较小的事物的一种指称,有时表达喜爱之情,有时则表达蔑视之意味,本文所说的小称只限于名词。
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最常见的小称后缀是“子”和“儿”,几乎可以加在各类实体名词后;英语中表小后缀有“-let”, “-y”等,这些小称后缀只保留在个别词中,不可随意搭配。由此可见,小称范畴虽广泛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语言中,但其使用范围和能产性并不一致。那是否证明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性极大,没有共性可言呢?
本文分别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子变韵,从而得出了子变韵来自于“子”的证据,也证明了汉语和人类语言存在共性。在本文中,汉语主要以辉县方言Z变韵为例,特别指出“Z变韵”来自于“子”这个语素的证据,特别是一些合口呼的字,在Z变韵时都加上了前高特征,这一特征应该是“-子”早期读音的反映和转化。其次,旨在证明英语中各类小称后缀也有共同的来源,即都来自于有着特定来源的人或物(person or thing of a specific kind of origin),和汉语中的“子”有着相似之处,从而证明汉语和英语符合人类语言的特点,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共性。
二、汉语语法化进程及其伴随的“音系化”进程:以辉县地区Z变韵为例
关于Z变韵,贺巍(1989:2-3)提到:名词逢词尾“-子”,在河南省北部有入声的地区,大都用变韵的方式表示,即Z变韵。Z变韵母一般适用于名词和量词,功用主要是相当于其他方言加轻声词尾“-子”字。而辉县就处于河南省北部有入声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Z变韵。王洪君(2008: 211-212)也指出:Z变韵流行于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它是以韵母或声母的变化表示类似普通话“-子”尾意义的一种构词法。目前发现的方言中Z变词的链条还缺少一些环节,因此不能完全确定它的本源就是“-子”。虽然从语法上看很可能是“-子”;从语音上看,是“-子”也说的通,但演化链条并不完整,只能说Z变韵很可能是“-子”的合音,但没有十分的把握。而辉县地区的Z变韵正好处于Z变词链条上缺少的环节之中,因此我们可以从共时的材料出发,找到历史的证据,从而证明辉县方言中的Z变韵确实来自于“子”这个语素。
从共时层面分析辉县方言的Z变韵,下表列举出了辉县方言Z变韵的例子:
首先,通过特征分析可发现Z变韵母都具有“后”“高”特征,即以-u/o或者鼻音-?结尾。因此,可得出第一条结论:(1)辉县方言Z变韵具有“后”“高”特征。但是若仔细对比可发现:三个例词“粽子”、“裙子”、“孙子”的基本韵分别为“??”、“yn” 和 “u?n”,但经过变韵之后多出了带有“前”、“高”特征的“i”或“j”。作者认为“i”或“j”应该来自于“子”,有可能是“-子”早期读音的反映和转化。因此,我们可以从共时材料出发,找到历史的证据,得出第二条结论:(2)“后”“高”特征Z变韵音节尾成分来源于(子变韵来自
于)“子”这个语素。
但是,值得思考的一点是:一方面Z变韵母带上了“后、高”特征,一方面又多出了带有“前、高”特征的“i”或“j”。如何在“前”和“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作者认为“前”和“后”之间只能是具有“中间”特征的“?”。这个猜想可从附近方言中得到印证,如林州方言中的“子”读作-l??/ ??。
其次,我们也可从历时角度出发分析“子”的发展过程。最初,它作为一个实词出现,如“子孙”中的“子”,之后意义开始虚化,加在“人”或“动物”等有生命的实体名词后;接着泛指“表小”功能,不再限于人或动物;再之后语音地位发生变化,开始变成一个独立的后缀;最后合入前字,形成变韵,即辉县方言的Z变韵,处于语法化过程中的音素化(phonogenesis)阶段(Hopper, P. J. & Traugott, E. C. , 2003)。另外,“子”的语法化过程也可印证作者之前的猜测:即“子”可逐渐变成央元音“?”。理由如下:一旦“子”的意義开始虚化,它的语音地位就会相应的做出改变,当虚化到一个最高峰时,就会变成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最易发出的一个声音,即央元音“?”。
此外,有一点作者感到甚是疑惑,即“桌子”在Z变韵中带上了鼻音特征,但是“桌子”的本韵中并无任何鼻音韵母存在。作者认为这个鼻音特征可能有两种解释:(1)可能是单纯的语音现象,因为“uo”本就具有“后”的特征,发音时若稍微靠后就易产生鼻音,这是纯语音的解释;(2)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儿”尾的残迹,“儿”最初的读音为“ni”,带有鼻音。若元音弱化,鼻音声母就很容易合入前字,因此这可能是“儿”尾在辉县方言中的残迹。另外,这种特殊的鼻音现象也可以从辉县地区的D变韵中找到证据,如在辉县地区有名为“蒋庄”,“赵庄”的村庄,在D变韵中分别被读作“t?u??”和“?u??”。“蒋庄”的“蒋”在D变韵中读音更加靠后;“赵庄”的“赵”本音中并没有鼻音,D变韵时却加上了后鼻音“?”。但是对于这种特殊现象,作者还尚存疑惑,无法确定是否来自于“子”,希望在今后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