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小偷与狗
2018-05-17祁生林
半夜时分,院子里传来“腾”的一声闷响,好似一颗沉重的杵蛋石,狠狠地夯在了女人水活活的心上,女人的心一下子碎成了八瓣。
女人吓的“妈呀”一声尖叫,飞快地将被子蒙在头上,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听声音,女人知道,有人从崖上跳进了院子。
女人居住的庄廓院依山而筑,前面和左右两边是土筑的高墙。只有后面,将原来的土崖斩下去二米来深,权作后墙,被斩出的崖沿上也没砌掩墙,因此,有人从崖上跳进院子,并不是难事。
女人躲在被窝里,竖起双耳紧张地谛听院子里的动静,但除了最初伴随“腾”的声响,似乎听到一声隐约的声唤外,院子里静悄悄的,什么声息也没有。寂静,反而使女人心里更加充满了恐惧。
女人胆小得出了名。未出嫁前,都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夜间起来解手,总要拉上母亲或妹妹作伴。如果没人陪伴,就硬憋着,那怕小肚子憋得酸溜溜地涨痛,宁肯在炕上烙“锅盔”般翻来覆去折腾,就是不敢去厕所。
嫁人后,起初两口子关系非常好,丈夫很会疼人,总是牛皮糖一样地粘在女人身边,如果女人有一时半会儿不在跟前,丈夫就会蔫皮塌神,萎靡不振,仿佛岔了伴儿似的。因此陪着女人起夜,倒成了丈夫求之不得乐此不疲的美差。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关系慢慢蜕化成了伴侣关系,丈夫开始懒惰了,夜里有些恋炕,常常赖在热被窝里,再也不愿陪女人去外面吸风饮露,冬天更甚。有时女人喊上半天,丈夫还是磨磨蹭蹭的,嘴里嘟嘟囔囔,老大的不情愿,全没了当初的利索劲。
但可喜的是,一双儿女渐渐长大了,丈夫不去,叫上儿子或女儿,同样也碍不了大事。
女人躲藏在被窝里,紧张的浑身冒汗,贴身的背心已被汗水溻透了,被窝里有些潮腾腾的。
时间不声不息地慢慢流逝,好半天了,院子里仍没有一丝动静。女人有些沉不住气,悄悄爬出被窝,撩起一角窗帘向院子里窥视。只见天半阴半淡的,似乎有一丝麻月亮,但不是朗照,所以院子里影影绰绰的,什么也看不清。但院墙边老杏树的叶子,却窸窸窣窣的,仿佛无数迷魂子拍手嬉戏,悸得女人胆战心惊,忙不迭躲进了被窝。
女人屏住声息伏在被窝里,巴望着天早点放亮。但老天爷偏偏与女人作对,时间过得慢慢腾腾的,像老太太爬坡,就是挪不快。无边的寂静如一条密实的大网,将女人连同黑夜紧紧裹捞在网心里,度秒如年。
女人夜里变得特别恐惧,还是近几年的事。短短几年,公婆先后故去,儿子和女儿都上了中学,读的是寄宿学校,除了每周回家背一回干粮,晚上不回家来住。为了供帮儿女读书,丈夫老是出去打工,即便冬季,也很少回家。偌大的院子,仅留下女人一个人居住,女人的心里就困得慌,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里,都生长着恐惧。
尤其是到了晚上,四下里都黑魆魆的,好似到处都潜藏着鬼魅。无缘无故的,女人会吓得头皮一绷一绷地抽紧了,心里瘆巴巴地发毛,悸出一身凉兮兮的冷汗来。莫名的恐惧,水似的渗入骨头缝缝里,在全身的血管里来回流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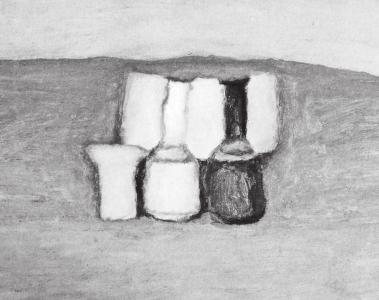
女人忽然想起了自家的小狗。那是一條不大的雄性哈巴狗,矮矮塌塌的身量,黑白相间的毛色,女人据此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尕花”。
想到狗,女人心里似乎有了依靠,仿佛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便低低地唤了一声尕花。但尕花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点回应也没有。
女人养过好几条狗,但都没有养长久,原因是近两年庄子里食狗肉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好的狗,养着养着,就让人偷去宰吃了。
尕花虽然是条极不起眼的小狗,但特别恋主,往往是女人走到那里,尕花就嗄嗄嗄地跟到那里,与女人形影不离。要是女人闲下来,尕花就一下子蹦到女人怀里,摇摇尾巴,仰起脑袋瓜子,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珠很无辜地望着女人,直到望得女人的眼睛里柔情似水了,才垂下头,幸福地爬在女人的膝头上,呼呼地打起瞌睡来。
但最近,尕花的情况却有些反常。因为尕花已经长大了,谈起了恋爱,有了男朋友,它的女友是前路口村长家的“黑妞”,一条毛色漆黑身体滚圆的四眼女狗,模样与村长有些相像。自从爱上了那个野丫头,时不时的,尕花就要偷偷地溜出去,与黑妞幽会,有时甚至夜不归宿,女人倒被它抛到了脑后。
自尕花泡上了黑妞,连带的村长对女人也心猿意马起来。村长觉得,将黑妞白白地送给尕花做老婆,有点太便宜了女人,他想找点什么补回来。于是,村长多次借着和女人说尕花与黑妞的事,假痴不癫地向女人示风,那鼓鼓的牛蛋眼里,淫邪的火苗子一蹿一蹿的,舔灼的女人脸上火辣辣地发疼。
女人对一肚子花花肠子的村长很反感,不想花马吊嘴地与村长调情,便装出一副不解风情的模样,拿话搪开村长的撩拨。村长自然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狠狠地咬咬后槽牙,悻悻地甩手走开。
麻杆子当捂棍——靠不住的东西,女人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句尕花。
就在这时,院子里却有了动静。女人的心又像春天泥塘里的癞蛤蟆,“噗嗵噗嗵”地狂跳了起来。
原来,头上套了半截女人丝袜的小偷从崖上跳下来,不巧恰恰落在一颗熟洋芋上,脚底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崴了脚。
那熟洋芋是女人晚上煮了喂猪,猪吃剩了,随便丢在那儿的,没想到却成了小偷的地雷,意外地派上了用场。
小偷倒在地上,除了崴了脚,其实并没受什么大伤。他之所以悄悄地猫着不出声,主要是怕声张起来,被人发觉了,自己崴了脚,走不脱,被人家拿住。
小偷在院崖下静静地伏了半晌,除了听到女人一声极轻微的唤狗声之外,没见有别的反应,便断定,这院子里除女人外,再无其它人,于是,胆子又陡然大了起来。
小偷从地上爬起身,不由自主“哎哟”了一声,一瘸一拐缓缓地向房屋这边走来,并“哐啷”一声,推开了堂屋门。
几乎在同时,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从炕沿下箭一般跃出来,“唿”的一声,扑到了女人蒙在头上的被子上,吓得女人又高声尖叫了起来,那声音岔溜溜的,异常恐怖——原来是小狗尕花。
女人弄明白是尕花压在自己身上后,胆气略略有些点回升,就瞌瞌巴巴地唆狗:去,尕、尕花、花,咬、咬……!
但尕花却伏着身子,硬是挤进了被窝,藏在女人腹下,身子抖得比女人更厉害。
女人绝望了,头顶被子,双手紧紧攥着被角,在被窝里瑟缩成一团。
小偷握着手电筒在屋内一通乱晃后,“啪嗒”一下拉亮了电灯。
见女人躲在被子里,小偷扑到炕前,猛力扯去了女人裹在身上的被子。
女人只觉眼前白光一闪,一把雪亮的杀猪刀,已横在自己面前。小偷低而凶狠地喝问女人:说,钱放在什么地方,快给老子拿出来!
女人胆战心惊,结结巴巴地说,掌柜子不、不在家,我、我不知、知道钱放在、在哪里。
小偷凶相毕露,舞起刀子,作势要在女人脸上乱戳。
女人的胆液都被吓脱坝了,只觉得交裆里蓦然一热,接着又是一片冰凉。因怕小偷真的动手戳自己,女人只得老实招承:钱、钱就塞、塞在炕柜的那双布、布鞋里,你、你个家取!
小偷见女人脸上浮上一丝羞色,又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知道女人出了状况,眼睛里就有了别的意思,情绪一瞬间变得格外亢奋,手里的杀猪刀挥舞的越发起劲了。
女人恐惧到了极点,吓得花容失色,担心小偷手里的杀猪刀伤着自己,下意识地伸手去挡,只觉右臂上有点凉飕飕的,定睛一看,臂上已多了一条隐隐的白线。紧接着,白线上渗出殷殷的血丝,慢慢连成一条瘦袅的红线。俄而,红线的两边不对称地洇出一粒粒饱满的小血点,起初像罂粟籽,渐渐变大了,有如油菜籽,最后膨胀至花椒籽大小,便定格了。于是,女人细白丰腴的甜藕般的胳臂上,便有了一枝缀满红蓓蕾的小小梅枝,含苞欲绽,娇艳夺目。
女人盯着自己受伤的胳膊,眼前一阵眩晕,昏了过去。
小偷见女人晕倒了,便丢开女人,跳上炕来,一把拧去炕柜门上的小锁子,日急慌忙一阵乱翻,最后从一条红缎被面扎成的包袱里,终于找出了一双新崭崭的千层底毛布掌鞋,并分别从两只鞋里掏出了一叠卷成一团的钞票。
小偷拿了钱,跳下炕准备要走,不经意间一回头,又改变了主意,重新跳上炕来,伸手向女人怀里摸去。
小偷这一摸不要紧,他的手触到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还没等小偷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手就被一个热乎乎软溜溜滑兮兮的东西一下子咬住了。
小偷痛得呲牙裂嘴,死命将手往回抽,没想到竟从女人怀里掣出一只狗来,原来是哈巴狗尕花,口里还紧咬着小偷的手不放。
小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从狗嘴里拔出了手指,但无名指的骨頭已经被尕花咬断了,血汩汩地冒出来,滴滴答答流个不息。
气急败坏的小偷飞起草一脚,把尕花踢下炕去。然后扯下窗帘,用力撕成条条索索,胡乱包扎了手伤,溜下炕,一瘸一拐地向院门走去。
刚出去没几步,小偷又返回了屋子。原来院门被女人从里面反锁了,小偷打不开院门,只好回来向女人讨要钥匙。
就在这时,院外突然传来高声呼唤女人的声音,并伴随着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女人已经苏醒了。听到敲门声,女人和小偷都非常吃惊,尤其是小偷,惊得面如土色,六神无主。
敲门声越来越紧,嘣嘣咚咚的,激越得如擂战鼓。
小偷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想赶紧找个地方躲避,目光急匆匆地在屋内扫视了一圈,见无处藏匿,正要出屋找个地方躲起来,但这时后崖上也响起了大声呼唤女人的声音,惊得小偷赶紧退回屋子,瞥见堂间地下立着件大衣橱,便想也没想,拉开橱门就钻了进去。
刚挤进去不久,小偷又三脚两步从大衣橱里蹿出来,拉息了电灯,又赶紧蹿进了大衣橱。突然,小偷又推开橱门缝探出半颗脑袋来,用手比划着向女人做了个砍头的威胁动作,又急忙把脑袋缩进了衣橱中。
女人理解小偷的意思,畏惧地对小偷点了点头,但小偷的头早已缩进了衣橱中,不可能看见女人点头了。其实,就是小偷站在女人面前,也不可能看见女人点头的,因为女人太恐惧了,那头点得似点非点,说白了,就是只有意识,没有动作。
这时节,外面的敲门声和呼喊声如点着了一大堆竹子,一声比一声又爆又急,惊得村里好几处的狗都狂吠了起来,
女人终于听清外面叫她的就是本村的人,想答应,但嗓子却像哑了似的,呐呐的就是发不出一丝声音。
外面的人大约等不及了,只听后崖边“腾”“腾”的两声响,似有人又跳进了院子。
女人不太害怕了,抖抖索索从被窝里爬出来,啪嗒一声,拉亮了电灯。
只听窗外有人叫女人:媳姐,媳姐,快开开门,刚才还见你房里亮着灯,怎么叫死不给个回应?
女人说,做啥哩,声音有气无力的,像三天没有吃东西。
窗外说,黑娃媳妇难产,想借你家的双牌车,往医院送个病人。说着,已有两个人推门进来立在了炕前,是本村的后生重孙和元旦。
女人还没有穿衣服,见两个男人站在面前,脸上一红,又急忙缩进了被窝。
两个年轻人闹了个大红脸,吐吐舌头,退出了女人房间。
女人窸窸窣窣了一阵子,穿好衣服,从钱桌的抽屉里,找出车钥匙递给了重孙。
重孙和元旦到院子里发车,女人也慌慌张张地追到院子里,并不断回头紧张地向身后瞧,仿佛身后跟了鬼。
元旦问女人,媳姐,有热水吗,打点来。女人怕小偷,不敢独自进屋,就拉着元旦回房拎出两只电壶,把热水加进小货车的水箱里。
呼隆隆一阵轰鸣,货车很快就发着了,女人怕丢下自己,两手攥住车傍沿,急吼吼地爬上了车箱。
重孙以为女人要去医院,便劝道,媳姐,你还是回去睡吧,送的人有好几个哩,再说你去了也没事干。放心,你家的车我怎么开出去的,就怎么送回来,你不用担心。
谁也没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尕花也爬上了车。这时,它正叼住元旦的一条裤角,嘴里呜呜噜噜的,死死地往车下拽。元旦心知有异,忙用眼神问女人。
女人眼里的泪水再也禁锢不住了,串珠似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滚滚溅溅的,不止不息。
女人疼爱地盯着尕花看了半晌,对着元旦向屋里呶了呶嘴。
元旦会意,急忙拉了重孙,两人跳下车,在尕花的引导下,来到了屋内。
只见尕花冲到大衣橱前,用前爪抓挠了几下橱门,又弹簧般跳到一边,头冲着橱门,汪汪汪地狂吠起来。
元旦一把拉开橱门。小偷情知自己成了瓮中之鳖,滚出柜子,爬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重孙找根绳子把小偷捆了,押出来对女人说,媳姐,今晚夕的事,我本来就有点疑惑,还以为你这个正经人,也麦衣儿底下放水,趁老哥不在家,在家里藏了个“扛夜”,谁知原来是夜猫子进宅了,差点冤枉了好人。
女人只觉得自己累极了,无声地对两个男人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双牌车载着孕妇和小偷,呜呜地向县城驶去。
女人瘫坐在台沿上,怀里紧紧搂着尕花,眼泪无声而尽情地流淌着,打湿了尕花的颈毛。
尕花惊讶地仰头望着泪流满面的女人,两只眼珠子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
【作者简介】祁生林,男,迄今在《小说精选》《青海湖》《黄河文学》《喜剧世界》《妇女之友》《法制日报》《农民日报》《青海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等作品数十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