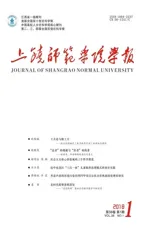“达者”的超越与“狂者”的执著
——试论苏、辛并称的贬谪文化意义
2018-04-03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词史上苏轼、辛弃疾并称,但是,这一并称是否只有歌词创作上的意义,抑或进而为文学上的意义呢?笔者以为尚可探讨。虽然苏、辛都是词坛大家,苏轼更是全能型的文学家,苏、辛并称属于文学范围是理所当然,而辛弃疾对苏轼也充满景仰之情的,这仅从其诗词作品出于苏、关于苏者计235首314处,居其所涉历代文化名人之首即可知,但奇怪的是,稼轩文学作品中虽涉及东坡者有如此之多,却很少提及苏轼的文学成就,这本身就很可令人思考其原因之所在。对此,笔者尝试于文化层面做一些解释和观察,探究苏、辛并称在文化史上尤其是在贬谪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意义。
一
从辛弃疾的作品中可见,辛本人主要是从以下诸方面来认识、认同苏轼的。
首先,是对苏轼人生体验的强烈共鸣。由于苏、辛都不能得志于时,都具有从儒家思想以外寻找人生哲学的经历,虽程度深浅有异,但可谓都是庄子和陶渊明的倾慕者。他们在羡庄、慕陶上有共同的感受。苏《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云:“渊明吾所师。”[1]1175辛《最高楼》言:“陶县令,是吾师。”[2]312他们将庄子思想用于现实,都有看破人生的齐物观。苏《任师中挽词》说:“贵贱贤愚同尽耳。”[1]1126辛《水调歌头》则称:“贵贱贤愚等耳。”[2]135他们都经历过人生的悲欢、荣辱、升沉,故对于苏轼所写的人生之深切体验,辛弃疾大都能予以再现。试看:苏《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云:“功名一破甑,弃置何用顾。”[1]460《二公再和亦再答之》云:“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1]579辛《玉蝴蝶》用其句、意:“功名破甑,交友抟沙。”[2]159苏《石苍舒醉墨堂》云:“人生识字忧患始。”[1]219辛《偶题》说:“人生忧患始于名。”[2]730亦同出一揆。像这样的例子于二人集中不在少数。
其次,是对苏轼感情体验的全面认同。苏轼有对人生的美好愿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3]161稼轩也说:“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2]164虽说东坡与稼轩都倾心于庄、陶,但实又是出于不得已的无奈,由于他们都是希望有用于世、能补弊政、力救时艰的人物,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会禁不住流露出对功业未成的愤懑。苏轼说:“我材濩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1]1222辛弃疾也说:“濩落我材无所用。”[2]196苏轼学庄,神往其独立之人格,不屈于世俗的志气。他宣称:“最后数篇君莫厌,捣残椒桂有馀辛。”[1]1409而辛弃疾也认同于此:“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2]243由于不能和光同尘,苏、辛都有“幽人贞吉”式的孤独感:苏云:“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3]249辛说:“不算飘零,天外孤鸿影。”[2]412凡此,都可见出二人在情感体验方面的相似性。
再次,是对苏轼过人的智慧和幽默之倾心。稼轩以坡公为师、为友、为典范,他常常与东坡作神交之游:“更着诗翁杖屦,合作雪堂猜。”[2]115“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2]154《西江月》一词更写道:
八万四千偈后,更谁妙语披襟。纫兰结佩有同心。唤取诗翁来饮。
镂玉裁冰著句,高山流水知音。胸中不受一尘侵,却怕灵均独醒。[2]514
“妙语披襟”的“诗翁”,是稼轩笔底屡屡出现的东坡形象。他将其视为“纫兰结佩同心”和“高山流水知音”,足可见出他对东坡的钦服和心仪。不仅两人在词中多处化用庄子而透露出相似的智慧和幽默,甚至稼轩也有东坡不无痛苦的谐谑。如苏《洗儿戏作》云:“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1]1130辛《清平乐》亦云:“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难公卿。”[2]524
正因襟抱相同,故稼轩的创作风貌也是沿苏轼一路而来。范开《稼轩词序》说他“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2]949。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亦云:“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2]952故历来苏、辛并提,几乎无一例外是在文学范围,具体说是在歌词创作上将其视为承传渊源的一个派系。仅从上述所列可知,苏轼所创造、所活用的语言和意象、思绪,似是很自然地进入到稼轩的思路,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但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从辛弃疾所引用、化用东坡作品的内容来看,很少有提到其文学创作的。据笔者统计,在与东坡相涉的300多处诗句词句中,仅有14处涉及到诗词、和韵之类,而真正评论文学创作本身的仅4处:“余诗寻医久矣”[2]134、“入手清风词更好”[2]393、“诗眼巧安排”[2]141、“下笔如神强押韵”[2]79;甚至他还反用苏意,如苏轼《与梁左藏会饮傅国博家》诗云:“论诗说剑俱第一。”[1]772辛词《水调歌头》却说:“说剑论诗馀事。”[2]114这似乎与后人看苏、辛关系的角度很不相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不愿只为文人却又无奈成为文人的辛弃疾,在认识同样也是以文而显的苏轼时,还另有一个独特的文化角度,并以此作为他人生的定位。试读辛弃疾在《霜天晓角·赤壁》中所写: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2]668
显然,“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是辛弃疾对苏轼命运的思考和判断,也是他对苏轼和自己人生文化角色的认定,其中有很深厚的含蕴。
苏轼自是以文章知名天下,辛弃疾也是文人出身,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即称之为“一少年书生”[4]117。但稼轩从不以词人自限,声称“说剑论诗馀事”,而后人亦予其以非词人而英雄的评价,如言其“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2]949,“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4]124等等。如果我们将《霜天晓角·赤壁》与其青年时作的《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作一比较: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2]170-171
更可看出,在稼轩心目中,“文章”也好,“诗书”也好,都应是像诸葛亮一样,运用于帷幄之中,落实在马背之上,是为驱锋镝、刻勋业而服务的。另外,其《最高楼》的“富贵是危机”[2]311一句,本出于苏轼《宿州次韵刘泾》诗:“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1]698稼轩虽未用其上句,实亦关于“晚觉文章真小技”,这与稼轩一贯将功业视为人生最高目标也是一致的。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看稼轩这两首词。前一首俨然是一篇微型的《赤壁赋》,其中既有凭吊古人功业、而悲叹自己建功无由的英雄苦闷,所谓“曹刘兴废,千古事”“半夜长啸,悲天地,为予窄”;又有对苏轼悲剧命运的思考和评判,惜苏之文才,叹其虽以文章知遇于皇帝,知名于当时,却终不得其力,未能成就辅国之大功,且屡遭贬谪播迁。后首词则是在贺同仁功勋(此处且不论此平寇之功的性质)的同时,隐然叹息自己功业未成。“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之语,原出刘禹锡诗《郡斋抒怀寄江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5]1139但此处却暗指王佐当上侍从官靠的并非状元文章而是军功,因此,“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实则与“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一样,亦含自伤身世的不平之鸣。作为“以功业自许”的人物,稼轩之成为两宋词人之冠,实是恢复大志难以实现而产生的“文化错位”。但是,一如韩愈古文运动的领袖身份超过他在重建道统中的地位,苏轼的政绩也比不上他的文学成就,而稼轩作为抗金的战略家,虽然如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所言,“其策完颜氏之祸,论请绝岁币,皆验于数十年之后”[2]950,但在一生功业上,同样还是难及他在词史上的地位,且即使是这种文人地位的辉煌,也是他们身后才有,当时他们是并未得其力的。因此“未得文章力”之语,实是辛弃疾对苏轼、对自己双重文化角色(恢复大业之志士与文学家)的异代同悲。
二
所谓“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既是辛弃疾对苏轼命运的思考和判断,也是他对苏轼和自己人生文化角色的认定,其中有很深厚的含蕴,与绵延两千馀年的贬谪文化密切相关。这是个相当大的论题,学界已有尚永亮等人的研究珠玉在前,本文不拟作全面论析,此处参酌尚先生的部分观点和论述,并结合“迁客”和“文章”,就苏、辛对贬谪文化的改变和发展作一些比较性的分析探讨。
根据尚永亮等人的研究,贬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在尧、舜时代即已有之,据《尚书·舜典》,舜曾“流共工于幽州,放勤马雚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6]14。然而,首先将它鲜明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则始于战国时期的屈原。屈子的人生是一出大悲剧: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7]1901,两遭流放;面对着专制昏昧的君主,他始终怀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7]1902的不灭希望,与沉重如山的现实忧患顽强抗争。他不仅以其宏伟的楚骚作品开创了千古贬谪文学之源,而且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感、高尚峻直的人格节操、对群小党人的奋力批判以及对理想九死不悔的执著追求,特别是殉国之举,树立了贬谪文化人格的一个难以企及的榜样。而屈原对于政治理想和人格节操超出一般的执著意识,也使他和他的悲剧具备了贬谪文化的模式意义。
屈原之后,贾谊是第二位既有贬逐经历又将其情感体验发之于诗文的重要文化名人。他高才博学,少年得志,然而未及大展鸿图,即因权贵的嫉妒而被逐出权力中枢。从这点来说,他的悲剧与屈原颇有相似之处。但是,汉代这个大一统的兴盛王朝毕竟不同于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朝政也远未到皇舆败绩的可危程度,因此,“他将人生关怀的主要目标由社会政治转向了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忠奸斗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一己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怀才不遇,从而在中国贬谪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表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8]23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贾谊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在《服鸟鸟赋》中说:“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纟墨。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7]1911-1912这里所透露出来的纵躯委命、随缘任化以超越现实忧患的意识,“无疑是对屈原所代表的执著意识的改变、消解和淡化”[8]236。只不过,由于“时代尚未给他提供实际超越的条件,而他过于专注自我的心性也不具备真正超越的机制”[8]239,其应自然、养心性、知天命的自劝并非得到真正的解脱。
屈原和贾谊代表了贬谪文化史上两种不同的模式。诚如尚永亮先生所言:“从屈原到贾谊,虽不剧烈但却清晰地显示了贬谪文化在执著与超越间游移演进的轨迹,而屈原和贾谊,则有如中国贬谪史上的两座峰头,既标志着贬谪士人在生命沉沦过程中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代表了忠奸斗争和感士不遇这样两种不无区别的主题及其价值和意义”。在屈、贾之后至唐、宋时代,贬谪士人们或“以屈原为楷模,自儆自励,向执著提升”或“引贾谊为知音,悲叹身世,从困境中走向超越”[8]240。对于这一时段中贬谪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向,尚永亮曾结合贬谪文学的发展下了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它的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在这两代中,又突出表现在元和、元祐两大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士人中,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堪为突出代表,而白居易则可作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士人的三个重要心理流程。如果将屈原赋作中展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应为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著走向超越。”[8]13尚先生这个论断所定的时间下限实际上止于北宋的元祐,换言之,他认为在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文人那里,贬谪文化的主要精神已经完成从执著走向超越的转换,“无畏、超越、乐观成为宋代贬谪文化的核心内容”,此后虽“于南渡之时略有演进,但并无质的变化”[9],其基本内涵并未逸出北宋的范围。
尚先生关于贬谪文化发展过程的论断固然言之成理,但亦不无可议之处。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复杂的,它的发展演变往往是多种线索互相交错,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状上升。就贬谪文化这一历史现象来说,由屈原和贾谊分别确立的执著和超越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并且它们之间也非两水分流,泾渭分明,而是互通互融,彼此影响。比如元和时期,就既有白居易这样在进取不得之后乐天知命、寻求超越的“中隐”之士,又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样念念不忘初心、执著追求理想的死硬分子;而在北宋中后期,除了以苏、黄等元祐文人为代表的“超越”派,还有王安石这样的“拗相公”,尽管两度落职,却依然执著于自己的变法理想,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经常为时事忧叹。至于南宋的文人,虽深受苏轼等元祐文人超越、达观的精神意识和人生态度的影响,但亦不乏狷狂之士,高蹈进取不顾身,历尽困厄不改节,为了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10]11582的胡铨是一例,本文所讨论的辛弃疾亦为一例。有这等人物在,又岂能断言贬谪文化中的以“执著”为内核的屈原模式在南宋已无所发展,全为“超越”所笼罩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辛弃疾对苏轼“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这一认识角度出发,对他们在贬逐中的思想与表现略加分析与比较,即可发现,苏、辛二人在贬谪文化史上均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样是迥出流辈、卓立于两宋词人之林的并峙双峰。
三
如尚先生所论,苏轼在贬谪文化中,是“超越”型的成熟代表。他对贾谊以下的贬谪文人的“超越”意识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发展和改造。这一点,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及自身特殊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
屈原、贾谊生活的时代,佛教尚未进入我国,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未如魏晋之时,当时的士人还缺乏解脱、超越的思想武器,加之屈原“执著中的绝望”和“绝望中的执著”所形成的独特执著意识,使其面对君王的昏庸和群小的谄佞,屈原只能以生命为代价走向最后的归宿,贾谊则忧伤哀怨、自怜自叹,虽企图超越而未能。而此后的贬谪文学中,怀才不遇也好,君恩不再也好,基本上总离不了封建社会宗法制下士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笼罩在两千多年贬谪文化史上空的依然是忧伤怨怒的氛围。即如敢言敢为的韩愈被贬潮州,也免不了哀怜幽怨。
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宋代,儒、释、道三家行世已久,渐由唐代的三家并行,变而为三家融合。就哲学思想体系来说,宋代的道学以儒学综融佛、道为特色。即使不是道学中人,伴随这一主流思想的生成和完成,士人们在出处问题上也已能够圆融地运用不同的思想以处世,由此形成了文化性格中的多元化取向。苏轼即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苏轼早以文章知名,又为蜀党领袖,本可实现其天下之志,但因政治上之党争,使之成为“迁客”,且其三次贬逐,地方离京城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艰苦,年龄也越来越老。在这种情形下,他却走了一条与屈原和贾谊完全不同的道路。虽仍然未忘国事,却不似屈原之入而不得出,能就眼前所有作为调剂,力图从容于忧患之中;他虽也有贾谊的忧伤哀怨,也不时流露出人生空漠之感,但承认人生悲哀而又力求超越悲哀,且能仍立足于儒家的有为,未失去进取入世之心,尽其所能地作出政绩。我们不妨从其所贬三州的三个细节来看其心态:
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11]1312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11]8113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11]8704
如果取“逃世之机”的态度,摆脱世俗名利之羁绊,哪怕生活在“世之事”中,也会性便意适,作江山主人;有了“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的顿悟,就可以超越世间万物,而与天地浑一,任凭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也如入无人之境而熟歇;人一旦超出于蚂蚁身小视短的窘境,将自己放到一个“岛”在“天地积水”的更为辽阔无垠的空间去观察世界,就可以进而感悟到“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因而神与天通,一切个人忧患都显得渺小而可以付之一笑了。由此,我们可看出苏轼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精神超越,不断地将自己的处世态度升华为与天地并存的精神境界,并站在哲理高度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了触处生春,无往而不乐的任性自适、旷达通脱的人生境地。
但苏轼并不像前人(比如说白居易)那样,得志时就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失意时就是以佛道出世思想为精神支柱,儒释道在他身上不是分离而是圆融一体的。在《贾谊论》中,他曾批评贾谊“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指责他“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认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应当像孟子那样,怀着“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的勇毅,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默默以待其变”,等待复用的机会[11]358-360。因此在其习佛道而随缘任运,看穿忧患“当下即是”,以应对环境、平衡心理的同时,也未必没有儒者“舍我其谁”“默默以待其变”的坚忍,而以陶之躬耕不为贫所折激励自己,也是儒家孔颜之乐的表现。
也正因如此,苏轼才能在面临着既要保存生命,又要解决生计的问题,甚至于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已做好葬身海外的思想准备后,仍能够做到既不改儒者之本色,同时又在处世态度、行为方式和思想情感上(而非学术上)调和三教。如果说贾谊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尚未达到真正的超越,那么,三教融合的宋代社会已为苏轼提供了超越的条件,而他丰富多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使他具备了真正超越的心理机制。总之,他以其“狂、旷、谐、适”的性格系统为发展贬谪文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
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多次被贬黜,闲退几达二十年的遭遇,其主要原因不是党争,而是“派争”。这里的“派”,不仅是主战派、主和派之谓,还包括勇于任事的“事功派”和循规蹈矩的“循默派”。辛弃疾富于军略,力主抗战,为政的作风又比较猛厉,讲实效不讲规矩,被上级视为难以驾驭,故而在南宋主和派长期当道,执政者多为信奉正统理学的循默之士的时代环境中,其才能必然难以尽情发挥,作风亦必然受到各种攻讦。由此, 他对贾谊“士不遇”的感受有深刻的体会,对贾谊其人其文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他熟识贾谊政论并在自己的万字平戎策中引用;他赞赏贾谊之大志,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对贾谊之忧多存理解、共鸣:“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2]176;“人生只合住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2]827等语,显然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而“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2]154出贾谊《惜誓》“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12]228;“坐稳得坎止”[2]691亦用贾谊《服鸟鸟赋》“乘流则逝兮,得坎则止”[7]1912。凡此,都可以看出他对贾谊在自伤中欲行超越这一贬谪文化模式的认可和发展。
循着这条线索,在功业难成、恢复不行,不得不投闲置散的状态下,他由苏轼的“不得文章力”而及于自身,继承了苏轼内省型的文化思考,步入传统,从庄子和陶渊明处汲取营养,医治创伤,来寻找文化的归宿。他认同陶渊明的独立人格精神和躬耕之乐,并且用庄子的哲理来看待人生的用舍行藏。如他在用庄意而写的《哨遍》中,即以蜗角触蛮之争来否定人世间的利禄功名,看穿人生的升沉荣辱,这是对功名失落的自慰;而《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做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2]465-466则是在进退出处之间作出了舍“长安”而就“山寺”的选择。他吟咏着“进亦乐,退亦乐”[2]12,以庄子的齐物观来处理出处矛盾,向着苏轼的达观靠近。试比较: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13]79
由来至乐,总属闲人。且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2]361
但只熙熙闲过日,人间无处不春台。[2]715
苏的闲人才是主人与辛的闲人才有至乐,二者无疑同一思路,都认为只有在主体摆脱外界的羁绊而完全放松的“闲”之精神状态下,才能享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由此可见,辛弃疾在许多时候是通过苏轼这个文化中介,向佛、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中寻找人生寄托和超越的。这就是苏轼作为辛弃疾文化近源的意义。
然而,辛弃疾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追求与苏轼终究有所不同。他尽管如苏一样崇陶,尽管也努力地学苏的超越,但即使身在田园,他的功业心也无法安静,他的英雄血也动辄沸腾。试读下面这首黜退期间所作的词: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2]91
我们看,他眼中的山,是奔腾动荡的:“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他眼中的水,是气势逼人的:“惊湍直下,跳珠倒溅”!他眼中的月,被小桥截成了弥满战意的弓;他眼中的松树,是待他检阅的十万士兵;他居住的小庐,是“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这等词句,直让人觉得是在战阵杀伐之中,英风豪气扑面而来。下半阕中,过片的一个“争”字,道出的其实也是作者不甘人后的心态;而谢家子弟的衣冠,相如车骑的雍容,则令人怀想起淝水之战的伟大功业,司马相如事业成功时的得意;至于发愤而作、雄深雅健的太史公文章这一喻体,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写照自己胸怀块垒,到底意难平的郁愤呢?刘辰翁说得好:
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讬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不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4]124
喑呜鸷悍的英雄慷慨本性,恢复中原的强烈功业向往,与“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引黄梨庄语。(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70页)的人生际遇相激相撞,使辛弃疾终不能以超越为归宿、得解脱,屈原的执著由此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给予他丰富的文化滋养。在闲退岁月中,他与苏轼贬谪期间少提屈原不同,屡言屈骚,且待机欲发,乘时而动。他所念念不忘的,既有屈原之怨怀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怨怒,怨孝宗之承诺有变,“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2]231,积愤始终难除;又有屈原“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道男儿、到死心如铁”[2]26,希冀恢复西北神州故土;同时他又具备屈原的志节坚贞,并未因失去禄位而吸取教训,或因行事果断威严得罪而反思改变自己。从文化性格来说,辛弃疾和屈原都属于执著进取的“狂者”,辛临终前大呼数声“杀贼”而殁,说明他对于理想的追求一如屈子,是贯穿了生命的始终的。不过,辛弃疾既有已发展至成熟阶段的“超越”意识作为文化近源以济之,又有英雄的血气提供顽强坚韧的抗压能力,因此当他面对“谗摈销沮”以致“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的无奈现实时,不必像屈原那样以身相殉,死给你看,而是一声长叹:“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2]231
综上所论,如果说,苏轼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贾谊的模式,追求并获得的是“达者”的超越,辛弃疾则在吸收、融合多种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把屈原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文化性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追求并坚守的主要是“狂者”的执著;苏轼在闲适中体现的是“自然人格”,辛弃疾在闲适中保持的仍然是“道德人格”*王水照先生指出:“辛弃疾的钟情自然以求闲适,原是保持一种道德人格的自我,……苏轼在闲适中追求的却是自然人格。”(见《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一文,王水照《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即使在再仕而再黜的晚年,他求证于道学之心性,上升于天地之参,“深自觉昨非而今是”,以“中庸”之“至诚”“尽性”作出了“内圣”的选择,但仍与苏轼以佛、老之乐天知命、随缘自适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认为,辛弃疾既承继了屈原、贾谊这两个贬谪文化史上有典范意义的传统文化模式,又以苏轼为文化近源而又有新变。这应是辛弃疾对贬谪文化的发展和贡献。
苏轼在其著名的赤壁词《念奴娇》中,自笑多情,感叹人生如梦;而稼轩的赤壁词《霜天晓角》却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2]668。“达者”与“狂者”的不同旨趣,于斯亦见。
[1] 苏轼.苏轼诗集合注[M].冯赢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辛弃疾.辛弃疾全集校注[M].徐汉明,校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3] 苏轼.苏轼全集校注·词集[M].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4]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39.
[6]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4.
[7]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9] 尚永亮,钱建状.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以元祐贬谪文人群体为论述中心[J].中华文史论丛,2010(3):187-227,39.
[10] 脱脱,等.宋史·胡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582.
[11] 苏轼.苏轼全集校注·文集[M].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2] 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28.
[13] 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