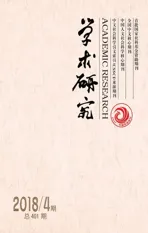古典政治哲人的理性至善与政治上的理智清醒*
2018-02-20林壮青
林壮青
在一个祛神(God)的世俗世界,无神信靠的人不会成神,也无须成神;但他必须成人,这是必死的人追求人作为人的形而上命定。因此,面对人类灵魂理性与激情的原初冲突,古典政治哲人认为,成人的首要是确立理性领导激情的权威,建立灵魂正义的微型城邦;然而,政治现实的急迫又必然引发激情反叛理性的权威。不过,古典政治哲人并不会因之而放弃理性的权威而纵容激情;同样,他们也不会因为必须维护理性的权威而毁灭激情。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阐述这个主题。首先,阐发柏拉图关于“事物活动”(ergon)的“自足性原则”;a布鲁姆把希腊语ergon译为“work”(活动)。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1968, 352d-353d.其次,根据这个原则,证明激情(欲望和意气)活动的非自足性,以此表明,古典政治哲人所认为的,无论是欲望还是意气都不能成为灵魂的最高统治者;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古典政治哲人是如何确立理性活动“领导”激情活动的权威地位,以及如何解决理性成人的最高可能与政治城邦的关系问题。
一、事物活动的自足性原则
古典政治哲人认为,b古典政治哲人主要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120.人的灵魂是由欲望、意气和理性三部分构成,每个部分有其各自的活动能力,与此对应,灵魂也有三种主要的“生活”:欲望追逐享乐的生活,意气追求荣誉的政治生活以及理性追求思辨的生活。a[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095b、1139a15-22。显然,三种生活都是人类所必需的,但它们并不总能平行不悖。三者间冲突的解决与否,涉及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先不说是何种品质的生活——是否可能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平常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调整三者间的关系,尽可能做到灵魂活动是有序的。然而,相较于平常人只关注正常生活是否可能的现实问题,政治哲人则必须思考这样一个最佳的解决可能:既能保护大多数人过上正常的快乐生活和政治生活,又不损害人作为人应当过上的理性生活。
要理解古典政治哲人以何种方式解决三种活动之间的冲突,首先需要阐发柏拉图关于“事物活动”的自足性原则。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每一事物都具有其自身的“本有活动”。本有活动是指,“非它”,一个事物就“不能完成”的活动。bPlato, The Republic, 352d-353d.也就是说,本有活动是其他活动所不能僭越的,若被僭越,这个事物就不能完成其应当完成的活动;本有活动成就了一个事物自身内在规定的目的。与本有活动相对应,该活动也必然有与其自身相适宜的活动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本有活动的德行。也就是说,如若一个事物的活动缺失其本有德行,该活动就不可能完满地实现,该事物也就不可能完成其自身内在规定的目的。比如,眼睛的本有活动就是看,看不能由其他活动替代;若被替代,看的活动就必然受到损害,不能完成其所应该完成的。与此一致,目明就是看的德行;若失明,眼睛就不能完成其本有活动。可见,事物的本有活动及其德行共同促成事物内在目的之实现,是判断事物活动正当与否的标准。
同时,本有活动也是区分事物的原则。因为,如果知道一个事物的本有活动,则与这个活动不同的另一个活动自然就属于另一个事物。因此,如果能够辩明每个事物的本有活动,就能判明每个事物各自应当承担的职责;同样,如果能够辩明事物活动的德行,也就能够纠正事物活动的错误方式。依据这个区分原则,柏拉图确立了著名的“一人一职”的分工理论和灵魂正义。因为,每一个人的自然天赋决定了什么样的活动最适合他自己,从而,决定了其在“合作关系”中所应该完成的职责;同样,灵魂中每个部分的本有活动及其德行决定了其在灵魂活动中的各自地位。
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事物的本有活动并非总是自足而无待的。因为,一个事物可能只是整体构成各部分中的“一”,其本有活动只是就其自身而言的,并非其所属的那个整体的本有活动,因此,并非每个事物的本有活动都有资格充当整体的本有活动。但整体又是由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的活动有资格充当整体的本有活动呢?这就需要进一步辩明哪个部分的本有活动是无待的。只有无待的活动才有资格充当整体的本有活动,也只有无待的活动才有资格规定与统摄其他活动。这个无待性就是事物的自足性原则。因此,解决灵魂三种活动间冲突的关键,在于辩明三种活动哪种才是灵魂本有而无待的。
欲望和意气为人与动物所共有,cPlato, The Republic, 441a8-b5.因之,不管是欲望活动,还是意气活动都不可能是人类灵魂的本有活动。d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999, 1116b.尽管这样,人们却往往把欲望或意气的本有活动视为灵魂的本有活动。鉴此,有必要从无待的角度,重新考察欲望和意气,从而,进一步确证它们活动的有待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欲望活动,还是意气活动都不可能作为灵魂的本有活动。按照柏拉图关于“可能性”与“可欲性”的区分,e柏拉图把“无待性”的证明分为“可能性”与“可欲性”两个步骤。[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450c7-d1。可以把欲望和意气活动是否无待的证明分为高度相关的两个步骤:第一,考察欲望或意气活动作为灵魂的最高生活是否可能;第二,假设这种生活是可能的,进一步考察,欲望或意气的活动作为灵魂的最高生活是否可欲。
二、欲望活动的非自足性
欲望的种类繁多,每一种类又可细分为许多具体的欲望,因而,不可能考察每一类、每一种欲望的活动是不是适宜作为灵魂的最高活动。但无论如何,欲望作为整体有其自身的本有活动,这个特性将显现出其作为灵魂生活的最高可能是非自足的。
(一)欲望的生活作为灵魂最高生活的不可能
欲望有其自身的本有活动,那就是,它“所要求的不外是它本性所要求的东西”,“永远不会要求任何别的东西”。a柏拉图:《理想国》,2012年,437e4-438a1。比如,渴这一欲望所要求的只是饮料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活动似乎是自主的,似乎自然“知道”该如何正当地追求自己所缺乏的。但是,欲望并没有能力“指示”其所缺乏的是多或少,是好或坏;且欲望还容易受到其他诸种激情,尤其是,由意气引发的比较性激情的影响,如虚荣、自尊、骄傲,而“忘记”自身所正当缺乏的,去“追逐”超越本身所真正需要的。因此,欲望本身并“不知道”自己所缺乏的是什么品质的东西。
尽管欲望并“不知道”自己所缺乏的是什么品质的东西,但依然可以假设欲望统治灵魂是“合法”的,那么,统治灵魂的就必然是某种或某类欲望。这样,不同类欲望间以及同类欲望间必然展开争夺灵魂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但哪类或哪个欲望有能力“判断”哪类或哪个欲望是主导性欲望,并有能力统摄其他欲望呢?因此,如果一个人企图以欲望作为灵魂的本有活动,那么,他的生活只能是有所待的生活。
再者,即使假设欲望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并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这种生活卓越与否的重要标志,那么,为了积累财富,欲望本身似乎也会不断地呼唤节制的德行:区分必要和非必要的欲望。b柏拉图:《理想国》,558d8。但放逐了理性,欲望何以对欲望做出必要和非必要的区分呢?即使这个区分是可能的,那由必要的欲望来引导非必要的欲望会不会像盲人带路一样呢?c柏拉图:《理想国》,554b7。这样,追求财富的灵魂所拥有的节制德行,与其说是必要的欲望引导非必要的欲望而形成的,不如说,是为了一个欲望而压制另外一个欲望的结果。d柏拉图:《理想国》,554d。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以一个欲望压制另一个欲望也有可能形成某种德行,但这样的德行并非真正的德行,因为它是必然性的结果,因而,这样形成的德行也必然不稳定,且易被瓦解。
(二)欲望的生活作为灵魂最高生活的非可欲性
但即使欲望作为人类灵魂的最高生活是可能的,还须进一步思考欲望生活是否可欲。
表面上看,欲望间的竞争也有可能形成可欲的德行,如节制。但欲望竞争形成的节制并不能完全平息众欲望间的战争,节制的外表必然隐藏着一个被不同欲望所撕裂的灵魂。e柏拉图:《理想国》,554d8-9。痛苦煎熬的灵魂最后“明智”地做出一个能够彻底消除痛苦的政治决断:既然节制是欲望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那么,欲望并无必要与非必要之分,更无高低之别,最好的生活,是欲望平等的生活,是所有快乐都值得追求和体验的生活。因此,应该赋予所有欲望追求自己生活的“自然权利”。f柏拉图:《理想国》,561c-d。但问题是,这样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理想国》中“健康”的城邦是一个诠释这种生活方式好坏的最佳例子。在卷二,阿德曼图斯建立了三个“理想城邦”中的第一个。一方面,建城的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然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建城的目的在于满足灵魂最低层次的生存(existing)欲望。苏格拉底说要在这个城邦里寻找德行正义,但在意味深长地列举了一大堆生活消费品后,他就悄然离开此话题,并以颂神的赞美诗来赞美这个城邦,称其为“健康”的城邦。g柏拉图:《理想国》,372b-e7。在这个藉神恩而建立的城邦里,人类的德行在哪里?与其说这是第一个“健康”的城邦,不如说,这是“健康城邦”的代表。“健康城邦”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极力推崇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其“劳动”与“报酬”将有着完全的一致性。h[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页。显然,任何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都不会对这类“缺乏德行和优秀”的“健康城邦”感到满足。格老孔称之为“猪的城邦”, 而尼采则客气地把“猪”称之为“末人”。
但非常可悲的是,面临上述困境给最美好的生活带来的挑战,许多智识人竟然无动于衷,反之,与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因为人类的理性无力解决这些困境。因此,与其追求什么所谓最美好生活,不如勇敢地把欲望活动作为本源,作为灵魂活动的最高权威,更有甚者,还企图把理性沉思也理解为快乐,将之等同于欲望的满足。
三、意气活动的非自足性
与欲望的非自足性论证相似,这部分也试图从“可能性”与“可欲性”这两个方面,论证另一个激情活动的非自足性,即意气活动的非自足性。
(一)意气活动作为灵魂最高活动的不可能
一般说来,意气的本有活动是愤怒。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勒翁提俄斯(Leontius)为了捍卫自己的灵魂秩序而自觉地展开与邪恶欲望进行斗争的动人场面。a柏拉图:《理想国》,439e2-440c。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往往也自觉地参照自己的灵魂正义,愤怒地声讨政治领域的非正义,彰显自己的正义观。然而,愤怒必须要有一个前提:“知道”什么样的灵魂秩序是“正义”的。但在理性引导意气之前,意气何以“知道”正义呢?从柏拉图培养护卫者以政治德行的教化中,可以看出,意气的本有活动并非愤怒而是模仿。因此,这里,主要依据模仿的特性理解意气活动作为灵魂最高活动的不可能。
模仿活动最主要的特征是其模仿对象的多样性。因为,它既可以追求高尚的荣誉,也可以追逐社会推崇的金钱;它既可以模仿英雄,也可以模仿富人……总之,它既可以追求永恒,也可以追逐流行;它既可模仿德性,也可模仿邪恶。意气模仿对象的多样性,源于意气自身并“不知道”自己所模仿的对象应当是什么。而意气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所模仿的对象应当是什么,是由于意气活动受制于社会舆论。所以,意气活动不可能有一个恒定的目标,其目标必然随着社会评价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在某些时候某个人所推崇的德行,在另一个时间,他自己也可能将其视为恶行;在某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推崇的德行,在另一个时代也可能被视为恶行。
再者,就算假定灵魂的最高活动是意气活动,但意气本身也没有能力“判断”自身应该如何活动,这就可能导致自身活动的极端化:过度与不及。在《优台谟伦理学》的“德行表”中,亚里士多德列举了14对极端化的意气活动表现,例如,鲁莽与怯懦,放荡与冷漠,挥霍与吝啬。b[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优台谟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20b38-1221a12。为此,亚里士多德设置了德行培养的中道原则,以避免意气活动的极端化,然而,其中道原则的设置必须在正确理性的指导下进行,c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02a.这恰恰说明意气本身不知道该如何活动。
(二)意气活动作为灵魂最高活动的不可欲
相较于欲望,意气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它为政治德行的塑造提供了可能,也显示出了人的优异性;但从成人的最高目标来看,政治德行也不是人类最高的德行类型。这里,主要通过讨论“人是政治动物”是否是成人的最高可能,来阐明意气活动作为灵魂最高活动是不可欲的。
意气活动所能造就的最高人类类型只能是“政治动物”。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看做介于“神”与“兽”之间的“政治动物”。d[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253a1-29。有激情的人会急切地不加反思地认为,“政治动物”是成人的最高可能,或者说,人作为人所能过的最高生活只能是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相较于柏拉图,他则更加强调激情在德行塑造中的重要性,强调德行的形成并非全然观照于洞穴外纯粹的善。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人理解为更具激情特征的政治动物也无可厚非。但亚里士多德并不因此就认为“政治动物”是成人的最高可能。其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不可能成“神”,但也不应该为“兽”。无疑,在这个意义上,人所能成就的只能是中道的“政治动物”。然而,政治生活又必须借助意气活动,而意气活动恰恰必然削弱人的理性活动;因而,即使在理性指导下,政治动物也不可能是人类最高的成人类型,只能说,它是大多数人所能成就的最高生活类型。其二,亚里士多德并不因此就否定人类成人的最高可能,因为政治生活低于哲人的生活。因此,“人是政治动物”就并非是对人最高生活类型的完整理解,它没有包含人作为人所有可能的生活类型,特别是,没有包含人类的最高可能生活类型,即理性地生活。其三,在讨论城邦的本质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要在其完成之后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尚未完成的事物不可能定义事物本身;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0b23-1261a8。同样,“政治动物”作为尚未成人的人就不能作为人类的最高类型。
四、理性活动的绝对性与政治城邦
在第二、三部分,依据事物活动的自足性原则,排除欲望和意气作为灵魂最高活动的可能。因此,在灵魂的三个活动中,只有理性活动是本有而无待的。所以,这个独具无待的理性活动就是灵魂整体的本有活动。基于此,古典政治哲人认为,理性具有统治激情的资格,成人的最高可能性只能是理性活动的可能;但他们并不因理性活动的这种绝对性而在政治生活中完全排除激情。这就是古典政治哲人的理性至善与政治上的理智清醒。
(一)理性活动的自足表现
根据事物活动的自足性原则,虽然确立理性活动是灵魂整体的本有活动,但还需进一步阐明理性作为灵魂本有活动的表现。
第一,理性是自身活动的原因。既然理性活动是无待而自足的,理性自身就有着内在的动力去实现其自身,那么,理性就是其自身活动的原因。因此,就灵魂这个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整体而言,理性的活动并不受制于灵魂其他两个部分的活动;相反,理性能够消除其他两个部分活动对自身活动的影响。
第二,理性具有认识最高善的能力。理性活动的自因决定了理性所探究的必将是事物的整全,而非个别的具体事物。因而,理性必将超越具体事物的意见领域,走出洞穴,观照最高的善。就人类灵魂而言,正是由于理性对最高善的追求,理性具有判断灵魂善恶的能力,知道灵魂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有能力辨别与消除僭越灵魂最高善的其他价值。
第三,理性地生活是人的内在本质。理性的自因及其认识灵魂最高善的能力决定了人作为人的最高生活是理性的生活,理性地生活是人的内在本质。在《申辩》中,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这对人而言恰恰是最大的好。”b[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38a6-7。
第四,人的生活(living)不同于人的生存(existing)。人的内在本质不但指明了人作为人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它也决定了人的生活比动物的生存具有绝对的高贵性。比如,狗的生存,宽容一点,也称之为生活,但无论如何,都不如人的生活高贵。人的内在本质无条件地要求,人作为人不但要把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区分开来,甚至也必须把人的生活与动物式人的生活区分开来。表面上,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必要,实质上,这种区分比人与神的区分更为根本。如果说,人与神的区分确立了理性在属人世界的至尊地位,那么,人的生活与动物式人的生活的区分就不仅仅确立了人类生活的高贵性,更是理性的绝对命令:人作为人的生活只能是高贵的、有德行的生活。人固然不能自认为智慧,与神比肩;但人作为人更不能自甘无知,情愿受欲望统治,放弃理性成人的理想,贬低生活的高贵性,把自己的生活不断地激情化,甚至动物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值得人过的生活需要付出德行的努力。c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098b-1099a.
第五,理性地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参照。理性的本有活动要求政治哲人必须以理性生活为参照,来研究与探究城邦的政治事务:城邦的政制构想,选择什么品质的人作为城邦的最高领导,如何分配职务,如何教化公民……一句话,如何使城邦秩序与正义灵魂相对应。a柏拉图:《理想国》,368d。
(二)确立理性统治激情的资格
与理性活动的自足能力相对,在古典政治哲人看来,激情活动属于不能自足的意见领域。因此,如果放逐理性,单纯地以意气或欲望的活动为人类的最高活动类型,人的生活就必然丧失了好与坏、高与低的判断标准;即使意气或欲望的生活不会发生冲突,也不能说明这些生活就是人类灵魂良善的生活。因为,以意气或欲望为最高生活类型的人生只能是不完全的人生或单向度的人生。他们或许有与其职分相应的德行,如工匠的节制,战士的勇敢。他们甚至有权声称,自己的生活是完全正当的、高尚的,但却没有资格说,他们的生活是良善的。毕竟,他们的生活缺乏人作为人最重要的德行,即理性地活动。因而,他们的灵魂是残缺的,不可能过上真正无待而自足的生活。他们只有与智者一起生活或者在其指导下生活,才能模仿或分有理性德行。
因此,对于古典政治哲人来说,要造就灵魂正义的人,就必须赋予理性以“领导者”的身份,意气和欲望以及由它们衍生的其他激情则是需要驯化的对象;理性与激情有高低之分,不容混淆,更不容激情僭越理性而成为灵魂的主宰。柏拉图认为,由理性对激情的驯化而形成的灵魂秩序,即正义,这种灵魂正义的生活是良善的生活。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形象,或者说,以一个真正哲人的形象比拟理性生活的高贵。与灵魂正义构成对峙的生活,是受任意激情彻底支配的生活,是灵魂混乱无序的生活。柏拉图以僭主的形象比拟激情生活的无序,认为,僭主的生活比哲人的生活痛苦729倍。b柏拉图:《理想国》,587e3。
与正义的微型城邦相一致,政治城邦也必须是理性统治激情的城邦。因此,最佳政制必须树立理性为“大宗师”,认定理性为政治的向导与指南,教化城邦公民认识自身的自然职分,促其按职分正当地参与政治活动,形成与政制原则相一致的政治德性。只有这样,每个城邦公民才能过上与自己的职分相宜的幸福生活。相反,如果一个政制混淆理性与激情,甚至颠倒理性与激情自然正当的领导次序,那么,城邦公民的灵魂秩序也必将是混乱与颠倒的,他们的生活也必将是悲惨的。
在《理想国》卷八和卷九中,柏拉图描绘了由最佳政制王制到荣誉政制,由荣誉政制到寡头政制,由寡头政制到民主政制,最后由民主政制到僭主政制的颓变过程。柏拉图描绘政制颓变的目的不在于揭示政制发展的历史规律,不管是线性的,或者是循环的,或者是螺旋式的,而在于再次确证理性统率激情的自然正当,维护理性的至善地位,并全面地展示,违背这个自然秩序将如何给城邦公民的生活带来种种悲惨。因为,由高一级政制到次级政制颓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理性与激情的区分,颠倒了两者不同的政治身份。
(三)理性的绝对性与政治现实的关系
固然,理性地生活是高贵的,但它却不是最先的、第一位的,急迫的政治生活往往先于理性生活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理性或哲学并非同步,也非亦步亦趋。政治哲人必须正确对待理性的绝对性与政治现实间的这种冲突。
既然理性地生活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因此,不管政治生活多么急迫,都必须坚持理性的绝对性。没有理性,人类不能生活;没有理性,人类也不能生活得好。政治哲人作为哲人,不能因为政治生活的急迫,就人为地迎合激情,抬高激情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漠视理性,取消理性,放弃人的内在生活是理性地生活的最高成人目的,而让激情僭越理性,建立一个只满足于激情生活的政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为政治哲人如何根据人作为人的本质,构建城邦而树立了一个典范。在《理想国》第一类城邦,即“健康的城邦”中,每个人都从事与其天赋相宜的技艺,并完全满足欲望生活的需要。但哲人并不会因之就认为这类城邦是完美的,因为,它不能体现人作为人的本质。在第二类城邦,即“发烧的城邦”中,虽然每个人(护卫者)的意气活动都得到完全的实现,具有了超越欲望生活的政治美德,然而,哲人认为,政治动物也不是人类最高的生活类型。因此,哲人必须继续前行,直至最终建立一个城邦,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完全理性地生活的可能。
政治哲人作为政治上的哲人,也不能因为理性的超越性而无视政治现实,疯狂地实施哲学王政制,彻底地消除灵魂中的激情。政治哲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每个人的灵魂都具有理性活动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并非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运用理性,因而并非每个人都能理性地生活。在此意义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离不开欲望与激情,政治世界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内容忍一些人灵魂的内在冲突,容忍一些人合法而非正义的生活。如果我们把《理想国》三个单一类型的城邦结合为一个完整的城邦,那么就可以看出,在完整的城邦中,人类灵魂的三个部分都有与其相宜的活动空间:欲望活动对应于第一类型城邦,意气活动对应于第二类型城邦,理性活动对应于第三类型城邦,两相不损害,和谐有序。理性作为灵魂的本有活动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绝对性而彻底摧毁欲望活动和意气活动。
政治哲人作为哲人,正是基于对理性活动的坚定“信念”,才能在激情的政治挑战中,坚守自身统率激情的绝对权威;同时,政治哲人作为政治上的哲人,又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现实的急迫,因此,在坚守理性权威的同时,又留给激情活动以一定的空间,并引导激情“同意”自己的生活必须是理性指导下的生活,从而实现理性与政治尽可能完美地结合。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也并非完全遵循柏拉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清醒地认识到理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修正理性的绝对性与政治现实的关系,试图通过激情的中道给政治德行的塑造留下更大的空间,或者说,以中道的方式,更好地处理理性与激情的关系。a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多次指出,德行的培养所依据的“知识”只能是“粗略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b26-27、1104a1。一位论者对此做出较好的阐明,“亚里多德一开始就强调了政治知识的限度。政治学的主题,即人的行为,允许多样性和不规则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可能期望获得自然科学或数学那样的严格知识。……他甚至认为,在政治和伦理事物中要求过分的精确性是一种不成熟的标志。我们从政治中抽引出来的任何一般法则,都只能是暂时为真,或者大部分情况为真。”b[美]史蒂芬·B·斯密什:《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但亚里士多德自始至终都没有否定理性的绝对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始和最后,他都强调了以理性的最高活动统一灵魂活动的重要性。为此,他不但把灵魂的德行区分为道德和理智两种德行,而且还把理智德行进一步区分为“思考不变”的事物和“思考可变”的事物。c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39a15-22。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区分的目的在于保护一个超越政治或道德领域的纯思世界。因此,亚里士多德虽然扩大了灵魂所涉及的范围,把植物和动物也看成是有灵魂的,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柏拉图的灵魂等级制,因为,理性活动仍然高于欲望和意气的活动。
总之,古典政治哲人根据理性的自足性原则,不但确立了理性对激情的领导地位,建立灵魂正义的城邦,而且还通过对灵魂秩序的模仿,建立了激情生活之可能的外在政治秩序。所以,古典政治哲学很好地解决了理性与激情的关系问题,既维护人类成人的唯一可能,即理性,又留给激情的政治生活一定的空间。相反,如果一个政治哲人违反了理性的自足性原则,颠覆理性与激情在灵魂中的政治身份,即使有可能建立一个外在的政治秩序,这个政制也必然发生颓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政制将损害人类成人的唯一可能——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