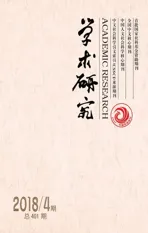历史性的历史:现象学的新理性主义
2018-02-20卓立
卓 立
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及其生活世界思想,虽已广为人知,并随着近些年胡塞尔后期手稿的整理出版而日益受到重视,但如何准确定位它却仍然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由于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引发的存在论转向在胡塞尔后期便已产生巨大影响,加上纳粹统治的因素和胡塞尔本人对正式著述的谨慎态度(大量后期著述没有在生前出版),导致对于整个思想界而言,后期胡塞尔思想的出现反而是晚于海德格尔及其后学的。这便导致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胡塞尔之所以会转向后期偏重历史性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从而纠正了自己前期的“近代哲学残余”,放弃了笛卡尔式道路。于是前期胡塞尔的先验哲学便成为一种胡塞尔晚年自己放弃了的错误,胡塞尔哲学由此便被理解为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过渡学说,其意义也就堕落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哲学史组成,用德布尔的话说即是“正是海德格尔的学说使胡塞尔所追求的‘唯一’哲学衰变为胡塞尔自己的哲学”。a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页。就此而言,倪梁康先生近期已经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一文中指出了胡塞尔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还早于海德格尔。b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因此胡塞尔关于历史性的反思,绝非受海德格尔影响,而只能是胡塞尔思想中必然的趋向。
关键是,众多研究者之所以会把胡塞尔哲学视为通往海德格尔的过渡哲学,这种说法不仅本身即隐含了历史进步和真理信念(实际上是把胡塞尔的错误哲学视为通往海德格尔这种正确思想的发展阶段),而且根本上是由于确信真理与历史是绝对冲突的,从而把海德格尔相对于胡塞尔的“正确”,理解为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对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正确。在这个时代,随着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德国现象学阵地的沦陷,分析哲学与现象学隔河对峙的格局似乎已经被打破,现象学越来越被理解为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进而也被理解为最终是反对理性主义的。
问题在于,真理与历史难道就真的只能是绝对的对立者?历史性的绝对化,是否只能意味着普遍真理是错误的近代立场?反科学主义(自然科学意义上)难道意味着必定是反理性主义?许多人似乎都忽略了,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胡塞尔正是在反科学主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想,明确表示:“我要重新强调的是,正确的和真正的哲学,或者说科学,与正确的和真正的理性主义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的任务仍然是实现这种与启蒙时代的具有隐藏矛盾的理性主义相反的真正的理性主义。”a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8页。也就是说,胡塞尔在该书中虽然承认了历史性的绝对性,从而提出了以生活世界理论为核心的历史现象学,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提出新的理性主义,并视之为真正的理性主义。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承认绝对历史性的理性主义呢?
一、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悖谬
显然,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旧的理性主义”或“错误的理性主义”,因而必须重新回溯理性主义的发展及近代理性主义。
近代西方哲学中,有一种与经验主义对立的唯理主义,指的是强调理性作为一种自在真理的立场;但更通常的用法是,把理性主义称为那种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力图遵循科学方法论,通过开显人类自身理性去把握普遍客观真理的知识论立场,在这意义上,所谓经验主义自然也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构成西方近代整个现代性思想的中枢,而它也就是我们本文所说的近代理性主义:它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意义上是与思想的蒙昧状态对立的,而在现代思想的意义上是与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立的。
最初的理性主义源于古代希腊对本质和本原的反思,胡塞尔因而把古希腊视为人类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b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22页。本原与本质不同,而所谓爱奥尼亚哲学传统与南意大利传统两大系统的差异,也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关于本原,希腊文为arche,也译为“始基”或“基质”。初民对世界的理解首先是一种实物化的思维,希腊哲学即是从具体事物存在的反思开始,也即所谓的自然哲学,这时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还没有确立,关注的重点是“实在之物”意义上的“多”中之“一”,或者说,多样化的具体之物根本上是何物?这便是本原思路的原初问题,这一思路的指向一定是“物”化的,是指向“质料”的。因为形态/形式支撑着具体的多。但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数作为本原提出的意义在于,数是几何形状的本原,或者说,是几何形态之“多”的“一”,这种“一”的朝向,使原来作为多样化的形态摆脱了“多”,而构成本原的源头。这便导致对本原的反思有可能脱离“物”化的“质”。这种关于形态的本原反思,导致本原朝向了抽象的不可见者,这就意味着本质的出现。本质,在这意义上不只是“一”,而且可以是相对于具体存在的,于是就指向了本质与现象的对立,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而这种从具体形态到本质的追问,也就成为从“变”到“不变”的追问,“变”中不“变”的问题,便取代并包含了“多”中之“一”的问题。不变的本质仍然可以是“一”,“不变”蕴涵着“一”,具备本原的关键特征,而本质又可以是事物所是之所系,流变的现象则指向“多”,“变”蕴涵着“多”,使得事物的“多”与“一”在本质中获得统一。在本质的反思中,由form到idea,从具体存在之形态形式,到对其本质的反思,构成了逻辑序列(如三段论)的追问。这是自然哲学的本原之思不可能通达的。正是从本质追问中,“一”与“多”的对立被转化为“变”与“不变”的对立,也即本质与现象的对立,而由形式到共相到范畴,最终对接了命题真理与形式逻辑,一种通常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形式理性便被确立起来。世界及其具体存在物由此被分解为质料与形式二元,形式是通向理念王国和真理的,而本原中包含的具体之物的思想路线则以“质”的名义隐匿下去,实际存在物被理解为依赖相对化的感觉来把握的赫拉克利特之流,是旋生旋灭的,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是自身矛盾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作为这些具体存在之物的记录,是对流变的现象的记录,也就不属于真正知识的领域。而理性作为对“变中不变”的“本质”的把握,便是对历史之无限流变的超越。而本质作为“一”对作为“多”的现象的统摄,是从“一”到“多”的演绎式方向(比如分有说、流溢说等所描述的),因而“一”与“多”之间是统一的。
近代之后,随着观测工具、数学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得以用数学实现对事物全体的精细描绘,导致这种形式加质料的世界公式被瓦解。伽利略的望远镜让天体运行不再是假说,最终变成数学化的可预测的天文学,从而彻底击穿了寄托天国的宇宙;而显微镜等让我们深入事物的内部结构,使事物的属性和质料都全面地被数学化,而不再诉诸“元素论”这种粗糙的假设,其结局,就是那个质料在被数学化的同时被形式化消解,“质料”由此无穷地后退,最终成为神秘的自在之物——因为凡是被认识的都会成为可数学化的形式内容。近代理性主义的基本设想就是一种消除“质”的数学普遍主义,在通过对全部“质”的同质化和单位化过程中,完全的精确性也得以实现,这使人类得以对“物”及作为“物”的集合的世界实现精确的预测与控制,从而发掘出了巨大的力量。就此而言,世界已经不合适理解为质料与形式的自在的二元对立,而是整体地转换为一个被认识的形式的世界与一个永远不可抵达的自在之物的对置,或者说根本上是建构着全部形式的普遍主体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内外二元对立。而把握本质的形而上学理想作为一个本体论问题,也就转变为内部的知识如何切入彼岸的自在之物的知识论问题。
在这种伽利略主义的展开中,首先意味着质的被彼岸化和自然的被本体化,或者说,在质的无限后退中“自然”得以出场并反转了它与形式的关系。因为当人类在“物”自身中“发现”了远比古代形式理念更为恢宏和精确的形式系统,这种发现导致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被人类掌控后,精确性导致的预测功能便完全击溃了形式逻辑的空洞解说(比如伽利略对木星的预测导致的巨大影响)。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是依赖于仪器对我们“感官”的扩大来实现对自然更深入的“发现”,再通过实验与归纳来展开数学与理论的,这便导致人类开始确信真正的理性是深藏在作为自然物之总和的“自然界”中,而这个“自然界”也就是自在的“物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自在的自然界作为全部自在理性的母体开始成为人类世界观念的核心假设,成为新时代本质观念的内核,即作为变化之源头的自在者,而自然规律和自然科学由此也成为理性知识的模板。这就是一种形式化的自然理性的奇异设想,即这种理性完全是形式化的,而且是远比古代的理念更为符号化的数学形式,但它又是作为“实际存在之物”的总和的自然的理性。而符号化的形式理性与实物化的自然理性在这里的奇妙统一,是以“质”的退隐为代价的。
其次,形式是在数学化过程中实现对自然的深入和对质的消解,而与形式逻辑的概念演绎不同的是,它不仅可以实现精确性,而且还意味着无限性的建立。或者说,当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普遍数学的世界,那么异质性导致的有限性理解便被完全同质的符号无限性所取代,因而,在一个数学化的牛顿时空的设想中,整个世界是无限延伸的。那么,在这意义上,一个自在的作为本质的自然界,就是一个作为无限性的本质,而不同于古代那个作为“一”的本质(如太阳或上帝),而这个无限性最终恰恰是由“自在之物”这个无限后退的“质”的无限后退来提供的。
再次,对自然的发现和形式对“物”的深入,是依靠经验知识的推进来实现的,这意味着由此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只能理解为被经验主体认识的知识,于是,“质”的无限后退也就意味着主体的无限扩大,形式与质料的本体论二元世界图式,就转变为永远对峙着的主体与自在之物的认识论的内外二元区分。支撑着自然界的形式认识的主体,也就成为一个形式理性化的普遍主体。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蕴涵理性的“自然”这个观念中,同时包含了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向:一者把它理解为是自在的作为“物的总和”的“自然界”;另一者把它理解为主体的现象知识的集合。其中前者实际上基于“物”与作为物的人的“心灵”的第一种内外对立区分;后者则基于“自在之物”与普遍主体的第二种内外对立区分。前者实际上就是经验主义哲学,后者则为唯理主义哲学。就此而言,前者的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以物理学为模板的自然理性,也就是说,支撑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知识合法性的是人作为自然物被预设包含的理性,它最终必须返回人类作为自然物的普遍生理—物理结构。而后者的理性主义则是以数学为模板的,它基于一种“非物”而又某种程度上仍是“自在”的普遍主体性设想,就此而言,它最初仍试图诉诸古代的本体论形式理性,但最终则只能走向先验的理性。
最后,对于古代理性主义而言,“多中之一”与“变中不变”的统一导致作为“变中不变”的本质既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殊相中的共相与普遍概念之间是合二为一的。而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中,对“变中不变”的把握被迫缩小到了“自然规律”这一有限范围。因为本质与概念不再是统一的,本质是指向了无限后退的“自在之物”,在这意义上,它并不是“一”,而是“多”与“无限”,但又被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变”的源头。也就是说,如果要从本体论上把握“变中不变”,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回溯到“自在之物”,而是以超越时间的“自然规律”来取代了这个“自在之物”。另一方面,概念与命题被理解为是在归纳和反思具体现象时进行的抽象思维结果,也就是它们仍然维持了对“现象”之“多”的“一”的地位,但如果它们要成为“变中不变”,就只能以作为对“自在之物”或“自然规律”的唯一描述才可能合法,而“自在之物”显然无法触及,因此概念和命题是作为对于“自然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描述才获得作为“变中不变”的合法性的。就此而言,近代理性主义的模板也只能是“自然规律”,只有它才能既是“变中不变”,又是“多中之一”。但要注意的是,自然规律作为“变中不变”在本体论上是并不纯粹的,它实际上是形式化的;而如果自然规律只是作为纯粹的形式,那么它最终就会被理解为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从而仅仅指向“多中之一”,这种“多中之一”并非作为本质的“一”,而是作为唯一正确的“形式化的描述”。这便指向了所谓融贯论的真理学说。
因此,近代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在继承古代探求“变中不变”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前提下(以“发现”自然规律的方式),在普遍数学化的伽利略主义蓝图下对古代理性主义的全面转换,而这种转换包含了许多自身冲突的信念和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这种转换最终是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对立世界图式取代了形式质料二分的本体论对立世界图式,其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本质变成了无限的自在之物这样一种“多”,现象则成为对应于“真实世界”的唯一正确知识这样一种“一”。也就是说,本质/现象与“一”/“多”的关系完全反转了,而如何把握永恒的自在本质的问题也就转变成了如何获得知识确定性,或如何确保知识是唯一地符合事实之“真”的“知识何以可能”问题。
这就意味着近代理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最终将导致其崩盘的内在理念。首先,近代理性主义继承了源自初民实物思维和古代理性主义的“存在信仰”,即那种把握某一“事物”必先预设此“事物”预先“存在”的信念,也即胡塞尔批判的自然态度下的“超越者”和海德格尔批判的“存在者”。根本上说,常识中我们只能是在“存在信念”的前提下,或者说把一切都先理解成是个“东西”,才能理解世界、事物、现象、认识活动和自我,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从这种信念出发,它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在近代的伽利略主义数学图景下,自然作为形式的母体被视为是预先存在的自在者,从而也就指向作为“万变”之源的本质,但对自然的认识又意味着把质消解为数学形式,而纯粹的形式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的“发现”而不能是作为根源的本质。因此所有被认识了的自然便都蕴涵着重新设定某种未知的预先“存在”作为更底层的自在者或本质;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回溯是数学的展开,从而也是无限性的展开,于是世界的无限性也意味着本质的无限性后退,或者说,恰恰是在本质的无限性后退中世界才展示出它的无限性。因此,自然既要作为预先存在的本质,又由于它在认识中被数学化导致其“预先性”只能无限后退,而无法如古代一样强行中止于“上帝”。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作为预先存在的“自然世界”还是作为“万变之源”的本质最终都无法出场,而那作为依据的“预先存在”的理念自身也是永远不能证明的。也就是说,一种基于“存在信念”的数学化的自然理性,最终是一个无法自证理性自身合法性的不彻底的理性,也是一种本质或“被发现者”永远无法出场的失败的二元图式。
其次,近代理性主义意味着一种将实际现存的世界与普遍化的命题知识对立的抽象主义,这种抽象主义决定了命题知识与“世界本身”之间永远实现不了预想中的一一对应之“真”。如前所述,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中,自然—本质成为“多”,而知识—现象成为“一”,也就是说,“一”与“多”的关系在近代被反转了。因为在古代,“一”是本质,那么从本质到现象就是从“一”生出“多”,从知识上就是从原理之“一”演绎出具体知识之“多”,“多”即使指向无限也是永远与“一”“符合”的。而在近代,本质成为自然则意味着从本质到现象是从“多”到“一”的过程,而认识则是如何从显现之“多”指向原理之“一”和确定之“一”,也即归纳如何指向“真”的问题。这便导致了一个重大困难,即当“多”成为“无限”时,从“无限”到“一”的返回便导致两者的断裂,因为“无限”在“一”之先,它的无限意味着不受“一”之完全统摄。所谓休谟问题,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困难,最终都与此有关。因此,抽象的方法,如果仍然是指从具体和“多”中“抽象”得到作为“一”的概念或范畴的话,最终必将导致个别与概念、实存与命题、知与行的背离,保留抽象思维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感性客体”和“活生生的,必然具有对象与他者的现实生活”。a丁耘:《胡塞尔现象学的转型意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2年第00期。近代理性主义的这两个根本悖谬,也就是张祥龙先生说的“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但其根本病根却不合适单方面视为“唯理论”,而是在于古代和近代的理性主义都不可能应付在近代之后才逐渐绝对化的历史性。b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修订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总结以上分析,古代理性主义是从追问实物之“多中的一”转向追问“变中不变”后在形式质料二元论中建立起来的本质主义。而近代科学对形式质料二元论的打破,导致自然的本质化和数学化,从而转化到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世界图景,进而导致“多”与“一”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也动摇了“变中不变”的理性主义设想,历史性问题便开始成为理性之自身合法性的关键。
二、历史性与现象学
要真正理解现象学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地理解历史性。在第二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上,倪梁康先生说,“我的理解:现象学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意味着:在本质直观中尽可能真诚地反思和反省自己,同时尽可能透彻地审视本己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尽可能切身地理解精神共同体以及它的历史性”,并认为绝大多数的现象学研究者都会同意他对现象学的这个理解。也就是说,“历史性”是构成现象学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历史性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本质,即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处于历史生成之中,而它恰恰是基于自在世界这个近代理性主义的信念,对应于胡塞尔所批判的“事实的历史性”。绝对的历史生成意味着绝对的变化,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对绝对的无穷而不可逆的变化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及其他现象学家往往将这种绝对的变化,混同于“赫拉克利特之流”,但两者在根本上其实是不同的。c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9页。对于“赫拉克利特之流”而言,其前设是存在物。如上所述,以爱奥尼亚派为代表的最初的哲学贯彻的仍是由实际存在物开始的反思,四根实际上也都是存在物;而“赫拉克利特之流”强调的是一切存在物都处在生生不息的流转过程中,这个“流变”是以“无物常驻”之“物”为前设的,就此而言,它指的主要是对立于不变者的变。从这一点出发,所谓世界、事件与历史都是变动之物的显现,而这种显现根本上是在场的,并且不是以一个绝对的预先在此的自然世界作为最终的前提,而至多只是以一个“周围世界”作为前提。而现象学反思的历史性,则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近代世界观念与历史观念。
如上节所述,在近代,一个无限的自然世界被预设为一切的前提和最终的本质,就此而言,现实世界不再是逻辑上后于“物”的“物”的聚合物,而是逻辑上先于“物”的“物”的源头与场所,“物”绝对地无条件地在预先在此的世界中。就此而言,流变便不再属于“物”,而是属于世界,多样性就不再是由于物的流变而导致,而是世界自身蕴含着无限的多样性,这种基于预先在此的自在世界的无穷流变的观念便是历史的观念,或者说历史的观念以世界的观念为前提。从而,由于世界的自在和无限性,历史也就指向了一种绝对的无限的变化观念,而这种变化指向的是一种在世界中的不断生成,或者说世界的无限地“涌现”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际上是指向了在世界中的变化,历史性即是这种变化的本质,因而,历史实际上取代了“隐蔽的质”,成为多样性的源头,永恒的理性与瞬时的流变/感知的对立,就转化为普遍的理性与多样的历史的对立。西方专业历史学(兰克与尼布尔之后)的诞生,或者说历史学作为知识的合法化,便是基于这种多样性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历史作为关于流变的记录欠缺知识的合法性(合法的知识是从一至多),但在近代,历史作为多样性的记录,则由于知识已经被理解为是从多到一的归纳结果而获得了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学,是作为记录材料的历史学,是等待归纳整理的多样性的素材库。而以自然规律为典范的真理,则必须最终是超越这种历史多样性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近代理性主义延续着古代理性主义追求“变中不变”的意旨,但由于“自然界”的自在化与本原化而导致其逐渐转变为理性对历史的超越这个主题。
实际上,历史性在哲学追问中是在近代才逐渐出场的,在传统哲学中追问的对象往往是时间,而不是历史。因为传统哲学关注的中心是流变,而依托流变的是被静观的对象或“物”,而物根本上是以占有空间的方式被理解的,由此产生出广延的思想。时间在这意义上是依附于空间的,因为对空间的占有的延续,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都将导致时间概念的产生。对空间的反思最终是指向对形式的反思,而当空间被数学化,时间也同样被数学化。确切地说,当我们反思的是“物”的变化时,我们根本上反思的是时间而不是历史。在一个科学实验中,探究的是可无限重复的数学时间中不变的运动形式,而不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间,所以实验才能被理解为是可无限重复的。由于传统哲学一直追问的是事物之变中不变,导致始终以时间作为致思方向,而以自然规律为典范的近代理性主义的普遍数学模式更加强化了这一点。时间问题因而是哲学中的关键问题,而历史问题若被提及往往是在讨论时间时被笼统地包含在内。这也是在现象学中长久以来不直接提出“历史现象学”的一个原因,因为时间问题被理解为是更为根本的和理性的,并已经包含了历史问题,反观历史由于与具体存在相关,从而不是“第一哲学”的目标a兰德格雷贝:《胡塞尔告别笛卡尔主义》,罗丽君译,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13页。。胡塞尔因而区分时间与时间性,b倪梁康:《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2010年第2期。并且,现象学的最初目标与历史性之间也似乎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的,以至历史问题最终将可能引发对现象学之无前提原则的越界cLembeck ,“‘Faktum Geschichte’und die Grenzen phänomenologischer Geschichtsphilosophie”,Husserl Studies, 1987, 4(3),p.221.。但如果我们真正去仔细反思一下就会发现,自现象学诞生之后,历史一词便显得越来越重要的。实际上,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通篇谈的与其说是时间,毋宁说是历史,尽管他在认为“历史性是存在的性质”之余,又视此在“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d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 426-427页。时间与历史之间往往混为一谈,然而可以肯定,历史一定是以世界之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一旦世界的观念发生变化,历史的观念也会随之而变。历史性问题在现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中的彰显,正是与世界观念的变化有关。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去仔细反思一下就会发现,自现象学诞生之后,历史一词便显得越来越重要的。实际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谈的“时间”是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所谈的真正的时间问题完全不同的。历史与时间不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最简单的区别,历史一定是涉及存在论的,时间却可以是在一种内在观念意义上讨论的,所以历史一定是包含着实际内容的,而时间却可以是数学化的。时间与历史之间往往混为一谈,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历史一定是以世界之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一旦世界的观念发生变化,历史的观念也会随之而变。历史性问题在现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中的彰显,正是与世界观念的变化有关。
问题在于,当我们用绝对的历史性来理解世界自身无限的变化,这便意味着在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限的变化生成之中,那么,对于以“自然规律”为典范的“真理”本身也就同样如此了。历史主义者主张“任何对规律和真理的认识都是历史形成的, 因此都是变化不定的, 都是随时代、民族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相对有效的。”a倪梁康:《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如上节所述,由于自在之物遥不可及,我们对“变中不变”与“多中之一”的把握实际上是汇集在“自然规律”及“真理”之上,而不是古代的本质。自然世界在这意义上既是形式的总和又是存在者的总和,而这意味着“自然规律”及“真理”既是存在者又是形式,它们是处于世界之内的。既然如此,“自然规律”及“真理”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即一方面我们把它们视为“变中不变”和“多中之一”,是终极的形式,是我们最终能够理解的世界的根本。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不变者的支撑,世界本身也将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如果数学知识是永远处于更改中,那么近代的普遍数学化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们把它视为是在世界中的存在者,那么它就一定同样是处于生成和变化之中,就不可能再是“规律”或“真理”。就此而言,那种将一切知识都作为关于“存在者”的知识的自然主义设想(如经验论)就成为相对主义思想的主要源头。因此,至少是在自然科学知识领域,近代理性主义采纳的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折中方案:存在作为永恒不变形式的自然真理,而它之所以永恒不变,因为认知它的普遍主体不仅必然只有这一种最终真理的认识,而也是基于它才得以认识世界,因而它也就成为最终的确定的一,而不是随着认知的无限推进被无限地展开的多样性之一。这样的信念,与对数学真理、欧氏几何真理、牛顿力学、绝对时空及普遍人性等绝对真理的绝对确信有关,它们构成了整个近代理性主义的中枢。
因此,自19世纪下半叶后,由于现代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到整个自然科学都对原来的实在观念、时空观念和物质观念做了根本性的修正,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近代世界观念已经彻底分崩离析。非欧几何的出现是决定性的,它虽然并不意味着欧氏几何是错误的,却意味着几何真理并非被“发现”的,而是被构建和选择的。而恰恰是从非欧几何出发,物理学得以向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突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被视为普遍主体和普遍理性之载体的人是演化生成的,通俗点说是“从猴子变过来的”。那么,构成自然规律及真理的支撑点的普遍主体也就只是一种历史生成物,这便导致人们从根本上放弃了原本在自然规律的真理信念中被悄然接受的唯理主义信念,即自然规律与普遍理性根本上都是历史生成物,从而也并非是永恒和绝对的。同时导致人类在19世纪下半叶被迫开始重新反思知识的合法性基础。而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所谓心理主义,也无非是在放弃了将人类知识视为基于普遍主体的先验方案后,转而将人类的物理—心理这一自然世界生成物视为全部人类知识的基础的自然主义方案。易言之,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之下,坚持普遍真理的唯一出路在于坚持普遍主体作为一切真理的根基根本上是“非自然存在的”,从而最终只能是先验的;然而当现代科学将普遍科学变成被选择的建构之后,历史性就被彻底地唤醒了,人类、普遍主体、普遍理性及全部人类知识整体地都变成一种自然历史生成物。这就导致了一个近代理性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还有什么真理是超越于历史的?如果连数学真理都是生成的,那么近代理性主义自身岂不也成为相对于某一时代有效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了?
三、现象学对近代理性主义的超越
正是基于近代理性主义的这些根本悖谬,关于人类知识合法性的反思突破了主客二元论的模式,开始重新寻找其合法性基础。首先是黑格尔试图突破传统形而上学,以辩证法突破实存与真理的对立,将历史纳入理性,使理性不再只是超越历史的理性,而且是包容了历史的理性;心理主义则用生成物的人类生理—心理替换超越的普遍主体,试图以可操作化的科学实证来重新奠定人类知识确定性的基础;而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则自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之后,致力于彰显人类精神内部这一不可被自然理性化的多样性层面,从而开辟出一条拒斥近代理性主义的诠释学路径,并导致“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认为自然的方法与人文学科之间毫无共同之处”。aT. M. Seebohm,“Naturalism, Historism, and Phenomenology”,Advancing Phenomenology, ed. T. Nenon, P. Blosser,Springer, 2010, p.8.总的来说,历史性本身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但历史性也正是近代理性主义逻辑悖谬的集体显现,导致在19世纪中叶后,由于自然科学自身的推进引发了对近代理性主义合法性的反思与超越。倪梁康先生说:“现代哲学随着狄尔泰的出现和作用而完成了两次实际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当代成为了一个历史意识尤为强烈的时代,一个历史哲学或发生的形而上学的时代。这是从横意向性、结构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对横意向性的本质直观的路向转向纵意向性、发生的形而上学、历史理性批判、对纵意向性的本质直观的路向。第二次则是上述从精神科学的解释学和历史哲学到后哲学时代的可能转型。”b倪梁康:《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现象学正是诞生于这种试图超越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正如张祥龙先生所说,它“是由西方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哲学中存在的内部困难和内部问题所引发的一场哲学运动”。c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修订新版,第6页。而历史现象学,从后期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到海德格尔,一直到梅洛-庞蒂d佘碧平:《梅罗-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72页。,都是为了进一步超越近代理性主义。“我们应当把胡塞尔现象学理解为近代哲学的出路之一”,所谓的“现象学还原”与“回到实事本身”都是为了抗拒“自在世界”这个导致理性主义自身悖谬的近代观念,“现象学的主体概念绝不属于近代哲学”,“它已经克服了后者与客体的隔绝(如绝对精神意义的主体)和外在关联(如灵魂实体意义的主体)”。e丁耘:《胡塞尔现象学的转型意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2年第00期。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驳,对先验(超越论)自我的强调及后期生活世界的先验(超越论)前提,自始至终都是为了维护理性的彻底性而要求先把“预先有一个自在世界的存在信念”排除出知识合法性领域,而“这样的实现,消解了康德意义上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之间的区分”。f尚杰:《现象学的问题如何发生——德里达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解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期胡塞尔激烈地反对历史主义,至少是那种他视为自然主义变种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则是为了突破近代理性主义抽象方法的逻辑悖谬。正如马里翁所说:“一方面,对个体的意向行为而言,直观起着根本的展示作用——我们瞄向特定的这一座而不是另一座房子……我们依据的是如此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通过被用作单纯支撑物的第一种直观,我们也能瞄向作为经验中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房子之本质的那座房子”。g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6页。当胡塞尔悬搁了外部自在世界这个不合法的前提之后,便意味着自在之物丧失了作为“万变之源”的本质意义,那么“变”与“多样性”的源头便只能诉诸“内部”的观念领域。也就是说,本质直观摆脱了近代理性主义“一”与“多”之间的断裂,将“变”(现象)与“一”(本质观念)都统一于纯粹意识之中,自由变更由此便是本质直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超越论)前提与本质直观这两个主要的主张是分别针对近代理性主义的两个逻辑悖谬的,因而只有同时坚持这两者才可能做到超越和完善近代理性主义,或者说建立新的理性主义。关键在于,当现象学把“万变之源”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的现象学,便开启了第二种历史性。在现象学的这种视野中,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被倒转了,人不仅不再是神的被造物,而且也不是被动生成于自在世界中的高级物种,而是一个自主的创造者,甚至世界也因人而获得存在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的问题被转移到了人类历史性的存在论这一关联中”,a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问题》,励洁丹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人成为世界的源头与中心,人是一切变化的真正源头,从生存着的创造着的人的角度去看,世界以及一切存在者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导致的是,生存着的人的历史性也就成为彻底的绝对者,以至理性再也无法凌驾它、超越它、拒斥它。本质直观最终催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胡塞尔前期坚持的彻底的纯粹的理性也被绝对的历史性吞噬。这也正是当前流行的广义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基本特征,而胡塞尔则由于其坚持先验的(超越论的)理性主义立场和反历史主义立场被后继者抛弃。对近代理性主义之“理性超越历史”立场的超越,就转变成现代哲学流行的“历史消解理性”的结局,其典型代表便是后现代主义。
前期胡塞尔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没有发现近代世界的历史性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历史性之间的差异,而径直以“人类主义”批判它。由于将历史性仅仅理解为近代世界前提下的事实历史性,导致胡塞尔前期现象学对近代理性主义的超越,根本上仍是一种“把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排除在外”b保罗·利科:《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方向红译,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第802页。的以理性超越历史的方案,试图维护的是一种“不存在于‘虚空中的某处’,而是一个存在于观念的非时间王国之中的有效统一”的真理。胡塞尔认为,“真理是‘永恒的’,或者毋宁说:它是一个观念,并且作为观念是超时间的。为真理在时间中安排一个位置,或安排哪怕是穿越所有时间的持续,这都是毫无意义的。”c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0、128页。而实际上在其现象学方案中唤醒的新的历史性却是绝对的,是不可能被哪怕现象学的“彻底理性”超越的。
问题在于,胡塞尔在后期已经注意到了新的历史性,这才引发了他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扎哈维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彻底性恰恰就在于其一体化地思考历史性、世界分析与超越论哲学。”dD.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E. A.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0.胡塞尔后期以《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为代表的历史现象学思想,不仅是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观念,而且仍然坚持了先验(超越论)的原则,“先验自我在意识层的起源层面构造了社会历史世界”,eJ. Owensby,“Dilthey and Husserl on the Role of the Subject in History”,Philosophy Today, 32.3 (1988): 222.从而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历史性,胡塞尔将这种历史称为“内在历史”,或“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历史。单斌认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性的根基在于人格自我的历史性,而纯粹自我则是非历史的。但是《观念Ⅱ》中胡塞尔在处理历史和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已经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回忆,对应于不同的历史性。尤其是对纯粹自我的习性之揭示,表露了纯粹自我作为习性的纯粹自我,已经是具有其‘个体化的历史’。”f单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问题》,《学术界》2015年第8期。这实际上意味着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是在坚持着理性主义路线上对前期的推陈出新,“历史思考是胡塞尔破解其现象学困境的理论选择”,g孔明安:《意义的历史及其回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5期。现象学因而“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 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h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这种意义上的胡塞尔现象学不再是“超越历史”的理性主义,而是类似黑格尔的“包容历史”的理性主义,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理性主义才能真正是彻底的和严格的。而从这样的新的理性主义出发,我们也才可能走向社会历史存在领域的重新回归,并重新奠定全部人类知识与人文社会历史理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