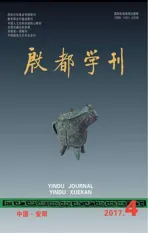西周金文兼语句研究
2017-12-21王依娜
王依娜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上海 201800)
西周金文兼语句研究
王依娜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上海 201800)
与殷墟甲骨文相比,西周金文兼语句的语义类型更加丰富。据统计,西周金文的兼语动词有“令、命、乎(呼)、卑(俾)、史(使)/事(使)、召(诏)、妥(绥)、鱎(薄)、遣、右(佑)”10个。文章第一次全面整理综括了西周金文兼语句的结构形式和语义类别,钩稽研索了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兼语句的主要特点和承继发展脉络。文章还对汉语兼语句的起源及其与使动范畴的发展顺序提出了一点新见解。
西周金文;兼语句;句型发展;使动范畴
西周金文作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出土材料,语料价值无可替代。西周金文兼语句的结构形式和语义类型是怎样的?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兼语句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又如何?兼语句与使动范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有待专门深入地探讨。
西周金文兼语句在管燮初、邓章应、张玉金①等人的论著中虽有论及,但都是举例性质的。可以说,对西周金文兼语句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尚是空白。考察西周金文兼语句,不仅有利于我们梳理上古早期汉语兼语句的发展脉络,而且对兼语句与使动范畴的发展顺序,对汉语史上一些重要句式,如使成式(动结式)②的起源研究也大有裨益。本文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与研究中心研制的《金文资料库》为依托,同时也考察了《金文资料库》后新发表的西周金文,对西周金文兼语语句进行了穷尽调查,统计出兼语句257例。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将西周金文兼语句分为四类语法结构形式和三类语义类型。
一、主要结构形式和特殊结构形式
西周金文兼语句的结构形式丰富而全面,不仅有齐全式、省略式、补充式,还有各种特殊形式,如兼语形式套接连动形式、兼语形式套接兼语形式等。
(一)主要结构形式
1.齐全式
兼语句的“齐全式”指的是“主语+兼语动词+兼语+第二动词”句式。兼语句中的兼语动词和第二动词一般不省略,这里的“齐全”主要指主语和兼语两个成分齐全。根据第二动词及物与否,又可以将齐全式分为第二动词带宾语的齐全式和第二动词不带宾语的齐全式。据统计,绝大多数兼语句为带宾语的齐全式,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带双宾语的齐全式。
a.第二动词带宾语的齐全式
这类兼语句中例句最多的是“乎(呼)”字兼语句,结构形式为:王乎(呼)某人+第二动词+某人,据笔者统计共有49例。如:
(1)王乎(呼)士曶召克。(克鐘,西晚,集成01.204)*铭文文字一般采用繁体,以下不再一一注 出。
其次是“令”字兼语句,有26例。“令”的施事一般都是大权在握者,其中施事为“王”的有14例。另有两例“令”的施事为“余”,均为指代,实则施事仍是“王”。此外,“令”的施事有“王姜”(1例)、“白(伯)龢父”(1例)、“弔(叔)氏”(1例)、“公”(2例)、“公鮘(姞)”(2例)、“厀”(1例)、“虢中(仲)”(1例)、“偨(遣)中(仲)”(1例)。如:
(2)隹(唯)王初伿于成周,王令盂寧佮(鄧)白(伯),鞲(賓)貝。(盂爵,西早,14.9104)
(3)王令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中甗,西早,集成03.0949)
在十几例第二动词带双宾语的兼语句中,最多的是“王+乎(呼)+兼语+第二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句式,其中第二动词一般是“易(赐)”或“册易(赐)”,表达“王乎(呼)某人易(赐)/册易(赐)某人某物”的语义,共12例。如:
(4)王乎(呼)宰利易(賜)師遽墌圭(珪)一、墍章(璋)椺(四)。(師遽方彝,西中,集成16.09897)。
主语前后还可以出现状语,如“昔乃且(祖)亦既令乃父死勓(司)傛人”中有三个状语:“昔”“亦”“既”。
b.第二动词不带宾语的齐全式
这类兼语句比较少,如:
(5)王使孟聯父蔑歷。(任鼎,西中[1])
(6)夨卑(俾)鲭(鮮)且撔旅斓(誓)。(散氏盤,西晚,集成16.10176)
2.省略式
兼语句的“省略式”指的是相较于齐全式的主语和兼语齐备,省略主语、省略兼语或者主语和兼语都省略的句子。其中省略主语的情况最多,“令”、“命”、“乎(呼)”、“卑(俾)”、“事(使)”字兼语句都有省略主语的情况。省略式中“卑(俾)”字兼语句出现省略的情况最多,在笔者统计的11例“卑(俾)”字兼语句中,主语和兼语齐全的仅有2例。其次是“事(使)”字兼语句。“省略式”举例如下:
(7)令乍(作)冊内史易(賜)免鹵百剒。(免盤,西中,集成16.10161)
(8)夥侕(則)卑(俾)我賞(償)馬,效[父]則卑(俾)復氒絲束。(曶鼎,西中,集成05.2838)按:“效[父]則卑(俾)復氒絲束”句承前省略兼语。
(9)隹(唯)白(伯)屖父乓(以)成傭(師)即東,命戍南尸(夷)。(競卣,西中,集成10.5425)按:“命戍南尸(夷)”句省略主语和兼语。
3.补充式
兼语句的“补充式”是指兼语句中第二动词后有补充说明时间、地点、对象等补语的句式。据笔者统计,这类兼语句共有13例,如:
(10)王令鱓(敔)追厩于上洛厪谷,至于伊班。(敔簋,西早,集成07.3827)
(11)王令東宮追乓(以)六傭(師)之年。(侮貯簋,西中,集成07.4047)
(12)余命女(汝)鯣(馭)追于摡。女(汝)乓(以)我車鱉(宕)伐匵(玁)敤(狁)于高陶。(不其簋,西晚,集成08.4328)
(二)特殊结构形式
西周金文兼语句的特殊结构主要有兼语结构套接连动结构和兼语结构套接兼语结构两种形式。其中套接连动结构的形式较为普遍,“令”字兼语句、“命”字兼语句、“乎(呼)”字兼语句、“事(使)”字兼语句都有兼语结构套用连动结构的形式,如:
(13)唯王令朙(明)公偨(遣)三族伐東或(國)。(明公簋,西早,集成07.4029)
(14)令女(汝)疋(胥)周師勓(司)剓(林),易(賜)女(汝)赤僡(雍)巿。(免簋,西中,集成08.4240)
(15)王乎(呼)譱(膳)大(夫)厇(馭)召大乓(以)氒友入攼。(大鼎,西中,集成05.2808)
(16)王命(令)同攱(左)右吳大父傴(司)昜(場)林吳(虞)牧。(同簋,西晚,集成07.4039)
兼语结构套接兼语结构的形式极少,仅见1例。
(17)王乎(呼)師敀(晨)召(詔)大師虘入門。(大師虘簋,西中,集成08.4251)。
二、兼语动词的语义范畴和兼语句的语义类型
西周金文兼语句的第二个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还可以是动词连动形式,比较灵活多变。但是兼语动词只能是一个及物动词,表达主语使兼语发出某种动作,兼语动词是兼语句成立的关键。殷墟甲骨文已存在大量兼语句,但语义类型单一,大多数学者如郭锡良、张玉金、陈练文、齐航福*郭锡良认为甲骨刻辞中兼语句只有使令类,第一个动词往往是使令动词“令”“呼”“使”,详见其《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载《古汉语研究》,1994年(增刊),第13-21页。张玉金也认为甲骨文中只有“使令”式兼语句,作其兼语动词的只有“呼”“令”“使”“曰”四个,前两个常用,后两个罕用。详见其《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语句》,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51-59页。陈练文认为在甲骨卜辞中,只有使令类动词“呼、令、使”可以出现在兼语动词的位置,其中“呼、令”经常出现,“使”出现的次数很少。详见其《殷墟甲骨卜辞句法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第78页。齐航福认为甲骨卜辞中兼语句有“呼”“令”“使”“速”四类。详见其《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社,2015年8月,第61-81页。等认为只有“使令”类兼语句,兼语动词有“使”“令”“呼”三个。西周时期,除了“使令”类兼语句外,还出现了“助引”类和“任命”类兼语句,语义类型更加丰富。
(一)“使令”类兼语句
“使令”类兼语句的兼语动词表命令、派遣等“致使”义,常为单音节动词,第二动词则有各种变化。为了说明上古早期“使令”类兼语句的发展脉络,我们将“使令”类兼语句细分为“令”字义兼语句和“使”字义兼语句。“令”字义兼语句的兼语动词除了表达“致使”义外,还表达较为强烈的“命令”义;“使”字义兼语句中的兼语动词表达一般、普遍的“致使”义。兼语动词的表义越单纯,其造句功能越强。“使”字义兼语句的出现是“使令”类兼语句内部的一次重要发展。
1.“令”字义兼语句
西周金文“令”字义兼语句的兼语动词主要有“令”“命”“乎(呼)”“召(诏)”4个。
a.“令”字兼语句
(18)今余隹(唯)令女(汝)死勓(司)傛宮傛人。(卯簋蓋,西中,集成08.4327)
b.“命”字兼语句
“命”由“令”加“口”分化而成。甲骨文兼语句用“令”不用“命”,西周金文“令”“命”均可构成兼语句。如:
(19)先王既命女(汝)劝傴(司)王宥(囿)。(諫簋,西晚,集成08.4237)
c.“乎(呼)”字兼语句
约70例,主语无一例外均是“王”,少数情况省略主语,根据上下文可判断省略的主语也应是“王”。如:
(20)王乎(呼)史鹚冊易(賜)劲(裼)劳虢儬攸勒。(剞盨,西中,集成09.4462)
d.“召(詔)”字兼语句
见1例。
(21)王乎(呼)師敀(晨)召(詔)大師虘入門。(大師虘簋,西中,集成08.4251)
2.“使”字义兼语句
“使”字义兼语动词有“卑(俾)”“史(使)/事(使)”“妥(绥)”“鱎(薄)”“遣”5个。
a.“卑(俾)”字兼语句
(22)夨卑(俾)鲭(鮮)且撔旅斓(誓)。(散氏盤,西晚,集成16.10176)
b.“史(使)/事(使)”字兼语句
兼语动词 “事、史、使”三字不分,表示使令,由其构成的兼语句简称“使”字兼语句,约22例。如:
(23)隹(唯)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弔(叔)氏事(使)妿(布)安偞白(伯)。(公貿鼎,西中,集成05.2719)
c.“妥(綏)”字兼语句
绥,使。见1例。
(24)休同公克成妥(綏)吾考乓(以)于僃僃受令。(沈子它簋蓋,西早,集成08.4330)
d.“鱎(薄)”字兼语句
见1例。王若曰:“師唃,卍!淮尸(夷)囓(舊)我卄畮臣,今敢鱎(薄)氒眾(衆)叚。”(師唃簋,西晚,集成08.4313)“鱎,借为薄。《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师薄于险。’杜预《注》:‘薄,迫也。’……叚,假借为睱。”[2]
e.“遣”字兼语句
见1例。
(25)弗克伐噩(鄂),倃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厮)馭鰃(二百)徒千。(禹鼎,西晚,集成05.2833)
(二)“助佑”类兼语句
“助佑”类兼语句是指兼语动词具有引导、辅助促成之义的句子。西周金文的“助佑”类兼语动词有“右(佑)”一个。“右”,佑,辅助、帮助的意思。“一般册命金文,在记述王各于大室,即位之后,便记受命者由傧者陪伴于其右,然后导引入门,行至受命地点,即太室之前,在中廷面北而立”[3],有27例。如:“右鞮(走)馬休入門”、“右(佑)乍(作)冊吳入門”、“右朢入門”、“右唃入門”等。
(三)“任命”类兼语句
“任命”类兼语句有些学者又称为“封职任免”类兼语句,兼语动词多表示封爵、授职、任免、降职等含义,第二动词大都是动词“为”“作”。如:
(26)王曰:“勭,令女(汝)乍(作)勓(司)土(徒),官勓(司)耤田。”(勭簋,西晚,集成08.4255)
三、先秦汉语兼语句的演进和发展问题
先秦汉语兼语句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勾勒先秦三个时期汉语兼语句的大致样貌,进而总结各个时期汉语兼语句的主要特点和承继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兼语句的起源问题,以及研究汉语兼语句的历史发展都大有帮助。
(一)殷商甲骨文兼语句的语法结构趋于成熟,但语义类型较为单一。
近年来,随着殷墟卜辞句法研究的不断推进,对甲骨文兼语句的探讨越来越系统和深入。已有研究表明,甲骨文兼语句已经大量使用。陈练文统计出《甲骨文合集》中兼语句有184例[4];齐航福通过统计庞大的甲骨文语料,得出兼语句2358例[5]。从句型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兼语句句型已经渐趋成熟。不但具备兼语句的齐全式、省略式和补语式,更有较为复杂的结构类型,兼语结构套接连动结构和兼语结构套接兼语结构都已出现。如:
(27)癸卯卜贞:呼弘往于隹比乘。(合集667正)
但是从语义类型看,殷商甲骨文兼语句的语义类型较为单一。郭锡良[6]、张玉金[7]等都认为:殷商甲骨文只有“使令”类一种,一致认可的兼语动词只有“呼”“令”和“使”三个。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殷商甲骨文的“使令”类兼语句内部语义小类也很单一,几乎全是“令”字义兼语句。“使”字义兼语句还处于萌芽阶段,兼语动词只有“使”一个。从用例比例看,《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统计出“呼”字兼语句1438例,“令”字兼语句912例,而“使”字兼语句仅有6例。“使”字兼语句占比仅为0.25%,“令”字义兼语句占比为99.75%。
(二)与殷商甲骨文“使令”类兼语句比较,西周金文“使”字义兼语句获得发展。
从殷商到西周,“使令”类兼语句自身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令”字义兼语句看,西周金文几乎完全继承了甲骨卜辞的“令”字义兼语句类型。甲骨文表达“令”字义的兼语动词有“乎(呼)”“令”两个,西周金文中有“乎(呼)”“令”“命”“召(诏)”四个。其中“命”由“令”分化而来;“召(诏)”与“乎(呼)”义近。
根据我们的统计,西周金文“令”字义兼语句占比为84.7%,在甲骨文中这个比例是99.75%。“令”字义兼语句使用下降,“使”字义兼语句却获得了较大发展,表现为用例更多,使用的兼语动词更丰富。西周金文中“使”字义兼语句占比上升到15.3%,兼语动词比甲骨文中多了“卑(俾)”“妥(绥)”“遣”“鱎(薄)”四个。“卑(俾)”“妥(绥)”“遣”均有“使”义,“鱎(薄)”训为“迫”,也主要表达“致使”义范畴。
(三)结合传世文献可知,西周汉语兼语句语义类型有了较大发展。
研究西周汉语语法所使用的语料有两个类别:一是传世文献,二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有《周易》《诗经》(部分)、《尚书》、《逸周书》。通过与西周金文相比,我们发现西周传世文献兼语句语义类型多出了“劝诫”类、“命名称谓”类和“有无”类。“《尚书》中‘迪’ ‘助’‘辅’‘供’等动词具有‘引导’义和‘辅助促成’义,构成‘助引’义兼语句。”[8]综合西周金文和同时期传世文献可知,西周汉语兼语句的语义类型已达六种,即“使令”类、“助引”类、“命名”类、“任命”类、“劝诫”类、“有无”类。当然,不同类型的兼语句使用频次有高低之别,其中“使令”类兼语句出现频次最高,是兼语句的主要类型。
(四)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兼语句语义类型持续丰富。
近年来,涉及或专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兼语句的研究者比较多,尤其是一批研究生对春秋战国文献有专门的研究。主要有管燮初、刘鑫鑫、谢俊涛、林琳、梁春妮、田飞、王玉兔、李红等。*管燮初统计《左传》有兼语855个,用作兼语的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主谓结构和者字结构。详见其《左传句法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刘鑫鑫:《上古汉语中的兼语句》,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老子》中“谓语由兼语短语充当的,凡3见。”详见谢俊峰:《<老子>句型研究》,2009年5月,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林琳:《上古使令类兼语动词的演进和发展》,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梁春妮:《春秋战国铭文句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8-92页。田飞:《包山楚简语法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第38-40页。统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兼语句23句,分“使令义”“助引义”“任命义”“命名义”“有无义”“使动义”“褒贬义”7种语义类型。详见王玉兔:《<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句法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第56-66页。李红:《<战国纵横家书>兼语式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总结出古汉语兼语句语义类型有9种,分别为“使令”“封职任免”“劝诫”“褒贬评论”“命名称谓”“有无”“以……为” “特殊兼语”“复杂兼语式”[9]。从该书各类兼语句所引例句看,除“封职任免”类兼语句没有引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料外,其他8种类型的兼语句都引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料。不过虽然“封职任免”类兼语句该书未有引用,但这类兼语句在春秋战国语料中是一定存在的。也就是说,汉语兼语句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备了古汉语时期的全部语义类型。也看得出,在这一时期,汉语兼语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四、兼语句起源及其与使动范畴发展顺序问题
关于汉语兼语句的起源,语法学界曾进行过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兼语句来源于使动范畴。“汉语使动用法先于使令兼语句”,发展顺序为“使动范畴(有形态变化)→使动用法(形态消失) →使令兼语式、使成式”。[10]那么,汉语兼语句是起源于汉语的使动范畴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
早在殷墟甲骨文中,使动式和使令类兼语句就都已经存在了。甲骨文中的使令类兼语句数量众多,上文已有分析。“甲骨文中的使动关系和传世典籍所见到的使动关系一样,主要表现在自动词上。此外还表现在活用为动词的个别形容词上。”主要有自动词“来”“归”“败”“先”和形容词“宁”“堇”6个。[11]如:
(29)贞,师般其来人。…… (合集1036)
(30)戊寅卜,丁归在师人。(合集21661)
(31)丙子卜,父乙异惟败王。(合集2274)
(32)翌日辛,王其田,马其先,……不雨。(京津4471)
(33)戊申卜,宁雨。(合集33137)
西周金文使动式有了进一步发展。“殷商时期的使动式还很少见,其动词限于不及物动词(包括形容词)”。到西周时期,“使动式进一步丰富。及物动词、数词、方位词等都可以有使动用法。”[12]如:
(34)邁(萬)年俗(裕)玆百生(姓)。(一式簋[13])
(35)僗(茲)僾(簋)卨(猒)皀,亦兤(壽)人,子孫其永寶用。(伉叔簋)
卨(猒)皀,本义是饱足,这里是使动用法,为“使我们饱足”的意思。
使动用法的表层组配是动宾,其深层语义是表达“致使”义,和“使令”类兼语句的功能异曲同工。从已有研究看,甲骨文兼语句句式相当成熟,而且用例相当多。而使动用法殷商时期却“很少见”,到西周时期,才“进一步丰富”。所以,认为汉语兼语句来源于使动用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从兼语句的出现和发展方面看,“令”字义兼语句中的兼语动词,如“令”“乎(呼)”“命”等,具有非常强烈的产生“令某人做某事”这一句式的倾向,“某人”即兼语,“做”是第二动词,“某事”是第二动词的宾语。也就是说,“令”“呼”这样的动词具有强烈的产生兼语句式的倾向。我们认为,人类要表达“致使”义这类概念范畴,“令”“呼”这些动词能够承担部分功能,自觉构建兼语句式。这类兼语句应该具有“原创性”,而非从使动范畴发展而来。
实际上,持有汉语兼语句式来源于使动范畴的观点,主要是受到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影响。汉语与藏缅语存在亲缘关系,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表达有粘着式、屈折式、分析式等形式。孙宏开从语言发生学角度构拟藏缅语使动范畴表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粘着式”;第二阶段是“屈折式”;第三阶段是“分析式”[14]。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潘悟云[15]、梅祖麟[16]、洪波[17]等。“分析式”表达主要是在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加虚化动词或助词。如哈尼语在动词前加bi33-表示使动范畴,动词dza31的意思是“吃”,在其前加bi33,变成bi33dza31,就成了使动用法,表示“使吃”的意思。贵琼语在动词后面加-ku33表示使动范畴,动词si55意思是“衣服破”,si55ku33就是使动用法,表示“使破”的意思。*例子引自孙宏开:《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第6-7页。
表达使动范畴的“分析式”类似于兼语句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形式相似,就认为汉语中的兼语句式是为了表达使动范畴而产生的。藏缅语族中存在用分析式表达使动范畴的语言,不等于说汉语就是这样的语言。“致使”关系是人们对事物间因果关系有所认识后的语言表征,是人类语言一个基本的而且普遍的句法语义范畴。长久以来对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等上古早期兼语句的研究不足,加之对传世典籍使动词的训诂一般要用一个动结式或者使令类兼语句表达,造成人们误认为汉语兼语句是为表达汉语使动范畴而产生的一种句式。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早在殷商西周时期兼语句就大量使用,并有其自身内部演化的机制和发展脉络,认为汉语兼语句起源于使动范畴是站不住脚的。
[1]王冠英.任鼎铭文考释[J].中国历史文物,2004,(2):20-26.
[2]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07.
[3]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13.
[4]陈练文.殷墟甲骨卜辞句法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8.
[5]齐航福.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社,2015:81.
[6]郭锡良.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J].古汉语研究,1994(增刊):14.
[7]张玉金.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语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1):51.
[8]周正颖,邱月.今文《尚书》兼语句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5,(1):41-48.
[9]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88-615.
[10]冯英.试论先秦汉语使动用法和使令兼语式的发展顺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69-74.
[11]董莲池,高云海.甲骨文使动、为动用法举例[J].古汉语研究,1991,(3):95-97.
[12]姚振武.汉语语法从殷商到西周的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69-84.
[13]吴振锋. 器铭文考释[J].考古与文物,2006,(6):58.
[14]孙宏开.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J].民族语文,1998,(6):1-11.
[15]潘悟云.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J].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48-57.
[16]梅祖麟.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能[J].民族语文,2008,(3):3-20.
[17]洪波.汉语历史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8-378.
H146
A
1001-0238(2017)04-0096-06
[责任编辑:邦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