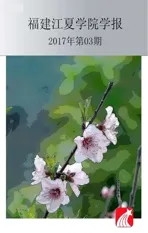清代徽州宗族救助形态
2017-04-15曹化芝
曹化芝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2.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淮北,235000)
社会·文化
清代徽州宗族救助形态
曹化芝1,2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2.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淮北,235000)
为了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保障宗族的可持续发展,清代徽州宗族积极担当赈恤贫穷的责任。宗族救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富裕族人散财施物;二是购置族产,建立制度化的赡助机制。徽州宗族救助的常态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穷族人的生活压力,既培育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同时也维系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清代徽州;宗族救助;基层社会
清代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制度严密,宗法观念浓厚。为了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保障宗族的可持续发展,徽州宗族积极担当赈恤贫穷的责任,“敬宗收族睦姻任恤之行,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穆然成风(卷9《人物志·义行》)”。[1]1在族人的生活中,一旦遇有天灾人祸,生计难以维系时,宗族便承担起救助的职责。可以说,徽州“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是以民间的宗族保障为主的”。[2]徽州宗族救助的主体是富裕族人,或官宦,或素封,或力田殷实者;救助对象多是鳏寡孤独废疾等贫弱族人。救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富裕族人散财施物;二是购置族产,建立制度化的赡助机制。徽州宗族救助的常态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穷族人的生活压力,既培育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同时也维系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传统的散财施物救助
散财施物是传统社会宗族互助的一种方式。这种救助方式的救助力度和范围因施济者经济能力不同而不等。同时,施济者关注点不一样,使得赡济对象也各异。潘光旦先生曾做过相关统计,自汉到宋大约有55件这种典型案例。[3]在清代徽州地区,这种社会救助现象十分常见。每遇灾歉,宗族中总有嗷嗷待哺之人。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则是富裕族人的责任所在。如歙县瞻淇人汪燧,中年贾于浙。康熙六十一年岁饥,散积谷五百石,以赈族人。歙县水竹坑人柯永芳,义笃宗族,岁歉即发粟平粜,以济贫乏。[1]37,51在宗族人群中,鳏寡孤独者悲情最甚,堪为可怜,成为救助的主要对象。婺源监生江廷球,族人孤贫月给钱米。[4]20歙县槐塘人唐维仁,族之幼孤者恤之,孀居者周之。歙县后坞人张明侗,族中孀妇及穷无告者计月授粮,幼孤者抚育之,俾其成立。路口人徐瑞玉周恤族之孤寡,章程条理比之范氏义庄。[1]27,51,25婚嫁丧葬是宗族生活中的重要事项,穷苦族人难以应对。就宗族发展来说,助婚实系宗族人口繁衍大计,赙丧乃宗法文化应有之意。对族中贫苦者,徽州宗族念一本之情,量行周恤之义,使婚姻有赖,死丧有资。黟县监生汤永懿,资助族人嫁娶,乐此不疲。[5]28歙县江嗣仑,凡族人婚嫁丧葬,岁多佽助。[1]35休宁黄鸿友,少随父徙江浦贸易,晚居故里,戚族中贫无丧葬婚嫁资者,辄输助而完成之。[6]83,84际村人戴吉先,捐职州同,宗族亲旧之贫者,“为营婚嫁埋葬(卷7《人物·尚义》)”。[7]5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文风兴盛,资助贫寒子弟学业则是族绅们施济的又一目标。对无力读书子弟,宗族或助束修之资,或对科举有成者施以奖励。如绩溪盘川王氏宗祠原例子弟乡试给盘费二两,会试给盘费四两。科举废除后,将两试川资移作学堂津贴,其中留学省垣高等学校或与高等学校同等之学校,每年给津贴钱二两;留学京师大学堂及与大学同等之学校,每年给津贴钱四两。[8]
一般而言,散财施物救助形式难以长期存续,施济范围有限。当然,也有少数实力雄厚的散财施物资助者,赡助范围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如滁村人汪朝烘,族姻之贫困者月有给,业儒者助以膏火,经商者贷以资,务俾各得其所。[9]12新馆贡生鲍立然,置祠田,设义塾,资婚嫁,助葬埋,给棺施药,惠及于族里者不可胜纪。大阜人潘景文,岁贡生,邻里乡党多所周恤,于族人尤笃,冬予被,夏予帐,生予钱谷,死予棺衾,凡有缓急,无不取给。西溪人汪景晃,业贾三十年,年五十以生产付子孙,专务利济。族之茕苦者,计月给粟,岁费钱百五六十千;设茶汤以待行旅,岁费钱六七十千;冬寒无衣者给之衣,岁费钱约五十千;疾病无医药者给以药,贫不能亲师者设义馆,岁费钱约二十千;死而无棺者给之棺,岁岁行之,至年九十时,所费以万余计,给三千余棺。[1]46,36,26
总之,散财施物救助方式具有较为灵活的特点,救助者熟悉施济对象的情况,接济及时,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和程序。然而,但这种救助方式随意性强,往往因缺乏制度性和连续性,人亡事息,难垂久远。
二、宗族救助的制度化
北宋仁宗皇祐元年,范仲淹在其家乡苏州建义庄,兴义学,设义宅,救恤族人,开义庄之滥觞。范氏义庄恤鳏寡孤贫,济婚丧,助学业,祀先人,集敬宗、收族、保族于一身,教养相济,制度井然。它的出现既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宗族救助走向制度化的标志。自南宋起,徽州宗族代有仿行之者。如休宁东阁人许文蔚,幼贫苦学,绍熙庚戌以上舍擢第,教授通州。出平生笔耕所储,倒槖买田百亩为义庄,以赡宗族,申省立约,为悠久计。[10]57休宁下东人金文刚,金安节之孙,用遗恩补将士郎,慕范文正公故事,置祭田,立义庄,画为定式,俾世守焉。[9]17元至正十一年,黟县黄友仁蠲租六百三十余亩,起创义庄,名曰“厚本”,于庄内立义学,延师教养子孙,割田之入赡师弟子,并周给宗族之贫乏者。[11]39
相较前代,清代徽州宗族捐设义庄之风更甚。婺源翀麓齐氏称:“近世士大夫家多仿范氏置庄赡族,于是祀田之外又有义田,夫富民为国之元气,义田为乡之元气。(卷3《祠堂·祀田》)”[12]如徽州人谢龄光捐置义庄田地三百六十亩,以赡其族。[4]19婺源贡生程思楢,族置义庄,输三千金。[13]46绩溪人曹乐捐田百余亩,置屋数十楹为义庄,约费万金。[4]18婺源城人胡瑛,好读《义田记》,手置义庄赡族。[13]21怀宁人太学生郝邦晟,少读书屡踬场屋,遂弃儒就贾,购义庄赡族。[6]86休宁人胡绍彭,因家中落,投笔经商,始饶裕,即购田百顷,立义庄,义学,名曰“师范庄”。[4]20歙县桂林人洪陶士,咸丰间岁饥,置义田,设庄赡族,名曰“桂荫义庄”。[1]89
不过,义庄田亩少则几十亩,多则数百亩,甚或数千亩,加上庄房,义塾开支及祭祀器具等费用,需费甚巨,不是一般家族所能担负。因此,更多的徽州宗族则以祠堂为依托,或置义田,或以祭田租余赡族。
祠堂是宗族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是救助贫弱族人的主要机构,“公堂丰足,合族受惠(卷8《家政》)”。[14]徽州是朱子故里,族必有祠,祠必有产。在族规中,开展宗族救助是其重要内容。绩溪耿氏《祠规》就如何抚恤族人专辟一章,内容包括:“苦情之扶助”,“废疾之扶助”,“遇难之扶助”,“成美之扶助”,[15]涉及救助范围及具体实施办法。
在诸种族产中,最为重要者莫过于祭田和义田。祭田是宗族为祭祀祖先而设,包括墓田和祠田等。祭产丰厚的宗族在祭祀开销之余,剩余部分则用来赡族。如婺源诸生叶炜,独捐千余金修祖庙,复置祭田,岁款倾廪以济族人。[4]19江村人江承炳捐金助建宗祠,置田为族党祭祀凶荒之备。[1]46绩溪许氏祀产丰厚,规定了救助细则:一是族中“年老又遭患难无子侄服亲,无田产者,于祠祀产拨租以养之”;二是“凡家贫,孤儿,寡妇与疲癃残疾,及年壮遇灾遇病,素行归真,衣食无赖而无服亲者,祠董拨祀租以赈之”;三是“族中子弟读书三五年,如果天资高妙与天资平等而志大心专者,其家贫无力,则祠董于祀租每年拨助学资”。[14]
义田是富裕族人捐设的族产,租息专门用来救助贫弱。其与义庄的不同之处在于,义庄既包括义田,还包括庄房、书田、义塾等族产,同时其本身还是一种专门的赡族组织,订有专门的庄规,涉及经营管理,贫弱救助以及家族教育等事宜。不设庄的义田规模一般较义庄田为少,由于没有建立专门的经营管理机构,多由祠堂管理。不过,相较散财施物,义田赡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设置义田往往是较为富裕宗族的建设目标之一。有清一代,徽州宗族设置义田较为普遍,少则几十亩,多则几百亩,为贫弱族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如石坑人张为镇输义田数十亩,以恤族之孤寡。[16]9江村人江裕璸,务农力田,置义田百亩,以给族之苦节者。伏塘坑人方德龙,置义田一百零九亩,以赡宗族,施药饵,推衣食,远近称善。江村人江承珍置义田百二十亩,以给族之贫乏。棠樾人鲍启运,敦本尚义,族党中孤寒无依者置义田数百亩以恤之。松明山人汪人御,尝置义田五百亩,周恤宗族。歙县鲍玉堂置田五百亩,以岁入赡族,捐义塚,施棺衾,修祠宇,行之不倦。雄村人曹景宸,置义田五百余亩于休宁,以给族之寡妇,并助族中乡会试考费。江村人江振鸿,敦本睦族,尝捐田千数百亩,立追远,周急二户,为阖族蒸尝及周恤贫乏之费。丰南吴邦伟与其兄邦佩慕范文正义田法,与叔祖,禧祖,之駦,之骏共出资万数金,于宣城湾沚置田千余亩,岁收其利,每年于季春孟冬之月给其族之颠连无告者,助丧助葬。[1]56,44,31,68,64,84,40,56,31限于个人力量不济,也有族人合捐义田的事例。如檡墅人洪世迎与族中声业兄弟二人输租百余亩,创置义田,以助祭祀,以恤孤寡。[16]8唐模人许以景偕兄弟置义田数顷,以济族之鳏寡。唐模人许以晟偕同堂诸昆季置义田百余亩,以赡族之无告者。[1]33,44
三、宗族救助的其他方式
除义庄、祭田及祠堂义田等宗族制度化救助方略外,置义仓、办义塾、设族会、建义居也是徽州宗族扶助贫弱的重要方法。
徽州族绅仿照朱子社仓之法,捐设宗族义仓,丰年积储,饥岁平粜,赈恤族人。如黟县附贡李长蓁出金三百,倡建家祠义仓。[4]23黟县吴永洋筹办至德社仓,以济族之贫乏者。[7]14歙县严溪庠生项景立敦本仓于族,以赡无告,平粜凡五六举,并续远族。[1]80祁门仙源例贡生许炳南,平生医药济人。其族向有义仓,以备岁饥,同治癸亥毁于贼掳,炳南独捐谷一千秤,以复兴之。[6]14歙县项士溥,乐善好施,奉父遗命买田,置庄于余岸,又立义仓于里中,以岁入租养赡族中四穷。[1]82祁门桃源洪氏阖族上下九百余口,贫富不一,一遇荒歉,穷者无以接济。全族于祠堂集议,决定建立义仓,共输银二千两,建仓购谷积贮,以备歉岁。[17]黟县韩村韩氏祠仓,赒贫乏,助婚娶。[7]20乾隆十六年岁饥,石壁下人方西畴出千金助建惠济仓,亲族之不能婚娶者佽之。[1]41
为了使义仓可持续发展,多数宗族以增置田亩的方法保证义仓有充足的谷物可供平粜。然而,这往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若租谷随收随粜,将糶谷之银买田未尝不善,设遇荒年,仓无谷糶,贫乏不能沾惠,义仓虽有如无”;二是“若贵价买谷平粜,所损益多,不数年而义仓废矣”。基于综合考虑,婺源齐氏制定了“长久之策”:义仓“蓄三年之谷,岁丰粜一留二,岁荒尽数平粜。平粜之法,贫户计口均分,鳏寡孤独多让二文,侭仓所储,谷尽而止。”齐氏以为,“荒年买田,其价必贱,以田价之盈补谷价之虚,无饥而贫者,大受饶益( 卷2《祠堂·祠规》)”。[12]
宗族将兴旺发达的希望寄寓在俊秀子弟身上,因此,助学兴教是徽州宗族的大事,有条件的宗族纷纷设立义塾,为贫寒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如茗洲吴氏所云:“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非小。(卷1《家规》》)”[18]黟县监生汤永懿造松山书屋,为族人肄业所。[5]28严镇人洪桂根尝设义塾训子弟读书。歙县呈狮人范信经商有成,建义学,族中子弟俊秀者尤加意培植,俾读书成立。昌溪沧山人吴景松以茶业起家,晚年归里,创崇文义塾,斥万金购市屋七所,收其租息,以资族中子弟读书。[1]72,68,86议叙盐运司知事黟县李彬彦,奖励人才,设义塾多所,课族党孤寒子弟。黟县南屏人叶寿萱,邑庠生,热心教育,恢复族中私立南阳初等小学,岁费独力支持,族中子弟及邻村之就学者达二百余人。[7]19,25
清代徽州地区设立文会或其他形式的族会活动也很兴盛。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宗族置有会田;二是族中官僚或富商捐输。族会的管理人一般由“斯文”充当,并订有专门的“会例”制度。就设立文会而言,宗族的意旨很明确,就是培养宗族科举人才,提升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如率口人程子谦捐赀置文萃会,以给族之应举者。[9]8歙县后塢人张明侗立飞霞文会,延师以教里中子弟。[1]51清代徽州地区由宗族创办的著名文会有:萃升文会,阜山文会,云谷文会,檀干园,南溪别墅,兴贤会馆,川上草堂,双溪书屋和云门书屋等。[19]79而宗族创建敦族会之类,则意在救恤贫乏。如率口人程子谦置敦本会以赈族之贫困。古林人黄焉学服贾江汉,久乃稍裕,效仿范文正遗意,倡立培元会,以恤四穷。率口人庠生程佑捐鉅项,置产生息,立培元会,以济族邻。[9]8,17,14
为贫无所居的族人提供栖身之所,亦是一些富裕族人极力而为的善举。郡城人胡璋,康熙甲辰武进士,尝以独力创宗祠,构楼屋数十楹,使近族得所居止。[1]23黟县四都西安人鲍颐,附贡生,道光中祖祠圮,独资移建,造余屋为聚族居计。[5]31婺源人俞德祖,贸易阜邑,居家输田数十亩,分给族中贫老,置两大厦,一居族无依男,一居族无依妇。[4]20歙县贡生鲍立然,弱冠失怙,弃举子业,与兄业鹾于杭,于里中营广厦数处,任族人居之,不取其值。[20]
四、结语
清代徽州地区完善的宗族救助形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新安理学、徽商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汉末以降,中原地区战乱不已,为群山封锁与外界阻隔的徽州成为避乱的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的中原士族迁居于此。他们历经世代繁衍,逐渐形成了“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的徽州式宗族聚落形态。自古以来,宗族就有守望相助的传统,而徽州宗族的聚落形态又强化了这种族人间互帮互助的救助风尚。同时,移植过来的中原士族文化与程朱理学融合酿造,培育出独特的宗族文化——新安理学。其既强调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又鼓吹建祠堂、明世系、墓祭始祖以及置祭田、义田等宗族建设方案,以此强化宗族的凝聚力。此外,徽州山多地少,为谋生计,很多徽人走上了外出经商之路。由于徽人在业贾过程中往往得到宗族的支持,一旦经商有成,多数族商会将部分商业利润输回故里,通过建祠堂、置族田义庄、办族学等方式回馈宗族。
总之,一村一族的聚落形态,程朱理学的熏染,一以贯之的谱牒系统,完善的祠堂组织,使得清代徽州人几无例外地生活在宗族网络里。相较单纯血缘文化的内在联结,徽州宗族丰厚的族产和完善的宗族救助体制就像一根无形的红线牢牢地将族人维系在一起。在遵循国家法律的基本前提下,清代徽州宗族将生活救助和儒家伦理相结合,寓劝惩于赈恤之中,既护佑着族人在传统的宗法状态中繁衍生息,又维持着基层社会的差序格局。
[1] 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尧纂.歙县志[O].民国26年铅印本.
[2]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248.
[3] 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M].北京:三联书店,1952:48.
[4] 吴坤修等修,冯焯续纂.重修安徽通志[O].清光绪七年刻本.
[5] 谢永泰修,程鸿诏等纂.同治黟县三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 朱之英等修,舒景蘅纂.怀宁县志[O].民国7年铅印本.
[7] 吴克俊,许復修,程寿保,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四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 王德藩纂修.绩溪盘川王氏宗谱[O].民国10年排印本.
[9] 何应松修,方崇鼎纂.道光休宁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 彭泽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O].明弘治刻本.
[11] 丁廷楗,卢询修,赵吉士等纂.康熙徽州府志[O].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12] 齐之傒纂修.翀麓齐氏族谱[O].清光绪十二年木活字本.
[13] 葛韵芬等修纂.婺源县志[O].民国14年刻本.
[14] 许文源等纂修.绩溪县南关惇叙堂宗谱[O].清光绪十五年活字本.
[15] 耿全等纂修.鱼川耿氏宗谱[O].民国8年木活字本.
[16] 周溶修,汪韵珊纂.同治祁门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7] 吴翟等纂修.茗洲吴氏家典[O].清雍正十一年木活字本.
[18] 洪钊修.祁门桃源洪氏宗谱[O].清光绪二十六年木活字本.
[19] 葛庆华.徽州文会初探[J].江淮论坛,1997,(4).
[20] 鲍存良等纂修.歙新馆鲍氏着存堂宗谱[O].清光绪元年活字本.
(责任编辑 王 珑)
The Salvation Form of Huizhou Clans in Qing Dynasty
CAO Hua-zhi1,2
(1.School of Literatur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2.Library,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China)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lan cohesion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an,the Huizhou clans in the Qing Dynasty activel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verty relief.There were mainly two ways of Clan salvation.One was that wealthy clansman gave the poor money and
property,the other they purchased Clan property and established of Institutionalized Assistance mechanism.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clan salvation in Huizhou alleviated the living pressure of the poor people to a certain extent.That not only fostered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clansmen about the clan,but also maintaine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Huizhou in Qing Dynasty;clan salvation;grass-roots society
D675.4
A
2095-2082(2017)03-0065-06
2017-01-04
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SK2015A096)
曹化芝(1974—),女,安徽寿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