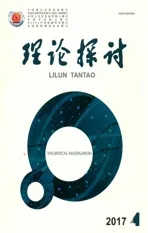“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2017-03-10范春燕
范 春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范 春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巴迪欧作为当代独树一帜的左翼哲学家,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在后现代氛围下重新召唤出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而不诉诸各种本质主义的幽灵。为此,他提出“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的概念,试图在反对作为“大写的一”的真理观的同时,重新举起普遍真理的大旗,并在反思20世纪革命政治的基础上重启共产主义观念的“第三个世纪”。
巴迪欧;激进哲学;激进政治;真理程序;减法政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转向晚期资本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受挫,在后现代和后革命的双重氛围下,西方的左翼激进主义也开始为各种“后”学所塑形。从哲学领域来看,主要表现在对普遍真理和共产主义观念的贬斥上。这对于一直坚持“激进哲学”*激进哲学,按照赫勒的定义,指的就是:“冒险把某种给定的价值提升到价值理念的地位”,然后根据这些价值理念对现存社会和主流规范进行总体性批判,以寻求和左翼激进主义行动的结合并促成对社会的激进变革。激进哲学只能是左翼激进哲学。因为在赫勒看来,尽管历史上的激进主义有两种形式——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但由于右翼激进主义既不接受哲学关于价值理念的讨论,也不在某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展开其激进行动,因此,“只有左翼激进主义才能拥有哲学,而右翼激进主义则没有”。参见:阿格妮丝·赫勒著《激进哲学》,赵司空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第130-131页。立场的阿兰·巴迪欧而言,时代赋予哲学的要务也就成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唤回“真理”和“观念”——不是通过诉诸过去的各种本质主义幽灵,而是立足“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面向未来进行“纯新”的创造。他的思考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如何在反对“大写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观的同时,提出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新认识;二是如何在批判20世纪“由大写的‘一’的欲望激发出的‘二’的对抗性法则”[1]68的同时,开启共产主义观念的新实践。这两方面的思考也集中体现在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上。
一、真理程序:关于真理、事件和主体的三位一体
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新举起了普遍真理的大旗*彼得·霍尔沃德曾这样评论道:“巴迪欧哲学中最首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肯定真理之严格的、确定的普遍性,并将这种真理从判断或阐释的合法性中抽离出来,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学者相区分。”参见: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p.xxii.。巴迪欧认为,后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谱系,在反对本质主义、与各种“大写的一”(UN)做斗争的同时,也“以多之潜能的名义对真理进行了审判”[2]77。而真理被审判的结果,一方面是左翼激进主义为各种后现代主义所感染而趋于碎片化和无力化;另一方面,是右翼激进主义趁虚而入、以某个具有实体性的“大写的一”填充真理废黜后的空位,并自诩为“资本主义现成政体的秉持正义的批判者”,从而“窃取了曾经属于左派的神圣位置”[3]。因此,对巴迪欧而言,当代激进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重新赋值于真理以消除后现代哲学的各种“副作用”的同时,坚持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当然不是再回到作为“大写的一”的真理,而是要提出一种真理范畴,使之与“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相适合,同时也能满足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设定。
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诉求出发,巴迪欧通过数学本体论、事件哲学以及主体哲学的建构提出一种“真理程序”(truth procedure)的概念,这一概念使得巴迪欧在和各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坚持了真理的普遍性原则。因为首先,真理作为“类性多元程序”,体现的是一种作为指类操作结果的普遍性,而不是作为既与性前提的超验性;其次,真理作为事件性的“纯新”生产,体现的是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而不是需要借助各种“上帝”帮助才能达成的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真理程序的展开体现的是以观念为中介的主体化过程,真理的主体也就是真理的身体,真理程序不是任何纯粹的“客观”真理。
1.数学本体论和真理的类性多元程序
巴迪欧首先确立了数学的本体论意义。在他看来,后现代哲学对真理范畴的消解和对数学的贬斥是同步发生的,数学被当作“一个没有对象的游戏”或是“符号的纯粹演算法则”和存在本身相隔离。比如,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数学只是一种逻辑的变体,在他看来,尽管数学提出一些真的和必然的命题,但却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或者说,数学仅仅表明了实存具有可以思考的法则,但这些法则和不可思考的存在(本体)之间却没有必然联系。而巴迪欧对此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数学讲述的正是“作为‘是’的是”[4],数学绝不仅仅是计算和等式,还包括许多完全不同于逻辑还原论的实存定理、基数定理、分解定理和代表定理等,而这些才是数学的本质和精髓所在:它体现了数学的深刻性和思想性,它提出的无限性问题、复杂性问题、类型化问题等,都体现着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性追问。换言之,数学并不代表某种空洞的普遍性,而是能够触及作为实存之基础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法则和本体论话语,只有借助于这些法则,哲学才能在实存和存在之间建立某种关联。
在此基础上,巴迪欧提出,要使普遍真理和“存在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相兼容,关键就是要重新理解“一”和“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只有借助于数学集合论的“类性多元”概念才能完成。所谓“类性多元”(generic multiple),其含义就是: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因其独特性(singularity)不能被缩减或化约为“大写的一”,而是指向了存在的“纯多”(pure multiples);另一方面,集合通过指类命名产生了“一”个集合,这个“指类”并不来自某个神秘的本源,而仅仅是作为命名操作的结果——通过这个操作,作为“纯多”的实体才能被加以思考,而不至陷入转瞬即逝的多样性的混沌之中。由于这一“指类”对集合内部的所有元素而言都是有效的,因此,这一“指类”对集合而言就是真理。可见,在“类性多元”概念中,“一”的操作所产生的类的普遍性并不消解存在的“多”,它仅仅作为一种操作性结果而不是既与性前提和存在的“多”相呼应。
正像集合是对“多”个元素进行操作,从中找到某种规则将其建构为“一”个集合,真理也是对存在的多的某种独特性生产——这种生产既不指向某个具有超越性的“大写的一”,也不是一个“‘已经’给定的或已经出现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程序的多之后果”[2]78,从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把真理界定为“真理程序”(truth procedure)。巴迪欧指出,真理程序主要包括四大类:科学真理程序、艺术真理程序、政治真理程序和爱的真理程序。真理的这四个类性程序之间既不能通约,也不能归为一个大写的真理。
2.“事件—真理”和对“纯新”的生产
如果说“类性多元”的概念使得巴迪欧能够把真理作为多元存在的某种生产性后果进行考察,那么通过对偶然性事件(event)的引入,巴迪欧又把真理程序变成了关于“纯新”的无限性创造。
所谓“纯新”,就是无法从当下情势中衍生出来的新事物,它需要和情势有一个断裂,而这个断裂必须经由突然爆发又很快消逝的“事件”*巴迪欧把“事件”界定为“特殊情势下或既定世界中身体和语言的正常秩序的中断”,参见:Costas Douzinas &Slavoj žižek: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 Verso, 2010, p.6.。换言之,由于“纯新”并不是内含于情势或世界中的可能性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偶然性事件的爆裂才能为那些从情势状态或世界合法性的有限视角来看完全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开辟道路。
在关于集合论的讨论中,巴迪欧已经指出,真理体现在集合对“纯多”的类性命名上,而这种类性命名指向的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指类”名称在当前的知识中找不到,它是从当下知识可命名领域的“黑洞”中绽出的,是“无中生有”。而在事件哲学中,巴迪欧又借助于拉康的三界说,把真理当作被符号界压抑了的“实在界”的征兆。巴迪欧指出,符号界代表着既定世界或特殊情势的稳定性结构,而真理则位于结构压制下的“实在界”,只有事件的发生,才能打破旧的结构和情势状态,使真理得以曝露,“纯新”得以生产。
由于世界和情势本身具有惰性,面对事件的撕裂总是倾向于整合以消除“真理—事件”的痕迹;但事件总要再次意外地发生(“每个事件都是一次突袭”[5]12),世界和情势不得不再次经受事件的洗礼和挑战。从另一视角来看,真理程序的展开也就表现为真理不断曝露,“纯新”不断创造的过程。换言之,“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形成了一种非连续的持续性机制——这种持续性机制既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也表达了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
可见,借助于“事件—真理”,巴迪欧既恢复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又不需要借助任何“上帝”的帮助——真理总是通过事件以一种“例外”的方式在世界的表象上将偶然和永恒连接起来[6]109。
3.主体化、观念化和真理的“三位一体”
“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如果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因素,最终仍会落入这样或那样的本质主义窠臼。因此,巴迪欧通过对主体哲学的建构,最终把真理程序的落脚点放置在“主体化”之上,即把真理程序视为真理和主体经由事件催化所形成的“合体”(incorporation)的过程。这也体现出巴迪欧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把“最强硬的形式主义与最激进的主体主义连接在一起”[7]的意图。
巴迪欧所谓的“主体化”,指的就是个体经由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按照自身实存及生活世界确立真理地位的过程。他把事件中突然浮现并在表象中取得最大值的一些重要宣言称为“原始陈述”(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主体要对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保持忠诚,就要不断地对“原始陈述”进行补充和新的创造,以促成和真理的“合体”,从而完成主体化。另一方面,通过主体的忠诚操作,真理也可以找到一个在世之身,使真理的新身体得以生成。真理身体的生成和个体“合体”真理完成主体化是同一个过程[6]114-118。
主体化的过程同时是“观念化”(ideation)的过程。或者说,正是由于“观念”(idea)的存在,作为新主体构成因素的个体才能意识到他或她从属于大写的历史运动,也才能成为真理身体的一部分。巴迪欧指出,“观念”作为真理和个体之间的中介,其作用就是准备和支持个体,使其能超越当下情势状态的束缚,从而在事件发生时进入真理程序。
在巴迪欧看来,“真理—事件—主体”的三位一体就包含在这样的一个个实例之中:“事件”发生,旧的情势状态被打破,真理得以曝露;主体经由“观念”的中介围绕“原始陈述”对事件进行介入、命名和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持久的操作,“纯新”得以生产,真理也获得了新的在世之身。
巴迪欧还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主体:忠诚主体、保守主体和蒙昧主体。忠诚主体通过对事件及真理痕迹的坚持,经由观念的中介开启了真理的新时代(如苏联共产党人经由共产主义观念开创了苏维埃的新时代)。保守主体指的是在新身体实存的前提下,仍然试图保留先前的政治经济形式(如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主体。保守主体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事件的后果,但也会基于改良的考虑反复掂量真理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把改良限定在先前的秩序框架下,或者说,“尽可能把这个新身体放在一个角落里”[6]123。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体也是由新身体导入的新主体,只是它要确保一种新保守主义实践的创立,即在与先前的世界保持一种连贯性的外表下创立一种与“大写的真理”保持距离的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对现在进行掩饰的现在”[6]124。而蒙昧主体则希望新身体死亡(如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为通过改革来维系超验性的永恒是不可能的,“为了对付新时代的出现,必须要在当下从整体上破坏真理的身体,并致力于清算任何类型的忠诚主体”[6]124。与此同时,蒙昧主体还要“提供一个完全虚构的身体来同真理的身体进行竞争”[6]124,而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身体,代表的不是普遍性的真理,“而是一个社会的绝对特殊性,植根于它特有的土壤、血脉和种族”[8]322。
二、减法政治:重启新的解放政治序列
虽然巴迪欧指出了真理的四个类性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但他的激进哲学更为关注的是政治真理程序。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作为集体性实践更能体现出真理的普遍性。在政治真理程序中,情势状态(state)就是“国家”(State),事件就是集体性的政治事件”(科学、艺术和爱并不是集体的实践,尽管“它们针对万物也普遍化了它们自己的独特性”),对空的普遍性命名就是“无产阶级”,忠诚主体就是“共产主义观念”所召唤出的激进行动者。
巴迪欧认为,政治真理总是能够以一种纯粹的经验方式来表达自身,因此,政治真理程序在某个具体世界中的刻写也表现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殊性的政治序列(sequences)[5]2。而他的激进哲学重点考察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一系列政治事件(主要包括1792-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1927-194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02-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1965-1968年的五月革命等)所揭示出的两个解放政治序列:一个是始于1792年法国大革命、延续了整个19世纪的“由共产主义观念所激发、通过起义推翻既定权力体系”的第一波解放政治序列;二是始于十月革命、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实现”的第二波解放政治序列[9]。
巴迪欧指出,尽管第二波政治序列解决了第一波政治序列中的遗留问题,即如何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但在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探索中却最终没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列宁和毛泽东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但最后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这表明:第二波政治序列内含的政治真理的可能性已经耗尽[10]113-114。巴迪欧认为,只有承认第二波政治序列的终结,并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对这一终结进行“内在化”处理,才能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启新的激进政治序列,迎来“共产主义观念的第三个世纪”[5]14。而他所谓的“内在化”处理,也就是以共产主义观念、原始陈述和一系列事件所揭示出的真理身体为坐标,把失败置于政治程序的内部去考察,而不是像法国的“新哲学”那样从一种恶的伦理学出发将失败归结为抽象政治的暴政,从而把激进实践从思想领域中逐出。
1.“一分为二”
巴迪欧认为,毛主义的“一分为二”原则可以作为思考新的解放政治序列的起点。他指出,“一分为二”原则强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分裂和斗争,体现了对“二”的欲望和对“一”的超越。相比之下,“合二为一”原则更为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综合(syntheses),但在综合的幌子下,“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古老的一”[1]69。对于革命的(而不是复辟的)辩证法而言,必须要欲望“二”而不是“一”——因为“一”所代表的是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即抹去事件痕迹并对现存世界进行缝合,而“二”代表的则是“事件—真理”及对现存世界的分裂。换言之,以真理实存为坐标的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必须要体现一种反对现存世界的分割性的思考,也就是一种“二”的思考——只有这种“二”的思考才是真正辩证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思考,“人的最高职责就是联合起来生产二、思考二、并将二付诸实践”[2]66。
“一分为二”原则并不等同于一种简单的对抗性逻辑——它不仅要欲望分裂,还要欲望创造。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曾经宣布它的法则是“二”——即一种指向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关于“纯新”的生产,但最终却回到了“一”——20世纪的斗争通过一个阵营对另一个阵营的胜利而终结。巴迪欧指出,为了打破20世纪末保守的情势状态,即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的局面,应该重提“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但“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并不是那种关于“群众与权力”“异见者与极权主义”的非辩证式分析,而是要在斗争和分裂的同时,进行“纯新”的创造性生产。巴迪欧强调,应该把20世纪那种关于“二”的外在性建构颠倒过来,即不是从客观性假设出发的“二”(阶级、性别、善恶……),而是要把“二”作为一种机遇的生产。
由于这种“纯新”的生产总是避免回到“旧一”,这个生产也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过程。换言之,“纯新”的生产必须和既定情势相分裂,但为了使这一分裂不会走向“综合”,还要把分裂和生产视为同一个过程,并一直坚持下去。在巴迪欧看来,只有忠诚主体的持久性操作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大写的二”(Deux)——一种避免回到“旧一”的辩证的、而不是并列的“二”。
2.差减式否定
“一分为二”原则实际上指明了新的解放政治的方向,即在和现存世界的不断分裂中开创关于“纯新”的无限性生产。这种关于“分裂和生产”的辩证法对于具体的政治过程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差减式否定”所带来的“增补”效应。换言之,“一分为二”原则并不指向对立面的消灭,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成为绝对的力量;或是指向对立面的融合,即“合二归一”;而是指向一种“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就其作为事件所曝露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而言,是一种“增补”,即实现了对空的命名;但就其过程而言,即如何从当前的总体化情势状态(即“一”)中生产出新质而言,则是一种“差减”,即一种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缩减过程。
巴迪欧所说的“差减式否定”,指的就是一种非破坏性的、建立在“最小差异”之上的否定。这种否定“对现实性的清洗,并不是在其表层来消灭它,而是从明显的整体中减去它”[1]74。换言之,差减式否定并不是对现存情势状态的颠覆,而是通过最小位移不断改变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旧的统治权力不断缩减,另一方面,新的主体性不断生长。巴迪欧强调,激进政治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破坏性否定。因为分裂和生产之间的辩证法要求必须经由“差减逻辑”才能在分裂中进行持续性的“纯新”生产。换言之,“新”作为一种“增补”,必须经由差减,而不是破坏,才能达成。尽管“为了新的到来,某事必须遭到破坏”[8]335,但破坏性本身并不是创造,破坏只是作为政治事件结果的特殊性,“新”则要从被排除掉的地方通过主体化来创造。巴迪欧还指出,把破坏当作创造新的纯粹象征,这种症候具有“积极的虚无主义”倾向,并会由于真理的绝对化而导致恐怖的发生*正如博斯特尔斯所评论的那样,从“破坏”转向“差减”是巴迪欧后毛主义政治学一个典型表现。巴迪欧通过对历史上一系列激进政治的反思,试图终结一种政治学上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的征兆就是一种指向“大写的真理”的“积极的虚无主义”——由于没有“真理—事件”的导引,真实的政治激情就会变成现实中的恐怖发作,最终归于一种虚无主义。参见布鲁诺·博斯特尔斯著《后毛主义:巴迪乌与政治(下)》,陈澄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7期。。
“差减式否定”指向的是矛盾的内在性法则。或者说,这种否定所包含的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种外部的对抗,而是通过不断抽离和对“空”的命名所实现的一种内在性反转。正如博斯特尔斯所评论的那样:“这种内在性方案并不呼唤一种神学的或类神话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呼应一种悖论式的褶子或皱褶;不是要跨过所有中间阶段的飞跃,而是要抓住影影绰绰隐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不是把人类历史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意识的分界线,而是要在既定情势中寻找潜在的‘反终结力量’、唤醒他们并赋予其反抗、颠覆和摧毁的能量。”[5]46换言之,新政治不是建立在外在于全部秩序的这样或那样的本质逻辑之上,而是着眼于权力和反抗、权力和非权力的接合点,“类似于一个麦比乌斯圈的正面和背面,只有伸展到足够远才能实现隐秘的反转”[5]46。
巴迪欧把这种建立在最小差异上的内在性方案称为“减法政治”。这种减法政治“不再是占据权力、取代已有权力,而是创造出自主空间,以迫使政府发明出与工人之间的新关系,这不是一种对峙,而是一种对内在的差别化空间的组织。捍卫的是独特性(singularity)而不是特殊性(particularity)”[11]。巴迪欧指出,“减法政治”的首要原则就是和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具体来讲,就是“拒绝被国家纳入、不向国家索要资助,拒绝参与选举等带有国家印记的政治行动”[5]13。其次,“减法政治”还要在事件所开创的政治序列中努力实现平等原则,在代表“纯新”的激进政治和代表情势状态的国家的间距中进行本地性操作,以最小差异或最小间隔来实现一种内在性反转。最后,减法政治和破坏性否定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在巴迪欧看来,如果和破坏性否定离得过远,减法政治就会滑向哈贝马斯所说的共识性民主,他指出,“今天,要提出一种关于否定的破坏方面和减法方面的新接合,使得破坏或暴力以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出现,也就是说能够保护通过减法政治所创造出来的局面”[11],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政治要能够成为破坏和减除之间的调节物或尺度。
3.非政党组织
巴迪欧认为,第一波革命序列以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告终,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起义和革命是否还是有效合法的途径?”[12]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如果由一个专业化、军事化,也就是严守纪律的组织队伍来领导革命的话,起义就有可能获得成功”[12]。正是列宁关于组织化政党的概念“让1917年的革命获得胜利”,继而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波革命序列也得以开启。但此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问题也就变成:如何通过“政党—国家”形式实现共产主义,即以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向非国家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列宁的“政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怎样具体实施集体化农业?如何处理中央化的工业,如何创建一个新的贸易形式?没有任何人知道”[12]。在巴迪欧看来,列宁的“政党—国家”很好地解决了第一波革命序列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但对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主要问题(即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却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苏联实践最终导致了国家主义,它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
巴迪欧认为,鉴于“政党—国家”的概念已经饱和,新政治就不能再采取第二波政治序列的政党组织形式。对于新主体的生成而言,更为重要的不再是政党的中介,而是观念的中介。新政治应该是“一种通过政治过程的思想规训而组织起来的政治”[10]108-109,这种政治无须按照和政党的关系来确立。此外,在日益碎片化的后殖民时代,如果说存在一个组织形式,那么它的角色只能是一种政治的促进者,而不是领导者,一个“让政治得以存在的集合体系”也肯定是位于“绑缚最少之处”。因此,巴迪欧指出:“今天的解放政治需要发明和试验某种非军事性的纪律模式,需要一种大众纪律。”[11]
正是在这种关于“解缚的”而不是“绑缚的”“松散的”而不是“紧密的”的逆向思维中,巴迪欧提出了他关于新的非政党组织的设想:“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联系紧密的派系,也不是斯大林所说的先锋队式的政党,而是一种不固定的普遍性存在;其功能就是要随时反对利益刚性的束缚;其品格不是其坚固性,而是对事件的可容纳性,即面对不可预料局势时的一种具有发散式的灵活性”[13];“它不仅是灵活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源于对所有呈现性的关联形式的物质性批判,以及在空的边缘上的操作,让同质性的多来对抗国家的异质性秩序”[10]66-67。
[1]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张莉莉.从结构到历史——阿兰·巴迪欧主体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6.
[4] [法]阿兰·巴迪欧.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M].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74-83.
[5] Costas Douzinas, Slavoj Zized ed:The Idea of Communism[C]. London and New York : Verso, 2010.
[6] [法]阿兰·巴迪欧. 第二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9.
[7] [美]布鲁诺·博斯特尔斯.后毛主义:巴迪乌与政治:下[J].陈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7):63-71.
[8] 陈永国,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Ala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J]. New Left Review, 2008,(3).
[10] [法]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M].蓝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1] 朱羽,等.当代政治与否定的危机——阿兰·巴迪乌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10,(6):72-79.
[12] 巴迪欧VS高歇:从马克思到列宁[EB/OL].蓝江,译.http://weibo.com/p/230418542ef2b20102vrgt.
[13] Alan Badiou. Metapolitics[M]. J. Barker, Tran. London:Verso,2005:74.
〔责任编辑:侯冬梅〕
B565.5
:A
:1000-8594(2017)04-0075-05
2017-03-05
范春燕(1971—),女,河南开封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