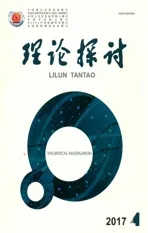论竞争文化中的竞争政治
——读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一书
2017-03-10张康之
张 康 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论竞争文化中的竞争政治
——读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一书
张 康 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是在近代建构起来的,所拥有的是竞争文化,是在竞争文化之中去开展政治活动以及几乎所有社会活动的。竞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了活力,推动了历史进步。但是,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反映在政治中,不但使政治背离民主的原初目的,而且导致全社会的利益冲突,在国际社会中,则经常性地以战争的形式去诠释竞争。即使是以和平的形式出现的竞争,得到规范的竞争,也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消耗,甚至会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竞争在逻辑上有着把竞争成本转嫁给无辜者的必然性,而人类的竞争则把其成本转嫁给自然界,从而破坏了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克尔伯格对竞争文化以及竞争政治做出了深刻反思,在他的这些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去提出终结竞争文化以及竞争政治的要求。
竞争文化;竞争政治;对立和冲突;合作文化
竞争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一旦缺少这些,它就会轻易地被不可谈判的道德价值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之间的敌对状况所取代”[1]。可是,当政治领域中的冲突结构化了,变成一种日常形态,而且又由于政治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就不能不把整个社会拖进无穷无尽的冲突之中。之所以工业社会无处不存在冲突,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所拥有的是竞争文化。可以说,正是这种竞争文化,使工业社会陷入无尽的冲突之中。当然,工业社会通过建立起法律制度并实施法治而实现了对冲突的规范、限制,把冲突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工业社会通过制度化的“分而治之”,而使冲突分散地存在于微观的组织或地域中,从而不至于演化成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就冲突对资源的消耗来看,如果加总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破坏力仍然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随着国际社会的冲突所包含的各种隐忧被人们意识到了,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对竞争文化进行反思。
一、竞争政治及其后果
博弈行为也许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博弈观或者说模式化的博弈思维则产生于竞争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对人的形塑,而使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竞争的社会中,不但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而且在人自身的行为选择过程中,都包含博弈的问题。这种普遍化的博弈行为根源于竞争文化,是因为竞争文化在近代社会得到完整的、周延的表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每一个角落,才使得我们随处可见博弈行为。“在竞争文化中,几乎每项制度,或曰文化博弈,都遵循一套竞争规则。这些规则不仅确保有赢家、有输家,还确保最强大的选手最有可能赢得比赛。当不太强大的选手同意加入这些博弈中,也就等同于他们愿意遵守这些规则,而这只会加速他们的失败。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比如抗议,与这些竞争规则是一致的。它们不仅强化这些旧博弈的正当性,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它们也确保最强大的选手最有可能获胜”[2]187。由于近代以来的社会所持有的是竞争文化,使得人们即便是在宗教、公益等活动中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挑起教派纷争和名誉争夺。
单就政治来看,我们发现,基于竞争文化的制度设计必然会要求政治生活中包含多党竞争、竞选等。如果一个社会尚未形成竞争文化,即使在西方霸权国家的胁迫下去移植西方的制度模式,也会表现出狐疑不定的状况,不愿意采纳多党制。或者说,在竞争文化尚未形成之时,即便引入西方国家的竞争政治,也会陷入动荡和动乱之中。虽然现代化的布道要比基督教更加成功,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地将竞争文化传播到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那些竞争文化与非竞争文化之间的地带,仍然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本身也反映了竞争,然而,却令拥有竞争文化的西方国家看着不怎么顺眼。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是,不允许任何地方在竞争上表现出某种三心二意。因为那会使这些地方的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都无法达到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那种典型形态。然而,这些地方却往往在捍卫传统文化精神的名义下拒绝接受西方国家要求它们完全接受竞争文化的做法,因而在这些地区与西方国家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和冲突。而且这种竞争会被宣布为制度、体制、文化、道路上的竞争,希望在竞争中证明自己在文化上的优越性。这似乎说明,整个世界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竞争文化的笼罩之下,除了接受竞争以及竞争政治,似乎无路可行。
竞争政治成为可能,依赖于政治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具体地说,表现为多党制。克尔伯格认为,“党派民主制的演变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源于这一臆说: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富有竞争性,所以,竞争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正常和必要的模式。当然,在经济学中,物质产品和资本的分配,或曰经济权利的分配是由竞争决定的。另一方面,在政治学中,公权力和决策权的分配,或曰政治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竞争。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的文化规范是相同的”[2]44。都源于竞争文化,或者说,竞争文化使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获得了同一性,都通过竞争行为去开展活动。如果说经济是基础的话,那么,在还原论的追溯中,就可以将竞争文化的生成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竞争文化的生成,也就赋予人们以竞争文化的观念,使人们可以从这种文化观念出发做出政治安排,并形塑出竞争政治。党派的发明无非是在竞争政治的逻辑中做出的,从属于竞争政治的需要。
但是,党派间为什么要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开展政治活动,其答案就是利益。克尔伯格说:“一切党派政治体系的核心都是政治利益观。这个术语广义上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的需要、价值观和要求。如此构想的利益被假定为个人或团体在决策过程中选择权的基础。利益据说(有意无意地)指导着对自身或本团体何为最佳选择的评估。在多元化社会中,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似乎常常相异或冲突。”[2]44-45如果在社会过程中去加以解决利益上的“相异和冲突”,无论是借助于道德的力量,还是法律的规范,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诉诸法律手段的话,立马就会遇到法律如何生成的问题。所以,必须把“相异和冲突”的利益搬到政治过程中加以解决。这样一来,产生于经济过程中的利益上的“相异和冲突”就转化成政治问题,不但经济形式,而且经济性质,也都被扬弃了,从而使利益上的“相异和冲突”获得了政治属性。这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及其得以产生的原因。
在政治过程中去解决利益上的“相异与冲突”的问题,首先需要将全部“相异与冲突”都揭示出来,这就要求各方都拥有充分的表达权。只有当人们拥有了表达权并能够表达,才能将他们的利益要求展示出来,并使他们之间的利益要求上的“相异与冲突”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每个人面前。但是,假若每个人都在政治过程中去进行表达的话,那么,所形成的必然是表达噪音。结果,不仅不利于展示利益上的“相异与冲突”,反而会掩盖了“相异和冲突”。因而,需要通过代表去把握利益诉求的中心和主要方面,并代为表达。为了使表达更有力量,将代表组织起来并形成党派,显然是最佳选择。这就是党派得以生成的逻辑。也正是这一逻辑,决定了党派必须代表从个人到团体逐级过滤和集中起来的特殊利益,通过表达去展示不同党派所代表的利益上的“相异与冲突”,进而进入讨价还价并做出决策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体上必然是竞争性的,只有通过竞争,才使每一个环节成为可能,否则,就会与民主的原则和要求相背离;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竞争性的,赋予民主政治以竞争的特征,把民主政治形塑为竞争政治。在竞争政治的运行中,竞争行为渗透到每一个方面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在议会中开展正式的、公开的辩论之外,在延伸到议会之外的的时候,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幕后交易也都是通过竞争的方式进行的。“游说团体和政治委员会的相互竞争,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向党派施压和塑造公众舆论”[2]47。在竞争政治的理想模式中,“游说团体和政治活动委员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在许多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中作为首要代理人的民意代表。于是正式立法机关之外的组织化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影响力至少已经和那些立法机关内部的竞争相当”[2]47。
竞争政治必然会使“决策成为对立的利益集团代表间的一种党派辩论,即口水战。在这些辩论中,政治对手们耍尽花招、争论不休,试图打败对手,并在公共舞台上获得制高点。这种对抗性的辩论模式体制化程度,最明显地表现于‘忠实反对派’的议会观中,这种观念或明或暗地被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或国会奉为圭臬”[2]46。问题是作为议会中的反对派,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公众福祉,只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反对派”角色,即忠实于自己的“反对派”角色而反对一切。即便党派假意为了公众福祉发言,也完全是出于积累政治资本的考虑,目标仍然是下次选举中的胜利。“党派们起初阐述自己的立场,目的是确保该党派自己的立场获胜。结果一个党派的身份便与其拥有的立场密切相关,其立场的失败导致该党派‘政治资本’的丧失。这样,决策过程便与选举过程形影不离,因为党派辩论在下一轮选举的期盼中,成为不断竞争的舞台,目的是为了扩展‘持久的竞选战役’,争取政治资本”[2]46。可见,竞争政治使政治本身成为全部政治活动的理由,以至于政治应有的目的被忽视甚至忘记。当政治成为政治家的事情,与公众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相关度也就下降到极低的点位。在这里,公众实际上只是政治家们开展竞争时的筹码。
在痛陈竞争行为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后,克尔伯格概括道:“竞争理想在持续进行的物质获取和控制的竞争中使工人与工人相斗,资本家与资本家相争,以及劳资之间相互对立。它还促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争相斗,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更为堪忧的是,“竞争已经不再是一种手段,相反,它成为企业家,也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主要目标”[2]42。在竞争成为社会目标后,人也就完全是为了竞争而生,为了竞争而活,竞争成为生活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其他方面都显得不再重要。试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可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因而整个世界也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到竞争之中。比如,“在由美国对大众媒体内容的全球主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影响——它将暴力、冲突、结党集社和好讼的文化表达不仅出口到其他西方国家,而且实际上还出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2]38-39。这是竞争文化的传播,借助于话语霸权,竞争文化事实上征服了世界。因而也赐予人类一个全球风险社会。
近代以来,竞争文化主导人的思维和行为,使人变得好斗,而且也将这种好斗的一面投射到国家行为和社会治理之中。如果计算一下各国军费开支的总和,那将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而且用于军事方面的人力资源同样是一个宏大的数字,他们显然是从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抽离出来的,不仅不用于生产和服务,反而每日都要消耗掉大量资源。比如,美国的航母战舰每日游弋于大洋之中,对于生产力而言,有何助益?从苏联的解体来看,正是陷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陷阱之中,致使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同样,就美国而言,当我们看到老旧的火车慢腾腾地爬行时,当我们看到城市地铁硕大的老鼠大模大样地在等待乘车的人群前游荡时,脑中闪过的是:这个国家在军备上那样的慷慨,在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方面却如此的吝啬。正是变态的竞争,“一方面,它导致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都能看到的日益扩大的贫富严重差距;另一方面,它加速了这个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大规模恶化”[2]55。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地球已经难以承受人类的竞争。当竞争的恶果转化成对地球的破坏并损毁了这一人类共同的家园时,竞争中的胜利者难道体尝的就不是“胜利”的苦果吗?
诚如克尔伯格所指出的,“竞争政治、竞争民族主义和竞争军国主义的对抗结构同样难辞其咎。鉴于这种认识,有必要寻找一种替代规范,以取代主宰当今政治领域的对抗主义规范”[2]109。的确,风险社会的现实已使此项要求变得非常迫切,我们的关注点也不仅仅是规范转变的问题,而是政治及其观念的根本性转型。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致力于政治及其观念的根本性转型,满足于在规范的调整方面做文章,也就不可能达到遏制竞争文化及其行为后果恶化的趋势。因为把重心放在规范调整上,至多只能去谋求强化那些抑制竞争的规范,也就会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抑制竞争的规范方面。那样的话,就必然会导致规范的繁复,从而使得规范执行起来变得困难,而且会引发规范力下降的问题;相反,如果我们探索竞争政治及其观念的根本性转型之路,一旦取得突破,就会获得全新性质的规范,既有的一切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二、竞争政治引发国际冲突
竞争文化是当今世界一切动荡不宁的总根源。显然,战争是一种野蛮的竞争方式。广义上讲,战争可以表现为决斗、家族暴力、血亲复仇、抢夺以及不同共同体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战争频繁发生,而且发动战争的随意性很大。到了工业社会,人们对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加之人类在整体上理性水平得以提升,一般说来,会在做出权衡和计算之后才会求助于战争的手段。往往是在政治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所以,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更为崇尚的是一种文明的和温和的竞争,并将竞争与战争加以明确区分。然而,在人们对竞争表现出无比崇尚的时代,往往只关注竞争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竞争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对于人的竞争行为所造成的那些对自然界的破坏,往往不去关注。
对此,克尔伯格直截了当地指出,“即使在没有真正战争的时期,武器的制造和储备,以及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训练和维护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损害。且不说军队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用于社会和生态生产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它还在环境记录上留下了最恶劣的一页,其程度之甚,任何现代工业都无可比拟——哪怕是在和平时期”[2]108。“在战争年代,环境付出的代价则更高昂。从越南的枯叶战到波斯湾战争的油田燃烧,生态破坏逐渐成为一种正当的军事策略。此外,许多新的军事技术,包括地雷、生化武器、核武器,甚至现在连常规武器也选择用核废料制造,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战争风险。在历史上,人类可以说第一次具备了一种军事能力,即让地球变得不适合多数生物生存,包括人类自己。尽管这种灾祸还未曾上演,但是,由于无数的军事试验、演习和对抗,地球局部地区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适合居住”[2]108-109。
也许人们会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是典型的竞争政治,与它们相比,欠发达国家在竞争政治方面要逊色得多,但那些拥有典型的竞争政治的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做得更好。直观地看,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将这一现象与“富人的后花园”相比的话,就会形成趋近于正确的认识。假如一个人是在竞争中胜出并成为富人,也许他是通过做了一桩曾经引发过环境灾难的生意(项目),并因此而致富,但他家的后花园却远离环境灾难,被保护得那样好,根本不可能让人联想到花园的主人与那场环境灾难有什么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由于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去获得利润,也就同时把环境问题推广到全球。所以,对于环境问题,是不应孤立地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去看的,更不应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能够成功地将环境问题转嫁到处于世界边缘地位的国家去,而且这种成功已经持续了若干个世纪。
克尔伯格在历数竞争政治的危害时,总是直接地把美国作为其描述的对象。的确,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美国,它总是被人们指责为战争的策划者。事实上,在二战之后所发生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性战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武器甚至士兵。由于美国在所有方面把竞争文化诠释到极致,所以,它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世界上一切军事冲突和暴力对抗的总策源地。也许美国在主观上并不希望世界动荡,因为一个动荡的世界也会直接地使它的利益遭受一些损失。但是,由于它深深地信仰竞争文化,而且在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一切事务上都采用竞争行为模式,一旦竞争激荡出的力量达到它自身无法容纳的程度,就会向外部释放,从而使世界陷入竞争的旋涡,出现动荡。另一方面,竞争文化也驱使美国必然会在世界上找寻竞争对手,不管另一个(些)国家愿不愿意,它都迫使那个(些)国家必须与它一道去玩一场竞争的游戏,在竞争中以击败对手为乐。
为了确保竞争制胜,美国也会寻找和培育盟友。或者说,既然美国认为竞争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游戏,它就无比渴望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那样会显得更好玩。因而它既需要对手,也需要盟友。实际上,它的所谓盟友只是他竞争中的打手,为了使这些打手变得更有力量,美国就必须武装它们,训练它们,需要激发出它们狼一样的进攻性。之所以那些充当打手的国家甘愿顺从和依附于美国,那是因为面对强大的美国,顺从会获得更大的安全感,而依附则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即便不是为了那些收益,它们也不愿意做美国的对手。但是,由于美国只允许它们在对手和打手之间做出选择,以至于它们也就不得不充当美国的打手了。同样,美国不允许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做它的打手。因为那样的话,竞争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美国必须将某个(些)国家塑造成它的对手,迫使那个(些)国家与它竞争。
总的说来,在美国把竞争文化推广到全世界的条件下,从逻辑上说,应当是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转化为它的竞争对手。但是,从现实来看,美国拥有大批盟友。美国之所以有盟友,是因为它的强大。如果它不能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强大优势,那些充当它的打手的所谓盟友立马就会向它露出狼一样的牙齿。近一个时期,之所以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策略,就是因为它已经感受到某种危机。那就是,一些本应充当它的打手的国家变得不再安分,有着向它展露狼牙的冲动。美国需要证明自己是强大的,希望那些打手安分地扮演打手的角色。同时,也需要诸如把中国说成是对手,而为它的打手们指出一个可以盯视的目标。然而,竞争文化是一个死局,美国受到其竞争文化信仰的支配而必须将竞争游戏进行到底,因而它就需要打手和对手。特别是为了维护打手对它的忠诚,就必须显示甚至维持它的强大。然而,在持续的竞争游戏中不可能有永远不输的赢家,永远强大的梦想只能在破坏竞争规则中才能实现。所以,美国在对竞争文化的信仰中所开展的竞争又要求它为了竞争制胜的需要而必须破坏竞争规则。也许偶尔为之不会对竞争文化造成破坏性的冲击,但美国为了维持它的强大,又不能不经常性地破坏竞争规则,以至于最终必将对竞争文化造成破坏性的冲击。
当然,美国有可能在摧毁了竞争文化后,成为再无竞争对手也无法塑造出竞争对手的国家。那样的话,它实际上变成为农业社会中的那种帝国。假若它成了那样的帝国,也就必然会陷入兴起和衰落的轮回之中,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自己走向了衰落。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一旦显现出衰落的迹象,那些本来作为它的打手和依附于它的所谓“盟友”,就有可能立即向它展示由它训练和培育出来的那种狼一样的牙齿,并将它撕裂。这就是竞争文化的逻辑向人们展示出来的一种美国的宿命。而且这个预言必然会应验,至于哪一天到来,完全是一个时间问题,结果将不会改变。实际上,美国也有另一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抛弃竞争文化,把信仰竞争文化的热情转投到对合作文化的建构上。但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缺乏危机意识的国家来说,这种浴火重生的痛苦是绝不可能去加以尝试的,除非我们的意见被美国人听取、接受并践行。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可以认为,美国的傲慢必然会决定它的宿命将不可改变。不过我们也相信,美国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做不到。但是,一个重要条件应当是,这样的国家必须是不受竞争文化熏染甚深的国家。虽然它在美国主导的这个竞争的世界中不能独善其身,但它可以不去忠实地扮演美国对手的角色。在美国迫使它必须开展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它始终采取一种守势,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合作文化的建构。通过持续的、以一贯之的合作行为选择去赢得合作的回应,不断地积聚起合作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合作文化,并将世界上的一切积极力量都吸收到合作体系中,实现合作与竞争的此长彼消。那样的话,最终胜出的就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其实,这里所使用的“胜出”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将是为人类历史开拓出合作文化得到普及并得到广泛信仰的新阶段。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界中,这样做需要无比巨大的理性定力。可是,就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这项伟大的事业而言,这种理性定力是值得付出和值得拥有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界中,为了人类的合作前景,在一定程度上用竞争去终结竞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了合作社会的到来,为了建构合作文化的目标,发生在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竞争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合作与竞争间的竞争制胜,并不是对竞争文化的迎合,而是为了扫除走向合作社会道路上的一些阻力。其中,所反映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即通过现实的行动去达成伟大的理想。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就合作文化的建构而言,我们并不主张通过竞争的手段,因为那是与合作文化的精神相悖的。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合作文化建构将是这场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运动欲加建构的一部分。这场社会变革的具体表现应当是:人们为了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而开展合作行动,并在这种合作行动中,自然而然地建构起合作文化,因而并不表现为必须通过竞争去终结竞争文化的状况。所谓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竞争,应当准确地理解为竞争与合作的此消彼长。
克尔伯格指出了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国家内部的竞争政治系统生态功能失调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2]108。国家间在GDP上的排名激发出竞相向前位跃迁的冲动,致使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等问题上,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全球性的合作来加以解决的,“然而,由于受制于这些不合时宜的国家主权模式,现存的国际秩序(或曰无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无法应对当前紧迫的生态问题。在这个现存的国际体系中,由于国家之间野蛮竞争,欲将长期的生态资本转化为短期的经济收益,因此,可持续性不得不让位于当前国家自我利益的追逐。这种竞争性国家主权系统无法负责任地解决环境问题。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国家监管机制的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强势的跨国企业的全球化运作,且几乎不用承担任何环境(还有社会)责任,因而经济全球化只会加重这些破坏生态的趋势”[2]108。由此也可以看出,全球化如果行进在竞争文化及其行为模式所指引的道路上,或者说,如果把全球化误读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并按照“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模式去推动全球化,就会把人类引向一个不容乐观的方向。不仅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甚至在所有的方面,都将把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全球化、后工业化必将意味着对竞争文化及其行为模式的扬弃,即便竞争行为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仍然是必要的,那也必须从属于合作,是包含在合作行为模式中的竞争行为,是受到合作文化规范和调节的竞争行为。
三、终结竞争文化的路径
克尔伯格在考察了诸多当代思想家的作品及其观点后总结道,“按照拉兹洛、博尔丁和其他同类理论家的观点,对抗关系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种族主义、竞争物质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失调的表现,都是人类社会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的体现,即无法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时代,按照人类集体利益发展所需的‘正和博弈’或‘综合’关系来调整社会系统”[2]99。就克尔伯格所考察的这些观点看,对竞争文化的怀疑以及对竞争后果的忧虑,可以说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但是,也必须指出,这些观点所代表的思考依然受到竞争文化的钳制。比如,从集体利益出发,显然是不能找到终结竞争文化的出路的。因为集体间仍然会产生竞争的问题,亦如从个人出发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集体无非是个人的放大,是以放大了的个人形式出现的,在竞争文化的支配下,依然会做出破坏力巨大的竞争行为选择。从集体出发与我们所推荐的“人的共生共在”这一出发点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从集体出发所做出的规划也只限于使他们去设想对竞争加以改良,即提出所谓“正和博弈”。
当然,通过强化竞争规范以及强化对某些社会技术的使用,也许能够达到“正和博弈”的效果。但是,那将是非常脆弱的,只要竞争文化得不到终结,就必然会遭遇回潮的问题。事实上,“正和博弈”也往往是出现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只能反映在具体的事项上,作为一种行为模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为人们一旦处于竞争过程中,就必然会更多地关注博弈的问题,是否“正和”,往往会被抛诸脑后。还有一点,关于集体利益关注的说教和“正和博弈”的制度安排肯定包含某种向集权主义方向移动的隐忧。如果人们为了避免走向集权主义时时采取防范措施的话,不但会使制度运行成本大幅提升,而且必然会陷入竞争的窠臼之中,甚至要比近代传统的竞争政治消耗更大的运行成本,使得社会无法承受。
20世纪中期,协商民主的理念被提出来,它既是近代民主传统的延伸,又包含突破竞争文化的路向暗示。但是,这仅仅是就其理论特征来看才能发现其在路向上有着不同于近代以来传统民主的逻辑,在实践上并未得到证实。因为在原有的竞争性民主的框架下,协商民主的理念并未转向实际应用的层面,一些倡导协商民主的理论家也努力去搜寻成功协商的案例,总的说来,并未出现具有充分证明力的例证。在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中,协商、对话、讨论、争论等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任何一项关涉社会治理的决策也都不可能等待长时间的协商,更不可能达成共识。虽然从逻辑路向上看协商民主可以成为竞争政治的一种矫正手段,但那仅仅属于理论上的一种思路。如果落实到实践中的话,立马就会发现,协商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一个社会能否承受这种协商成本,显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在竞争政治已经造就出的那种政治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作为协商前提的平等由谁来提供,或者如何获得?显然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作为协商前提的平等无法获得的话,协商民主的构想又在何种意义上不是空想呢?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协商民主的理念向实践转化时,是否需要考虑我们时代的特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已经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耗时费力的协商能否发生?同样是一个无法做出乐观估计的问题。再一个方面,在人的自利性假设之下,人们只关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只会带着个人利益实现的要求去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中,至于那些与自己利益无涉的事,是不愿意参与协商的。那样的话,公共利益如何得到维护?所以,协商民主并未给我们展示出可以终结竞争政治的希望。事实上,在竞争文化中,它只能是一种空想。
哈贝马斯也许没有从根本上告别经济决定论的思路,所以,才会天真地以为,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就会放弃个人主义的观念,进而使社会的竞争文化得到消解。他甚至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说“这些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社会富裕程度,预防某些基本的生活风险和满足‘基本需求’不再成为问题。因此,个人主义的优先系统就不是那么太突出”[3]。这显然是一种无根由的乐观态度。从实际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激烈,富裕的西方社会不仅没有告别个人主义的优先系统,反而在个人主义的路线中制造出金融危机,并将环境灾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所以,并不是一个社会变得富裕了就会自动告别个人主义的优先系统。如果说人类能够走出个人主义的窠臼,那也是在人们充分地意识到人的共生共在的意义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当人们用人的共生共在的观念替代了个人主义,才有可能在是否开展竞争、如何开展竞争,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展竞争等问题上做出理性的选择。那样的话,人们才会告别竞争文化,即不受竞争文化的支配。
对于竞争文化,生态学的出现无疑构成一种挑战,或者说,生态学在诸多层次上对竞争文化质疑甚至否定。因为生态学的生态系统观念给人们展示的是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依存,“与对抗关系不同的是,生态世界观强调互惠与共生——另外两个关键的生态学概念——的极端重要性。尽管自然界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侵略和掠夺,但是生态学认为互惠和共生同样重要,甚至是一种更基本的生态动力学”[2]102。不过,虽然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新观念,表达了对竞争文化的否定,但有一点还是生态学所未看到的,那就是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相比,人类社会在竞争文化及其行为的作用下,已经达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正是社会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人的共生共在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求。
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中,生存竞争在没有人的干预的条件下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物种间的竞争能够得到自然因素的调节,而人类社会在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使得以往调节竞争的因素——规范、规则等——都面临失灵的问题,以至于竞争陷入轮番升级之中,不断恶化,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这说明,生态学对生态动力的肯定也已经不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类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克尔伯格还提出了人类不同于生态系统之处:“自然界呈现的侵略和掠夺,多是表现在物种间而非物种内。尽管在物种内,比如一些动物之间,存在着某些极具挑衅性的争夺交配权的行为,但是它们通常只是虚张声势,很少真枪实弹地伤害对方。相反,在所有的‘社会物种’中,人类所体现出来的侵略行为,无论其范围抑或程度,皆无可比拟。许多进化论理论家因此总结道,在人类这种物种内,侵略行为是通过文化习得,而非由生理决定。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从侵略文化转向互惠文化已经刻不容缓。”[2]103所谓侵略文化,其实是竞争文化的极端表现,从根本上说,人类间的相互伤害,是竞争文化所形塑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定式。
总之,人类社会不同于生态系统。人类是生态系统的破坏者,是因为人类中的竞争而把一切消极后果最终投向了生态系统,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中,竞争在周期性地导致社会失衡和失序之后尚能得以恢复,即因某些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进步而恢复平衡和秩序,那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单单依靠技术进步已经无法恢复社会平衡,甚至会导致秩序的全面瓦解,从而危及人类整体的存在。所以,正是人类社会的存续要求,把我们引向建立合作文化的构想中,无可选择地要求我们通过合作文化的建构去为人的共生共在提供保障。无论竞争文化在工业社会中提供了怎样的社会动力,也不管竞争行为在何种意义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在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都需要加以终结和废止,并代之以合作文化和合作行动。
竞争政治无非是竞争社会中的政治。在竞争的社会中,“抗议、游行示威、党派政治组织、诉讼、罢工和非暴力反抗行为已经在许多社会宣传运动中成为行业工具。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暴力和恐怖主义也被运用于追求社会变革的过程中”[2]69-70。正是这些,轮番升级地推动了竞争和对抗,使社会风险加剧。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竞争文化的产物,并在竞争文化的作用下表现出路径依赖。如果说从这些因素中解读出社会变革的动力的话,也会看到它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实现某种人们以为是社会变革的运动,但它在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一场虚假的社会变革运动。因为它并不终结竞争和对抗,而是改变了竞争和对抗的方式。或者说,把既有的在竞争、对抗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推翻,让处于劣势的一方夺取优势,然后开展更激烈的竞争和更残酷的对抗。所以,在既有的竞争和对抗模式中去寻找社会变革动力是不可行的,不可能真正促进社会变革。真正的社会变革应当是竞争文化、竞争行为模式的彻底终结,并代之以合作文化和合作行为模式。在合作文化和合作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无疑也会存在竞争行为,但它将是作为合作的补充因素而存在的,所发挥的是促进合作的作用。因而那种有限的竞争行为是从属于合作的需要的。在合作的社会中,人无论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都是行动者,会在合作行动中展示自己的创造力,诠释自己的独立性。
在从竞争文化向合作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应是让人们普遍确立起人的共生共在的观念,而且这也是合作文化建构的关键点。在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未来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都是在竞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受到竞争文化的熏染。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人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造就出来的,他们接受了被认为是理性的理论和观念,深信自己是自私的,从来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自利追求的正当性,也往往把合法性与正当性混同起来,认为凡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正如克尔伯格所指出的,“许多人都是在竞争文化中成长起来,对自我利益的野蛮追逐已经变成了规范化,甚至理想化,因此不难想象,他们发现自己很难以非对抗的方式与持不同利益的他人相处。将非对抗的纠纷解决方式放置于对抗的心理结构环境中,这种做法只会导致这些非对抗方式的功能更加失调”[2]127。要求这些人告别竞争文化并转而接受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又是一条无可选择的道路。所以,在我们的时代,虽然谈论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也不乏认真探索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积极成果,但是,“即使这些方式具有可行性,可是它们的结果却经常受到现存法律和管制框架的制约,而这种框架本身就是由同一个政党系统决定的。将非对抗的纠纷解决途径放置于对抗性的统治结构中,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非对抗方式的效能”[2]127。我们的直观感受是,无论是在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交往过程中,谈论合作,不但显得虚伪,而且总是包含几分滑稽的成分。当美国政治家同那些处于世界边缘国家的领导人大谈合作的时候,连动物园中的猩猩都会笑掉大牙。
当然,这并不是说谈论合作有什么不妥,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在竞争文化的情景下怀着自利的目的去谈论合作,甚至是在武力威慑之下去谈论合作。我们渴望人类的广泛合作,但那是在合作文化背景下的合作。所以,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的转型,必须把终结竞争文化和建立合作文化作为其基本内容。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克尔伯格指出,“为了评估非对抗方式在处理所有人类事务中的实际效用,有必要找到一种综合或全面的文化形态,并且这种文化形态中所包含的意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必须能够增强而非破坏公共领域的互惠式思考、讨论和行为方式,最后在这种文化形态中评估这些非对抗模式的应用情况”[2]127。我们将这种文化称作为合作文化,它的深层心理结构是围绕着人的共生共在建立起来的;人们基于合作文化去开展合作行动,又是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行动目标的。虽然人们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有分歧,可一旦人们告别了竞争文化,在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目标下去开展行动,所有分歧都不会演化为人的冲突和对抗,反而会在人们探寻更加合适的问题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
[2] [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M].成群,雷雨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3] [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7.
TheCompetitiveCultureinCompetitivePolitics——ReadingKielberg’s“BeyondCompetitiveCulture”
ZHANG Kang-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We live in a competitive society, which built in modern times and formed competitive culture, it is in the competitive culture that to carry out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almost all social activities. Competition has enabled our society to gain vitality and promoted historical progress. Howev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mpetition is also great. Reflected in politics, it not only makes the political departure from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democracy, but also leads to conflict of the interests in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often interpret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orm of wa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 in the form of peace, even in a standardized competition, it will inevitably bring huge cost consumption, and even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humans can not afford. More importantly, competition has the inevitable logic to transfer the cost of competition to innocent people, and human competition transfer the cost to nature, thus undermining the survival of the whole human conditions. Kellberg has mad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e of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tics. On the basis of his reflection, we need to put forward the demands of ending the culture of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tics.
Competitive Culture; Competitive Politics; Antagonism and Conflict; Cooperative Culture; Human Symbiosis
D0-05
:A
:1000-8594(2017)04-0030-08
〔责任编辑:刘建明〕
2017-05-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16JJD720015)成果
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行政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