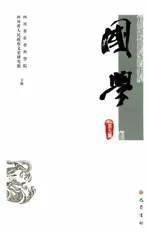八卦起源占卜論分析
2017-03-05王先勝
王先勝
八卦起源於占卜或數卜是學術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種觀點,或可謂主流認識。如:馮友蘭認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龜兆而來,是標準化的“兆”;高亨認為八卦中的陰陽爻象徵占筮用的兩種竹棍,八卦是有節和無節兩種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鏡池認為陰爻和陽爻象徵古代結繩記事中的小結和大結,古人用結繩方法記録占筮之數,後來衍化為八卦;郭沫若認為八卦中的陰陽爻源自男女生殖器,陽爻取象於男根,陰爻取象於女陰。由於“諸種假設均缺乏文物驗證”[注]唐明邦:《周易評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5頁。,所以它們現在主要是作為一種歷史記憶和資料,或可懸而不論。
在當代,由於殷周數字卦的發現和破譯,以及一些研究數字卦的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某些並不恰當的推測和判斷,使得“八卦起源於占卜”的觀點似乎有了考古依據和綫索,所以無論易學界還是非易學界的學者,在認識上大都更加傾嚮於“八卦起源卜筮論”。如:唐明邦先生認為張政烺1980年提出的“八卦由古代數卜記録符號演化而來”“這一發現為探討八卦起源、筮數同卦象的關係,打開了新思路”[注]同上,第15頁。。鄭萬耕先生認為馮友蘭、高亨、李鏡池等人的“卜筮説”乃至章太炎、錢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張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説”“都是無從確證的猜測”,而張政烺的理解雖“仍屬猜測,但它具有相當的考古文獻上的根據,為我們探討卦爻畫的起源,開闢了新的途徑”[注]鄭萬耕:《易學源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年,第13-14頁。。陳詠明先生一方面認為張政烺對殷周數字卦的破譯與朱自清關於“八卦符號源於數卜(數目)”的推想相印證,同時又説,“八卦的形成、發展和運用,都是為了占筮,須從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離方嚮”,“由於人類社會的發展,生活内容日趨複雜,即使可以增加内涵,八種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變化了,於是加以推衍,成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於是卦象涵蓋的内容加多,應付的事變也加多”[注]朱伯崑:《周易知識通覽》,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32-36頁。。朱伯崑先生在四卷本《易學哲學史》中有類似的説法:“……八卦所以演為六十四卦,看來是出於占筮的需要。隨著占筮的發展,八種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於是加以推演,成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可以應付無窮事變了。”[注]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1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13頁。周山先生認為張政烺先生研究的數字卦“實際上就是《易經》卦體的前身”,“《易經》卦體中的陰陽爻畫源於數位,是可以確定的”,“ 陰陽爻畫源於數位,應是歷史的真實”[注]周山:《解讀周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6、9、11頁。。李零先生説,“從近年來古文字學家對一種所謂‘奇’字的破譯,我們已瞭解到《周易》的易卦本是來源於一種用十進數位表示的數字卦,不但原先未見用横畫斷綫表示的陰陽二爻,而且就連這種陰陽二爻最初也是用數字表示”,認為“我們要想理解古代易學,有兩點必須抓住,一是‘數’,即卦如何由數而變成,這是筮法的關鍵……”[注]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99、206頁。。樓宇烈先生更是專門撰文論述道:“根據現有考古發現的文物資料,可以肯定地回答:作為易卦卦畫的基本爻象‘--’與 ‘—’是由原始筮法中的筮數演變而來的,它的原始形式和意義是‘數’,而且是某個有具體數值的‘數’。……當具體筮數演變為抽象的奇偶數代表後,人們纔會從卦畫爻象中認識到一切筮數最後都衹歸結為兩種爻象(--和—),以後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則正是從這裏出發,推演出來的。”[注]樓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在此,我們有必要看看有可能支持“八卦起源占卜論”的考古材料以及學者們的相關認識,試對它們作些檢討和進一步的思考與分析,以求得對八卦起源問題特别是對有關考古材料與“占卜論”之間關係(即考古材料是否支持“占卜論”)的進一步明晰。由於相關論述較多,其結論又類同,而且主要來自於早期研究數位卦的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尤其是張政烺先生的認識,因此我們衹需選取一些關鍵環節和典型認識進行分析,如有疏漏、例外以及異議,歡迎補充、批評與指正。
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中,張政烺先生所統計的周初32例數位卦中共有168個數位,涉及一至八字,其出現次數分别為:一,36次;二,0次;三,0次;四,0次;五,11次;六,64次;七,33次;八,24次。其中以六、一兩字出現次數最多,分别為64次和36次,而二、三、四都是0次。他認為這是個必須注意的現象:“易以道陰陽,陰陽不成對還有什麽易理可講?”但是將所有奇數出現的次數加起來,其和為80(36+0+11+33);將所有偶數出現的次數加起來,其和為88(0+0+64+24):二者大體平衡。所以他認為二、三、四這三個數字雖未見,但實際上還是存在的,推測應是二、四併入六,三併入一所致。古人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古漢字的數字從一到四都是積横畫為之,一、二、三、亖自上而下書寫起來容易彼此混淆、極難區分,因此將二、三、四從字面上去掉,歸併到相鄰的偶數或奇數之中,“所以我們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現偏多,而六字尤占絶對多數的現象”。於是他推論:“占卦實際使用的是八個數位,而記録出來的衹有五個數字,説明當時觀象重視陰陽,那些具體數目並不重要。這是初步簡化,衹取消二、三、四,把它們分别嚮一和六集中,還没有陰爻(--)、陽爻(—)的符號。”[注]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後來在《帛書〈六十四卦〉跋》一文中,他更明確地得出結論:“在百十來個古筮考古資料中,一和六出現頻繁,一是奇數也是陽數,六是偶數也是陰數,使人很自然地感覺到一、六就是陽爻(—)、陰爻(--)的前身。”[注]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張先生這些分析是很細緻的,但關鍵問題就出在最後的結論上。在1980年的《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中,他並没有明確肯定陰陽爻畫來自數字卦的六(∧)、一兩數,而是就考古材料和張先生當時所見陰陽爻畫存在的年代(即在數字卦之前没有發現陰陽爻畫的八卦符號)就事論事,是符合實際的。四年後他在《帛書〈六十四卦〉跋》一文中的結論也是就事論事的敘述,但是它可能意味著張先生對“八卦符號源於數位卦的一、六”在認識上更加明確了。客觀地講,如果不做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嚴密的學理分析、論證,商周數位卦的存在是可以有兩種解釋的:一種是,它們可能是古人利用八卦進行占筮而得到的卦象(即早已有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就像自《周易》産生至今用八卦六十四卦進行占筮一樣,所謂“數字卦”即是用筮數記寫的卦象即占筮結果;另一種即張先生最終認可和持“八卦起源占卜論”者所主張的——數位卦的數位由於存在嚮一、六兩數歸併的現象,導致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的産生。為什麽張政烺先生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中更為謹慎,没有明確肯定八卦源於數字卦,而四年後這種傾嚮性認識卻更為明確了呢?筆者推測它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當時没有發現年代早於數字卦的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符號(如果有,也許張先生不會主張八卦符號源於數位卦的一、六);二是張先生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中提到,江蘇海安青墩出土有崧澤文化時期的八個六爻數字卦,其年代距今5500年左右——如果這一證據確鑿,那麽數字卦嚮爻畫卦演化就多了一點需要給出解釋的麻煩。不過據李零先生《中國方術考》説,承張先生相告,所謂崧澤文化數位卦是依據了錯誤的資訊,故放棄[注]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03頁。。早於商周數字卦兩三千年的崧澤文化數字卦是不存在的,這可能是張政烺先生在《帛書〈六十四卦〉跋》一文中更加傾嚮於“八卦源於數位卦”的原因之一。但是,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符號源於商周數位卦在學理上是講不通的。
張政烺先生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中指出:“易以道陰陽,陰陽不成對還有什麽易理可講?……説明當時觀象重視陰陽,那些具體數目並不重要。”[注]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這些論述的大前提是:數位卦中所有的數位都被區分為陰陽二性,是陰陽的象徵和代表,没有這個前提,便不會有數字卦釋讀的成功,亦即不會有“數字卦”的成立和存在。即那些“數字卦”不會被釋讀為數字卦,不會被認為是與八卦六十四卦相關的“卦”(或者更簡單一點説,張先生對商周數字卦的釋讀本身就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基本知識和原理去理解和認識“數位卦”的)。張先生對32例數位卦168個數位的統計、分析也證明這個思路和理解是正確的、合理的。所有數字被區分為陰陽二性的三爻數位卦、六爻數位卦(即張先生和學界所論商周數字卦)必然意味著陰陽爻畫的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且它們是先於數位卦的存在而存在;數字卦衹是用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進行占筮而得到的結果,即用數字記下的卦象。雖然,當時或現在我們還没有看到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符號在商、周時期的存在或普遍存在——實際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符號在商周之前是存在的,如新石器時代馬家窑文化、大河村文化均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出土[注]如青海柳灣出土Ⅱ3式46∶15彩陶盆外壁畫的是復卦,柳灣Ⅱ3 式214∶4彩陶盆外壁畫的是頤卦,柳灣Ⅱ1式760∶31侈口雙耳陶罐外壁畫的是臨卦,柳灣Ⅱ4 式902∶23彩陶盆外壁畫的是三爻離卦,青海柳灣所列馬廠類型彩陶單獨紋樣之487號是剥卦和復卦的組合(均見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又如甘肅海石灣下海石出土半山類型或馬廠類型雙耳彩陶罐外壁畫有三爻的坤卦、六爻的復卦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海石灣下海石半山、馬廠類型遺址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1期,封三彩圖3、4。前者在雙大耳罐的腹中部畫一道弦紋,下接雙綫倒三角紋作二方連續圖案分佈一周,上畫兩個三爻坤卦符號在雙耳之間對稱分佈(圖一);後者在雙大耳罐的腹中部偏下畫一道弦紋,下接雙綫半月形紋飾(考古學者一般稱為垂帳紋)作二方連續圖案分佈一周,上畫兩個六爻復卦符號在雙耳之間對稱分佈——為了將復卦的初九爻與其下的弦紋區分開,畫者特意將弦紋畫成弧綫形,使其中部遠遠地離開復卦的初九爻,以免二者混淆使人誤會(圖二)。坤卦象徵地、土,復卦寓意冬至過後“一陽來復”,為一年之始,這些象徵和寓意在當時可能已經存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仰紹文化第三期白衣彩陶缽上有一周三組六個六爻坤卦符號,而且其數量關係完全吻合古天文曆法之曆數(王先勝:《考古學家應嚴謹對待器物紋飾》,《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3期)。考古學者一直把它們稱為“綫段”或者“平行條紋”之類,而且往往忽視它們的條數、數量關係和實際面貌可能採用寫意的畫法,致使辨認和研究要非常認真細緻並且嚴格對照器物本身的刻畫纔行。,衹是由於考古學者大多不識或者没有引起注意和重視,而對易學有所研究的學者又都没有全面、深入、細緻地瞭解史前出土材料,更談不上研究,甚至也没有這方面的意識,導致整個學界還處於沉睡之中。簡言之,認為八卦符號源於數位卦,陰爻(--)、陽爻(—)來自商周數字卦的六(∧)、一兩個數字[注]徐錫臺:《〈周易〉探源》,《人文雜志》1992年第3期。,這完全是顛倒了二者的關係,倒果為因。如果没有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張政烺先生對32例數字卦168個數字的分析、理解又從何談起?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的數字卦不管出現多少個不同的數字,它們都是由三個數位或六個數位組成,即衹有三爻的八單卦符號與六爻的六十四卦重卦符號,而没有人們意想中的其他爻數的“卦”[注]目前見諸報導和釋讀的商周以來的數字卦在100例左右,其中僅有少數幾例卦符不是三爻或六爻。這幾個例外的四爻卦、五爻卦可能是因為器物殘損或者是因為銅器銹蝕而尚未完全“剔出”的原因所致,如《續殷文存》卷上第7頁載“八八六八”鼎文(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古器物上另有幾例非三爻、六爻的爻畫卦,即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一個五爻卦、《吴愙齋尺牘·吴清卿學使金文考·讀古陶文記》第七册所載的一個四爻卦以及傳世商周青銅器上用連綫“——”斷綫“---”組成的四個四爻或五爻卦,但據張政烺、馮時等先生研究,認為它們是六爻爻畫卦的一種簡省畫法,而且有内在的規律性(略當於後世易家所説的“互體”),簡省得很科學(張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94-398頁)。,證明它們全都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至於具體用到或出現哪些數字各有差别,衹是因為占筮方法不同而已。如李學勤先生的研究:“淳化陶罐、扶風和灃西卜骨筮數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現一,其次六、八,少見五、九,没有七,可暫稱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數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現六,其次七、八,少見一、五、九,可暫稱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區别甲、乙兩種揲蓍法的標志。”[注]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31頁。),其中六、一兩數特别多(或者再加上“八”),張政烺先生指出是為了避免書寫和認讀的誤會而將二、三、四按陰陽原理歸併到六、一之中(或將偶數歸併到“八”中,與歸併到“六”中意義是一樣的),這個認識非常正確;而年代更晚的上海博物館購藏戰國竹書、馬王堆漢墓帛書以及阜陽漢簡等上面的卦畫實際是陰陽爻畫八卦符號,而不能視為數位卦(陰爻作“∧”而不作“--”,顯然與陽爻“—”更容易區分,而不致因兩條斷綫連在一起或過於接近而讓人誤識為陽爻“—”)。所以,“由於商周數字卦歸併二、三、四到六、一,再由六(“∧”)、一變成陰爻、陽爻”這個發展程式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關於戰國中期楚國卜筮簡如天星觀簡、包山簡和新蔡簡上的筮卦,有的學者認為它們是用陰陽兩爻組成的卦象[注]同上,第277、283頁。,有的學者認為它們還是數字卦[注]宋華强:《楚簡數字卦的再討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06年8月23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06,2008年3月16日。,乃是因為對其中的筆畫認讀有分歧,而無論它們是數位卦還是爻畫卦,都不影響本文這裏的分析和認識。甚至無論將來發現年代多早、多晚,用哪些不同的數位記録的卦象,衹要它們都是規律性的衹有三個數位或六個數位組成一個卦象,而具體記寫中出現的數位歸併都是按照陰陽原理進行的,那麽,它們就一定是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占筮所得的便於計算、推算以及變卦的數字卦象之類。所以出於需要或者可以保留原樣,但將偶數、奇數組成的卦象换成通常的陰陽爻畫八卦符號更為簡潔和便於記憶;如果衹需要簡單的卦象寓意和記憶,就不必保留數位卦象而可以直接寫成陰陽爻畫卦,或者任意兩個偶數、奇數都可以代替和表示。
張亞初、劉雨先生在張政烺研究之後,也蒐集了36例商周數字卦材料(其中包含幾例用三條斷綫和一條連綫組成的四爻、五爻卦符,他們認為是與揚雄《太玄經》有關的資料,如有的可釋為《太玄經》的“争首”“鋭首”,同時也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卦畫”[圖三]。張政烺、馮時先生認為它們應是六爻卦符的簡省,略當後世易家所講的“互體”[注]張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94-398頁。),並説,“上述36條材料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數目字的組合,而且都是由三個或六個數位構成的組合。這不能不使我們與導源於數卜的我國古代占筮法——八卦聯繫起來。八卦的每個卦由三個爻(單卦)或六個爻(重卦)組成,每個爻也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至於當時“是否有卦畫,尚不得而知”[注]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位記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張亞初、劉雨兩位先生是直接認為或判斷八卦符號“導源於數卜”,並未作論證。而所謂“每個爻也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僅僅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占卜記寫占卦筮數時纔成立的,所以不能倒果為因用於論證八卦起源。關於“導源於數卜”,他們作注曰:“《左傳》僖公十五年:‘龜,象也;筮,數也。’説明龜卜,吉凶表現在龜甲裂紋所成的象上;用蓍草來筮,吉凶表現在蓍草成卦所得的數上。《考古》1976年第4期,汪寧生同志在《八卦起源》一文中,又從民族學的角度找到了數卜的例證。”這段話是否證明或説明八卦起源或“導源於數卜”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筮,數也”説的是八卦筮法,是根據占筮所得的卦象及據以畫出卦爻的筮數(分陰陽,並可以設計規則進行計算、推算,等等)來判斷吉凶,如《周易•繫辭》“大衍筮法”即如此,所以《左傳》這段話並不表示八卦“導源於數卜”,更談不上證明。汪寧生先生《八卦起源》一文中談到的有關數卜之民族學資料,有的與八卦無關,有些則與八卦相關:如西盟佤族“司帥報克”占卜法,“其法是用小木棒在地上隨便劃許多短綫條,然後計其總數,看是奇數還是偶數,奇數主凶,偶數主吉”,這種方法與八卦没有關係。汪寧生認為與古代筮法最相似的要算四川涼山彝族的“雷夫孜”占法。其方法是:“畢摩(彝族巫師)取細竹或草稈一束握於左手,右手隨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餘之數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個數字。有時亦可不用細竹或草稈,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上隨便劃上許多刻痕,再將木片分為三個相等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個數字。然後畢摩根據這三個數是奇是偶及其先後排列,判斷打冤家(過去彝族奴隸主操縱下的一種械鬥)、出行、婚喪等事。”汪先生以為數分二種而卜必三次,故有八種可能的排列和組合;用一畫代表奇數、二畫代表偶數,此即陽爻(—)、陰爻(--)的由來;把奇數和偶數八種可能的排列情況,分别用這兩種符號畫出來,這就是八卦的由來。汪先生據此認為八卦起源於數卜,其實也是倒果為因:無論細竹(草稈)法或小刀刻木法,得到的都是陰陽爻畫的八卦(如果記下三個數,則是數字卦;但“畢摩根據這三個數是奇是偶及其先後排列”,即按奇偶把三個數歸類,它就衹能是陰陽爻畫的八卦,衹是没有或不一定要畫出八卦符號),而非數位卦(如前所述,即使數字卦,其存在的前提也是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它講述和表明的衹是一個起卦方法和過程,即利用八卦符號進行占筮的過程,而不能證明八卦起源於數卜。正如“大衍筮法”一樣,它是對八卦(六十四卦)的利用,而不能説明八卦起源於“大衍筮法”。汪先生文中對四川阿壩地區藏族用牛毛繩八根打結、羌族數麥稈、雲南傈僳族數竹竿33根等占法語焉不詳,但以占卜三次而數分奇偶論,其法都應該是對八卦的利用,而不能説明或證明八卦的起源。這裏還有必要指出,汪先生 “八卦原不過是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所用的一種表數符號”的説法是錯誤的:“雷夫孜”等占法按操作程式一次得出或奇或偶之數,如用陽爻(—)或陰爻(--)表示,或可認為這時的陽爻、陰爻乃是“表數符號”,但操作三次所得之八卦符號(如用“奇奇奇”代表乾卦、“偶偶偶”代表坤卦等)卻不是“表數符號”,八卦並非數(雖然起卦過程中要用到數,並産生一些數)。汪先生文中也説到古人占筮時“感到八種卦象太少,於是將八卦相重衍變為六十四卦,揲蓍之法也愈演愈繁,要經過‘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意即六十四卦亦“導源於數卜”,這當然也是不足為訓的。崧澤文化數字卦不可靠,撇開不論。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出土的龍山時代陶壺上有一個三爻數字卦[注]蔡運章:《遠古刻畫符號與中國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這個結論我覺得也難以確定。但是排除陶寺這個不確定的數字卦,筆者發現馬家窑文化馬廠類型陶器刻畫中,有兩個並列在一起的確鑿無誤的六爻數字卦,均是一五六五五六巽卦(有一個也可能是一六六五五六蠱卦),而且在這兩個數字卦的下端還夾了兩個重疊的數字“六六”[注]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單獨紋樣第470號。,它們應該是在起卦過程中廢棄的卦爻(圖四)。按汪寧生先生的邏輯推測,至少陰陽爻畫的三爻八卦在馬廠類型中已産生(否則不必或不可能有六爻數位卦),而如前所述,馬家窑文化的確有不少三爻乃至六爻的爻畫卦,這自然也否定了“八卦符號起源於商周數位卦(數卜)”的説法。
樓宇烈先生作有《易卦爻象原始》一文,專門論證陰陽爻畫八卦符號與陰爻(--)、陽爻(—)起源於商周數字卦[注]樓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該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對其觀點做了論述:其一,樓先生依據張政烺先生《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説海安縣青墩遺址出土的數字卦“所使用的數目字有二、三、四”,説明“在易卦的發展過程中,最原始的形式是直接記録占筮時所得的筮數,從一到八,八個數目字都用”,而到商周時就“從字面上把二、三、四去掉,而用一、五、六、七、八這五個數目字”。這是嚮八卦符號轉變的第一個“簡易的步驟”。由於海安縣青墩遺址出土的是否是數字卦没有確定下來,因此樓先生的這第一步論證就失去了依托。其二,樓文仍然依據張先生上文《補記》所列湖北江陵天星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上的易卦,並依據張先生所説“二、三、四、五、七已被取消,集中到一、六兩項下。這裏的八、九似是再生的,九從一分化出,筆跡可辨,八或許是從六分化出來的。這便成為《周易》的前身,稍加修正即是《周易》了”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實際上張先生這個説法似是而非,它在易理和邏輯上是講不通的:數位卦中出現的數位衹是與占筮(起卦以及運算、推測吉凶)的方法有關,而與是否是三爻卦、六爻卦或者其他爻數的卦没有關係,比如用一到九、一到十或者其他的幾個數或者衹用可分陰陽(偶數、奇數各一)的兩個數,但它仍然是三個一組、六個一組,它們就仍然是而且衹能是三爻的單卦或者六爻的重卦(事實上,迄今為止,我們發現的所有數字卦都是這樣,包括史前數字卦),根本不存在易卦性質、結構、爻數上的改變或者演變,即用多少個數位、用哪些數位占筮都與八卦六十四卦的本源、起源没有關係。不同的人各自都可以設計自己與衆不同的占筮方法,從而可以得到各種不同的數位卦,確如張先生所説“那些具體數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是幾個數字組成一組,那些數字又是否按陰陽原理運用和存在。其三,樓文一方面説“從現有考古材料中,我們還没有發現僅用一、六兩個數位構成的卦畫”,一方面又説“但現存易卦爻象確是由一、六兩個數字演變而來,且其原始含義即是一、六,這也是無可懷疑的”,表明其牽强附會、强行“論證”的特點。樓文用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和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中的易卦符號來證明其觀點,也屬牽强附會。帛書《周易》陰爻近於“八”形,阜陽漢簡《周易》陰爻作“∧”形,二者均不作“--”形,當是“由於竹簡或者帛書上的行欄很窄”,為避免模糊混淆而“有所變通”[注]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327頁。,而不證明它們由商周數位卦的六(“∧”)演變而來。照樓文的邏輯,這三個符號“演變”的順序應該是:阜陽漢簡“∧”最早,帛書《周易》“八”其次,最後是“--”。但實際上阜陽漢簡《周易》晚於帛書《周易》三年[注]同上。,而且上海博物館所購藏楚簡易卦陰爻也作“八”形,其年代在戰國中期[注]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38頁。,遠早於阜陽漢簡“∧”,樓文的論證如何能够成立?更不用説史前時代已有陰(--)陽(—)爻畫的八卦符號。樓文又説“一、六兩個數雖已由具體筮數演變為筮數中一切奇偶數的代表,且進而抽象化為符號式的爻象,然而在易卦中它的數值稱呼並未消失”,以“直至今本《易經》卦畫中的‘--’還是以‘六’來稱呼它”證明 “爻象‘--’是由‘六’這個數目字演變而來的,它的原始意義就是筮數六,以後成為筮數中一切偶數的代表,因而它的名稱叫‘六’,是‘用六’”。 但是由數字卦的“一”演變而來的陽爻在《周易》中為什麽又不稱“一”“用一”,而要稱“九”“用九”呢?樓文衹得説:“由於史料的間缺,目前對這個問題確實很難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又發揮主觀想象説,“一和九作為數的始和終,從終始的相對意義(或終則復始的循環往復)上講,存在著變换其稱謂的可行性。筮人在筮法中充分運用數變的神妙,以使其筮占變化莫測,其中呼一為九可能就是這種强調和運用數變的結果”。這個想象的解釋當然不能説是論證,所以樓文自己也説“當然,這也衹是一種假設的解釋,稱一為九的原因,未必就由此而來”。其實,《周易》九、六問題衹是《周易》學裏面的一個常識問題:《周易》“大衍筮法”設計筮數用六、七、八、九,分别代表和象徵四象之老陰、少陽、少陰、老陽,其中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分别代表和象徵陰陽“兩儀、兩極”,也就是代表陰陽,所以《周易》八卦符號裏面的陰爻稱“六”、陽爻稱“九”,又有“用六”“用九”之説,所以《周易》占筮講六、九可變,七、八不變(六、九分别代表老陰、老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可變)。違背常識常理將其生搬硬套拿去證明陰爻來源於數字卦的六怎麽能够講得通順呢?樓文三個方面的論述没有一個方面是可靠的,所以其説“通過以上對考古文物資料的梳理,我們對於易卦爻象‘--’‘—’的原始意義及其演變的主要過程,基本上是清楚了”,實在言過其實。筆者還想指出,樓文的論述存在問題較多,違背易學常識常理以及想象、想當然的東西較多,當然該文自身也列出一串一串的問題不能回答,限於篇幅和主旨,這裏就不繼續分析和討論了。
徐錫臺先生在張政烺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説:早在原始社會崧澤文化中已出現數字卦,由一、二、三、四、五、六這六位元數字排列組合而成。這種數字卦經過千年的使用,進入商周時期人們省去積畫二、三、四這三個數字,增補了七、八、九這三個數字,即用一、五、六、七、八、九這六位奇偶數字排列組合成重卦;進入戰國中期又省去五、七等兩位元數字,衹剩下一、六、八、九四位元數字;至西漢文帝十五年又省去八、九兩數衹剩下一、六,如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竹簡上的易卦;至漢武帝時期,由於篆字改為楷字,故將“∧”垂直成陰爻符號,實際上陰陽符號仍是一、六兩位奇偶數[注]徐錫臺:《〈周易〉探源》,《人文雜志》1992年第3期。。上已言及,崧澤文化數字卦是没有明確和肯定的,這當然要影響到徐先生的論證。但是我們假設張政烺先生前文所介紹的崧澤文化數字卦是成立的,考察徐先生這裏的論述和認識,也有許多似是而非之處:其一,崧澤文化數字卦出現一、二、三、四、五、六這六位元數字是僅就張政烺先生列舉的兩個數字卦而言,並不能確定原始社會的數字卦就衹使用這六個數字,所以認為由原始社會使用一、二、三、四、五、六這六個數字發展到商周時期使用一、五、六、七、八、九這六個數字没有確定可靠的基礎和依據。其二,商周數字卦中出現一、五、六、七、八、九這六個數字並不意味著占筮時不使用或不出現二、三、四這三個數字。如前所述,這三個數字仍然是要出現和使用的,衹是因為這三個數字與一都是積横畫而為之,畫數字卦時上下重疊容易互相混淆發生混亂,故占筮後記筮數時將二、三、四分别歸併到六、一兩數之中。所以徐先生認為的原始社會占筮用一、二、三、四、五、六這六位元數字,發展至商周用一、五、六、七、八、九這六位元數字,至戰國中期僅用一、六、八、九這四個數,至西漢文帝僅用一、六兩個數字,這種占筮所用數位的發展演變順序是不成立的。其三,徐先生認為戰國中期數字卦省去五、七,僅用一、六、八、九四個數,依據的材料是湖北江陵天星觀楚墓竹簡。據張政烺先生統計、分析,天星觀楚墓竹簡上的易卦共有八組十六卦,所用數目字為:一,37次;六,49次;八,5次;九,4次;殘缺,1次[注]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由此可知,天星觀楚墓竹簡易卦其占筮過程中並非衹用一、六、八、九這四個數,而仍然應該如其他商周數位卦一樣,也使用了二、三、四、五、七等數位,衹是在畫數位卦時將後者按奇偶分别歸併入一、六兩個數字而已。故徐先生擬構的占筮用數從原始社會至商周至戰國中期的發展演變順序是不成立的。其四,張政烺先生提到四川理番縣出土的雙耳陶罐上有兩個易卦,一個秦代的為一八七一八九(離下,離上,離),一個漢代的為一六十(艮)[注]同上。。這條資料同樣不支援徐錫臺先生擬構的占筮所用數位發展演變順序,徐先生文中引理番縣雙耳陶罐易卦資料(且錯為“九八七一八九”)以證其占筮數位發展演變順序[注]徐錫臺:《〈周易〉探源》,《人文雜志》1992年第3期。,當然也是不足為訓的。總而言之,無論商周數字卦或是湖北江陵天星觀楚墓竹簡上的數位卦,其産生和存在的前提必然是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那些數字衹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進行占筮而産生,而非八卦之源。當然,崧澤文化中的數字卦(假使張政烺先生論文介紹的資料是成立的)與四川理番縣出土的數字卦也不例外——前文已指出,易卦中使用或出現不同的數字應該與占筮方法及對數字的歸併方法有關。而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上僅用一、六(∧)兩數字的易卦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一樣,它們實際是陰陽爻畫卦的另一種寫法,而非數位卦,更不是來源於數位卦的一、六。
徐錫臺先生認為商周時期人們以一、五、六、七、八、九這六位奇偶數排列組合成二百一十六個單卦,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個重卦,二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六爻,而六十四卦是在秦漢時纔出現,在商周時期是不存在的[注]同上。。這個認識是否正確呢?我們認為它是不正確的:其一,商周數字卦出現一、五、六、七、八、九這六個數字,並不意味著占筮時衹出現和使用了這六個數字,而是一至九這九個數字都有出現和使用,衹是在畫卦時將二、三、四這三個數字歸併入六、一兩數之中。這個事實證明,商周數字卦所反映的占筮方法是將其中的數字按照陰陽歸類後呈現的卦象(即八卦、六十四卦卦象)來判斷吉凶的,而不是按照可以出現的兩百多三爻數位卦、幾萬個重卦數字卦、二十多萬個數字爻象來判斷吉凶的(如前所述,保留原始數字也可能與用三爻、六爻的三個數、六個數進行計算、推算以幫助判斷吉凶有關),否則就不能也不應該對二、三、四這些數字按陰陽進行歸併。進一步而言,衹要歸併現象存在,商周數字卦就一定是按陰陽兩個因素(可以用任何兩個不同的符號代替)排列組合成的三爻八卦、六爻重卦來判斷吉凶的。其二,按徐先生的邏輯,商周數位卦應是由一至九這九個數字排列組合而成,當遠不止二百一十六個單卦、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個重卦以及二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六爻。同理,距今約5500年的原始社會崧澤文化中也當如此,因為其數字卦據公開的兩條資料已出現一、二、三、四、五、六計六個數位,而且還可能使用了其他數位(崧澤文化數位卦不成立,但還有馬家窑文化數位卦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史前考古學文化中的數位卦)。同理,《周易》“大衍筮法”筮數用六、七、八、九,其判斷依據也應該是這四個數排列組合成的43即64個單卦、46即4096個重卦以及24396個數位爻象。我們都知道,“大衍筮法”不是這樣一回事,更不意味著《周易》有4096個重卦而不是六十四個重卦(按照徐先生的邏輯推理,六十四卦在《周易》中也還没有産生,還需要繼續“演化”)。可見按筮法用數、數位卦中出現的數位來推斷八卦的産生和演化是荒謬的。其三,根據《周易》“大衍筮法”可以對商周數位卦做一些合理的推測:“大衍筮法”用六、七、八、九四個數,占筮得到的六爻卦其六個筮數之和最小為36(六爻皆為六)、最大為54(六爻皆為九),求爻象是用天地數55去減,前者相減得差19,據六爻卦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反復數到19得“上六”爻;後者相減得1,據六爻卦自下而上數到1得“初九”爻,它們就是占筮所得用於判斷吉凶的爻象。如果按照同樣的方法去看商周數字卦,筮數為一至九,得出的六爻卦其六個筮數之和最小為6(六爻皆為一)、最大為54(六爻皆為九),按同樣方法求爻象也是很簡單的事。而且,即使是史前數字卦,可能也是用同樣或類似的求卦求爻方法。總之,商周數字卦用了一至九9個數位,根本不意味著它應該或可能存在以及使用了數萬個重卦、數十萬個爻象(因為存在按陰陽歸併筮數現象,所以這種連“可能”都没有),所以徐先生所論完全是没有理據的。其四,如上一段所述,徐先生所論占筮用數從崧澤文化至漢代的發展“演變”順序是不成立、不存在的,它們不支持也無法支持徐先生所論商周時期有四萬多個重卦、二十多萬卦爻到秦漢纔有六十四卦這個歷程。其五,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及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上的易卦僅用一、六兩數(實際是兩個符號)排列組合成六爻卦,實際即陰陽爻畫的重卦六十四卦,與商周數字卦、天星觀楚墓竹簡數字卦、馬家窑文化(或者崧澤文化)數字卦等有著根本區别:前者是陰陽爻畫卦的另一種寫法(用其他任何兩個不同的符號或者數位分别代表陰、陽爻,排列組合成六十四卦,其卦爻象、含義完全不變),後者是利用六十四卦占筮所得卦象及爻象。兩者完全没有什麽“演化”關係,連邊都沾不上,根本不能用於證明和支持“今本《周易》絶不是商周時期的作品,而是秦漢時代纔出現的”。
李零先生在《跳出〈周易〉看〈周易〉》[注]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一文中列舉了自數字卦研究興起以來學者關於八卦符號與數位卦關係的兩種認識。他不同意金景芳和李學勤先生主張的“八卦起源與數字卦無關”,而堅持傾嚮於張政烺先生和多數學者主張的“《周易》卦爻來源於商周數字卦”的觀點。其理由有三:“因為第一,至今我們還没有發現任何早於古本《周易》(戰國一種,西漢兩種)而與今本卦爻相似的材料;第二,與這些古本年代相近的簡本《歸藏》,其陽爻作‘—’,陰爻作‘六’或‘八’,形式也非常相似;第三,這樣理解也便於和早期的‘數字卦’相互銜接。”李零先生説的古本《周易》是指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易卦和阜陽漢簡及馬王堆漢墓帛書上的易卦,它們都是用“八”(或者“∧”)表示陰爻、用“一”表示陽爻,所以“《周易》的卦爻從戰國到西漢一脈相承”。前面已經指出,學界至今“没有發現”與商周數字卦年代一致或者年代更早的陰陽爻畫八卦符號,並不等於它們是不存在的,不等於“没有”。所謂“没有發現”衹是與學者們的視野和研究範圍、程度有關,與部分考古學者不懂、不關心、不重視有關,與易學界不熟悉和瞭解史前考古材料、罕有人全面深入瞭解和研究史前刻畫圖案、紋飾有關。這個問題類似於數字卦研究在張政烺先生以前的情形,没有發現和認出“數字卦”不等於它們是不存在的。所以李零先生的第一個理由不能成其為一個理由。李零先生説的“《歸藏》”是指湖北江陵王家臺出土的秦簡易卦,學界公認它們屬於陰陽爻畫的六十四卦系統,其抄寫年代大約在戰國晚期,所以李零先生説它們“與這些古本年代相近……形式也非常相似”,不能讓他改變“《周易》卦爻來源於商周數位卦”的流行認識。其第二個理由與第一個理由大體上是一回事,第一個理由不能成其為理由,第二個理由當然也不能成其為一個理由。李零先生的第三個理由“這樣理解也便於和早期的‘數字卦’相互銜接”就更不是一個“理由”了,所謂“銜接”衹是時間上的“銜接”而不是也没有什麽其他 “銜接”,上面已作分析。王家臺秦簡《歸藏》,其陽爻作“—”,陰爻作“六”(即“∧”)或“八”,但它們不是數字卦,正説明“陰陽爻畫”八卦六十四卦不是一定要用斷綫“--”、連綫“—”的方式纔可表達,任意兩個可以區分或象徵陰陽二性的符號、數位(“∧”“八”形近,又都是偶數,故混用一點不影響卦爻的性質、意義;雖然“一”“六”或“八”都表示數,但是在王家臺秦簡《歸藏》中不是作為需要計算數量關係的數來使用的,故其衹象徵或代表陰陽)都可借用,當然它們也佐證了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易卦和阜陽漢簡及馬王堆漢墓帛書上的易卦即陰陽爻畫卦是正確的,相反後者不能視為數字卦。
由於1993年後又發現一些新的商周數字卦,其中有“十”這個數字,李零先生在前文中便稱商周數字卦為“十位元數字卦”,而且這種“十位元數位卦”在戰國時期仍在使用(見於楚簡),所以他説“就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而言,我們認為,最好還是按直觀特徵把它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十位元數位卦’(是否可以稱“易”還有待證明),一類是‘兩位元數字卦’(“三易”)”,而“兩位元數字卦”《連山》《歸藏》《周易》(指王家臺秦簡《歸藏》、上博楚簡、阜陽漢簡、馬王堆帛書等易卦)“當然有可能是從‘十位元數字卦’簡化而來”。他還認為“我們不能簡單説在‘十位元數字卦’中,一與五、七、九無别,六、八也是一樣(否則何必還要不憚其煩地把這麽多的數位全部都寫出來呢)。況且,按通常理解的‘大衍之數’,我們也不可能得到‘十位元數字卦’”。李先生這些理解和認識存在一些混亂、誤解和似是而非的地方,也有理解不够深入透徹之處:其一,所謂“十位元數字卦”是什麽?還不是三爻卦、六爻卦(李先生據以論述的安陽殷墟出土卜骨《小屯南地甲骨》4352上的數字卦“十五六”和岐山鳳雛甲組宫殿基址出土卜甲H11∶235上的數字卦“六六十”都是三爻數字卦),衹是筮數中有一個“十”而已,並非十個數字組成一個卦。一般可以把三爻、六爻的數位卦稱為三位元、六位元數字卦,李先生“十位元數字卦”的説法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它們是十個數位組成的一個卦即十爻卦,可見“十位元數位卦”一説不妥、不通、不對。其二,衹要是三爻數位卦、六爻數位卦而且數分陰陽,它們就一定是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的筮數卦象,對此前文已經闡明不再贅述;數位卦中出現“十”衹是與占斷方法(即起卦以及判斷吉凶的方法)有關,如同數字卦中出現“八”或“九”一樣,其中的學理前文已經闡明亦不再贅述。其三,王家臺秦簡《歸藏》、上博楚簡、阜陽漢簡、馬王堆帛書等易卦屬於《連山》《歸藏》《周易》系統(李零先生也承認這點),即陰陽爻畫的六十四卦系統,其中的一、六或八不是用來供筮人計算以推斷吉凶的,而是陰陽爻畫的另一種畫法(六或八即陰爻,前面已經述及),所以把它們稱為“兩位元數字卦”真是冤哉枉也。其四,《周易》“大衍筮法”用六、七、八、九四個數,我們起卦占斷得到的三爻卦、六爻卦旁邊都要寫上這些數(以便計算求爻象、推斷吉凶以及變卦等)——如果對六十四卦卦象很熟悉,就不需要畫出陰陽爻那種卦畫,而衹要按規則寫出六爻的數位就行(比如商周數字卦就應該是這樣),按李零先生的説法它們即“四位元數位卦”。照李先生以及其他“八卦起源於數位卦”論者的邏輯,不是八卦六十四卦符號現在都還没有産生、《周易》一書這兩三千年都不該存在了嗎?其五,“大衍筮法”衹是古代筮法中的一種,我們没有必要要求古人都用這一種筮法,没必要要求商周數位卦都按照“大衍筮法”産生(前面已經談到商周數位卦中已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筮法,雖然具體怎麽操作我們還無從知曉)。要得出卦爻數位在一至十之間的數位卦衹是一個技術和程式設計問題(張政烺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中設計了一種得到筮數在一至八之間的六爻數位卦的方法),數位卦中有“十”並不構成八卦六十四卦在商周或者史前時期存在的障礙。比如將一把蓍草或竹棍(可固定為64根或100根等)隨意取出若干根不用,然後揲之以九或揲之以十記録餘數(餘數為十便不再繼續揲蓍,而作為筮數記録),重複六次便得到筮數在一至九或一至十之間的六爻數字卦。所以李零先生大可不必為古人擔憂。其六,無論商周數字卦還是戰國楚簡數字卦,在畫卦時按陰陽、偶奇作了歸併是事實,李零先生也承認這一點。為什麽没有完全歸併為六、一或其他兩個奇偶數組成的易卦,我覺得那正是因為它們是“數字卦”的原因,否則它們就不是數位卦,不能叫數位卦,而應該是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衹是用兩個不同的數位代替了陰陽爻畫之斷綫、連綫而已)。按理,既已將二、三、四嚮一、六(或八)作了歸併,那這些數字就不是用於計算的,如李零先生説的那樣“何必還要不憚其煩地把這麽多的數位全部都寫出來呢”?我覺得數字卦可能是這樣産生的:所有筮數都是有用的(比如用於計算和推求爻象),占筮活動結束之後刻寫數字卦時為避免某些混淆,纔將二、三、四按陰陽作了歸併,而筮人(一般都是專業工作者)對卦象又非常熟悉,他們不需要畫出陰陽爻畫的八卦符號,而衹需或者習慣於記下各爻的筮數即可(甚至也可能是一種行規),於是得到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卦的樣子。
張亞初、劉雨先生已注意到商周數字卦雖然出現一、五、六、七、八五個數,其中奇數有三個,“但在每一個卦中,最多衹同時出現其中的兩個數,也就是説,嚴格地遵循著兩奇兩偶(也就是後世所説的兩陰兩陽規律)”[注]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位記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管燮初先生分析了42例商周數字卦,發現每卦均為六爻,一個卦的爻文至多四種没有例外,因而認為數字卦爻不僅分陰陽,而且還分老陰、老陽、少陰、少陽[注]管燮初:《數字易卦探討兩則》,《考古》1991年第2期。。張政烺先生曾經釋讀西周中方鼎上兩個左右並列刻在一起的六爻數字卦“七八六六六六”(剥卦)與“八七六六六六”(比卦),依據《左傳》《國語》之例可稱為“遇剥之比”或者“遇比之剥”,二者的關係屬於卦變[注]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易辨》,《中國哲學》第14輯。轉引自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16頁。。200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長安縣黄良鄉西仁村西周遺址採集到陶拍4件,其中有兩件上面都有成組的數字卦:一件(CHX採集:1)左右並列兩個六爻數字卦“六一六一六一”(既濟)與“一六一六一六”(未濟),按《周易》卦例二者也屬卦變關係,一個是本卦一個是之卦(圖五);另一件陶拍(CHX採集:2)上刻著四個數字卦“八八六八一八”(師)、“八一六六六六”(比)、“一一六一一一”(小畜)、“一一一六一一”(履)(圖六)[注]曹瑋:《陶拍上的數位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李學勤先生説:“從易學的觀點來講,這樣的發現應當説是驚人的……兩件陶拍上的筮數,轉化為《周易》的卦,全然與傳世《周易》卦序相合。師、比、小畜、履四卦是《周易》第七、八、九、十卦;既濟、未濟二卦,是《周易》第六十三、六十四卦。這樣的順序排列,很難説出於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師、比、小畜、履四卦在上經十八卦中自成一組。師與比互覆,為五陰一陽之卦,小畜、履互覆,為五陽一陰之卦。既濟、未濟也是互覆,為三陽三陰之卦,在下經十八卦末自成一組。”他推斷CHX採集:2上的“筮數‘八八六八一八’師卦是實占結果,其餘則是依《周易》續配,因為實占如此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可以看出當時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變’錯綜關係的概念”[注]李尚信:《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36-237頁。。據于茀先生研究,包山楚簡中有6組數位卦,把每組數位卦轉换成相對應的周易卦,則每組數字卦由本卦和之卦組成,以本卦、之卦特别是互卦卦爻辭的占斷結果與包山楚簡相對應的占辭相比較,基本相合,説明包山楚簡中的數字卦應當是周易卦,而且已包含互卦的觀念[注]于茀:《包山楚簡中的數位卦》,《北方論叢》2005年第2期。。這些材料和研究證明,迄今發現的所有數字卦無疑都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的卦象筮數,而絶不是陰陽爻畫的八卦六十四卦還没有産生。如果説前面我們主要是從學理、易理上分析八卦六十四卦不是來自和起源於數字卦並輔以史前數字卦、爻畫卦材料來佐證的話,那麽這些材料、現象和研究正是數字卦乃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卦象筮數的内證。而且這些材料和研究還證明,商周、春秋戰國時期筮人占筮以及畫卦都習慣於僅僅畫出筮數卦象(如前所述,也可能是行規、職業、專業導致的習慣和傳統),而不需要畫出陰陽爻畫卦(迄今為止我們没有發現例外),這也應該是迄今我們没有看到和發現同時期陰陽爻畫卦的主要原因。而且商周數字卦現象還説明,先秦時期(甚至史前)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利用、筮占的相關知識已經非常成熟,筮人對它們非常熟悉。由於我們至今没有發現商周時期用斷綫(--)連綫(—)這種我們熟悉和視為正統的陰陽爻畫的八卦符號,又對史前考古材料尤其是紋飾瞭解、研究不够,導致一個本來比較簡潔、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變得異常複雜、困難,出現了不少不合邏輯、學理、易理的研究、猜測。
自張政烺先生破譯和研究商周數位卦以來,“八卦起源於占卜”的認識在學界得到了强化。“八卦起源占卜論”長期流行於中國學界,但大多數人都不想一想,也不問一問:為什麽衹有三爻、六爻的數字卦,而没有四爻、五爻、七爻、八爻的數字卦?為什麽八卦符號衹有8個三爻卦、64個六爻卦,而没有邵雍和朱熹所推測的那種16個四爻卦、32個五爻卦以及128個七爻卦等等?數字卦又如何推演出“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這種《周易》宇宙生成觀?八卦的根本乃是由陰陽二性的三數或六陣列成的八個三爻卦和六十四個六爻卦,這是確定不移的。任何“數卜論”要在方法與結果上與八卦、六十四卦建立起聯繫都衹能靠人為設定,而無法從學理上、邏輯的必然性上進行推導或證明。就數卜的本質而論,它産生的“卦”可以是兩爻卦、三爻卦、四爻卦、五爻卦、六爻卦、七爻卦、八爻卦、九爻卦、十爻卦甚至更多,而且其方法和程式亦可多種多樣,古人如何為那些幾萬、幾十萬乃至更多的卦、爻設定具體的占卜範圍、吉凶内容?這種設定又有什麽必要?“占卜論”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原始人類很愚昧,没有理性和抽象思維能力,没有明晰的數的概念與認識,不可能有繁複的數學知識,他們對世界和事物的認識是朦朧的、混沌的、没有理性的,這樣的人類如何能够以及為什麽要把世界萬事萬物細分成幾十萬乃至更多的類别,又用幾十萬乃至更多的卦爻象去對應它們?如果不能,數字卦就不是什麽“數卜”,而是八卦六十四卦占卜之卦象筮數(或筮數卦象);如果能,其前提便失真失據,“八卦起源占卜論”也無法立足。又,古人如何以及為什麽從那些可能多達數十萬數百萬的兩爻卦、三爻卦、四爻卦、五爻卦、六爻卦、七爻卦、八爻卦、九爻卦、十爻卦甚至更多爻數的占卜數位組合中選定三爻卦、六爻卦(而不是其他爻數的卦),用於占卜以及表達他們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萬象的認識與理解?他們依憑的是什麽?如果能回答出這個問題,那也就等於説八卦六十四卦在“數字卦”之前便早已産生了。
除了數字卦問題,還有不少學者推測和認為占筮源於龜卜、八卦起源於龜卜,這裏也需要分析一下。
鄭萬耕先生説:“據近人研究,占筮源於龜卜。《周易》卦畫自下而上與後來成為通例的甲骨刻辭的順序相一致,而六段爻辭與卜句契辭六句之數尤合。《周易》中斷定吉凶的辭句同甲骨卜辭相比,許多字也是相同的 ……這説明,《周易》六爻成卦和其中的占辭是脱胎於或模仿卜辭的。”[注]鄭萬耕:《易學源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年,第8頁。究竟八卦怎樣從龜卜發展而來,這段話語焉不詳。朱淵青先生認為龜卜序數與筮數有著密切的聯繫,如《周易•繫辭》占法説“挂一以象三”,《屯乙》三二八七、三四七五兩甲所刻序數左右都是一至七,而“一”為左右兩組共用,《老子》又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卜甲序數左右共用“一”有“一以統始”之意,故“挂一”不用,來自龜卜數。再如《周易·繫辭》説“分而為二以象兩”,合於龜甲卜辭左右對貞,數、兆、辭相隨,數的刻記、貞辭語法均習慣左右相對、一正一反。又如易數以五為生數、十為成數,而龜甲序數由一至十而止,卜用多龜至“五”而止,“五”為本數加倍而為十,故序數至十止。又引孔穎達《左傳正義·僖公四年》“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為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為短”,認為“龜卜兆象的序數由一至十,而卜用多龜則至五而止。一二三四五是為本數,易筮以七八九六為數,故稱末數。末數引申本數而來”[注]朱淵清:《周易探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29頁。。這些聯繫即使成立,也未能説明龜卜序數怎樣變成了數字卦,而且為什麽又不能是龜卜序數、兆辭的刻記方法模擬和演繹了陰陽八卦的原理、觀念呢?如前所述,距今四千多年的馬家窑文化數字卦中已有一、五、六等筮數,它們又怎麽可能自商周龜卜序數一二三四五“引申”而來呢?所以朱先生説的“當記録兆象的序數的數理邏輯被應用起來時,符號化的筮數便逐漸替代了形象化的卜兆,於是商人便開始通過數去解釋、預卜自然萬象;當商人發明筮數時,他們就開始尋求各種演繹數的方法,最終八卦六十四卦出現了”[注]朱淵清:《周易探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30頁。不僅與考古材料不合(如馬家窑文化中數字卦、筮數),而且也是用一種抽象的、含混的、含義不能確指的説法代替了論證。有些論著推測“最古老、最簡單的數卜,應是用兩個相同的能够標明正、反兩面的物體,拋擲落下後看其正、反面的數目,拋擲的結果可能兩正或兩反,或一正一反。如果把兩正定為吉兆,那麽兩反就是凶兆,一正一反是中間狀態”,而且“這個時期卜的最好用具是蛤殼”,但“隨著人類社會活動範圍的增大,這種簡單的占卜,不能適應越來越複雜化了的社會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決定重大問題時,人們不想草率從事,必然要進行多次‘卜’,卜具也自然會從衹有表示兩個數目的物體,發展成為數量較多的物體,把卜的結果用數位記録下來,就産生了‘數字卜’——筮。組成卦的數位,已經不再表示物體的數量,而是某種趨嚮的象徵”[注]郭志成、李郅高、劉英傑:《中國術數概觀·卜筮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第108-109頁。。這裏仍然是用假設、含義不明確的説法在卜與筮(數字卦)之間建立了虚假的聯繫:用蛤殼或其他物體拋擲看其正、反面,實際得到的是“象”而不是“數”,如一反一正、兩反兩正、三反三正,衹能各自規定為“陰”“陽”,而不能都記數為一、二、三。商周數字卦中一至十這十個數都有,“卜具”應該有十個而且必須規定每卜衹記正面或反面數,這樣卜六次纔能得到商周那種數字卦。但商周數字卦衹有三位元、六位卦而且存在按奇偶、陰陽對二、三、四進行歸併,故此種“卜”法如存在實即求卦法,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而不證明八卦六十四卦源於數卜。
屈萬里先生認為《易》卦因襲龜卜,他對二者作了多方面的比較:“(一)卦畫上下和順序合甲骨刻辭的順序;(二)《易》卦反對的順序合甲骨的左右對貞;(三)《易》卦爻位的陽奇陰偶合甲骨刻辭的相間為文;(四)《易》卦九六之數合龜紋,那些意境雷同的情形,都不會是偶合。”所謂“九六之數合龜紋”是指:由於龜殼是雙層的,外為盾板,裏為骨殼即龜甲,盾板由一條中綫(千里路)一分為二,再由五條横綫分為相疊的六排,而腹甲被紋路割為左右四排,上部中央又有一小塊“内腹甲”,屈萬里先生認為腹甲有中,其數為九,盾板無中,其數為六,有中是陽,無中是陰[注]屈萬里:《易卦源於龜卜考》,黄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屈萬里先生的研究除九六之數與龜殼紋路的比附較為牽强外,頗有道理,但亦未能説明八卦符號及陰陽爻畫怎樣據龜卜産生,也與商周數位卦無涉。李大用先生又據五塊西周甲骨論證八卦起源於龜卜,認為甲骨灼後基本上有“--”、“—”兩種形式,甲骨卜兆多以三條裂紋為一組即一事三卜,於是有八種可能即八卦之産生,在殷人“卜用三骨”“習卜”的基礎上,周人通過“卜用三兆”“重卜三兆”而得到八卦、六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注]李大用:《周易新探·後記》,北京:學苑出版社,1990年,第25頁。。雖然李先生指明了八卦符號陰陽爻來自於龜卜裂紋,但僅據五塊西周甲骨論證八卦起源,顯然並無説服力。事實上甲骨兆紋是没有規律的。《史記·龜策列傳》説:“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有學者分析認為:“兆之所以為兆,就因為它變化無窮。殷代的甲骨卜和歐洲的肝臟卜在形式上相距甚遠,而有一點卻是非常相近的,那就是甲骨卜的裂紋和肝臟上的經絡有相同之處:它們都是無規則的,就像一座森林,仿佛到處都是路,又仿佛一團亂麻,一條路都没有。而神意就隱藏在這種有路和無路之間。這種特殊的紋路本身並不是神意,但它能把你引嚮神意,神意就從那裏被引申出來。”[注]朱狄:《信仰時代的文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53頁。總之,雖然不少學者都在説占筮或八卦起源於龜卜,但迄今未能説明八卦符號和占筮與龜卜之間的内在、必然聯繫,而衹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關於甲骨刻辭與陰陽八卦象數的吻合之處,筆者認為應是前者模擬後者,而不是後者源於前者,因為遠在商周之前的史前時代已有六位元數字卦、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如前所述,馬家窑文化馬廠類型那兩個並列在一起的六位元數位卦下端還夾了兩個重疊的數位“六六”,它們很可能佐證史前時代畫卦也是自下而上。故商周甲骨刻辭自下而上的順序應該是模仿和類比了八卦符號的畫法。不僅如此,由於卜筮並用至少在殷代武丁、康丁時代就“有案可查”了,占筮所得之數字卦與占卜所得之兆紋、筮辭與卜辭見於同一甲骨也不奇怪,甚至卜辭中還“應該區分出一部分卦辭”來[注]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位記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曹定雲:《新發現的殷周“易卦”及其意義》,《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1期。。
1984—1987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一批墓葬龜甲,其年代為距今9000—7800年。在清理出的349座墓葬中,有23座高規格墓葬出土了龜甲,其中14座隨葬成組的完整龜甲,每組個數不等但均為偶數,或二或四或六或八,1座隨葬一個完整龜甲,其餘隨葬龜甲碎片[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下册,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978頁。。大部分完整龜甲和部分龜甲碎片中均伴有數量不等的小石子或水晶子,多者八龜殼中共有173顆,最少者為3顆,而且有些墓葬龜甲石子有黑白或顔色深淺之分。負責賈湖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張居中與宋會群先生合作研究,認為賈湖出土這些龜甲和“龜腹石子”與數卜和八卦起源有關,並對其卜法、筮法作了一些推測[注]宋會群、張居中:《龜象與數卜——從賈湖遺址的“龜腹石子”論象數思維的源流》,劉大鈞主編:《大易集述》,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下面我們對其研究作一些分析。
張、宋兩先生推測的第一種占卜法為“奇偶占斷法”,即“把裝有若干石子的龜甲握於手中,反復摇動,利用晃動之力,振出若干石子,然後查驗振出石子(或留於龜殼内的石子)數目,據其奇偶數目以斷吉凶”。這種方法與數位卦無關,若衹進行一次得不出八卦,若重複進行三次、六次可得陰陽爻畫之八卦六十四卦,但它衹是對八卦六十四卦的利用而非起源。張、宋所舉民族學資料即流行於臺灣的“文王龜卜法”(用三枚銅錢置於龜殼,重複進行六次振動,排出六爻卦)也是對六十四卦的利用,而與起源問題無涉。张、宋兩先生推測的第二種占卜法為“陰陽筮卦法”:把若干黑白石子混合置於龜腹,利用龜靈祈禱,摇動龜甲振出若干石子,按次序排列位置,先數奇偶再看黑白(陰陽),據奇偶和黑白之“象”定吉凶。此法同“奇偶占斷法”一樣,也與數字卦無關,若求三爻八卦、四爻十六卦、六爻六十四卦仍然意味著它是以八卦、十六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而與起源無涉。张、宋兩先生推測的第三種占卜法為“奇偶排卦法”:利用一龜(内裝石子)多次振動操作或多龜同時振動操作可得一組奇偶數以斷吉凶。這種方法也與數字卦無涉,因為一墓八龜殼石子可達173顆,僅白色石子即有138顆,平均每個龜甲在17顆以上,僅用白色石子振出石子(或留存於龜甲内石子)數目範圍也在1—17顆之間,與我們所知數字卦無關,衹能求得陰陽符號表示的卦。由於到賈湖三期時,一墓四、六、八龜的現象完全消失,代之以一龜和二龜,而年代更晚的下王崗、青蓮崗、大汶口文化時期,基本上是一墓一龜,少部分一墓兩龜,兩龜以上者極少見,所以他們認為“賈湖早、中期的奇偶排卦法尚處於摸索階段,較少的吉凶斷詞數目和較多的得卦數目具有明顯的矛盾,人們還無法把握4—8個奇偶全排列所帶來的數百種卦的結果”,因此墓葬占卜用龜嚮一龜、兩龜的方嚮發展,這就是八卦、六十四卦的來源。我們認為,這個推測仍然是不成立的:其一,它與我們所知的數字卦無涉。其二,它不可能是徐錫臺先生所論筮數不分奇偶、陰陽的“數字卦”,因為一墓八龜各占一次可能得到的卦爻將遠比六位奇偶數排列組合得到的四萬多個重卦、二十多萬爻多得多。其三,即使占卜結果按奇偶、陰陽成卦,二爻(兩龜)四卦、四爻(四龜)十六卦、六爻(六龜)六十四卦、八爻(八龜)二百五十六卦也是無據,因為迄今我們所知秦漢以前的易卦衹有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而無其他品類。其四,要得到四爻十六卦、六爻六十四卦、八爻二百五十六卦均可衹用一龜(分别占卜四次、六次、八次)、二龜(分别占卜兩次、三次、四次)而不必一墓葬四、六、八龜。其五,若説八龜得八爻二百五十六卦數目太多没有必要或“無法把握”,那麽賈湖人自始至終都不必要一墓葬六龜乃至八龜,即葬八龜的現象本就不該出現和存在。其六,由葬二、四、六、八龜嚮葬一、二龜方嚮發展是化繁為簡,至商周數字卦時代由三爻八卦嚮六爻六十四卦發展是因為“不敷日用”由簡趨繁,二者同為“八卦起源卜筮論”,出發點和理論、觀念相同但推論互相矛盾,證明“八卦起源於數卜(卜筮)”這個前提不可靠。其七,按張、宋兩先生推論,八卦六十四卦在賈湖三期及後來的下王崗、青蓮崗、大汶口等文化中應已産生、定型,這與八卦六十四卦據商周數字卦而來也是互相矛盾的,也證明“八卦起源於數卜(卜筮)”這個前提不可靠。總之,賈湖龜腹石子及史前墓葬龜甲這些現象和葬俗不説明也不證明八卦起源於數卜、龜卜。
按筆者的理解,賈湖遺址葬二、四、六、八龜的習俗應是對陰陽八卦的崇拜所致,用偶數(成對)龜以象陰陽,最多止於八數是對八的崇拜,而對八數的崇拜當源於四時八節、四方八位,亦即八卦(按陳久金先生研究,八卦起源於曆法即八節[注]陳久金:《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説》,《自然科學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年第4期。,而在中國古代文化和古人的思想觀念中,四時八節與四方八位又是相對應的,如商代四方風名所藴含的意義[注]連劭名:《商代的四方風名與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其緣由當與古人的天文觀測、天象觀測有關,而且八卦統一時空這種傳統觀念至今依然影響深遠)。即依據易學的象數觀念和思想,賈湖的葬俗本身即意味著八卦早已産生,它是對陰陽八卦的一種形象演繹,就像當代彝族等少數民族仍用八角形圖案表示八卦一樣。八卦在賈湖時代已經産生尚無更直接的考古證據,但據筆者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器物紋飾的分析、研究,至少在仰韶時代(前5000—前3000年),中國古人已用圖形和數量關係將八卦六十四卦、十月太陽曆、河圖洛書的數關係非常熟練、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注]王先勝:《考古學家應嚴謹對待器物紋飾》,《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3期;王先勝:《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器内涵探討——兼及古代紋飾的釋讀及其方法問題》,楊伯達、郭大順、雷廣臻主編:《古玉今韻——2007朝陽牛河梁紅山玉文化國際論壇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至於葬一龜、二龜,應是用它們象徵和表達太極、陰陽之義。葬二、四、六、八龜嚮葬一、二龜方嚮的發展,並不意味著占卜或筮卦的由繁至簡,而衹是對太極、陰陽、八卦崇拜的不同表達方式所致(如果用龜腹石子占卜,一龜、二龜均可求得八卦六十四卦)。當然,在賈湖文化中,葬二、四、六、八龜的區别可能也有身份、地位之别。另外,賈湖遺址第一次發掘發現M16葬龜殼碎片三堆(為四個個體)、M17葬龜殼七堆(為六個個體),且二者均置於墓主脛骨上[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遺址的試掘》,《華夏考古》198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册,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57頁。,筆者認為它們與仰紹文化濮陽西水坡45號墓脛骨與蚌殼組成的北斗[注]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應有相近的含義,即脛骨是立竿測影的象徵,三堆龜殼可能象徵心宿三星或參宿三星,七堆龜殼則象徵北斗七星(四個個體刻意破碎作三堆、六個個體刻意破碎作七堆處置,可以視為内證)。所有這些理解從易學的角度去看,從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思維的角度去看,都是順理成章、極其妥帖的。
考古學家在論證八卦起源於商周數字卦或數卜、龜卜、筮占時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認識和表述,易學界的專家在涉及這個問題時也同樣如此。如:余敦康先生認為八卦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占卜,説“龜卜、筮占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占卜形式,都是這個時期的産物。由於筮占的特點是根據蓍草排列所顯示的數與形的變化來預測吉凶,所以與其他的占卜形式相比,具有一種潛在的優越性,可以通過無數次的排列,逐漸把數與形的變化推演成一個整齊有序而又穩定規範的符號體系”。“拿《易經》來與原始的筮占相比,最顯著的差别就是《易經》除了那套並無高深意義的抽象的卦爻符號以外,又增加了一套由卦辭和爻辭所組成的文字表意系統,其卦爻符號是繼承了原始的筮占而來的……”[注]余敦康:《易學今昔》,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第3頁。按我們平常所説以及一般意義上的理解,“筮占”就是指用蓍草或竹棍等起卦、排卦,如《周易》“大衍筮法”、彝族“雷夫孜”占法等,都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而像汪寧生先生所舉西盟佤族“司帥報克”占法,僅據一次性所得的奇偶數斷吉凶,則與八卦無關。余敦康先生所説“根據蓍草排列所顯示的數與形的變化來預測吉凶”僅是一種猜想,而且對於它怎樣與數字卦、與陰陽爻畫的八卦符號發生聯繫,並没有給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説法和模式;接下來“逐漸把數與形的變化推演成一個整齊有序而又穩定規範的符號體系”同樣是一種猜想,而且也没有給出一個“推演”模式,没有具體説明“穩定規範的符號體系”(八卦六十四卦)是怎樣從蓍草的“數與形的變化”中得來的。這樣的猜想怎麽就證明卦爻符號“是繼承了原始的筮占而來”而且“並無高深意義”呢?又如,周山先生認為,在三個或六個一組的數字卦時期,尚没有卦名,即便有,也不可能與後來的八卦或六十四卦卦名相同,因為三個數字能組成103個卦,六個數字能組成106個卦,因此作為爻畫卦的八卦、六十四卦衹能在數字卦之後,即“八卦、六十四卦衹是到了僅有陰陽二種符號的時候,纔能應運而生”[注]周山:《周易文化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10頁。。這裏也存在著錯誤和似是而非的認識:三個數字如組成三爻卦有27(33)卦,其重卦應有729(36)卦,六個數字如組成三爻卦有216(63)卦,其重卦應有46656(66)個,如前述徐錫臺先生所理解的,而非103或106個。但商周數字卦和馬家窑文化中的數字卦等並非這種數不分奇偶的“數字卦”,相反它們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的,前已述及。因為徐錫臺先生所論數不分奇偶的“數字卦”是不存在的,也與考古材料不合,所以認為八卦六十四卦來自於那種數不分奇偶的“數字卦”衹是一種空想。周先生“作為爻畫卦的八卦、六十四卦衹能在數字卦之後”既無學理支持,也與迄今所見數字卦無涉。易學界更普遍的現象則是直接援引和接受了考古界的認識,如潘雨廷先生所言“約至東周起,正在由‘數位卦’逐步發展成為今日所用的‘陰陽符號卦’”[注]潘雨廷:《周易表解》自序,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以及本文開始所引陳詠明、朱伯崑先生所述,不必贅言。
總結:“八卦起源於占卜(或稱數卜、龜卜、卜筮)”是一種無根無據的觀念和認識,既没有學理支援,更没有考古證據。八卦並非由數字卦發展而來,更非源於龜卜、數卜。數字卦的存在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為前提,它們衹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進行占筮而得到的一種結果,而商周龜甲及史前墓葬龜甲也都與數位卦的産生無關,更與八卦六十四卦的産生無關。本文列舉了史前數字卦、爻畫卦材料,前者也衹能是利用後者占筮而得到的卦象、筮數,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以及爻畫的起源,需要另行研究,已非本文主旨,無須贅言。
後記:本文有些部分(如與徐錫臺先生的論述相關者)是以崧澤文化數字卦的存在為前提,若崧澤文化數字卦是不存在的,不影響本文的分析和結論。


圖一 下海石三爻坤卦陶罐

圖二 下海石六爻復卦陶罐

圖三 商周異形卦爻符號

圖四 馬家窑文化數字卦

圖五 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CHX採集:1)

圖六 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CHX採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