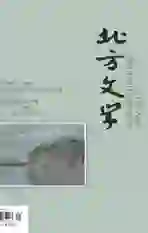陕军东征,殊途同归——浅论《白鹿原》与《废都》
2016-11-10刘岩
刘岩
摘要:《白鹿原》与《废都》是当代文坛两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是“陕军东征”的两部代表作。陈忠实与贾平凹两位陕西籍作家面对着同样的历史转型背景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重启,但基于不同的文化根底他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陈忠实秉承以“关学”为中心的关中文化,而贾平凹则受南北交融的楚汉文化影响颇深。二者的不同选择充分地体现在这两部作品中,也体现在作品引人注目的性描写中。然而,他们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知识分子在剧变的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
关键词:《白鹿原》;《废都》;比较;文化;性描写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长篇创作收获颇丰,而1993年绝对是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长篇创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更是给中国当代文坛砸下了两记重锤,它们的出版在京城引起了强烈反响。两位陕西籍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扬鞭起程,并与同时期其他陕西作家(高建群、程海、京夫)一起谱写了“陕军东征”[1]的神话。
一、陕军“东征”前的秦地社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经济影响文学的表现之一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2],“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3]。正是由于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转变,由此影响了知识分子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明显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4]。作家作为社会变化的敏感群体,更是率先感受到了物质与精神的不平等,物质方面极大丰富,但精神层面却有所缺失,他们试图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作家面临怎样的选择?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陕西作家的范围。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陕西”作家并非严格的地理意义上的隶属于陕西这个行政省份的作家,更切合实际的表达应当是“秦地”作家。秦地按照地理学的角度划分为三个部分: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地,我们常说的“三秦”即由此而来。秦地历史悠久且深处内陆,传统文化蕴含深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逼近,秦地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旧有的文化系统濒临解体,传统以一种破碎的形式散落在三秦各地。秦地曾经谱写过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近现代以来核心地位的丧失使得秦地人民封闭保守,也使秦地作家充满了忧患意识,他们拿起笔,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传统进行了反思:或是从传统反观现代,或是从现代思考传统。然而不论哪一种反思,都离不开秦地的传统和历史,作家们在悠久的秦地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把不完整的、破碎了的秦地记忆重新拼接成一幅幅鲜活的“陕军东征”图。
二、作家身份的一致性
“陕军”作家在身份上的共同性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地理上的一致。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他们的群体特征体现为“对文学事业执着如一”,“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十分关注农民的命运”[5]。以陈忠实为例,他创作《白鹿原》之前,亲自到蓝田县认真翻阅了《蓝田县志》等历史资料,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并做了大量文学艺术上的准备,十年磨一剑才有了《白鹿原》这部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的成功。正是秦地历史悠久的原因,使得秦地作家的作品多多少少都带上了历史感,发达的史学、作品中援引的历史素材、以秦地史实来组织故事创作人物等等,作品中的“史”似乎无处不在。自柳青的《创业史》起,陕西作家浓重的史诗意识就展现在为陕西农村谱写的一幅幅史诗画卷中。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再者,农民也是陕西籍作家的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思考农民的命运、关注农民的发展,这似乎成了陕西作家默认的任务。即使是在《废都》这样一部描写城市及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农民的影子依然充斥其间,甚至主人公作家庄之蝶骨子里都脱不出农民的身影,乡村描写已然淡出,但作家的灵魂却安妥在乡村之中。
然而作家身份的一致性更直观的体现是在作品中,尤其是秦地独特方言的运用和秦地民歌秦腔的出现。
方言土语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地域特征的鲜明标志。在陕西作家的作品中,秦地方言土语的出现频率极高。下面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尻(kāo)子”,指的是臀部,即屁股,关中土语也称作“沟子”。这个词一般见于陕西籍作家描写农村的作品中,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多见。如《白鹿原》中写到白嘉轩“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
“骚情”,意思是热情过分、讨好献媚,也有调情之意。如《白鹿原》中的鹿子霖这一辈子听尽了谄媚讨好的话,最后他对小长工说:“从今往后不准你尽给我说骚情话!”又如《废都》中庄之蝶在刘嫂家里对唐宛儿说调戏之语,反被唐宛儿搪塞:“这里可别骚情,人家把你当伟人看的!”“骚”字一般认为含有贬义,但在陕西籍作家的作品中该词的出现并非惹嫌之意,而带上了一种亲近人之间的调笑逗乐之感,比如夏捷总说唐宛儿是个“小骚精”,事实上这表现的是两人之间的亲昵。
“麻达(搭)”,意指麻烦、问题。如在《白鹿原》中,鹿子霖想把冷先生和白嘉轩结成亲家,对白嘉轩说:“我向冷大哥自荐想从中撮合,八字也都掐了,没麻达”。正如“中”之于河南方言,“麻达”是关中方言最具代表性的词汇之一。
除此之外,秦地民歌——秦腔也是地域特征的重要表现。
秦腔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传统戏剧剧种之一,以关中方言语音为基础,关中称“秦”,因此而得名。秦腔作为一种地域戏曲文化,经作家之手进入作品,成为新的文学元素。在《白鹿原》中,秦腔是作为一种文化氛围出现的。搭戏台子唱大戏,这是关中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小说中的重大事件如田福贤惩治“农协”分子等也都与戏、戏台子分不开。秦腔是老百姓喜爱的东西,更是关中文化的代表。“白孝文也是个戏迷。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秦腔戏的崇拜者和爱好者。”在《白鹿原》中作者直接明白地用一句话道出了秦腔对于老百姓的重要性,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一族之长,无论你是富家子弟或是贫家儿女,在秦腔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崇拜者和爱好者”。在《废都》中则多次出现了不同人物开口唱秦腔的场景,如柳月唱的陕北民歌《拉手手》“你拉了我的手,我就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山圪崂里走。”唐宛儿唱的陕南花鼓“口唇皮皮想你哩,头发稍稍想你哩,眼睛仁仁想你哩,实实难对人说哩。”拉手、亲口、想念这些表达情爱的奔放大胆的词就这样被秦地人民大大方方地唱出来,由此可见秦腔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带着泥土气息的,它来自民间、长在民间,它的唱词甚至有些难登大雅之堂,即俗话常说的秦腔“不雅”。但读读这些唱词就可以感受到秦地人民表达情与爱的勇敢热烈,以及他们骨子里的个性、自由和随性。
三、两位“东征”作家基于不同文化的不同选择
即使是同样的时代背景,相似的地域身份特征,不同的作家仍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给秦地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破碎的文化传统如何复活成了作家们思考的问题。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位“东征”作家基于不同的文化根底的影响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陈忠实说“关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封建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形态落后、心理背负的历史沉积最沉重的地方,人很守旧,新思想很难传播”[6]。陈忠实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关中人,他的身体里深深流淌着关中文化的血液,重礼贵教、质朴务实的文化核心对他造成了深远影响。《白鹿原》中处乱不乱的白嘉轩、行为世范的朱先生、学为好人的鹿兆谦,他们虽是不同身份、不同阶级的人,但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了关中文化的深沉厚重,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在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背景下,关中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在陕西,农民运动如“风搅雪”般轰轰烈烈的展开,一些民间家族祠堂被拆除,新思想大量涌入并与旧有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白鹿原》就是对于关中儒教文化遭遇现代化之后该如何发展的深沉思考。
陕西作家在前辈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后起的陕西文坛另一座高峰路遥也是现实主义的高手,陈忠实等作家也遵循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使得陕西文坛成了当代文坛现实主义的重镇。但贾平凹是个例外,他接受了南北融合的楚汉文化,作品自然也带上了独特的南国风味。不同于陈忠实写“史”的做法,贾平凹写的是一种“心迹”,他将《废都》写成了“自我倾诉的心灵史”[7]。他似乎超脱出普通大众的思维,站在现实生活之上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此表达对现代文化的忧虑。从商洛市到西安市,贾平凹从乡走到城,但他并未真正在城中落脚,而是在城与乡之间徘徊,乡在他的心中是美好的、不可放弃的,然而乡终究敌不过现代都市文明的侵扰。城,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腐化堕落的温床。西京城里四大名人的惨局似乎成了“废都”最有力的说明,是城市使得人类种族退化。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的“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显得更为突出”[8],他不得不在“废都”中生活,他看到的是人性的丑恶,从而带着挽歌般的心境怀念自己记忆中的故乡,思考满目疮痍的当下。
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引人注目的性描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私人化写作还未成大气候,因此这两部小说大胆的性描写给人当头一棒,它们有着冲破禁忌的先锋性。由于不同的地理因素,两位作家接受的文化也不同,比较起来,两部小说的性描写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白鹿原》中除了写到主人公白嘉轩的性生活之外,也描写了其他很多人物的性活动,但这些描写都显得含蓄而文艺,作者让你看到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性交场面,不论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性性行为,还是两情相悦的性生活,都经过了作者的一层遮盖,读者只能隐约看个大概,却看不到真容。如小说中写白孝文和田小娥第一次“行”了的画面:“一次又一次走向欢愉的峰巅,一次又一次从峰巅跌下舒悦的谷底,随之又酝酿着再一次登峰造极……”。作者用省略号告诉读者更多没有写出的文字。陈忠实遵循的性描写原则是“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不把性描写作为吊某些读者胃口的诱饵”[9],这使得他的性描写带上了庄严感和严峻性。在这部作品中,性成为了透视人性和人物心理的神秘深邃的窗口,作者“将性和诱惑之间的界限予以了正确的把握”[10],突出的是“身体”解放,在爱和性之上所要揭露的是封建文化封建道德,是关中人物的心理结构,是儒家文化被“性”破坏之后的发展,是灵与肉的冲突。《白鹿原》通过多对男女不同的爱情、不同的性生活多角度地展示了关中百姓的情爱意识中性、爱与道德的冲突,以此警示面对被破坏了的儒家文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让其继续发展。
《废都》则与《白鹿原》截然相反,它的性描写直白而暴露,是一种“自然化的、裸露式”[11]的写法,且集中于主人公庄之蝶一人身上,写他与妻子牛月清、情人唐宛儿、保姆柳月、陌生女子阿灿的性活动,以及与景雪荫、汪希眠之妻的感情纠葛(也有少量性描写)。书中出现的所有女子,甚至包括只有一面之缘的妓女,她们都为庄之蝶神魂颠倒,但在读完小说之后读者似乎并不能感受到庄之蝶身上散发出的强大魅力,显然这些都是作者的一手安排,可以认为是男性(尤其是知识分子)自大的想象,正如学者黄平所说庄之蝶惊人的魅力“正是基于‘作家或‘名人的文化想象”,“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想象,成为‘性的支点与动力”[12]。作家试图将男性“无所不能”的魅力注入知识分子体内,将男性自大的想象通过文化、知识这一途径进行现代转化,并将其作为男性魅力的来源,让那些与庄之蝶并不同类的非知识分子女性因此而沉迷,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奉献。当庄之蝶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成了“西京市的庄之蝶”,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之时,他便拥有了名声、荣誉、金钱,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着不切实际的虚荣感,他利用女性对名人的盲目崇拜与她们发生肉体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精神交流,有的只是肉体上的媾和。读完整部小说,“堕落”两个字似乎最符合心境,实际上也就是“废都”之“废”。这种宣泄式的性爱笔者更倾向于称其为“情欲描写”而非“性描写”,它更偏向于人的原始的自然属性。
四、结语
一只白鹿,一道原,一位族长。
一头老牛,一座都,一个作家。
面对同样的经济、文化环境,陈忠实用以关学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体系谱写了一曲白鹿原的赞歌,贾平凹则以南北融合的楚汉文化为根底高唱了一曲废都的挽歌。
陈忠实思考的是被“性”所破坏了的儒家文化该如何发展,面对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又该做出何种回应。他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历史演变结合起来,将儒学与现代文化语境进行对接,展示了儒学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当代命运,从而提出了传承与舍弃的问题。传统文化是一代又一代的前辈留给我们的,其中既有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财富,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污浊,因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最合适的态度。面对无法整体保留的传统文化,我们要传承其精粹并为之找到新的生长点,白鹿原上的朱先生所代表的以安、静、定为特征的关中文化正是如今跳、动、快的社会所缺乏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儒家文化的复兴自有其必要性,这也正是《白鹿原》的现实意义所在。
贾平凹则以反常态的思维站在另一个角度上思考“人类文明病对人类的危害”,并以此“烛照出文明对人性的蚕食”[13]。就连一头有灵性的牛都鄙夷生活在城市中的这群人,作家用一种近乎病态的灵感去写废都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目的是为了让城市人在废都中苏醒,因此他把废都写得越“废”,就越能唤起人们的“醒”,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污浊了的现代化的强有力回应。小说放肆大胆的性描写也确有其意义所在,作者采用这样一种饱受非议的方法来表现其对人性的揭示和叩问,却正符合他在小说扉页所写的“心灵真实”。他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唤起人们重振文化的信念,并为此而行动。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了作家和读者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起着腐蚀般的作用。“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下保持和发扬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传统”[14]。不同的文化根底、不同的描述表达,“殊途”的两位“东征”作家在历史转型的相同背景下用作品“同归”,回答了同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面对如此环境该怎样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这不只是经历了现代化冲击的曾经封闭自守的陕西作家面对的问题,也是生活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我们每一个面对传统的现代人无法忽略的问题。面对汹涌而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如何立足、如何发展、如何与经济并存共生,文学又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在现代生活中充当精神先锋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完成文学自身对这个社会所负有的上层建筑的责任,当代知识分子应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的热忱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用自己的笔、用厚重的文字来做出自己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陕军东征”是20世纪90年代震动文坛的一个文学现象。所指作品主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和程海的《热爱命运》.
[2][3][14]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21-325.
[4][13]刘宁.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以柳青、陈忠实、贾平凹为中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第1版):42,238.
[5]参见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商务印书馆,2013(第二章):113.见田中阳.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1).
[6]陈忠实.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路[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64.
[7]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58.
[8]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J].文学评论,2014(3):116.
[9]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4.
[10]黄均.<废都>与<白鹿原>中的“性描写”比较[J].剑南文学,2013(9):79.
[11]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M].华夏出版社,2000:118.
[12]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