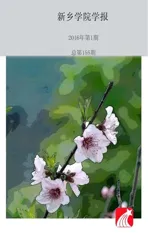《瓦尔登湖》中的《圣经》典故汉译述评
2016-05-24肖胜文马烨文
肖胜文,马烨文
(1.九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2.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瓦尔登湖》中的《圣经》典故汉译述评
肖胜文1,马烨文2
(1.九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2.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文章从不同年代选取4个具有代表性的《瓦尔登湖》汉译本,按照“隐性意义是否可以推断”的标准,从隐性信息明晰度和翻译方法两个方面对《瓦尔登湖》中《圣经》典故的翻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如下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译本准确率不断提高,注释数不断增加,直译法不断减少,加注补义法不断增多。文章还分析了形成这些趋势的原因。
关键词:瓦尔登湖;《圣经》典故;汉译
一
美国著名作家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至少有66处引用到《圣经》内容,还有至少4个人名跟《圣经》中的人名相同。这些引用的内容有的跟《圣经》有关,有的跟《圣经》无关,译者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误解,并误导译本读者。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圣经》内容很不熟悉,而梭罗对《圣经》内容烂熟于心,在《瓦尔登湖》中信手拈来,或明引,或暗引,或反引,融会贯通,浑然天成,毫无牵强之迹,这就对《瓦尔登湖》汉译者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先,译者要知道文中哪些地方用到《圣经》典故,并对作者用典意图非常清楚;其次,译者要采取各种技巧向译文读者准确传达作者用典意图又不失译文的流畅和严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瓦尔登湖》中的《圣经》典故翻译质量的高低反映了该译本的质量。
关于典故翻译方法,许宏[1]、朱耀先[2]、胡泽刚[3]、曹明伦[4]等均提出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可归纳为直译法、加注补义法、增译达意法、代换法和意译法等几种。
《瓦尔登湖》汉译本很多,仅就大陆而言,据杨爱华[5]统计,“1949—1990年期间译者只有徐迟一人”,“1991—2000年……出现了4位新的译者,他们是刘绯、许崇信、林本椿与袁文玲”,“2001—2010年……译本有26种,译者多达28人”。201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青年翻译家李继宏的译本。笔者按照年代不同选取4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汉译本,即1982年版徐迟译本(以下简称徐译)[6]、1996年版许崇信与林本椿译本(以下简称许译)[7]、2007年版潘庆舲译本(以下简称潘译)[8]、2013年版李继宏译本(以下简称李译)[9],以“译文隐性信息是否可推”为标准,对其《圣经》典故的翻译从信息明晰度和翻译技巧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希望从中找出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给《瓦尔登湖》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正确的解读,减少误导,并在名著重译方面给译者提供一些借鉴。
二
受篇幅所限,本文只是从《瓦尔登湖》第一章前20处《圣经》典故翻译中选取了几条进行比较分析,以求窥斑见豹。标“*”部分是译文中译者所做的注释。
【典故6】I have looked after the wild stock of the town, which give a faithful herdsman a good deal of trouble by leaping fences; and I have had an eye to the unfrequented nooks and corners of the farm; though I did not always know whether Jonas or Solomon worked in a particular field to-day; that was none of my business.[10]14
【徐译】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使忠于职守的牧人要跳过篱笆,遇到过许多的困难;我对于人迹罕至的田庄的角隅也特别注意;却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因为这已不是我份内的事了[7]16。
【许译】我也曾照料过镇上的野兽,这些野兽总是要越过篱笆,给忠实的牧人带来一大堆麻烦;我还得照料农庄各个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尽管我并不总知道约拿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是否在某一块田地上劳动,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7]14。
【潘译】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窜过围栅逃逸,让一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是跟我毫不相干的事。
*为《圣经》中的人物[8]18。
【李译】我曾看管镇上的野兽,它们经常跨越篱笆,给尽忠职守的牧人造成许多麻烦;我查看农场里人们不经常走到的边缘和角落;不过我并不知道今天的约拿和所罗门到底在哪块田地干活;这完全不关我的事。
*泛指农夫[9]13。
【点评】Jonas和Solomon的确是《圣经》中的人物,但普通美国人也喜欢用《圣经》人物名字给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取名。这里的Jonas和Solomon都泛指一般的农夫,其中Jonas作为普通人名一般翻译成“乔纳斯”,作为《圣经》人物翻译成“约拿”。因为所罗门作为以色列国王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如不加注,徐译和许译容易造成误导。潘译的注释已经造成误导。李译加注很好。
【典故15】
After all, the man whose horse trots a mile in a minute does not carry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he is not an evangelist, nor does he come round eating locusts and wild honey.[10]26
【徐译】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6]28。
【许译】总之,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着最重要的信息;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蜜的。
*《圣经》说施洗者约翰在荒野中修行,以蝗虫和蜂蜜为食。——编注[7]41
【潘译】反正骑着马儿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来最最重要的消息;他可不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他跑来跑去也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蜜。
*此处指基督教《四福音书》作者之一约翰。《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3~4节说:约翰在旷野里传道,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8]56。
【李译】总而言之,如果有人骑着马,每分钟跑一英里,那他携带的消息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他既不是传播福音的人,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蜜的。
*洗礼者约翰的食物。《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10]36
【点评】“吃蝗虫和野蜜”用来形容约翰传福音的辛苦。该典故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也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
只有徐译没有加注,其他三个译文都加了注。但是除潘译外,其他三个译文都把作者用典的意图传达错了。He is not an evangelist, nor does he come round eating locusts and wild honey的意思是“他既不是来传福音的,也不是吃着蝗虫和野蜜来的”,梭罗想借此批评那些利用现代化工具传递信息的人既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重要消息,自己也没有吃什么苦。
【典故16】
The pantaloons which I now wear were woven in a farmer’s family,——thank Heaven there is so much virtue still in man; for I think the fall from the farmer to the operative as great and memorable as that from the man to the farmer;——and in a new country, fuel is an encumbrance.[10]54
【徐译】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谢谢天,人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哩;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其伟大和值得纪念,正如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而新到一个乡村去,燃料可是一个大拖累[6]58。
【许译】我现在所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做成的——谢谢老天爷,在人的身上还保存着如此多的美德;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农夫降为一个技工,正如从一个人降为一个农夫那样重大而值得纪念;而在一个新的乡村里,燃料简直是一种累赘[7]51。
【潘译】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人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身上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美德呢;因为我觉得,农人一下子降为技工,就像人降为农人,两者同样伟大,令人难忘。新来乍到乡间,燃料是一件够你伤脑筋的事[8]69。
【李译】我现在穿的裤子是某个农夫家里织的——谢天谢地,人身上还是有许多美德的,因为我觉得农夫堕落为工匠,其落差之大和引人注目的程度,并不亚于人被贬为农夫——而燃料在初来乍到的乡村地区倒是个大麻烦。
*指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圣经·旧约·创世纪》:“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9]44
【点评】李译加注,且正确理解作者用典意图。许译没有加注,隐性信息不明晰。徐译和潘译都没有加注,且错误理解作者用典意图。梭罗认为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从人降为农夫,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一种堕落,如果再从农夫降为工匠,脱离了尘土,脱离了自然,就更是一种堕落,所以这里的great决不能翻译成“伟大”。
【典故19、20】
The Jesuits were quite balked by those indians who, being burned at the stake, suggested new modes of torture to their tormentors. Being superior to physical suffering, it sometimes chanced that they were superior to any consolation which the missionaries could offer; and the law to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fell with less persuasiveness on the ears of those who, for their part, did not care how they were done by, who loved their enemies after a new fashion, and came very near freely forgiving them all they did.[10]63
【徐译】那些耶稣会会士也给印第安人难倒了,印第安人在被绑住活活烧死的时候提出新奇的方式来虐待他们的施刑者。他们是超越了肉体的痛苦的,有时就不免证明他们更超越了传教士所能献奉的灵魂的慰藉;你应该奉行的规则是杀害他们时少噜苏一点,少在这些人的耳朵上絮聒,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如何被害,他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仇敌,几乎已经宽赦了他们所犯的一切罪行[6]68。
【许译】耶稣会会友也让印第安人弄得不知所措,当印第安人被捆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时候,却向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推荐新的折磨方法。既然不为肉体的痛苦屈服,他们有时可能也就不需要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安慰;待人如待己的原则,在那些不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的人听来,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敌人,已经近乎原谅对方所做的一切[7]59。
【潘译】耶稣会会士已被印第安人所挫败,这些印第安人在被绑住活活烧死之际,竟向行刑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折磨方式。他们虽然肉体受苦但并不屈服,有时候他们对传教士所给予的安慰也无动于衷。你们应该奉行的法则是,行刑时在他们耳边少说规劝之类的话,至于他们如何被折磨至死,倒是他们自己都并不在乎。不知怎的,他们反而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他们的仇敌,对后者所做的一切罪恶几乎全给宽赦了[8]81。
【李译】耶稣会的传教士遇到印第安人就束手无策,因为有些印第安人在身受火刑的时候,竟然还建议行刑者采用各种其他处罚方式。他们既然对肉体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传教士所提供的安慰自然也就毫无用处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在那些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们的人听来,是没什么说服力的;这些人以新的方式去爱他们的敌人,几乎毫不怨恨地原谅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当下耶稣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9]51
【点评】李译加注指出典源所在,翻译非常准确,不仅译出显性意义,从对上下文的翻译看,译者对典故的隐性意义也完全理解。
徐译、许译和潘译都没有注释,这两个典故字面意思很好翻译,但隐形意义是否译出就必须从上下文中推断。
徐译中把suggested new modes of torture to their tormentors翻译成“提出新的方式虐待他们的施刑者”是把作者原义完全理解反了。把with less persuasiveness on the ears翻译成“少噜苏一点,少在这些人的耳朵上絮聒”也是与“原谅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一致。从这些上下文的翻译可以看出,徐译对这两个典故的隐性意义根本没有理解。
许译基本上理解了这两个典故的隐性意义,只是把came very near freely翻译成“已经近乎”似乎没有注意到freely的含义,此处应该是“毫无怨恨地、心甘情愿地”的意思。
潘译将with less persuasiveness on the ears翻译成“行刑前在他们耳边少说规劝之类的话”,把came very near freely forgiving them all they did翻译成“对后者所做的一切罪恶几乎全给宽赦了”,说明译者并未完全理解这两个典故的隐性意义。
谢洛夫正是这样一位处于世纪之交的画家,他才华横溢且富有创新精神,在艺术上承前启后,力求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是研究俄国艺术史无法回避的一位关键人物。谢洛夫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他借鉴西欧画风进行个人情感表达的实践,为俄国传统肖像画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风。其次,他的肖像画开创了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和社会属性的新方向,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谢洛夫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俄国艺术在各种流派、思潮的交汇融合中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为俄国绘画艺术走向现代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三
下面我们对4种翻译版本中这20处典故的翻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从表1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如下趋势:
第一,后译版本注释数不断增加。
第二,后译版本准确率不断提高。
第三,从整体趋势上来看错误率是降低的,但针对具体译者情况可能不同。
第四,后译版本采用加注补义法越来越多,直译法越来越少,增译达意法和意译法偶有运用,代换法无人使用。

表1 对4种翻译版本中《瓦尔登湖》典故翻译情况的统计
注:李继宏译文有一处(带*者)既用了增译达意法,又加了注释,因此同时使用了两种翻译方法。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趋势的原因。
第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原文的理解越来越深,对原作者的了解越来越多,后译者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注释数不断增加、准确率不断提高是必然趋势。
第二,随着科技进步,通信手段和检索手段日益发达,遇到不懂的地方,译者请教、查询越来越方便,这也是译文准确率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译者可以越来越方便地实地考察作者当年生活的地方,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这些都可以加深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从而提高译本的准确率。
至于翻译方法的使用,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圣经》典故的翻译,民族色彩太浓,使用替换法容易造成混乱,故无人使用。本次统计数据再次证明,在翻译典故时,加注补义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笔者认为,随着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中美之间共享信息越来越多,加注补义法会逐渐减少,而意译法或直译法会逐渐增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无需阅读注释就能明白某个典故背后隐含的意义。
前面讲的是总体趋势,但落实到每个具体译者身上,影响因素就非常多,如中英文水平、翻译态度等,都会影响译本的质量。
Levine在谈论《尤利西斯》时说:“理想的读者必须异常熟悉西方文学传统。”[1]这话同样适用于《瓦尔登湖》。理想的译者首先是理想的读者。笔者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完美的《瓦尔登湖》汉译本。
参考文献:
[1]许宏.典故翻译的注释原则:以《尤利西斯》的典故注释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78-83.
[2]朱耀先.汉英成语典故翻译方法刍议[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97-99.
[3]胡泽刚.谈谈典故的翻译[J].中国翻译,1988(5):24-33.
[4]曹明伦.谈谈译文的注释[J].中国翻译,2005(1):88-89.
[5]陈爱华.时间的玫瑰:国内《瓦尔登湖》翻译出版情况研究[J].中国出版,2011(8):57-60.
[6]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7]梭罗.梭罗集:上[M].塞尔,编;陈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8]梭罗.瓦尔登湖[M].潘庆舲,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9]梭罗.瓦尔登湖[M].李继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10]THOREAU H D. 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edited and Annotated by Sun Shengzho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3.
【责任编辑郭庆林】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1-0036-04
作者简介:肖胜文(1971—),男,湖北孝感人,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二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YY01)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