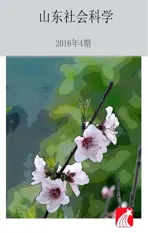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性思考
2016-04-04林美卿苏百义
林美卿 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性思考
林美卿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生态平衡为标准,规范人的思想、行为、情感等因素,遏制“假”、“恶”、“丑”,张扬“真”、“善”、“美”的人性凝练、形成过程。生态文明与人性密不可分,人性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超越人性“善”与“恶”的片面性,在思想、制度、情感三位一体的人性维度上协同共建,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实效。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文明;生成论;人性
目前,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剧的考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月18日第1版。是谁造成的?源头在哪里?生态文明是什么?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怎样建设?为什么这样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人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从人性的角度审视生态文明建设也许是解决生态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生态文明与人性的价值关系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生态文明早已渗透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中,并且成为当前人类诉求的文明新形式。从形式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从内容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形成的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发挥人的感性、知性、悟性能力创造出人化自然的和谐世界,这是一个为人性“立法”并不断彰显、磨练、生成人性的过程。何谓人性?人性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性问题源于人对自我意识的反思和确认。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生态文明与人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关联。“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到人性中。”
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人性生成的条件。生态文明以及其它任何文明成果都会内化为人的认知并在一定的境遇中成为人的行动指南,人在感性、知性、悟性等层面通过一定的社会行为方式表达出来,这时就会演生出“善”与“恶”的社会人性。如果生态文明缺失,那么,在生态的维度上,人类的行为就会失去约束标准,任凭个人的本能、邪念与贪欲,过度占有、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不良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人性“善”与“恶”规范的真空,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无序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只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制度、情感三位一体的人性维度上协同共建,才能有效规范人性,使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性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人性是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其中历史积淀及预设的人性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假如没有人性也就无所谓人类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就缺乏应有的人性基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通过人的本能行为表现出的人性本无“善”、“恶”,但在一定理念、欲望驱动下具体变现的过程中,人性的“善”与“恶”不断生成,这是人类实践的过程,也是逐步人化自然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凝炼形成一定的生态文明体系。
可见,生态文明与人性密不可分,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生态为标准,在人性基础上规范人的思想、行为、情感等因素,遏制“假”“恶”“丑”,张扬“真”“善”“美”的过程。这不仅是为人性“立法”,更重要的是为人性“执法”。面对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困境,只有强化人性“立法”与“执法”并重,生态文明建设才是可能的。因此,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类文明的基础问题,也就是人性的问题。一切生态问题都必须联系到这个主体性问题来思考。每一个人作为偶然的有限存在都会感到自己是无奈的人,超越生态难题,实现生态的完美和谐,这不是个人的能力所及,但人的行为导致生态失衡这又是事实。微不足道的地位和处境不是人们犯错误的理由,任何一个人又是自由的人,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从而显示行“善”者的人格高贵和作“恶”者人格低贱。“恰恰由于有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人才能够成为责任主体,‘善’‘恶’从而才变得有意义”*何中华:《“人性”与“哲学”:一种可能的阐释》,《文史哲》2000年第1期。。通过对生态文明的人性思考,我们真正感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知道怎样活、为什么这样活的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成为财富、资源的卑贱的奴隶,成为环境的破坏者,从而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与使命。
二、生态文明与人性的困境
在生态文明发展历程中,自然界是逐步人性化、丧失人性化、再回归人性化的自然界,人是从适应自然界的动物式生命过程演化为创造自然适合自己生存的人的形成过程。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形象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体现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关系,是“物的依赖关系”阶段,那么工业文明则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是“人的依赖关系”发展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发展阶段,而生态文明则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回归。
在早期的原始狩猎文明中,人是自然的奴隶,人是以生命的自然本能对抗自然、适应自然以获取生存的条件,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形成了自然原始宗教,这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原始阶段;在农业文明中,人掌握了自然规律,形成了畜牧业、农业等相关产业,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按照自己的诉求改变环境、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但人类基本上还是依赖自然、靠天吃饭,人与自然是协调共生的统一关系;然而,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口的激增,人们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界成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牺牲品,人与自然走向分离与对抗,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说明人出了问题,人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目前学界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出质疑,对此,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丰子义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 并不在于确认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 而在于使这种主体性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端的程度。”*丰子义:《生态文明的人学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这种“极端的程度”意味着什么呢?只能说明人性的异化。“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历史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马克思形象地阐明在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在“非人化”、“异化”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界成了人类学的自然界、“敌视人”的自然界,而非人化的自然界。“任何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占有自然界,但是,在现实劳动中,占有表现为异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周林东:《人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73页。工业文明时期的自然界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解放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马克思提出通过废除私有制来解放自然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然界是真正人化的自然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认为只有通过人的解放,才能解放自然界,因为自然界不能解放自己,只有人才能解放自己。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要经历一个生态文明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只有实现了人的人性化,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生态失衡的根源,从表面来看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果,从深层分析则是人们的思想、心理的折射,是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展示,从本质上说则是人性异化的表现。人是在自己的思想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从事生产、交往等各项实践活动的,并不断创造人化的世界。不容置疑,通过人的活动形成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但从实质上看,人所创造的世界则是人的思想的现实化,同时现实的世界又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人与世界的联系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性不断彰显、磨练、形成的过程。人性“本善”、“本恶”不仅仅是形而上学本质的预设,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的行为而展示出的动机与效果的“善”或“恶”。这里既存在普世的价值标准——良知、良心,这都是不证自明、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理念,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东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每一个人必须明确: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真”“善”“美”?如果对这些人性的基本规定都模糊不清,那么,做人必然就成问题。面对人的问题而导致的全球生态问题,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坏后果的发生?行动的合法性是什么?从东西方文明的分析比较中也许能发现问题所在。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物质与意识二元分离的认知思维模式首先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为人性本恶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知性和感性层面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外王”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开辟了西方灵与肉分离的先河,确定了人性的理性原则,特别是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化了人性的理性精神,康德把人性定位于兽性与神性之间,再到黑格尔把“善”与“恶”的人性规定动态化、辩证化、合法化,将人性发展到理性化的顶峰,始终将“人是理性的动物”作为文明构建的主线,凡是符合理性的就是“善”,否则就是“恶”。事实上,不论理性多么发达,人类的文明离不开人的动物本能,人的情欲、生命是人类文明创建的根基,这样的基本生活常识被近代及以前理性思想家们积极向上的偏好遮蔽了。这种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灵与肉二元对立思维的结果,一方面,理性取代了上帝,人成了自然的主宰。伴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人类文明跨入新时代。另一方面,人性及社会全面异化。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但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去发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成了美丽的谎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特别是人性出现了全面异化的现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严重危机。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发展,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实证理念占据了人们的灵魂,人没有了敬畏、谦卑之心,一切以取得(地位、荣誉)、占有(财富、资源)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人成了理性的工具和符号。人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来到世界的,人的生命、良知成为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物品;资本的逻辑法则促使人们贪婪地掠夺各种资源,腐朽消费理念导致生产、生活的过度消费,生态从而走向了恶性循环。人类的思想认识进入了灾难性的误区,人作为孤独的个体,是世界的旁观者,每一个人与自然、社会、他人是对立的,正是这种畸形的思想认知造成了生产、生存、消费等行为对自然、社会及人的危害,导致人性在生态层面上的“恶”。非常遗憾的是人类在满足自己的过度贪欲而制造罪恶时却浑然不觉。面对人性本恶,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坦言,君主必须掌握运用野兽的统治方法:像狮子般凶残,狐狸般狡猾。“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王水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人性险恶形同残忍的野兽,令人发怵。更有趣的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禁闭》中感言:他人是地狱。
现代西方哲学家尼采提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二千多年的欧洲文明被颠覆了,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面对虚无的世界,人普遍感到痛苦、焦虑,精神遭到前所未有的煎熬,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粉墨登场,企图挽救人类生存的根基,消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破除人性本恶的理性基础,强调生命、肉体、非理性对于理性的先在性,把灵与肉对立的关系颠倒过来。结果适得其反,人一旦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普遍的理性坐标,仅仅根据肉体的感受性来做人、做事,这样的人性更加险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面对人性异化与生态困境,西方生态主义学派走出纯粹的形而上学探讨怪圈,从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出发,从人的知性层面解读了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并在行动上指出了具体道路。默里·布克金在《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中分析了人与自然统一的有机社会,阐释了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对生态危机的根本影响,提出了“自由市镇主义”这一人性解放的方案。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生态危机的相关人性理论。高兹、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就是生态危机、人的危机;莱易斯认为人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生态危机就是人性的危机,提出解放自然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刺激生产,深刻批判了现代西方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人性显“恶”的政策,深刻批判了现代西方社会人性异化对自然的恶劣影响。
西方文明发展史表明,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矛盾发展史,是趋“善”抑“恶”的人性矫正、生成的历史。《创世说》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性本无“善”、无“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选择做出了某种行为(或违犯了理性)并对世界产生了影响,这时,人们根据行为人的动机和效果来评价人性的“善”或“恶”。“原罪说”揭示了人的灵与肉的纠葛,其实质就是人的肉欲战胜了理性。这既是经验事实,也是理性预设基础上形成的人性本恶论。人有了理性,才有能力区分“善”与“恶”,才有可能行“善”或作“恶”,可见,“善”与“恶”是人类文明发展必要的组成部分,其根源于人的灵与肉的矛盾性存在,具有人性的合法性。从理论上看,“善”有“善”的理由、“恶”有“恶”的根据;没有“善”也无所谓“恶”,没有“恶”也就没有“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正是由于“恶”的存在,给人们带来痛苦与灾难,人们才努力向“善”、行“善”,追求至“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才会和谐有序、积极向上,人类才有希望。但从实践上看,人类没有能力继续遭受“恶”的打击,抑“恶”向“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如果继续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任凭人类贪欲的肆虐,则意味着人类面临更大灾难的发生。面对西方世界的全面危机,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探讨人类的未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孔子的智慧就是一种人性本善的智慧。
在中国文明发展中,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辩证思维模式,灵与肉始终是统一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理念为人性本善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精神都是人性本善论在思想层面的根基。费孝通教授用四句话生动形象概括了中国人的人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超稳定的村社制度背景下,在知性层面上,封建皇权制度、血缘宗法制度促使人性本善论发扬光大,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标准,人治社会得以形成。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华民族走向了人性本善的“內圣”发展之路。光阴荏苒,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教化,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有生命的、感性的、情的世界里,人不是世界的旁观者、打量者,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共在。人生的意义就是在时光的流失中享受生活。这种人性本善论预设下的思维和生存方式也许是中国近代科学没有发展的原因,这是历史的遗憾,不过,也是历史的幸事,中国近代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完好,生态问题仅仅是中国近30年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西方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的理性经济。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法则都是自私自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人性本恶理念指导下,中国人的人性以及生态将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人性本恶论完全否定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法则和价值理念。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儒家道德伦理占据主导地位,每一个人都是有情有义、“美美与共”的“善”人。为了情和义,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个人淹没在家族、集体和国家中。两种完全相反的人性预设如何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实现两者的统一呢?生态文明建设也许就是最佳的契机。目前,人性本善论与人性本恶论两种性质相反的东、西文明在中华大地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与交锋,不论是在精神的层面,还是在生活实践层面,给现实的每一位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烦恼,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生态文明与人性的超越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什么样的人性才能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是否坚持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展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否定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这些问题以及生态危机考验着我们的人性选择。“解决任何重要问题的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所有问题都不会得到任何确定的解决。”*[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面对东、西方多元的文明理念,我们选择什么?如何选择?存在主义告诉我们:选择与否都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力。正是通过不同的选择与行为,人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这种人性生成论观点以及当前中华文明的困境给每一位中国人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度和思考的空间,也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和中国人的人性超越。现代西方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也许能给当下的人们指明人性演变的方向。他指出:“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圈。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这也是生成论视角下的人性论。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人性,人性是人自我塑造的过程,人是通过自我的创造性活动而成为具有某种人性的人。
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表达了更深刻的人性思想:劳动创造了人。马克思不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明劳动创造了人的肉体,而是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劳动对于人的价值。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对象性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了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身上得到了佐证,并创造了属人的世界,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人真正懂得了思想、法律、道德等文明理念和规则,能够按照理性原则自我约束和节制,生成了懂得必然法则的文明人、具有人性的人。离开劳动无法理解人的生成和人性。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为人,和其它动物区分开来,这也是众多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达到的境界。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把具有不同人性的人区分开,真正把人看成具有社会性的人。在劳动和社会交往中,不仅创造了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等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资本家必须千方百计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也只有这样,再生产才是可能的,自己才能生存。这种市场机制将人性的“恶”扩大到极致,人正常的欲望变成了贪欲,为了金钱,可以不要人格甚至生命,人的生命都成了获取资本的工具,更何况一般的动物和自然资源呢?资本主义制度使人性异化,从而导致生态危机,马克思的预言早就变成了社会现实,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性生成的前提——“制度”“规则”“理性”是怎样内化为一个人的行为规则的呢?一切秘密都隐藏在生活的世界里,人的行为首先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也就是基本的肉体的需要,较多地表现为动物性;其次是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精神的需求,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说”从知性的层面、逻辑地预设了人的行为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阐释了自然的人性观,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可见,不论是人性本善论,还是人性本恶论,不论是预成论视角下的人性论,还是实践论、生成论视角下的人性论,都是人性论,都是在人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之为人的东西。如果说人性本善论注重考察人的内在思想和动机,对于人的自我修养,达到“内圣”、世界和谐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价值;而人性本恶论注重人的行为效果,对于达到“外王”、征服世界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两种思维模式下的人性论,都是为人类的行为建立合法性的人性基础,主观动机都很善良,但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同。以人性本恶论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审视世界,以外力征服的方式改造世界,他人、自然界、社会都成了异己的对立面,形成了人与人恶恶相报的历史以及人类遭受自然界报复的现状,促使工业社会、法治社会形成;以人性本善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明,以情理不分的整体思维方式洞察世界,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包容万物,通过自己的道德良知行为感动世界,形成人治社会占主导的农业文明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不论是对立思维模式下的人性本恶论,还是统一思维模式下的人性本善论,都根源于人的矛盾性存在。“对立”与“统一”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不可分离,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因此,发挥人的悟性,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超越人性本恶论与人性本善论各自的片面性,实现两种人性论的统一,在思想认识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形成共识,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增强人的知性,建立健全规范的法律法规体系,创新科学技术系统,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引领人的感性,培育生态情感,生态情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只有在思想、制度、情感三位一体的人性维度上协同共建,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实效。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文明能否够挽救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这是考验人类智慧的试金石。生态文明给人类未来指明了方向,给迷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扬弃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在人性的层面上矫正、规范人的认知和行为,把生态文明作为衡量人类一切行为“善”与“恶”的标准,遏制“假”“恶”“丑”,张扬“真”“善”“美”,从而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篇章。“如果人要成为自身,他就需要一个被积极地实现的世界。”*[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4-0114-05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13CZXJ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美卿(1963—),女,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苏百义(1964—),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1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