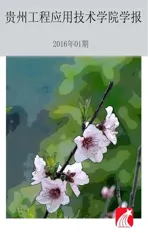“于//於”字介宾补语历时比较及其认知分析——以《左传》与《搜神记》为例
2016-03-18马克冬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毕节551700
马克冬(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于//於”字介宾补语历时比较及其认知分析——以《左传》与《搜神记》为例
马克冬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毕节551700)
摘要:通过对《左传》与《搜神记》中“于/於”字介宾补语的历时比较,修正以往关于“于”和“於”异同的某些看法,如“於”字可引进“原始意义”处所,“于”字也可引进“后起的意义”,包括时间、对象等。“於”在《左传》中已显示出取代“于”的趋势,而在《搜神记》中二者则进一步合流。从认知角度看,“于/於”字介宾补语前移作状语,其衬托作用更强,从而突出动词,使其成为语义焦点;同时,使语序与客观现实的逻辑顺序一致。
关键词:“于/於”字介宾补语;历时比较;认知分析;《左传》;《搜神记》
“于”和“於”经简化现已合二为一,对此,何乐士先生曾指出:“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於’有取代‘于’之势。”不过两者“是在语法功能、分布、意义、来源等方面都曾有过重要异同的两个介词”,通过对二者异同的分析,可辨别古书的早晚和地区等,并为此呼吁在重印古籍时保留这两个字的本来面目,以便进行研究。[1]
《左传》与《搜神记》分别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中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在语法研究方面皆具有重要的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言和口语开始分离,此时的很多语料,口语色彩较浓,反映了当时生动活泼的用语状况。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搜神记》的语料价值不容小视,它同《世说新语》一样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搜神记》中的语法现象,并将其与《左传》加以对比,对汉语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面,以“于”和“於”为例,比较《左传》与《搜神记》中相关介宾短语作补语的情况,从而修正以往关于“于”和“於”异同的某些看法,并从认知角度分析其句法位置前移作状语的原因。
一、《左传》与《搜神记》“于/於”字介宾补语比较
“于/於”字介宾补语分别指由介词“于”、“於”加上名词性宾语构成的介宾短语,且其在句中充当补语成分。就《左传》与《搜神记》而言,此类介宾补语主要包括四类,即处所补语、对象补语、时间补语、施事补语。具体情况如下:
(一)处所补语
“处所”的外延很广,既指具体的处所,也包括抽象的处所(范围、方面、地步等)。这在两书的介宾补语中皆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其一,《左传》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1196例①,其结构类型有“V(Vt/Vi)+C(于+名词)”、“V(Vt)+ O+C(于+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盟、淫、济”等,后者有“合、享、遇、作”等。这些动词大多表示居止和运动,此类补语表示的处所可以是所在、所从,也可以是所至。如:
(1)冬,同盟于幽,郑成也。(《左传·庄公十六年》)
(2)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左传·桓公八年》)
《左传》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814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位、立”等,后者有“舍、内”等。如:
(3)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左传·成公十六年》)
(4)乃内旌於弢中。(《左传·成公十六年》)
其二,《搜神记》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26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C(于+名词)”、“V(Vt)+ O+C(于+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钓、出、死”等,后者有“生、沉、见”等。如:
(1)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搜神记》卷一)
(2)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搜神记》卷四)
《搜神记》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145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浮、吝、至”等,后者有“受、送、缚”等。如:
(3)君吝於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搜神记》卷六)
(4)然则射可至於此乎?(《搜神记》卷十一)
这两例中的介宾补语分别表示“所在的范围或方面”、“所到的地步”。
(二)对象补语
对象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接受者、涉及者及状态的比较者等。
其一,《左传》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244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A+C(于+名词)”、“V(Vt)+ O+C(于+名词)”,前者述语为“告、献”和“贰、协”等,后者为“请、嫁”等。如:
(1)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左传·桓公九年》)
(2)齐请师于周。(《左传·庄公十四年》)
《左传》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690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A+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有“赴、求”和“恶”等,后者有“讼、请”等。如:
(3)将求於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4)死,将讼女於天。(《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其二,《搜神记》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8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A+C(于+名词)”、“V(Vt)+ O+C(于+名词)”,前者述语为“白、祈”和“同、类”等,后者为“学、诉、发、表”等。如:
(1)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搜神记》卷十七)
(2)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搜神记》卷十四)
例(2)中的介宾补语表示“老翁”与“兽”在状貌方面相似。
《搜神记》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39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A+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有“投、归、在”和“大、异、比”等,后者有“请、求、致”等。如:
(3)扶南王范寻养虎於山,有犯罪者,投於虎,不噬,乃宥之。(《搜神记》卷二)
(4)目犹未开,形大於常犬。(《搜神记》卷十二)
例(3)中的介宾补语表示给予的对象,“虎”是有所得的一方。
(三)时间补语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或终止的时间。
其一,《左传》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12例,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终止的时间,其结构类型为“V (Vi)+C(于+名词)”,述语动词是“至”。如:
(1)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左传·昭公十三年》)
《左传》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13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至”等,后者有“履、举、归”等。如:
(2)微武子之赐,不至於今。(《左传·昭公十三年》)
(3)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余於终。(《左传·文公一年》)
其二,《搜神记》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2例,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时的时间,其结构类型为“V (Vi)+C(于+名词)”,述语动词是“极、起”。如:
(1)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搜神记》卷六)
(2)相思之名,起于此也。(《搜神记》卷十一)
《搜神记》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9例,其结构类型有“V(Vt/Vi)+C(於+名词)”、“V(Vt)+O+C(於+名词)”,前者述语动词有“至、见、成、备”等,后者有“立、收、考”等。如:
(3)始见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备於太和。(《搜神记》卷七)
(4)民为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搜神记》卷二)
(四)施事补语
其一,《左传》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2例,其结构类型为“V(Vi)+C(于+名词)”,述语动词是“嬖、偪”。如:
(1)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左传·庄公十九年》)
(2)许灵公畏偪于郑,请迁于楚。(《左传·成公十五年》)
《左传》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有18例,其结构类型为“V(Vi)+C(於+名词)”,述语动词是“保、伤”。如:
(3)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左传·哀公七年》)
(4)郤克伤於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左传·成公二年》)
其二,《搜神记》中此类“于”字介宾补语有3例,其结构类型为“V(Vi)+C(于+名词)”,述语动词是“伤、闻”。如:
(1)故晋太康中,陈留阮士瑀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已而双虺成於鼻中。(《搜神记》卷十二)
(2)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搜神记》卷二十)
《搜神记》中此类“於”字介宾补语仅1例,其结构类型为“V(Vi)+C(於+名词)”,述语动词是“毒”。
(3)及帝晏驾,王室毒於兵祸。(《搜神记》卷七)
二、从介宾补语看“于”、“於”的异同
关于“于”、“於”的异同,王力先生认为:“‘于’字大致等于‘於’,但是上古‘于’‘於’不同音。……也有一些古书是‘于’‘於’并用的,如《左传》。在这些书里,‘于’‘於’是有大致的分工的:如果所介的是地名,一般用‘于’不用‘於’;如果在被动句或描写句里,一般用‘於’不用‘于’。很少例外。”[2]又说:“‘于’是‘於’的较古形式,……‘於’字后起,除了继承‘于’的原始意义外,它还兼有后起的一些意义,而这些后起的意义就不用‘于’来表示。”[3]
不过,通过对《左传》和《搜神记》中“于/於”字介宾补语的历时比较,可以发现一些与以上表述不一致的用例,如“於”字可引进“原始意义”处所,“于”字也可引进“后起的意义”,包括时间、对象和施事等。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从总体数量上看,《左传》中的“于”字介宾补语用例为1454个,而“於”字介宾补语用例为1535个。表面上似乎二者数量势均力敌,后者稍多于前者,但稍微留心一下,即可发现四类介宾补语中,除第一类“处所补语”是“于”多(1196个)“於”少(814个)外,其他三类介宾补语皆是“于”少“於”多,即对象补语分别为244个和690个,时间补语分别为12个和13个,施事补语分别为2个和18个。
《搜神记》中的“于”字介宾补语用例为39个,而“於”字介宾补语用例为194个,接近前者的五倍,显示出取代“于”的趋势。在四类介宾补语中,除第四类“施事补语”中“于”多(3个)“於”少(1个)外,其他三类介宾补语皆是“于”少“於”多,即处所补语分别为26个和145个,对象补语分别为8个和39个,时间补语分别为2个和9个。
其二,从“于/於”字介宾补语各类所占比例的对比来看,在《左传》四类介宾补语中,除第一类下降外,其他三类皆上升。其具体情形是:在《左传》中,“于”字介宾补语和“於”字介宾补语的主要用法皆是表示处所,但前者占其所有用法的82.25%,而后者则下降到53.03%;表示时间时,二者的比例差不多,前者为0.83%,后者略有上升,为0.85%;而表示对象时,“于”字介宾补语占其所有用法的16.78%,“於”字介宾补语则上升到44.95%;表示施事时,二者的比例差别最大,前者为0.14%,而后者则上升到1.17%,是前者的八倍多。
可见,在表示对象和施事时,《左传》中的“於”字介宾补语的数量明显多于“于”字介宾补语。其原因在于:“于”字的产生早于“於”,在甲骨文中有“于”而无“於”;引进处所是“于”字最早的用法,引进对象和施事的用法产生于引进处所的用法。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甲骨文中的“于”字“应该是先用来介绍行为的处所,再扩展介绍行动的时间和动作涉及的对象”[4]。总之,“于”、“於”产生时间的先后与“于”字用法的扩展过程基本一致,导致二者在《左传》中有所分工,即先产生的“于”以引进处所这种旧用法为主,而后产生的“於”以引进对象和施事等新用法为主。
其三,与上述《左传》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搜神记》四类介宾补语中,除第一类增加外,其他三类皆减少。其具体情形是:表示处所时,“于”字介宾补语为66.67%,而“於”字介宾补语则增加到74.74%;表示对象时,“于”字介宾补语占其所有用法的20.51%,“於”字介宾补语则略有减少,为20.1%;表示时间时,与表示对象的情况差不多,前者为5.13%,后者减少为4.64%;表示施事时,前者占其所有用法的7.69%,而后者减少的幅度最大,仅为0.52%。
赵大明认为:“到了汉代,‘于’、‘於’已经基本合流”,并据此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最迟在战国中期,因为“于”、“於”在书中的差异表明二者正处于交替的中间阶段,而伪作者不可能将这种差异完整地保留下来。[5]《搜神记》中“于”、“於”用例的比例所出现的变化,则反映出“于”、“於”在中古已进一步合流的特点,即分工已不如《左传》明确,用“於”引进“原始意义”处所的用例增多,同时也可用“于”引进对象、时间和施事。当然,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后起的“於”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其语法功能的多样性,在《左传》中已显示出来的“於”取代“于”的趋势在《搜神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处所补语句法位置前移作状语的趋势
从历时演变的角度看,由《左传》到《搜神记》,介宾短语的句法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介宾补语前移作状语。下面以数量最多的处所补语为例,分析其前移作状语的情况。
(一)由介词“于”构成的处所状语
其一,《左传》中这类状语皆引自古书,只有5例。如:
(1)《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左传·文公三年》)
其二,《搜神记》中这类短语作状语时,非引自古书,而是在叙述句中,有8例。如:
(1)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搜神记》卷十六)
(2)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搜神记》卷十七)
从表面上看,其用例数量变化不大,但是只要将两书中此类短语作状语与作补语的用例结合起来加以对比,即可发现《左传》中作状语的比例为0.42%(作补语的为1196例),而《搜神记》中则上升到23.53%(作补语的为26例)。
(二)由介词“於”构成的处所状语
其一,《左传》中这类状语有25例。如:
(1)子於郑国,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犹有鬼神,於彼加之。(《左传·襄公十年》)
其二,《搜神记》中的这类短语作状语时,有38例。如:
(1)数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搜神记》卷二)
(2)於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搜神记》卷十)
同上,从表面上看,其用例数量变化不大,但是只要将两书中此类短语作状语与作补语的用例结合起来加以对比,即可发现《左传》中作状语的比例为2.98%(作补语为814例),而《搜神记》中则上升到20.77%(作补语为145例)。
(三)综合比较
对于由“于”和“於”构成的处所短语,如果忽略二者之间的区别,将其用例合在一起统计,并将其作状语与作补语的用例加以对比,即可发现二者在《左传》中作状语的比例为1.47%,而在《搜神记》中已上升到21.2%,同样表现出很明显的前移趋势。其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四、对介宾补语句法位置变化的认知分析
笔者曾对介宾补语作过相关分析,但主要是从语言本体出发,涉及介宾短语的语义、谓语复杂与否等方面。下面,着重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一)图形与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术语,前者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后者指为突出图形而衬托的部分。在句法分析中,两者有重要的作用。
赵艳芳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作为图形的主语和作为背景的宾语最为突显,其他后景(background 或setting)如状语是不突显的。”[6]尽管原文分析的对象是英文,但是可借鉴其理论来探讨汉语句法问题。例如:若将介宾短语视为背景,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视为图形,那么介宾补语前移作状语,其衬托作用更强;与此同时,更加突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使其成为语义焦点。如:
(1)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搜神记》卷一)
此例中,“于井上”作状语,是因为前文“井”已出现,它是已知信息,不是语义焦点;“呼之”则是提供的新信息,是语义焦点。当然,也有例外,如本例“飞从井出”按理应为“从井飞出”。不过,这正好也反映了中古汉语此类结构正处在前移的过程之中,存在一些两可的现象很正常。
(2)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搜神记》卷十七)
此例中,“于神座上”只是介绍魅发出动作的处所(即背景信息),其语义焦点则是“吹作角声音”。
(二)语言的象似性
语言的象似性是相对其任意性而言的,指语言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是有理据的,可加以论证。如戴浩一提出时间顺序原则,指“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7]。尽管其论述的对象为现代汉语和英语,但对古代汉语中的语法分析也非常有意义。范晓也指出:“时间顺序就是一种逻辑顺序,它往往会映射到语法结构的成分排列次序上。”[8]
据此,汉语语序应与客观现实的逻辑顺序一致,表现为按照时间先后、原因—结果、工具(凭借/依据)—动作等顺序安排句法成分。许多介宾短语句法位置的前移就与此有关,如:
(1)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搜神记》卷十六)
此例之所以将“于市”前置作状语,就是因为临摹客观现实中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即必须是先到市场,才能“货之”(卖枕)。
(2)数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搜神记》卷二)
此例中,“於宅前林中”是“得之”的地点,置于其前作状语,符合客观现实中先去某地、继而发生某事之逻辑顺序。
(3)於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搜神记》卷十)
此例中,“於字”是对“‘禾’、‘失’为‘秩’”进行分析的依据,即从字形上加以分析。
总之,运用相关的认知理论,对介宾补语句法位置的变化进行分析非常有意义。与《左传》相比,《搜神记》中许多“于/於”字介宾补语前移作状语。从认知角度看,其衬托作用更强,从而突出动词,使其成为语义焦点;同时,使语序与客观现实的逻辑顺序一致。
注释:
①《左传》中的相关统计数字参见:(1)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1-118;(2)赵大明.《左传》介词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0、151-152。不过,将后者中“动作的施事”这一小类独立出来,称为“施事补语”。
参考文献:
[1]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7-118.
[2]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459.
[3]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332.
[4]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C]//古汉语语法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92.
[5]赵大明.《左传》介词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7.
[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53.
[7]戴浩一.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国外语言学,1988(1):10.
[8]范晓.关于汉语的语序问题(二)[J].汉语学习,2001(6):18-28.
(责编:明茂修责校:明茂修)
Diachronic Comparison on Yu(于)/Yu(於)Preposition-Object Comp lementsand Cognitive Analysis——Taking Zuozhuan and Soushenji for Example
MA Ke-dong
(Schoolof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Bijie,Guizhou5517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iachronic comparison of the yu(于)/yu(於)preposition-object complements in Zuozhuan and Soushenji,the paper corrected some previous views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yu(于)and yu(於),such as yu(於)can introduce the original meaning place,yu(于)can also introduce the later meaning,including time,objectand so on.Yu(於)had shown the trend of replacing yu(于)in Zuozhuan,and yu(于)and yu(於)converged further in Soushenji.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the yu(于)/yu(於)preposi⁃tion-object complements went forward as adverbials,the foil function was stronger,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verb andmaking itbecome the semantic focus.At the same time,itunified theword order and the logic order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Key words:Yu(于)/Yu(於)Preposition-object Complements; Diachronic Comparison; Cognitive analy⁃sis; Zuozhuan; Soushenji
作者简介:马克冬(1971-),男,安徽马鞍山人,文学博士,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简帛文献。
基金项目:毕节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左传》与《搜神记》介宾补语之比较研究及其认知分析”,项目编号:20101002。
收稿日期:2015-11-21
中图分类号:H 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39(2016)01-00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