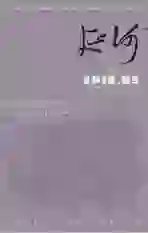冬至·清明
2016-03-17陈毓
陈毓
冬至
福德老汉是在立冬夜里过世的,冬至一过,他的哮喘就犯了,说来也是老毛病,每年天一冷就犯,天一回暖,自然减轻。哮喘是年轻时候挑担走四川落下的,福德老汉总这么说,但他老伴鹤庆不这样想,她笑话福德老汉是怕死不服老。人老了,病自然来,你都八十岁了,还想活八十岁?像你现在这样,耳背,多喊几声也能听清白,眼老花,多瞅几眼也辨得准人,能吃得下面,也啃得动饼,能睡得去,醒的来,要谢天谢地啦。
豁达的鹤庆真的是寿终正寝,一觉不醒去了。这是三年前。
鹤庆去了,福德老汉说自己的福气被鹤庆带进坟里了。他爱吃一辈子的南瓜洋芋糊糊面,现在没人能给他做出来,他爱吃的细玉米面锅贴没人能做出来,酥烂的含在嘴里听得见吱吱响声的红烧肉也没人能做得出来,一大早醒来就要喝的罐罐茶一辈子虽是福德老汉熬,现在似乎也没以前香醇好喝了,想来是没有鹤庆分享的缘故。
福德说自己名字里有个福字,现在知道福是和鹤庆系在一起的,以前听鹤庆议论生死,却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鹤庆后头,本来他就比鹤庆大。现在鹤庆去了,留一个孤独的自己在人世上是艰难的,他除了会熬制罐罐茶,厨房的事情一概不懂,不懂更不动,油瓶子倒了会不会扶起还说不定。鹤庆死了,鹤庆的许多话福德现在倒常常想起来,以前她活着,她说话他基本是听不见的。
扶起来我也不会用油炒出好吃的菜,福德老汉嘟囔。一个人活到了八十岁,活着这件事就简化成了一日三餐,而现在这一日三餐,也似乎变得像个大工程一样艰巨。
福德和鹤庆年轻时生养过一个儿子,后来儿子没了。他们也没能再生养,福德说祖宗这一脉到他这里断了,好在福德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和弟媳去世早,儿女却丰盈,现在,来空寂寂的东院走动的,就是西院弟和弟媳家的连顺媳妇的脚步声。连顺随建筑队去青海修路,几年在这里,几年在那里,都是修路。每回过年连顺提着礼物来看他和鹤庆的时候,福德都会说,铺路架桥,积德行功哩。
福德喜欢连顺,连顺话不多,连他那个媳妇也是话不多,一辈子未说话先笑,乐意不乐意从来都没见大声说过不字。这样的媳妇真是打着灯笼难找。
连顺媳妇进来的声音福德没听见,福德说,你进来的声音我咋每回没听见。
那我往后脚踩地踩重点。连顺媳妇笑一笑。
下次再端了饭碗进来,福德还是会说,你踩地可用力啦,我咋听不见?
你老耳背!连顺媳妇大声喊。把脚在地上跺,问福德老汉,听见了没?
福德老汉呵呵笑,看见你跺脚,听不见响。
连顺媳妇也笑,老小老小,老了咋都成孩子了。
孩子,一儿一女都在城里,打工的,陪孩子读书的。各自忙。倒是她显得闲,如果身体不出问题,日子似乎是好过的日子,吃饱容易,穿暖也容易。只是日子里咋就没个心劲呢。这样的想法连顺媳妇偶尔有,她看着屋后的小树林偶尔发一会儿呆,那里有公公的坟、婆婆的坟,婶子的坟,将来也会有她的坟、连顺的坟。她坚持清明冬至都要去坟地化纸钱,她喜欢买黄表纸,回来用真的人民币,十块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尽量用十块二十块的,有时候也用五块的,一张一张在黄表纸上认真地拓印,用木板子嗒嗒拍出闷闷的声响,她想使每一张黄表纸上都烙上真钱印子。她不用一百元的纸币,觉得那会给老人添麻烦,老人本来吝惜舍不得花钱,你给他大票子,他花不出去,更舍不得了。连顺媳妇不喜欢买假币,那是对逝者不恭,即便另一个世界,也不能使假耍滑。
清明吊子洁白地挂在青枝绿叶间的感觉让她觉得生死没那么分明的界限,冬至上坟时点燃几枝香,印过钱印子的黄表纸燃出的味道混在松柏的香气里,都让她心里安静。以前丈夫儿子都在家的时候,上坟是不要她这个女人出面的,现在丈夫儿子不在家,她毫不迟疑地担当了上坟的责任,只在除夕夜里,她看着丈夫儿子去坟地时候她才自觉隐退,让他们走在她前面。
眼前她要每日三餐伺候的老人其实根本不构成她的负担,她给自己做饭,添一瓢水,就把老人的饭也顺带做出来了。以前婶子健在的时候,做饭还轮不上她,婶子麻利干净了一辈子,甚至连去世都麻利干净,这是咋修行来的?而她的婆婆和公公,去世前一个在床上躺了一年,另一个进出医院半年。受了些罪。
她发现老人这几天吃的越发少,她担心是饭菜不和他的胃口,到该做饭的时候就大声喊话,问老人想吃什么,老人抬起头,很认真地看她,直到她问他三遍五遍,还是那句她早知道的答案,吃啥都没滋味,你想吃啥做啥。
连顺媳妇往自己屋里走的时候心里没主意,她真盼老人能给她提个要求,他说了,她一定满足。这天在问过老人后,连顺媳妇做了素馅饺子,她看见冬阳下蒙在塑料薄膜里的韭菜鲜嫩嫩的,就决定做韭菜鸡蛋的饺子,加半个土豆泥在里面,糯糯的,软软的,好吃。
饺子端给福德,福德吃了几个,就不吃了,连顺媳妇看着有一瞬间的伤心,她想不吃就是不行了的意思。她去接碗筷,福德忽然看着连顺媳妇,问,你叫啥名字?问得连顺媳妇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有点发愣,她当然有名字,只是孩子们不可能叫她的名字,孩子的爸永远和她白搭话,从来不唤她名字,村里同辈人以及长辈,总叫她连顺媳妇,难怪老人要问她名字了。连顺媳妇说自己的名字还是有点羞涩,但她还是大声说了,她说伯呀,我叫存珍。
“存珍”的声音一出,像是带着一股光焰,从院子的这边飞往那边,于是,院墙边的竹林发出一串飒飒的竹叶摇动的声音。
这个傍晚,存珍去问福德老汉想吃什么她好去做的时候,本来是不报得到答案的心思的,但她意外得到了答案,福德老汉说他要吃荷包蛋,要吃三个荷包蛋,他拃着手指,清楚地表示“三”的意思。于是,存珍去煮了五个荷包蛋,福德三个,她两个。
第二天,福德老汉死了。
像鹤庆婶子一样,寿终正寝。
存珍在发现福德老汉没了气息的第一时间给老汉穿好寿衣,她走出屋子,看见一群麻雀从竹林里呼啦一声飞起来,越过院墙飞向蓝天,想,这个院子从此变成实心子的空寂了。她把脚大声在地上跺,说,伯呀,你老听见了吧?
清明
看见杜鹃占满窗台的那些绿植,杨双绪就觉心绪缭乱,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的植物一律养在清水中,竟也能活、能长。植物的根系依着器皿的形状,曲折回旋,一根根、一圈圈堆放杯盘碗盏,既脆弱又顽强。若十天半月不添水,那些红啊绿啊也枯萎。植物有根,但杨双绪直接称杜鹃窗台上的植物为无根植物。杜鹃这次生了气,伸手就把一株风信子从瓶中扯出,瓶口窄,杨双绪听见类似红酒瓶开启的“啵”的一声响,杜鹃抖擞给杨双绪看风信子的根,使杨双绪吃惊,那些没了依托轰然悬垂的根系,竟是植物本身的几何倍数。
杨双绪有次梦见他和娟子双双变成了这样的植物,在一枚窄口径的瓶子里,艰难地向外探脑袋,踮脚生长。把梦说给娟子,娟子不屑,摸杨双绪的脑袋,问他咋还褪不掉诗人善感的毛病。
自从那些植物摆满窄窗台,开合窗帘的活儿,杨双绪就不再干,他一动手,总有一个瓶子或杯子打碎在地上。杜鹃不得不说杨双绪的手邪气。至此,早起睡前,拉窗帘就成了杜鹃的专职。有次杜鹃先上床,努嘴让杨双绪关窗帘,杨双绪钉在窗边不动弹。杜鹃生气,杨双绪似乎更气,他说明明是植物都能爬过脚背的山野长大的孩子,进了城,咋就变得如此琐碎小气?这点毛毛根根,能和发出海啸般的森林涛声比吗?
这次不欢后,杜鹃把植物都送了人,但下一月,相似的植物又来到窗台上,占满窗台。
眼看清明节到了,过年时爹就嘱咐杨双绪,前几天又打电话叮咛,要杨双绪清明节早回家,请了风水先生,看坟。按说春节刚回家,再在清明节回老家,不划算。杨双绪把回一趟老家在金钱情感在的天平上计算,还是坐上回老家的火车,他觉得父亲矫情,在他看来,父母亲最少还能活三十年。距离坟墓远着。
这是习俗,杨双绪说服自己。比如祖父母。祖父两年前去世,祖母五年前去世,但停放在阁楼上的祖父母的柏木棺材,却惊吓过杨双绪的整个童年。在被母亲支使,不得不上阁楼拿东西,战战兢兢,寒毛倒竖是杨双绪最不堪的童年记忆。等到祖父母真的躺进用油漆漆得锃亮的柏木棺材,听吹鼓手渲染着闹哄哄的葬礼场面,从葬礼上流行歌曲的嬉闹到童年的恐惧,让杨双绪有点恍然梦中。杨双绪弄不清童年恐惧的到底是什么。死人?鬼魂?死人不是和块石头一样无声无息吗?杨双绪就有半夜从墓地过也不惧怕的大胆记录。至于鬼魂之有无,杨双绪至今也未理清。
和四十天前拥挤的火车比,此刻的火车太安静太舒服了,凭窗眺望的杨双绪有一瞬间的幸福感。
火车过平原,进深山。一进山,天哗啦一下,变得那么蓝、那么深,在那片蓝天下,一堆堆、一簇簇,一条条、一溜溜的金黄菜花,点缀在碧绿的麦田中,让眼睛舒服,让心怀舒服,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和春节比,此刻的大地像刚刚睡了个饱觉醒来的人,褪去所有的倦意和不爽。杨双绪感叹他有多久都没和土地,和自然真正亲近过了。春节回家,他基本上天天都是醉着的,不醉的时候他在牌桌上。此刻他有点激动、有点感慨,被杜鹃嘲笑的爱抒情的毛病似乎又上来了。
但临出发前追赶来的杜鹃这会儿却是沉默安静的,她托腮凝望窗外,她不再嗑瓜子,不再翻动手机,就那样安静地看窗外大地上的风景,杨双绪第一次发现安静下来的杜鹃有分他陌生的美。使他意外,又心底愉悦。
下火车,再上公共车,之后换坐地蹦蹦。
而去看坟的路还得依靠脚力,其实坟地当然已经确定,就在祖父母坟地坐落的地方,走过十几里乡路,爬一面缓坡,在曲折如绳的山道上绕,就是祖父母的坟地。山洼里,一片花梨树林中的平阔处。
杨双绪早已走出一身细汗,被微风悠悠吹拂,觉得心怀舒畅。听近处叽叽一阵阵的鸣叫,山鸡不时自脚下扑啦一声飞远,鹧鸪在远山的叫声显得山格外深远。
看坟的仪式先是在祖坟挂清明吊子,烧纸钱,放炮仗,那些距离祖坟近的坟墓,哪怕不沾亲不带故,也要一一照顾到,烧纸,不可疏漏。这是近邻胜似远亲的意思。父亲叮咛。
化过了纸钱,就见风水先生时而远观眺望,又眯着眼睛近查,确定下父母未来住所坐落的地界,定下木楔,随后再选日子请劳力垒出一个空坟。最后一项仪式就是杨双绪代替父亲在祖父母的坟头磕头。自从杨双绪能一个人独自上坟,每年上坟磕头就是杨双绪的事情了,父亲最初只是象征性地跟来,理一理坟头的草啊树啊。后来就不来了。他有儿子呢。
给祖宗每回磕头的时候,杨双绪都在心里联想到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双绪。他要绪的,不仅是父亲这一脉,外公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孩子,他作为下一代男丁,他也有责任绪上母亲这一脉。
履行祖上传承下来的法定仪式,由天地作证,杨双绪在每一处坟头依次跪下,连磕三个响头。这一次,父亲神态严峻地监督在身边,目光如炬,紧盯他的举动,不放过任何细节,保证仪式的美满完成。在杨双绪膝盖骨触地的瞬间,那一记沉重的跪响,由杨双绪的膝盖,传达到父亲脸上,在那里转换成无言的欣慰与放心。是的,长眠地下的先人借此得以安心,也借此感到慰藉。
天气晴朗,草木繁茂,空气使人沉醉。杨双续随父亲走出山林的那一瞬,心中感动,他很想说,他将来死了也要葬在故乡的山林里,看春天花朵含苞待放、草木盛大,秋天花梨树落叶飒飒,头顶青天朗朗。季节流转,生死轮回,生生不息。这样的轮转使死亡也显得温暖安详,像祖父母,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仿佛落叶乔木进入冬天,就是一个静美。
这一刻,杨双绪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童年惧怕空洞的棺材,而面对祖父母的死亡,他却没一丝生离死别的惧怕和遗憾。他觉得一个活人的身后有个方位明确的墓园,有一群哪怕面容模糊也是亲人的祖宗在那里耐心等候,迎接你回去,同归一处,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我之未来,将在何处?是枕着故乡的青山长眠,还是装进石制小盒寄居别人的城市?天晓得。杨双绪在鹧鸪的叫声中回望青山,青山在他此刻的注视里,含情脉脉。
回到东莞,杜鹃买来一个大缸,说服房东让她放在窗户下面的院子里,那里能晒到阳光,也能接纳雨水,杜鹃偷偷告诉杨双绪,未来,不管他们搬到哪里住,这个缸都随着,而且要保证缸里的橡子发芽生根,长成巨大的橡子树。等他们将来变成一撮灰,也有一个类似故乡的生态接纳他们。
杜鹃说,橡子是她清明回家看坟从老家的树林里捡来的。杜鹃的话让杨双绪发了一个呆,他疑惑自己从来都没真正理解过杜鹃。杨双绪一瞬间生出自责。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