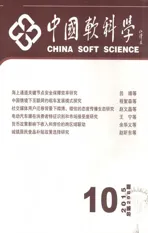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研究
2016-01-19王志章韩佳丽
王志章,韩佳丽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研究
王志章,韩佳丽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而成本分摊机制的构建则是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从随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城市公共成本六个方面,计算出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所需增加的人均支出额约为3.2万元。由于我国农民工总量多、基数大,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庞大的资金,全部由财政负担并不现实。因此,本文在分析当前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机制现状的基础上,从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政府 “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摊机制入手,提出了创新成本分摊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测算;分摊机制

城镇化是每个国家及地区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客观规律,也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城镇化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目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美国、德国、日本分别达到了82%、74%、91%,相比而言,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仅为54.77%。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不区分二者的概念。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强调“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表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包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这对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产业,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1%提升到54.77%,平均每年提高1.02个百分点。根据Northam(1975)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曲线*Northam根据世界各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提出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认为城镇化发展可以分为“起步——加速——成熟”三个阶段。定律,中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于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镇,城镇人口快速增加[1]。然而,当前的城镇化发展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只是数量和规模上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进了城,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成为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子女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根据国内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半市民化”现象严重[2-3]。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城镇化”理念,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由速度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本质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长期以来,由于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的庞大,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成为了当前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难点。基于此,本文在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测算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由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摊机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第四部分是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现状的综合测度;第五部分提出创新多元主体分摊机制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转移的动力机制上,部分学者指出城市工业制造业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4-5]。Lewis(1954)建立的二元结构模型以及Todaro(1969)发展的人口流动模型,都从理论模型上证明了城乡收入差距是农业人口转移的主导因素[6-7]。随后,研究的视角开始转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上来,Seeborg(2000)指出单一的新古典模型已经难以解释中国巨大的人口迁移,政府应努力消除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8]。Lee(2007)认为,城镇基层政府缺乏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9]。Vandana(2008)指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满足城乡迁移人口的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会产生相应的成本[10]。而如何制定合理的内部化措施是使社会成本“费用最小化”的关键[11]。
国内学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来,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规则、成本估算以及成本分担。在制度规则方面,赵立新(2006)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指出当前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在于私人关系型的社会资本不足、制度型与组织型社会资本严重缺失[12]。韩俊(2009)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延缓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13]。黄锟(2011)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在于两方面: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巨大社会成本[14]。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提出要加快劳动就业、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就业、落户,使其真正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福利[15]。在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估算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在8万—10万[15-17]。而最近的研究却表明,以往的成本估算存在一定缺陷,通过重新测算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仅需4000元[18]。在成本分担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有两方面成本:一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需求[19];二是培育农业转移人口适应城市经济的能力[16],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应该由谁来承担?面对如此巨大的成本,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担机制[20]。部分学者认为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应由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承担,同时也需要企业发挥积极作用[21-22]。吕炜(2014)认为应建立起由农民工、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分担机制[23]。
通过上述国内外文献的梳理表明,制度障碍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根本性因素,只有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才能有效进行。而在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方面,由于测量方法及口径上的差异,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因此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重新测算,进而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测算
已有的研究在测算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口径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本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定义,即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一致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界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包括六个方面: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其他社会保障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城市公共成本。
对于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测算方法,总体而言,大多学者都是采用了分类加总的方法,即先求出各个项目的单项成本,最后加总求和。但在具体计算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绝大多数研究仅考虑了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之后政府需要增加的各项财政支出,而忽略了其在农村地区所享受的各项政府补贴。鉴于此,本文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乡补贴差额对其市民化的成本进行重新核算,如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应测算城镇人均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差额。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一是各类统计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14》;二是财政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三是各类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以下是具体测算过程:
(一)随迁子女教育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由农村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加上农村初中在校学生数计算而得。约为4000万,约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城。已有的研究在核算随迁子女教育成本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基本上是简单的把城镇中小学的人均教育成本乘上随迁子女数量作为随迁子女进城增加的教育成本,而忽视了全国无论城乡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当前农民工子女一部分在农村就读,一部分已随父母进城读书,国家对这些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补助。因此,在核算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增加的社会成本时不应简单按城镇学生人均成本计算,选取城乡小学、中学义务教育经费的差额更为合理。
2013年城镇小学生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6926.28元,同期农村为6854.96元,城乡差距为71.32元;城镇初中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9272.43元,农村为9195.77元,城乡差距为76.66元。城镇小学生教育公用经费2118.19元,同期农村为1973.53元,城乡差距为144.66元;城镇初中人均教育公用经费2987.21元,农村为2968.37元,城乡差距为18.84元。由此每个小学生占用的教育经费城乡差距为215.98元;初中学生则是95.5元。城乡小学、初中教育经费人均差额合计为311.48元。
另外,由于随迁子女进城就读必然会带来增加校舍问题。如果新增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全部采用新建校舍解决,按照教育部城镇九年义务教育建设的规划指标,中小学生校舍建筑面积人均8.25平方米;根据2013年全国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为1765元/平方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由房屋竣工价值除以房屋竣工面积计算而得。,从中测算出随迁子女增加的校舍成本约为每人14561.25元。
根据已有研究,都是将随迁子女人均教育成本计算到每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上,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每位农民工都带有子女进城,鉴于此,本文首先计算出随迁子女增加的总成本为59477311443元(包括小学、初中的教育成本以及增加校舍的成本),在此基础上平均分摊到每位外出农民工身上为358.08元。

表1 2008-2013年农民工规模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2014)
(二)医疗保障成本
目前,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则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1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6.7%,2012年到16.9%,2013年则上升到17.6%。虽然外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还是相对较低。
2013年政府加大了对城镇居民及农民的医疗保障投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由2012年人均240元提高到人均280元。2013年全国新农合参保率达到99%,也就是说几乎全部农民都参加了新农合医疗保险。由此将农民工市民化后,与该农民相应的医疗补贴只是由农村转移到了城镇,增加的医疗保险成本应该是财政补贴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的差额。而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6610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7.6%。如果将剩下没参保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共计13686.64万人。2013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人均为96.68元,新农合的财政补贴则是人均61.71元,城乡差距为人均34.97元。从中测算出增加的医疗保障成本为478621.80万元。

表3 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 单位:%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三)养老保险成本
2009年,我国推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此,我国的居民保险体系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构成。直到2014年,政府正式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2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在2013年,全国已有半数省份已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不再区分城居保与新农保,因此本文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来衡量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政府的主要投入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增加养老保险成本应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差额。2013年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为2851.41亿元,人均885.03元;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为1235.16亿元,人均248.27元,城乡差距为636.76元。
(四)其他社会保障成本
财政部对其他社会保障的支出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企业缴费,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2013年,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是8.21亿元,人均5元;对工伤保险补助19.59亿元,人均9.84元;对生育保险的补助为5.78亿元,人均3.53元。 除了对社会保险的补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最可能增加的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支出。2013年,全国财政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为每年人均3219.27元,农村则为1380.96元,城乡差距为1838.31元。

表4 2013年公共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数据来源:2013年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财政部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14》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财政部网站
(五)保障性住房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全部依靠政府财政补贴不现实,较为合理的办法就是由政府统一建设保障性住房,为部分农民工提供公租房或廉租房。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农民工中租房居住(与人合租以及独立租赁)的农民工占36.7%,比上年提高3.5%,而且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大,越依靠租房方式解决居住问题。2015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王宁表示,目前,政府通过公租房、廉租房及提供租房补贴等方式解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按照国务院24号文件指示,廉租房的建筑面积标准控制在50平米以内,按三口之家算人均分摊面积16平米左右。而香港是世界上公营房屋制度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政府提供保障房的比例为30%。假定按照香港的标准,政府需要为有4983万人提供公租房或廉租房,剩下的70%将自行购置房屋。根据2013年全国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为1765元/平方米,从中测算出农民工市民化增加的住房保障成本人均约为28240元。

表6 2013年按城市和住宿类型分的外出农民工人数构成 单位:%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六)城市公共成本
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对城市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娱乐等基础公共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必然给城市增加额外的负担。城镇公共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公共管理成本也随之上升。根据《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46亿元,全国共有城镇人口73111万人,人均基建成本约为115.71元。另外,国研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会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约为560元。进而测算出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均城市公共成本为675.71元。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现状的综合测度
对于政府而言,从横向层级来看,农民工的流动绝大部分是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但由于地区间财政资金划拨的独立性,流入地政府不愿意承担流出地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杜旻(2013)研究表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供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这也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候鸟式迁徙”现象的主要原因[24]。根据有关学者的调研表明,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公共服务政策趋同,没有适应农业转移人口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别化的公共服务体系[25]。从纵向层级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务工地集中在城镇地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起农业转移人口大量的文化教育、交通邮电、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成本,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政负担,不愿意对农民工的管理进行资金投入。据调查发现,各省市召开的两会上都明确提出了推进市民化的工作,但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却没有市民化这项工作的资金安排[26]。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农民工务工企业应承担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费用,而目前企业普遍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支付采取消极的态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企业也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多数企业设法逃避农民工的社保费用。另一方面,现行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缴费标准门槛较高,如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用人单位应缴纳工资总额的20%,过高的费率也会让企业望而却步。根据2013年农民工检测报告,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虽然继续上升,但除了工伤保险为28.5%外,其它类别均未达到20%,总体水平还是很低。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局限的经济实力加上企业的消极态度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参保意愿。企业除了没有履行好缴纳雇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义务外,在农民工用工强度、发放工资、签订劳动合同方面也没有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13年外出农民工从业时间平均为9.9个月,月平均25.2天,日平均8.8个小时,与2012年相比超时工作农民工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其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相比2012年上升了0.3%。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1.3%,不到一半水平,而且比2012年相比还下降了2.6%。此外,在就业培训方面,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年提升了1.9%,但还是相对较低。在住房条件的改善方面,2013年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或者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分别占46.9%和8.2%,和去年相比都呈下降趋势。企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消极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以及能力。

表7 人均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测算结果 单位:元/人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2609元,扣除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为892元,可支配的收入仅为1717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要用于子女教育投入以及家庭其他支出。加之意识观念较为落后,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较低(见表3)。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为看不见的未来买单,必然是疑虑重重,这就造就了农民工“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的失衡现象[27]。由此可见,当前农民工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负担市民化的成本。
从以上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三大分摊主体都存在着一定问题。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应当在市民化的成本分摊中承担主要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是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互相推卸责任,都不愿为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买单,且没有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支出政策;企业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在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就业培训以及住房条件改善方面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是市民化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个人职业能力来看,都缺乏承担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能力。综上述,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机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因此,本文接下来对如何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五、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机制的对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总量问题,二是支出结构问题。据前文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财政及社会资金总量庞大,全部由财政负担并不现实。根据国研中心报告,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妥善安排,不会成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科学合理地构建一个由农民工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摊机制,以保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够顺利进行。
(一)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的责任主体
1.政府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政府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承担主要支出,同时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负担成本支出的比例,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成本分摊各有侧重。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在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应当承担较大比重,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将财政投入的重心集中在地方性公共事项,如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管理、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从而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享受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除此,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问题上,还负有监督的责任与义务。中央政府应发挥调节作用,协调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够有序进行。
(2)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
根据2013年外出农业转移人口流向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外出农业转移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中西部地区外出农业转移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其中,中部地区跨省流出农业转移人口中有89.9%流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流出农业转移人口中有82.7%流向东部地区。总体而言,东部是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净流入地区,中西部则是净流出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并且享受到了农业转移人口输入的人口红利,因此,东部地区应当负担一定比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但是,由于东部地区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流入地,承担了其它地区的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因此,政府应协调好财政支出在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之间的分配,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各地区顺利进行。
(3)地方各级政府
根据2013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8.5%的农民工流向直辖市务工,22%流向了省会城市,33.4%流向地级市(包括副省级),35.7%流向小城镇。由此可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主要集中在地级市、小城镇,因此,地级市及小城镇需要承担大部分农民工的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省级政府要根据农业转移人口的分布状况,统筹安排好各项财政补助在省内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可以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省内跨市、县镇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2.企业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在分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上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企业而言,主要是解决社保部分,需按期足额缴纳雇佣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配套资金上企业承担的部分。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都在30%以下(如表3所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都没有交足各自应该缴纳的部分。由此,企业需完善雇佣民工社保问题,承担起工伤、失业、生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缴费责任。为了使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政府可以给吸收较多农业转移人口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3.个人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市民化的受益主体,其自身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以降低由企业、政府承担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压力,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顺利进行。对此,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承担市民化后的生活成本,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除此,还需要承担社会保障的部分成本,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个人需缴纳的部分。
(二)强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的政府责任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中央政府要发挥好调节指挥作用,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方面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结构。各级财政在安排支出时,需要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调节省、市之间的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方向是财政由流出地转向流入地;地方政府调节本地区内的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方向是县镇之间转移以及农村向城镇调整,如调整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在中央与地方、农村与城镇的负担比例。
2.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土地挂钩政策
农业转移人口对于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有着不同的经济意义。于流出地政府而言,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出去,其相应的土地指标继续留存在本地区,相对扩大了本行政区域的土地面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助于经济增长。对流入地政府来讲,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入增加了本地区的人口总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土地指标,政府需要额外加大土地投入用于城市扩建以满足该部分人口的需求,因此成为某些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可以创建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土地指标增减挂钩机制,将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出地的土地指标转移到流入地政府。或者由流出地政府向中央财政上缴一定比例的土地收入,再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对流入地政府进行专项补助。
3.渐次推进市民化进程
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多、基数大,如果一次性全部市民化将面临高昂的财政支出。因此,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应选择渐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可以使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城镇长期生活,且收入稳定,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业转移人口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另一方面是加大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投资,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农民工职工技能培训,以适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发展。
(三)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的企业义务
企业应积极履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的社会责任。首先,企业应该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定期足额为雇佣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严厉打击企业的逃缴行为,完善法律法规,约束企业的行为。其次,企业可以在政府的资助下积极参与建立劳动者权益保护资金,借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此外,企业应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同时积极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条件改善和子女的教育改善。然而,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国际市场需求疲惫,国内经济正处于“新常态”下,内需与外需的下滑使得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因而政府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应当意识到企业当前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对积极响应农民工参保政策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从而激励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承当应有的责任,构建可持续性的企业分摊机制。
(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摊的个人能力
要使农业转移人口有能力负担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就必须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能力入手。首先,工资性收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农民工工资的有效发放,杜绝拖欠工资的现象,保证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收入。其次,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绝大部分农村土地都处于荒废状态,政府应加快土地确权进程,从而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一定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此外,对于在城镇务工的农民,政府应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和服务,积极引导农民工就业。
参考文献:
[1]NORTHAM R M.Urban geography[M].New York:Wiley,1975.
[2]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9(10):66-72.
[3]魏后凯,苏红健.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5):21-29.
[4]威廉·配第.政治算数[M].陈冬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5]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LEWIS 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2):139-191.
[7]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8]SEEBROG M C.The new rural-urban mobility in China[J].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0(129):39-56.
[9]LEE C K.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0]VANDANA D,POTER R.The companion to development studies [M].Hodder Education,2008.
[11]OECD.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M].云萍,祁中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12]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0-45.
[13]韩俊.调查中国农村[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14]黄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制度设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16]张国胜.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9(4):56-69.
[17]张占斌等.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测算与时空分布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10):1-7.
[18]丁萌萌,徐滇庆.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J].经济学动态,2014(2):36-43.
[19]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张国胜.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J].经济学家,2013(1):77-84.
[2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5-29.
[22]俞雅乖.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8):127-131.
[23]吕炜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财政约束与体制约束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4(5):3-9.
[24]吴萨等.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新的制度安排[J].宏观经济管理,2013(4):54-56.
[25]杜旻.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化趋势社会融合及其管理体制创新[J].改革,2013(8):147-156.
[26]田园.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3):17-22.
[27]聂国梅.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基本养老问题研究[J].人民论坛,2015(14):151-153.
(本文责编:王延芳)

A Study on Estimation and Sharing of the Public Service Cost
in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WANG Zhi-zhang,HAN Jia-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igrant is the core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is the key in the procedure of urbanization.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added per capital of public service is 32 thousand yuan in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igrant,including children education,health care,pension insurance,other social security,affordable housing expenditure and urban public cost.Due to the great amount of agricultural migrant,the citizenization requires huge amount of money,and all by the financial burden is not realistic.Therefor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rinity of agricultural migrant,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agricultural migrant;citizenization;public service cost estimating;sharing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5)10-0101-10
作者简介:王志章(1956-),男,湖北当阳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应用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 (批准号:12ASH004)。
收稿日期:2015-06-28修回日期:201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