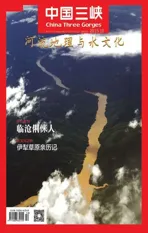故乡的阿朵
2015-09-13许文舟编辑吴冠宇
文/许文舟 编辑/吴冠宇
深山环绕的乌木龙,“阿朵”并不是一朵花,它是一群天真淳朴的俐侎女孩,是俐侎女孩年满13岁前统一的名字。淡淡的微笑浮在她们红润的脸上,似有朵朵把春天送回人间的山花正在盛开。。
阳光下的康家坝河闪动着奇异光泽的鳞影,偶有花瓣顺着流水飘荡。岸上阵阵口弦吹皱一池涟漪,流年间的阿朵,懂得任尔抚弦入韵,让生活的烦恼被情人谷的河水涤荡。
在深山环绕的乌木龙,“阿朵”并不是一朵花,它是一群天真淳朴的女孩。阿朵是俐侎女孩未满十三岁时统一的名字,十三岁行过穿裙子仪式之后俐侎女孩们就宣告成年,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名字。“阿朵”一词,现在似乎不再受到年龄的限制,只要是未婚的俐侎女孩都会被称为阿朵。
与俐侎妇女的朴实、豪爽和落落大方比起来,俐侎女孩总是隐约带有些羞涩。她们长期生活在乌木龙,重峦叠嶂的深山阻隔了年轻阿朵们和外界的接触,面对陌生人时,她们在不经意间总会表现出来的胆怯与羞涩却恰到好处地诠释着一种美。这种美不是现代都市商品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她们的举止言谈中透出来的一份谦逊、一份温柔、一份爽朗,在当今社会已不多见了。淡淡的微笑浮在她们红润的脸上,似有一朵把春天送回人间的山花正在盛开。
因为需要几分聪慧,织女的身份往往是被看作成俐侎女人的本事。
在俐侎山寨,对阿朵们来说,生活中所能倚持的不是天赐的容颜,而是手里的技艺。纺织在俐侎社会中就是这样一项技艺,因为需要几分聪慧,织女的身份往往被看作成俐侎女人的本事。每个俐侎女孩大约从七八岁开始,就要学习纺线、织布、绣花、制衣,几乎家家女子无论长幼,都会飞车走线。
我在乌木龙的多次行走,每每都能听到俐侎人家传出的吱吱嘎嘎的机杼声,也总是绕不过会想到《子夜四时歌》里的一段:“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当男人们已经离开田亩到远方去谋生计,俐侎女人却还停留在机杼声里,被织出的布匹淹没。现代社会的分工,让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俐侎女人虽然也用不着慢条斯理地在织机前一直劳作,但织机依然是俐侎人家的传家宝。在俐侎女人的手中,时间的边角废料、农闲的短憩,都被喂进了织机,织得一寸是一寸。
俐侎人的服装大部分靠自己织布、染色、缝制。随着国家对大蔴的禁种,俐侎人只好从集市上买来棉花经过轧花、弹花等工序,在自制纺纱机上纺棉,再织成布匹。俐侎人崇尚黑色,制衣所用的布匹百分之九十都会浸到一种由板蓝根叶熬制的液体里浸泡数日,黑色才会占领棉纱,浸淫到布的内心去。这一过程即为靛染,也称“染靛”或“染布”。靛染有复杂的工序且带有几分神秘,是一块布成色的技术环节所在,其中包含了俐侎人几百年间的探索与寻觅。靛染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浸染、敲打、晾晒,过程劳累而枯燥。靛染好的布匹会被缝制成一套套俐侎服装。一套普通的服装,需要20天左右才能缝制完成,缝制嫁装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一套衣服从纺棉、织布到印染、缝制,全是俐侎女人在操持。衣服的数量是衡量俐侎女人贤惠能干的标准,于是一台织机就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织,成为了俐侎女人的宿命,她们把青春织进布里,爱情织进家庭。俐侎女人手上沾满的青蓝色也会在时间的晕染下逐年变深。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年轻阿朵不愿意再被织机和传统而单一的蓝黑服饰禁锢,她们也会走进售有时尚服饰的现代商店,学着海报上城市女孩的时髦打扮,很快就融入了城市街道上的人群中。只有在“桑沼哩”的三天里,年轻的阿朵们才会穿上袖边缀有五彩花纹的无领对襟长衣的传统服饰,腰束黑色腰带,下穿筒裤,外系长围腰,头戴方格花布巾。
穿着这样的一套服饰费时费力,而阿朵们的精心打扮,只是为了在“桑沼哩”上遇见心仪的阿幽。

桑沼哩节上的俐侎女孩。 摄影/许文舟

永德乌木龙乡俐侎人家仍然有织机,仍然有织布的俐侎女人。 摄影/许文舟

穿着俐侎传统服饰的女孩。 摄影/许文舟

小小阿朵。 摄影/许文舟
在“桑沼哩”的草甸上,我发现许多俐侎女孩相约着,从不同的寨子来到这里,加入到舞蹈的队伍里来,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着身体。比身体更加忙碌的是她们的眼睛,在寻找着另一个世界。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当山寨里满山的红杜鹃开得有些放肆时,俐侎人家家户户都要过一个名叫“桑沼哩”的节日。“桑沼哩”是俐侎语的发音,翻译为汉语是“桑树脚下出热水,相约到那里去沐浴”的意思。它对于俐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寨子里的青年男女都会在这个节日里围着篝火唱起山歌,跳起舞蹈,交友择偶,谈情说爱。
这个时节,总有男人为心上的阿朵抚笛弄笙,赞赏她眉目如画。俐侎阿朵心思澄明,不会为各种世俗的对比与考量遮蔽了发现真爱的眼睛。听起来有些童话的味道,但俐侎女人就是这样理解爱的。每年的“桑沼哩”,乌木龙赠出最多的不是各种金银手饰,而是阿朵们手工刺绣的鞋垫、手工缝制的背包和手工织出的围巾。
2005年春,我曾应朋友之邀到一个名叫菖蒲塘的俐侎寨子跟踪拍摄“桑沼哩”节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族群和他们特有的节日。菖蒲塘在乌木龙的北边,我从临沧去到乌木龙转车时,这个小小的山乡已被各地的游人车辆挤满。乌木龙只是大山间的一个小镇,镇子依山势而建,一条主干街道穿城而过,镇上商业和市集就都集中在此,临沧到永德、昆明到永德、凤庆到永德的车辆都得穿过乌木龙这条又窄又弯的小街。“桑沼哩”期间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的人,就都堵在了这条街上,车辆在节日前后的几天都无法正常通行。虽是还未赶到节日的活动地点,但从这拥堵的交通倒是可以一窥“桑沼哩”的热闹了。
俐侎山寨往往搭建在高寒山区,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食粮都很贫穷,但俐侎人的骨子里却有着一份对生活的乐观。对于会走路就能跳舞,能说话就会唱歌的俐侎人来说,不管明天锅里还有没有米,灶里还有没有柴,他们一定会在今夜将竹笛吹得激情饱满,一定会在芦笙的伴奏下,赤脚将大地踏出飞扬的尘埃。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简单却深刻的哲学问题,也不妨成为俐侎人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年轻一代的族人已经无法了解到那段被追逐的历史了,他们穿着时下流行的服装,在学校里与汉族同学上着同样的课程,只有节日里他们才会穿上属于俐侎人的服装,在“桑沼哩”的三天假期里重新回到俐侎人原本的生活中。老一辈的俐侎人,却依然停留在未被现代物质文明侵入的昨天,他们选择在草长莺飞的二月里唱歌跳舞,让这个月份充满怀旧的味道。
“桑沼哩”的三天,是俐侎人身体和心灵都重归自由的三天,没有任何世俗的条条框框去约束他们。他们可以寻找自己过去的情侣,也可以交到新的异性朋友。许多婚事也由此诞生而穿插于节日期间,铜质的唢呐一发话,就有一双双新人生活到了一起。
阿朵们相信天上真的有掌管着姻缘的月老。一高兴,就让人间相爱着的人琴瑟和鸣;一不高兴,就令其分道扬镳。分手的不一定不爱彼此,做一家的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面对儿女的一见定终身,俐侎长辈往往很坦然,凭空出现的男人会把小小的阿朵的心掳走,而这只能归为命运或定数。在面对婚变时,俐侎人也认为那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神也拦不住要走的女人。
菖蒲塘的“桑沼哩”温泉水塘在村旁山脚的断头岩下。山崖宽近千米,高约百米,温泉水从崖壁的岩洞里直接流淌出来,水质清澈,水温常年在28℃。水塘就在这崖壁外紧贴山势修筑的梯田之间,如果不走近,在远处很难看出在长满碧绿稻苗的田地间还有一塘塘温泉水。洞口边有一个小小的祭台,贴着祭祀用过的鸡毛和烧香残留下来的痕迹。崖壁的洞口很小,仅能容一人屈身而入,温泉水从洞内流出,形成了一道小溪,洞内的空间倒是阔了许多。
白天,这里泡着一村子的男人,一直要到黄昏降临,才到山上抽烟喝酒。夜色深沉下来之后,热水塘才交给了俐侎女子。
二月的滇西春来早,桑树说绿就绿,杜鹃说开便开。就算白天有雨从云层筛下,细密得如同尘埃,一到夜晚,似乎有意让给月亮展颜,天便晴得不见一丝云彩。夜色轻轻网住大山,也将俐侎女人网到热水塘里,尽情地让温暧的地热水浣洗掉往日劳作的艰辛。偶有几朵花顺着温泉水流而下,漂到阿朵们的面前,这是俐侎男人为了俘获阿朵们的心而使用的小小招术,散发着鲜香的花朵省略了许多情话。
夜晚的菖莆塘村外边的天然草甸成了俐侎青年男女对歌跳舞的平台,月光如水一样地倾泻下来,给俐侎山寨平添了几分浪漫。这个夜晚对于身处这方水土的人来说,除了歌与舞,恐怕世上再没任何存在了。夜色渐晚,草甸上的人群越聚越多,将一堆篝火团团围住。歌声此起彼伏,对和相间,俐侎歌曲曲调优美,一咏三叹;歌头吹着竹笛,副歌头吹着芦笙,动作幅度越跳越大,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在“桑沼哩”的草甸上,我发现许多俐侎女孩相约着,从不同的寨子来到这里,加入到舞蹈的队伍里来,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着身体。比身体更加忙碌的是她们的眼睛,在寻找着另一个世界。年轻的阿朵在这天身着最好的衣服,最美的笑容会在这天绽放,她们期盼一朵表达爱恋的花朵,跨过康家坝河来到自己面前。
事实上,乌木龙的穷山僻壤,足以让这些年轻的阿朵心力交瘁,而外出打工,不用看雨水的心情、老天的嘴脸,每月见现的工资怂恿着她们把未来托付给了远行。
俐侎女孩的爱情很少受到世俗约束,她们想爱谁就爱谁,她们想什么时间结婚就什么时间结婚,即使自己的爱人一无所有,只要这个男人会唱歌,能将爱情从口里唱出来,就可以;只要这个男人能喝酒,喝完酒后能上山狩猎能下河拿鱼,就行。俐侎女孩看重的是感情,不在乎结婚的形式。而订婚的信物也不过两瓶自酿的酒或是一筐茶这样简单的物资。
居住在永德乌木龙乡的俐侎男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由男方砍一段长约10厘米、直径约1厘米的樱桃树小木棒,刻上能说明男女属相婚配日期之类的图案,女方准备一根红丝线。大喜之日,将红线拴在小棒上与新人一并送入洞房,便被视为“合法”夫妻,这个小木棒便是“西卡”(意为结婚物证),由新人珍藏直到白头。若有夫妇感情破裂要离婚,就请来原来做媒的媒人将“西卡”一破两半,双方各执一半。若女方先于男方另嫁他人,她的新婚丈夫要向原配男人纳一定数额的聘金聘礼,烧掉原来的“西卡”,才能拥有新的“西卡”而步入婚姻殿堂。如果离异后想要破镜重圆,再请来原媒人,将各执一半的“西卡”合拢,拴上红线即可。这可不是杜撰,早些年俐侎山寨的传统婚姻仪式就是如此。
在她们看来鲜红的结婚证与樱桃树小木棒的作用差不多,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罢了。俐侎女孩一旦成婚之后,就会相夫教子,过着与苦荞一样清贫的日子,她们相信双手,相信稼穑,当她们的头发里不再有鲜花而是让麦糠与瘪谷粘满的时候,粗糙的手指握着的针仍然会在布匹间飞快地穿梭,仍然会把生活的种种绣得针脚不乱。
当然,随着经济大潮的侵入,俐侎人的婚姻也有决堤的案例,也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被大山以外的世界的精彩所诱惑而分道扬镳。青春的阿朵就像康家坝河的浪花,只朝一个方向绽放,那个方向就是远方。事实上,乌木龙的穷山僻壤,足以让这些年轻的阿朵心力交瘁,而外出打工,不用看雨水的心情、老天的嘴脸,每月见现的工资怂恿着她们把未来托付给了远行。千万不要责怪阿朵。现代生活对身在深山的阿朵们产生了很大的诱惑,阿朵到异乡打工,她们用初中水平的数学一计算,打工的绩效胜过种苦荞的收入,于是她们姐带着妹,妹带着弟,有的甚至是全家一起远离故乡,来到别人的城市。她们用织布的手擦拭着一尘不染的杯子,她们用绣花的耐心伺侯着挑剔的主人,她们的嘴变得吹不动山中的绿叶,笑容也被世俗包装得严丝合缝。我在走访中得知如今距离第一个阿朵从乌木龙出走去深圳也已有二十余年了,这不能说明什么,外出打工收入也并非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反正没有给乌木龙带来足以安慰自己的酬劳。
时间久了,身在异乡的阿朵们有些已经淡忘了家乡,让自己融入了外界的精彩;有些在历经生活的种种艰辛后,放下了诸多精彩和诱惑,返回故乡。乌木龙的大山将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阻隔,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月圆时刻,依然会有情意绵绵的古调歌谣被年轻的阿幽们唱起,唱醉了阿朵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