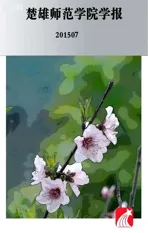论废名诗歌中的“禅意” *
2015-03-19刘纪新
论废名诗歌中的“禅意”*
刘纪新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废名新诗的创作量不大,却因为禅意盎然而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在他的诗中,有的禅宗意味纯正,有的又融入了基督教文化。同时,废名的诗无法完全摆脱人间情怀,偶尔会在美丽的“色界”流连忘返。
关键词:废名;诗歌;禅
收稿日期:`*2015-04-10
作者简介:刘纪新(1969—),男,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5)07-0055-05
Abstract:Fei Ming’s new poems are not many, but are unique for their Zen connotation which, while pure in Zen, is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in some way. On the other hand, Fei Ming’s poems show that the poet cannot completely get out of the secular world.
废名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极为罕见的曾经真正在精神上皈依佛教的人,他在文章中曾经明确表示:“我信佛,信有三世。”[1](P22)在《阿赖耶识论》一书中,他批评康德和中国的程朱一派说:“可惜他们终是凡夫,不能进一步理智与宗教合而为一了。照我的意义,哲学进一步便是宗教,宗教是理智的至极。”[2]至于废名所说的“理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在这里无须深究,只就他认为宗教高于哲学来看,他已经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宗教,而是从宗教的角度看待哲学。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黄梅是佛教史上的圣地。据冯健男介绍:“禅宗五祖弘忍是黄梅人,他受衣钵于四祖道信,传衣钵于六祖慧能,这在佛教史和哲学史上是有名的和重要的事情。黄梅县城外西南一里许有东禅寺,是慧能受于弘忍处;县城外西北三十华里有四祖寺,县城外东北二十五华里有五祖寺,都是著名的丛林,尤其是五祖寺,规模宏大,建筑成群,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是旅游胜境。”[3]废名在黄梅生活到16岁,这期间五祖寺、东禅寺香火不绝,使其深受佛教文化的熏浸。
废名在北大求学期间,仍不忘研读佛经,曾经因佛学见解不同与熊十力扭打,此事被周作人写入文章,被后人传为趣闻。“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4](P59)
20世纪30年代中期,废名更加专注于佛学研究,并于抗战期间完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该书反驳熊十力的观点,反对进化论等“近代思想”,同时鲜明地表达了废名的宗教信仰:“我所宗仰的从我的题目便可以看得出是佛教。”[1](P2)
“现代作家中,废名是从心到形体悟禅宗的极少数人之一”,[5]他不像一般文人只对佛教义理感兴趣,不事修行。据说废名坐禅功夫不在僧人之下,入境后,身体自然舞动,“有如体操,不能自己,仿佛自成一套……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4](P59)抗战前,废名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将家人打发回老家,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寺庙里。
1931年,废名在北京西山卜居期间创作了一批诗歌,禅意盎然,原想整理出版,最终未能如愿。今天只能见到《〈天马〉诗集》一文,大概是他为诗集所写的序言,由此可见废名当时创作状况。“我于今年三月成诗集曰《天马》,计诗八十余首,姑分三辑,内除第一辑末二首与第二辑第一首系去年旧作,其余俱是一时之所成;今年五月成《镜》,计诗四十首。”[6](P223)
一、禅意盎然
我独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海》*本文所引用的废名诗句出自《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招隐集》(废名,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和《新发现的废名佚诗40首》(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1期)。
这是废名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他曾经说:“我当时自己甚喜欢它。要我选举我自己的一首诗,如果林庚不替我举《妆台》,我恐怕是举这首《海》了。”[7](P113)诗人立在池边看花,这样一朵“亭亭玉立”“出水妙善”的荷花,对于佛家而言不是一般的花,其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行,深得佛家喜欢。在佛经中,经常以莲花为喻,如“譬如莲花出自淤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大智度经·释初品中尸罗波罗密下》),“清白之法最具圆满……,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无量寿经》)。另外,佛座也被称为“莲台”,佛国也被称为“莲界”。
在佛教中,荷花代表着佛性,人可以因观花而悟道。在《海》中,废名面对荷花,自然心领神会,诗人说:“我将永不爱海了。”这里的海如何解释?从全诗背后的佛学理路来看,应该是废名观花悟道,舍弃现实,进入禅境,所以这里的海应该是指俗世,就是色界。同时,考察“海”这个意象在废名诗歌中的象征意蕴,也是如此。在《妆台》中,诗人梦见自己是个镜子,沉到海里也是个镜子;在《十二月十九夜》中,深夜独坐,燃起一只灯,便有了“身外之海”。在这两首诗中,海就是俗世和色界。由此来看,《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海,应该是指现实世界。当诗人要弃绝现实世界的时候,“荷花微笑道:/‘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如何理解“你的海”?这个海肯定与前面的海不是一个海。按照禅宗观点,一切物象都是心相的外化。如此来看,这个海是心海。心海犹在,身外之海就无法弃绝,但是一旦荷花从心海长出,就大不同了。佛家喜欢荷花,正是以她象征佛性,从污泥中生而不染污。当荷花从心海长出,诗人的禅悟就圆满了。“对禅宗而言,世俗存在与西方乐土之间的差别,仅仅取决于‘迷’与‘觉’:当人未悟佛性时,他便是凡夫俗子,所处之域亦为世俗的世界;一旦由‘迷’而‘觉’,则可立地成佛,而西方净土亦将随之而至。”[8](P283)
在禅宗看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就是无明。众生可以通过修行“见”自己的佛性,就是明心见性,一旦进入这个境界,就得以解脱。所以,禅宗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在废名的诗中正是刻画了这种境界。在《无题》中,“得到解脱”“微笑死生”;在《梦中》中,在梦与现实之间悟得一个“空”;在《自惜》中,“自喜其明净”。
二、佛与基督
废名早年虽然深受佛教文化熏陶,但是到了北京大学之后,作为“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又接受了西方文化滋养,在他的诗中出现了基督教的影子。“五四”时期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就曾经说:“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9](P64)陈独秀更是号召“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10](P177)对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不是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而是当作一种可以为我所用的文化资源。例如周作人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废名诗中的基督教文化正是如此。
耶稣叫我背着十字架跟他走,
我想我只有躲了,
如今我可以向空中画一枝花,
我想我也爱听路上的吩咐,
只是我是一个画家,
一晌以颜料为色,
看不见人间的血。
——《耶稣》
“废名作品的晦涩在新文学中是首屈一指的”,[11]废名的诗“是新诗坛上第一的难懂”,[12]这其中包含内容与表现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内容来看,废名的诗有着深玄的宗教背景,对于不了解佛理禅机的人自然难以体会诗中意蕴,这种晦涩不能只责怪作者。废名也说:“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clear得利害。”[13](P101—102)废名诗的晦涩也表现出他在艺术手法上确实存在问题,卞之琳就曾经指出:“他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14]
回到《耶稣》这首诗来看,初看上去很晦涩,其实只要懂得一些禅宗知识,并不费解。“耶稣叫我背着十字架跟他走/我想我只有躲了”,这是无须多做解释的,这是说诗人拒绝皈依基督教。诗人在拒绝了耶稣的引领之后,“向空中画一枝花”。“画”作为一个动作,在废名现存不多的诗作中经常出现,是很值得深究的一个现象。除了《耶稣》一诗,还有“我想着把我的花园里画一枝佛手”(《上帝的花园》),“梦中我画得一个太阳”(《梦中》),“爱画梦之光阴”(《空华》),“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梦之使者》),“我催诗人画一幅画罢”(《画》),“我想我画一枝一叶之何花”(《点灯》)。从这些诗句来看,不论是“诗人”“厌世诗人”还是“我”,应该指的都是废名自己。诗人不去写诗,却要作画,这其中很有意味,而且画的又不是真正的画,多是虚空中的、空想中的画,其中正是大有禅机。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第一卷)在阐述禅宗眼中的自然时,就是以画作喻:“譬如工画师,及与画弟子,布采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笔亦非素,为悦众生故,绮错绘众象。”在禅宗看来,自然万物都是心相外化,都是虚无之物,是空。但是,这个“空”并非存在于“色”以外,而是以色证空,籍境观心。正如马祖道一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祖堂集》卷十四)由此看来,为求得禅悟,一方面要视自然万物为空,同时又不能脱离自然万物,要籍境观心。自然万物就如同画中山水,既空又不空,既虚无又蕴含真理。废名正是深得此道,一再在诗中作画。
在《耶稣》中,废名又说自己看不见人间的血。在佛家看来,世间万象都是色,都是空,血也是空。所以在废名眼里血与颜料无异,不过是给他作画的。修禅的人要由色悟空,人间的苦难,不论是十字架还是血,都是空,都是给我参禅悟道的“画”而已。视世间万物为空的废名自然不会听从耶稣的吩咐,不会肩起十字架,而是在空寂中解脱了凡尘。以上从佛禅的角度解读这首诗,是为了突破它深玄的禅学背景,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这首诗,其实并不晦涩。
在《耶稣》一诗中有三个角色:一个是代表基督教的耶稣,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佛。佛在禅宗里就是我心中的佛性,在诗中就是那个成为了“画家”之后的“我”。诗中的十字架和血都是属于基督教的,画家与花属于佛教,属于这个尚未成佛的“我”的就是“路”和“走”。作为精神的“走”,可以向外“走”,皈依一个外在的上帝,也可以向内“走”,孤明独发,明心见性。最终,这个“我”拒绝了耶稣,走向佛禅。
三、徘徊于“空”与“色”之间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虽然有不少人曾经涉足宗教,其诗歌创作也得到了宗教文化的滋养,但是,他们大多都没有真正皈依宗教。宗教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在价值转型时期重建价值的一种文化资源,冰心、金克木、陈梦家等都是如此。废名与他们不同,不仅把宗教当作一种文化资源,而且身体力行地修行,还写过专门的佛教著作,作为一位现代诗人,他在佛教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他的诗却并不都是禅意盎然,不都是那么纯净。不论废名后来撰写《阿赖耶识论》期间是否真正皈依了佛门,是否得到解脱,至少在他卜居北京西山期间,在创作《海》《耶稣》等诗歌的同时,还创作了不少佛性不纯的诗歌,可以看出他对于“身外之海”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有时甚至表现得很强烈。
《妆台》常常被视为废名的代表作之一,该诗创作于《海》之后四天。
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
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将放上她的妆台,
因为此地是妆台,
不可有悲哀。
废名曾经谈到这首诗的创作心境:“当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确实是一个镜子,而且不惜投海,那么投了海镜子是不会淹死的,正好给以女郎拾去。”[7](P111)由此来看,解读这首诗的关键就是读懂这面镜子。镜子的意象在废名的诗中出现得非常频繁,可以说“镜”的意象也是打开废名诗歌这个黑匣子的一把钥匙。1931年,废名曾经打算结集出版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就命名为《镜》。在《镜铭》一诗中,他以镜自比。诗歌中镜的意象就更多了,例如:“如今我是在一个镜里偷生”(《自惜》);“病中我起来点灯,/仿佛起来挂镜子”(《点灯》);“海是夜的镜子”(《十二月十九夜》);“我不愿我的镜子沉埋,/于是我想我自己沉埋”(《沉埋》);“时间如明镜,/微笑死生”(《无题》);“自从梦中我拾得一面好明镜,/如今我晓得我是真有一副大无畏精神”(《镜》);“余有身而有影,/亦如莲花亦如镜”(《莲花》)。从上述镜的意象来看,都蕴含着禅机。
镜子在佛教中是一个重要喻象,深谙禅机的废名自然懂得其中奥妙。“明镜的作用是朗照对象,它圆明无垢,本身是虚空清净的,其中本没有像(相),然而它能映现万有,但所有像(相)也是虚幻的。显然,镜是心之喻。”[15](P122)修禅的人常常以镜比心,镜本身是“空”,但它能照见世间万物,同时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心相外化。“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所以,心与物的关系就像镜与镜像的关系。
搞清楚了这个禅学背景,这首诗就不那么玄奥了。在禅宗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正如人心中都有一面明镜,但是被种种迷妄遮蔽,人的修行,“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四十二章经》卷一)。废名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镜子,是暗示佛性显现。而后写道:“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海的意蕴前文已经分析过,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世间、世俗人生。既然已经彻悟,证得佛性,即使处身俗尘,仍然不染于心,依然是“心如明镜台”。
到此为止,这首诗中的禅意依然纯净无暇,但是后面就不同了,废名的人间情怀,对于人间的留恋,对于美的钟情开始流露出来。
既然“镜子”落入了俗世,那么被女郎拾去,放上妆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因为此地是妆台,/不可有悲哀”就出问题了。先看妆台。世间万物本来就是“色”,是幻象,而妆台是化妆的地方,是在虚幻之物上再涂脂抹粉,在虚幻上再加一层虚幻,在迷妄之上再蒙上一层迷妄,可见这妆台距佛性更远了。在这种地方,禅家应该尤为超然,但是诗人却是充满了情绪。废名的诗以节制情感著称的,甚至给人以情绪寡淡之感,所以这里的情绪就显得颇为突出。废名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女子是不可以哭的,哭便不好看,只有小孩子哭很有趣。所以本意在妆台上只注重在一个‘美’字。”[16](P200)在修禅的人看来,美貌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无之物,应该从中悟到“空”,但是废名注重的却是“美”。在佛家看来,“三界无安,犹如火斋”,沉迷其中,难逃轮回之苦。而废名置此于不顾,只希望女郎保持一个美的形象。可见废名对于“身外之海”还是迷恋的。他迷恋色界,不能看透色界虚无,并从中证得佛性,可见废名并没有真正彻悟和解脱,这个精神的港湾并不那么安全。
再如《星》一诗:
满天的星,
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
东墙上海棠花影,
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
清晨醒来是冬夜梦中的事了。
昨夜夜半的星,
清洁真如明丽的网,
疏而不失,
春花秋月也都是的,
子非鱼安知鱼。
如果只看前半部分,这首诗是纯净的佛家之诗。不论是星还是花影,都自以为自己是永恒的,就如同凡夫俗子把世间万物看成实在之物。其实,春花秋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是虚幻之物。接着,诗人又追述说,这些也不过是昨夜一梦,在虚无之上再加一层虚无,一切都是空。但是此后诗的内容开始转变,诗人以赞叹的口吻写道:“清洁真如明丽的网,/疏而不失”。对这类春花秋月之类的事物极尽赞美,显然有违佛理,这同《妆台》结尾一样,表现出诗人对世间之美的留恋,过于执着于色本身,而不能由色悟空。最后一句“子非鱼安知鱼”,在佛家看来,更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废名引用了庄子与惠子于濠梁之上的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秋水》)在纠缠不清的诡辩中,其实是把佛家眼中空与色的质的差别模糊了,这在佛家看来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佛家讲“色即是空”,是说色本身是空,要通过色悟到空,色本身没有意义,是虚无,是迷妄。“凡所见色,皆是见心。”但是该诗中,废名却怀疑春花秋月可能也是真的,而且沉醉于春花秋月之美。这就看出,废名还是一个人间的诗人,他并没有真正在禅宗中得到超脱。
废名不仅多次表现出对于人间的留恋,对于“色”的沉醉,有时甚至直接写道:“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掐花》)。可见,他并不是完全以佛理禅机决定进退,而是放任性情,以主体的意志决定取舍,不在乎是否合于佛法,不是让主体融化在佛禅的境界,而是让佛禅为我所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废名对佛教禅宗的切入和痴迷,恰恰是与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17]“废名从一种宗教——佛教——中找到了一个内在的、超验的维度”;[18]“废名的禅意更是一种‘哲学’,一种关注生死问题的哲学。……很显然,废名希望以文艺的形式探索生命哲学的内容。”[19]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废名与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同他的老师周作人一样,很难把灵魂安放在宗教之中,宗教只能是他们建立价值关怀的一种文化资源。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从最为本质的动因来说,中国现代作家希冀在各类宗教那里寻求的,乃是一种精神的避难所,他们急于解决的是作为现代个体的信仰危机。”[20]废名也是如此,虽然他多次大谈自己如何信佛,但是从他的诗中却透露了人间情怀,表现了诗人对于“色界”的留恋。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其中,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进入20世纪之后,佛教的影响遭到削弱。“当以文学介入现实政治成为时代创作的主流心态时,像佛学这样以了脱生死为目的,以探求人生根本问题为宗旨的文化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制约就会被削弱甚至淡化。”[21](P5)废名的诗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异军突起。废名新诗的创作量并不大,但是因为他的诗中饱含禅意而在新诗诗坛上独树一帜,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禅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史上,诗人大多都把视野投向西方,以西方文化为诗歌创作的文化资源,废名却返回中国传统的佛禅精神,希望以此来弥补这个时期“形而上文化层面的缺失”,[22]从而使他的诗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品格。
参考文献:
[1]废名.阿赖耶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废名.阿赖耶识论·序[A].阿赖耶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冯健男.说废名的生平[J].新文学史料,1984,(2).
[4]药堂(周作人).怀废名[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5]郭岚芬.独特的人生关注——论佛禅文化思想对废名小说创作的影响[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
[6]废名.〈天马〉诗集[A].废名文集[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7]废名.〈妆台〉及其他[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8]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周作人.山中杂信·六[A].周作人经典作品选[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10]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A].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11]贺仲明.在传统中间寻找异路——论废名的方法学意义[J].人文杂志,2010,(1).
[12]罗振亚.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评废名的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2).
[13]废名.说梦[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14]卞之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J].新文学史料,1984,(2).
[15]张节末.禅宗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6]废名.论新诗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7]刘勇,李春雨.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J].中国文学研究,2007,(1).
[18]刘皓明.废名的表现诗学——梦、奇思、幻和阿赖耶识[J].新诗评论,2005.
[19]张洁宇.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20]张桃洲.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格[J].江海学刊,2003,(5).
[21]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2]杨春时.文化转型中形而上的缺失及其代价[J].文艺评论,1996,(5).
(责任编辑王碧瑶)
On Zen Connotation in Fei Ming’s Poems
LIU Jixin
(School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Province)
Key words:Fei Ming, poetry, 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