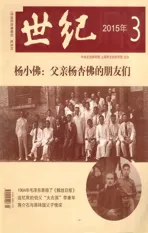杨兆龙与司徒雷登、庞德——民国政府末任最高检察长杨兆龙(六)
2015-03-08郝铁川
郝铁川
杨兆龙与司徒雷登、庞德——民国政府末任最高检察长杨兆龙(六)
郝铁川
“特务嫌疑”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复旦大学给杨兆龙所拟的三大罪状之一,但罪证却没有列出一条。相反,他一生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事情。
一生反帝爱国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别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其中捕去学生40余人,射杀学生4名,击伤学生6名,路人受伤者17名,死亡3名。6月1日复枪毙3人,伤18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这场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正在东吴法科读书的杨兆龙表现积极,被学校学生会推选为代表加入上海学生会,任该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对日本和英国当局的谈判交涉,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赔偿受害者家属损失。这是杨兆龙第一次参加反对日本英国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学生运动。
1929年经老师吴经熊推荐,杨兆龙受聘为租界临时法院推事(法官),专办华洋诉讼案件,并受其师委托撰写《上海租界法院成立以来办理涉外事件之报告》。任职期间,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坚决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对为非作歹、触犯刑律的洋人依法判决,绝不宽纵,因此常与陪审的外国领事发生冲突。创办于1864年的英文《字林西报》曾多次报道杨兆龙的事迹,盛赞他为“公正的青年法官”。杨兆龙在自己的自传中说:“外国领事团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故向南京司法部提出条件,即不准我(杨)在改组后的法院任推事,司法部部长魏道明屈从外国领事之要求,将我去职。”
1936年日本加紧侵华,国内抗日呼声普遍高涨,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富有爱国思想的杨兆龙,决定放弃原定赴俄、波、捷考察之计划,结束在柏林大学之法学研究,于这年夏季毅然回国,投身抗战。他一边为政府起草抗战所需要的法律文件,一边撰文呼吁废除领事裁判权,先后发表了《领事裁判权与危害民国之外籍人民》《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等论文。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海牙等邀请他到国外,他认为这样做就如同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白俄”,因此,断然拒绝。
与司徒雷登仅属一般师生关系
1916—1922年,杨兆龙在镇江教会私立润州中学读书,校长是约翰·林顿·斯图尔特( John Linton Stuart),他1866年由美国来杭州传教,后来又娶了位美国姑娘,共同在浙江一带传教。夫妇两人热衷于创建学校,选拔天资好的孩子读书。杨兆龙学习勤奋,英语特佳,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而深得校长赏识。校长特意安排了杨兆龙与他的赫赫有名的儿子——燕京大学校长、比杨年长28岁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相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经过两个阶段和两种不同评价。一是改革开放前众口一词的痛批,这是因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时评文章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二是改革开放后有人在网上发表纪念他的文章,觉得毛泽东的文章有点冤枉他。司徒雷登约在1954年撰写的《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也于201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底写着这样一段话:“司徒雷登,他因毛泽 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在中国家喻户晓,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他是名副其实的‘燕园之父’,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奔走呼号,由燕京大学奔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全部是由他指示校方解决路费的。1949年,回到美国的他患上了脑血栓,此后的13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伴随着他,直至去世。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因为,在中国安葬是他的意愿,他评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毛泽东当年对司徒雷登的评论错了吗?大体没错。首先,毛泽东没有抹杀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和抗战事业所做的贡献。他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表明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贡献。他当年在美国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建立了燕京大学(当时共花费360万美元建成),任校长和校务长27年。据统计:燕大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表明司徒雷登曾经是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率领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这才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宪兵第二天就逮捕司徒雷登,他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在其《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一书中也说道: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主持下,“不像其他大学那样直接处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下,学生的活动受到种种干扰和镇压,学生很容易被逮捕和监禁”。燕大的外国教授多数能明辨是非,秉彰正义,同当时普通美国人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反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燕大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学生的抗日思想得以较自由地抒发,燕大学生在当时的北平学运中实际上处于前卫和骨干地位。

其次,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坦承,司氏原来赞成中国按照西方两党制那样建立一个国共“联合政府”,他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当时觉得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他在该书中写道:“共产党军队在1949年取得胜利,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共产党在人民面前的姿态是争取信任、广交朋友。不管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还是国外观察家,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中国民主化,并努力使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政治宣传上,共产党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致力于‘土地改革’的党派,一个不受莫斯科控制的有上进心的党派,同时也不受共产国际管理、不受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摆布。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共产党,它只是‘土地改革家’。”(见该书第238页)因此,司徒雷登认为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以他想适度支持中国共产党,制约国民党,建立西方两党制的国家,同时也防止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妨害美国反苏的国际战略。司徒雷登的这种态度也是美国政府一个时期的想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他们想象的那种政党,而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政党,根本利益不同于美国,因此,他们立即改变了政策。对此,《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写道:“后来,一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指示到了我手里,该指示声称,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此改变。共产党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中国又有特殊的历史、人口和其他因素,如此庞大的人口,让极权的手段无法覆盖整个国家,而有些共产党人的心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一切是否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见该书第195、196页)
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这种改变是支持的,他也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1949年10月,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是否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政府垮台了,不要再理会它了,主张承认新中国,而司徒雷登却说:“我出席了整场会议,这些人的话使我感到气馁。我之前也说过,虽然国民党政府是有错误的,但是它始终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革命才诞生的。长期以来,国民政府被异己分子,特别是共产党所攻击;而在国际上,它又受到日本等国的外交压迫和武装侵略。可谓是内忧外患,所以它是无暇顾及‘国计民生’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抗战8年后,面对以苏联为后台的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时,国民党军队无法团结一致进行有效的对抗。这也导致了它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最终不得不撤离到台湾。但是在这次该死的会议上,大家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国民政府的身上,从未考虑过国民政府的处境。”(见该书第234、235页)
杨兆龙一生只与担任大使前的司徒雷登交往过。杨兆龙在给组织的自传材料中,主动提到过和司徒雷登的交往。杨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与心理学专业,学制四年,但他仅用两年即修满学分提前毕业,成绩优异,获哲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司徒雷登对他说,你学的哲学心理学搞研究可以,但解决就业吃饭问题比较困难,建议去学法律,这样好谋生。司徒雷登的话也正合杨兆龙的心意。他曾阅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深觉哲学与心理学不能救中国。经司徒雷登的推荐,赴上海东吴法科夜校求学。杨兆龙女婿陆锦璧教授告诉笔者,燕京一别,杨兆龙除了参加过一次司徒雷登的宴会之外,就再也没有和司徒雷登交往。毕竟司徒雷登的活动领域是外交,而杨兆龙的活动领域则是法律。
因此,杨兆龙和司徒雷登的交往属于学生和老师的正常交往,是司徒雷登从政之前的事情。在这里当然找不到“特务嫌疑”的依据。
希望借助庞德推动司法制度改革
杨兆龙做过律师,深知当时中国司法之黑暗。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所做的博士论文题目即为《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制度之比较》,论文对中外司法制度广泛比较,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改革中国现行法制的创见。答辩会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教授亲自主持。历时四小时的答辩,赢得了评委专家一致的赞赏,论文被评为优秀。庞德对杨说:“你是接受我考试的第一个中国人。东方人的思维方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庞德说,你对英美法系已有了解,但还应对大陆法系进行研究。因此推荐杨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随库洛什(Krauoch)教授研究大陆法。
杨兆龙认为:“司法为亲民之政,人民生命财产之所系,颇受社会之重视。政治之良窳,每于此觇之。”他从国外留学回来后,相继发表《关于疏通监狱之研究》《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等文。抗战一结束,他就向当局提出聘请世界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推动司法制度改革,获得政府允准。
1946年6月庞德夫妇到达中国。经过短期考察,7月12日在杨兆龙的协助下,庞德就初步完成的研究工作提出四点建议:(1)中国现行的大陆法系异常完美,仍应保持。一般浅识之外人改革法系之意见,均不足采。(2)现行法典大体完善,法律思想亦颇进步。(3)中国人应对自己抱有信心,不应盲从外人,尤应于最短期内创造、培养合于自己国情之法律制度。(4)关于解释法典巨著中国犹付阙如,今后应聚集有名学者潜心研究,合力完成此类伟大著作,以免法律适用时发生困难。因若无此等巨著,则不仅许多法律问题不得解决,即法律生活亦将不能统一。
8月7日,庞德在杨兆龙的协助下,草拟完成创设“中国法律中心”计划纲要,建议中国成立研究中国法律的中心组织,编写《中国法通典》。8月20日,又提出关于改进中国法律教育问题的报告。司法行政部根据其建议,曾决定邀请国内法学专家编纂一套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法律教科书,以利于培养法律人才。名义上由谢冠生主持,实际上由杨兆龙与庞德合作来推动此项工作。意见可归纳为下列数点:(1)保留本位法系,加强法律教育,储备司法人才;(2)提倡法律著述,统一法律解释;(3)法律应作弹性之规定,留有解释余地;(4)法律学校不仅训练法官律师,并且训练文官和外交官;(5)鼓励中国法律专家(包括法学教授、法官、律师)注释中国法典。由司法部主持其事,其机构可称为法律中心;(6)专家由主持人聘请,组织七至八人委员会,用以解决学术上之争议;组织三至五人小组,襄助或指导专家从事著述工作。
1947年9月,庞德作为司法行政部顾问再次来华。在11月召开的全国司法行政会议上,庞德和杨兆龙联名提交三项议案:《请确定简化司法程序之基本原则案》《关于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的承接与赔偿如何实施案》《关于人民身体自由之保障程序如何实施案》。这些提案大都获得会议通过,交由职能部门办理。
1948年5月司法行政部设立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制实际调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纂等工作。委员会下设“法学著作编纂委员会”和“司法调查团”。法学教科书的编纂一事由庞德、杨兆龙共同主持,司法调查团由两人分任正副团长。从1948年6月开始,庞德、杨兆龙率领的调查团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司法情况调查。这年的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庞德,因为国共内战、局势动荡原因,要他中断在华的讲学和调研活动,返回美国。
学术界对庞德的评价是:他一生从学者、教师到法学院院长,几乎是整个法学领域最博学的人,能够通晓所有法律部门。他即使在做院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缺过学生的课,甚至当有的教员生病了,他可以直接接过这门课,讲出令人满意的效果。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法学大师。
庞德没有搞“全盘西化”的企图,反而提醒中国要注意英美法系的弊端,保持既有的罗马法系模式而不应采用英美法系;应该通过统一法律教育和法律著述,培养中国法律人的法律适用能力,使得制定良好的中国法典成为真正规范中国人民生活的法律。各种评论都认为庞德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法学家,不像司徒雷登那样有过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经历,没有参与过政治党派活动。杨兆龙与其交往,属于学者和技术官僚之间的业务交流,不存在“特务嫌疑”活动,也找不出“特务嫌疑”证据。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下,莫须有的“假想敌”难以避免。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1940年在哈佛读书时见过陈立夫,并为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教过一年日文。为此,解放后周一良写过一页又一页的解释文字,说明他只是代表中国留学生出面,要求陈立夫和美方交涉,免服中国留学生兵役;而他给美军上课,只是专为美军训练对日作战的翻译,并无其他政治活动,但这很难说服组织的怀疑,入党问题长期被搁置。1955年,周一良随同翦伯赞到荷兰参加汉学家会议,意外见到30年未见的堂姑母周仲锦,周仲锦请吃饭,周一良生怕以后说不清自己,不敢前往,回国后即向组织汇报。北大西语系教授季羡林1935年开始,留学德国10年。当时正值希特勒统治时期。季羡林虽于1950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因这段历史情况复杂,无法搞清,也长期被搁置。季羡林心急之下,向校方提供了留德日记原本,供党组织查证时使用。日记中有年轻时经历的男女感情、人际评价等隐私内容,原本不便公开却变相成了不少人的阅读物。1956年北大专门派人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收集三十几份证明材料,又研究了他当时的著作和经济生活情况,证明季羡林当时就反蒋爱国,反对希特勒,因而为他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前,“海外关系”、海外经历往往是人们的“政治包袱”,而改革开放后,“海外关系”、海外经历又往往成为人们的财富。此一时、彼一时,历史居然如此捉弄人,让多少人情何以堪!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导)
责任编辑殷之俊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