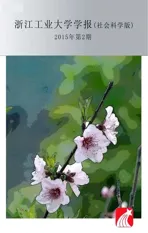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中的政府干预
——基于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
2015-01-22侯银萍
侯 银 萍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中的政府干预
——基于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
侯 银 萍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通过引入政府命令和法律实现了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通过“进入许可制”的配置方式使得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具有了浓厚的身份性。建国以来的集体土地实践表明,政府权力的过分干预与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呈负相关。我国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在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政策主导向法治主导变革的基础上。
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强制性制度供给;制度效率;限政;法治
土地制度是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权制度。从集体土地的物权构造上看,集体土地物权制度有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和集体土地担保物权等权利形态,其中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主的正式制度所规范的人们基于集体土地利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即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土地制度背后的利益分配是权利各方产生矛盾纠纷的症结所在,而公平的土地利益分配取决于土地产权的合理配置。由于国家的出现,产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因此产生了“社会租金”[1]。由政府垄断契约的保护权,有助于契约方公正地交易,有助于维护双方的意志和利益。在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政府提供的有关产权界定和分配等“游戏规则”能够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并且能够为产权交易和资产评估提供统一的标准,以此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国家作为第三方当事人,通过提供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确定产权实施和实现的基本规则。青木昌彦认为,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实施中,国家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张,国家逐渐成为产权保护和合同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有疆域内排他性和强制性管辖权,居民并不能轻易退出管辖。中央政府能够垄断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实施司法裁决,并向私人征税[2]。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然而,当统治者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不相容时,国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导致产权的低效,国家的过度干预和过度管制常常妨碍产权的充分实现,从而导致产权残缺。“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获得了允许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力”[3]。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索取高额的租金,侵犯甚至剥夺私人的产权。经济交易因此受阻或者转为地下,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甚至停滞状态。
一、政府强制性供给主导着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方式
在实行分散决策型体制的国家中,市场经济是基础,制度的演变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能否诱导出新的制度安排,取决于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4]。然而,我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大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何时变、怎样变,都是由行政权力中心定夺,继而引入政府命令和法律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这种变迁方式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
(一)层级隶属的行政权力侵蚀了农民的土地产权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是国家通过暴力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民使用的过程,也是国家建立乡村基层政权以结束松散的农村结构的过程。国家通过打击地主富农,将其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发给农民土地所有证书,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对土地的安全感,从而赢得了农民尤其是贫农、雇农和中农对党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土地改革,国家从多层面建构农村基层组织,对政权巩固和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种类型是国家在各地农村中组织贫农雇农和中农成立的农民协会,负责执行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事务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第二种类型是以乡为基础建立的以代表会议制为主要形式的乡政权;第三种类型是在农村建立的共青团、妇联等党的基层组织。各类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结束了农村“天高皇帝远”的历史,原来松散的农村结构被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正因为广大农民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加之政令统一和上下一致,土地改革得以低成本快速完成。
农业合作社阶段,农民协会逐渐被解散,农民基本丧失了表达意愿的途径;国家加强了乡政权和合作社对土地的控制;农民土地所有制被取消,农民的土地产权被严重削弱。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建立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框架下的。农民把土地无偿转归人民公社所有,由人民公社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经营,农民沦为纯粹的劳动者。人民公社体制赋予了公社一级的政府对土地的支配权,通过“一平二调”的方式也满足了县级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人财物的绝对控制。各级地方政府利益的一致为土地制度安排的顺利实行排除了障碍,而分散又无权状态下的农民只能成为制度的被动接受者。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强行嵌入,在同工同酬的土地收益平均分配模式下,内部诸多搭便车行为和消极劳作模式为奥尔森所理解的集体行动作了注脚[5]。
人民公社制度导致农民的土地产权被压缩殆尽,国家的土地制度安排使农民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农民自发的反抗行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常发生。然而,农民多次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自发行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被国家否定并抵制的。这二十多年间,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并没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制度变迁。国家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认同了个体的自发行为,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土地承包制,由此推动了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一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执政党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促使它把个体和组织理性强制推行为公共规则,并依靠其‘暴力潜能’优势来维护的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不是在社会经济自然演进基础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6]。
土地承包制是在农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制度。在我国,农民集体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公有产权。农民集体所有权并不是集体组织的农民对土地享有的共有所有权(私有产权)。农民不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份额,无权行使所有权权能。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如村委会)行使的。而现实中,集体经济组织在村委会的选举、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受到乡镇基层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形成了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政府通过集体所有制对农村土地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权。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言,我国的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7]。
(二)“进入许可制”的土地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用益物权浓厚的身份性
农村土地有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之分。在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用地的具体使用者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其集体成员的身份享有社员权,通过向集体组织申请并与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拥有使用农用地的权利。在承包期间,农户离开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地;农户对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要经得发包方的同意或者报发包方备案;流转后的登记需要向县级以上政府申请登记,否则土地的流转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者集体的农户进行非农业建设所使用的土地,包括农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等。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主体受到现行制度的严格规制,一般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的成员,包括本集体组织的农户、乡镇企业及农村公益事业单位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基于其社员身份和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用于居住,其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基本是一种无偿无期限的使用权,并具有浓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色彩。然而,农民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其拥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基础。超出本集体组织的宅基地使用权几乎是不允许流转的,既不能转让给非农村居民,也不能在土地市场交易。当农户离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时,由集体收回宅基地的使用权。
乡镇企业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可见,乡镇企业的主体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本集体的农民(或占投资比例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的设立、变动、注销均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如农村中的医院、学校等公益性事业单位需要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才可以使用。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若要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入股等方式与他人合办企业的,也必须向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政府的过度干预制约着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制度效率
(一)政府的干预强度与土地用益物权制度效率的关系
政府权力介入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方式和程度,决定了国家在土地产权中的作用。国家作为经济人的利益主体,决定了国家在土地制度中不可能中立。国家过度的干预和管制会造成土地产权的排他性和让渡性的残缺。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所无法克服的供给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其在运行伊始土地用益物权制度效率就处于下降状态,交易成本也会随着制度的运行逐渐上升。国家通过其强大的第三方实施权力供给着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政府对土地产权制度的干预强度,控制着土地产权制度的运行状态。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维护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适当的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下降,但是绝不是干预的越多越好,这里存在着政府干预刚性。在政府干预与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临界点范围内,政府干预的增强有利于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维护,但是超过这一临界点之后,政府干预的增强会导致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快速下降。因此,国家作为资源要素的过度利用,表现为政府权力的过分干预,这必然会造成土地产权制度的加剧低效甚至无效。政府权力的过分干预与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二)政府干预对土地使用制度效率的影响
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所有、农民租佃经营”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通过政治运动直接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并无偿分配给农民。国家通过政府干预授予农民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下的“土地使用权”。农地产权的重新配置虽然是由国家主导完成的,但是国家在农地产权结构中的所占的比例很低,农民拥有相对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客观上,农民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改变了当时土地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所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权利配置严重失衡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高效率,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1952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48.5%,年均增长14.1%,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1951 年全国人民购买力比上年增加 25%左右[8]。
随着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和城市土地全面国有化的形成,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得到空前强化。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土地各领域并成为土地要素的决策者、支配者和收益者。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不断加强,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在不断快速下降,国家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在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比例甚至一度接近100%[9]。土地权利的剥夺带来了人们土地获利空间的丧失,人们对土地投入的动力不复存在。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造成土地产权制度的低效,继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整体经济的倒退。农村中人均粮食产量直到1979年仍无法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人们的消费水平在1960年初到1980年的20年间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而这段时期的耕地面积连年持续下将,人均耕地面积由1958年的2.43亩下降到1982年的1.46亩,下降了40%[10]。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调整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强度和对土地产权结构的占有比例,降低了政府权力的干预程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期限上不断延长,“两田制”、“土地入股”、“土地抵押”等权利流转方式的试行,使其权利结构不断完善。这些均表明了政府权力对土地产权制度的干预较前一阶段有了很大程度的减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我国土地市场的迅速发展,继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
然而,随着全国城市化的发展和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政府对土地产权制度的控制仍处于较高的水平。这表现在政府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导致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产权不对等;政府征收作为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唯一途径,导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入市流转以及农民和集体的土地收益受损等等。这些问题表明了现阶段政府对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干预制约着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效率,政府权利的干预仍然有很大的降低空间。
三、“限政”与“法治”是规范政府干预的治理之道
当前,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面临的问题广泛涉及政治、法律、经济、人口等多个方面。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框架下运行,土地用益物权制度才能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制度价值。这需要完备的宪政体制支撑。因此,我国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在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政策主导向法治主导变革的前提下。对于政府而言,宪政意味着政府受到宪法的约束与控制,政府权力不能超越宪法的规范,对于公民而言,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人们的财产权利和交易自由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政府对人们财产权利的限制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宪法依据,这样人们能够运用法律武器对抗政府的干预。
(一)“限政”是实现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的基石
“限政”即有限政府,是指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的政府[11]。有限政府体现了宪政的本质和目的。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有限政府以保护私权利为宗旨,以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为目标,并成为现代政府理论的有益发展模式。虽然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政府是不存在的,但一个权力过大的政府难免会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一个腐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政府必然会严重威胁或者侵害到个人的财产权。
土地作为日益稀缺的资源,对国家和政府的意义越来越重大,政府并没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它本身也是经济人[12],自然具有占有土地的欲望和动力。政府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和动力去扩张政府的范围和规模[13],在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政府缺乏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必然会导致政府的土地权力愈发膨胀,个人享有的土地权利日渐萎缩,个人在土地用益物权具体权能的享有和行使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逐渐加重,以致最终丧失独立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可见,土地用益物权的明确界定和权利的自由行使离不开对政府权力的有效限制。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有限政府的实现:
1. 完善集体土地的市场配置。市场经济是合乎自然与人性的、天然的自由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的市场配置可以自发地运转、自动地配置、自动地调节土地资源,弥补土地权利主体的有限理性,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实现土地权利主体的利益需求。稳定健全的土地市场配置能够有效遏制政府权力的扩张。纯粹的市场配置与纯粹的政府管制都是不完善的,但相比较而言,政府比市场更加危险,政府的作用应当仅限于充当市场竞争的裁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缺陷。在土地的市场配置中,属于土地权利主体之间私人领域的事务,即便政府管得了,政府也不应插手。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空间与市场的配置空间是零和格局,留给市场配置的空间多一些,政府干涉土地问题的空间就相应少一些。对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而言,营造一个自由竞争、繁荣的农地市场配置局面,使政府权力仅限于对市场经济的政治表达,这样有利于减少政府权力对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侵犯,从而保障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的私权。
2. 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土地权力的范围。在我国公有制体制下,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由中央政府代表行使权利,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拥有支配土地的实际权力,却没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权力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责任仍然由中央政府承担。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土地权力范围,明确两者在土地权力行使和土地管理方面的职责,才能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土地权力的滥用。在我国,各地方政府拥有较为固定的管理地域和管辖人口,各地区的公民对来自政府的侵权,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予以制衡,公民相对政府的弱势,导致了土地私权利的弱势,地方政府不需要讨好公民,也就不会积极维护公民的土地私权利。在处理土地问题时,牺牲土地用益物权人的权益就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土地权力范围能够减少政府的越权行为,预防政府对人们土地权利的侵犯。
3.健全独立的司法和监督体系。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4]。有效的权力制约能够避免政府权力的滥用,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威胁,降低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三权分立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即在于通过权力的分立制约保持了权力的均衡。司法权制约政府行政权的前提是司法权的独立。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的创始人孟德斯鸠认为,当立法权与执法权集中于一人或同一机关时,当司法权不能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分离时,自由也就不存在了[15]。可见,没有司法的独立就没有司法的权威性可言。
在我国,集体土地用益物权方面的纠纷和诉讼,数量大、涉及范围广,人们对政府的意见较大,许多纠纷和诉讼在主体上是民告官。然而,司法部门在处理这些土地纠纷时,普遍存在捍卫法律尊严无力、保障公平正义无能的现状,司法判决远远没有达到维护法律秩序、正义、效益等应有的社会效果,上访不断、围堵政府、聚众闹事等不稳定事件随处可见。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把司法机关视为中立的纠纷解决者,而是把它看作是其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唯有司法与政府彼此独立,司法才能实现尊重法律、制衡权力、救济权利的神圣使命和应有功能。同时,政府对土地享有的权力还应当置于社会公共监督之下。对政府而言,社会公共监督主要体现为一种他律监督机制,即政府对土地的权力行使和管理要受到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机构及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16]。有效的社会公共监督机制能够防范政府权力行使中产生的寻租腐败、资源浪费和管理低效等问题。
(二)“法治”是维护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的屏障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保障公民财产权和制约政府权力。法治与有限政府是推进宪政改革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法治的要义是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赋予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法治政府在对公民采取不利行为之前,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律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必须是明确和公开的,而且政府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付诸实践。可以说,法治为公民权利创设了一道防护墙,使其免受政府的侵扰,并确保他们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不必惧怕国家和政府。通过创设这道防护墙,有力地保障了公民财产安全和人格独立。
1.法律规范应具有最高的权威。在土地问题上,我国有着过于依赖政策,忽视制度的传统。虽然政策具有灵活、高效、果断的优势,但政策容易造成行政权力过大、裁量权过大、法制被束之高阁等恶果。法治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治国之道,即主要依靠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而不是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政策的作用只是法制的辅助,政策的规定不能逾越法制的框架,政府的行为高度制度化。制度化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现成的宪法和法律,更在于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具有遵守这些法律和制度的观念。制度立场的中性既有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扩张,又充分维护了私人领域的权利自由。
2. 法律规范应具有公正性和规范性。宪法在内容上应当符合法治精神,即民主政治、权力制衡、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17];法律在实体上应体现法律的原理、规范和理想,并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正义和公平,在性质上应属于“良法”[18];在形式上,实现法律之间的衔接和互补,形成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在我国,规范土地用益物权的宪法、法律及相关法规之间不乏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规定,甚至出现下位阶法律规范违反上位阶法律规范的现象;一些重要的土地用益物权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仍缺乏相应地方法律规范;这些导致实践中土地用益物权的基本权利无法可依,具体法律适用混乱,没有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引证,因此产生的纠纷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可见,在法治要求下,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安排应当兼具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1] 詹姆斯·M·布坎南.财富与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7-79.
[2]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53-155.
[3] 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A],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8-189.
[4] 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发展研究,1992,(4):24-27.
[5] 叶国文.农民、国家政权与现代化——当代中国土地政策的政治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110-113.
[6] 罗红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1949-2008)[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249-252.
[7]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10.
[8] 王琢,许浜.中国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与耕地绩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0-16.
[9] 赵德起.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分析——国家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07,(6):72-80.
[1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320-329.
[11] 肖勇.论“有限政府”[J].社会科学研究,2003,(2):23-25.
[12]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Ⅱ[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2.
[13]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33-636.
[14]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5-108.
[1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0-156.
[16] 张中祥.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价值.过程.结果[J].南京社会科学,2001,(3):34-38.
[17] 吴敬琏,等.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法治不一定有宪政[J].同舟共进,2008,(7):7-10.
[18] 陈国权.论法治与有限政府[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5-9.
(责任编辑:金一超)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System Arrangement of the Collective Land Usufructuary Right
HOU Yinping
(College of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Modern property rights are based on the state. Rural land use system belongs to a top-down mandatory system changes and has strong identity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country, the practice of the collective land has demonstrated that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efficiency. The reform of the collective land usufructuary right must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unlimited government to limited government and policy-oriented to the rule of law leading.
the collective land usufructuary right; mandatory system supply; system efficiency; limited government; the rule of law
2014-11-17
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2015Z018)
侯银萍(1978-),女,江苏徐州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民事法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
D912.3
A
1006-4303(2015)02-01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