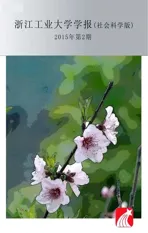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以埃及为例
2015-01-22褚蓓娟
褚 蓓 娟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以埃及为例
褚 蓓 娟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中国文学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的发展,高校教学成为中国文学在埃及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埃及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大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加强了中阿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学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国文学追求的审美价值的普适性,深深地吸引着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埃及人,对埃及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中国文学的对外输出总量相比,中国文学在埃及的传播还很薄弱,加上文化的差异,民族信仰的区别,大多数埃及人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因此,加强对阿拉伯世界的中国文化传播还需继续努力。
跨文化;中国文学; 海外传播;埃及;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成立之后的海外汉语教学包括了语言教学、文学教学以及中国文化方面的普及传播等等方面,本文只限于讨论文学在埃及的传播状况,不涉及语言方面。
一、中国文学在埃及高校中的教学
中国文学在埃及高校中的教学传播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埃及是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立中文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目前,埃及有苏伊士运河大学(Suez Canal University)、 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 、 爱因夏姆斯大学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阿勒旺大学(Hellowan University)、米尼亚大学(Minia University)等10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系统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其中爱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历史最为悠久,早在1958年就已设立中文系,由于中东战争而导致的经济困境,一度中文系停开。1977年重新开始建系招生,1981年首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现在爱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学生数最多,本科在校生总数达1000余名,历届毕业生分布于埃及的教育、文化、旅游、文教、工业、投资等各个领域。而开罗大学和苏伊士运河大学除了中文系之外还分别设有孔子学院。在设有中文系的学校,都有足够的中文教师,这些中文教师均来自中国的高等院校,具有一定的高校教学经验,有比较高的职称,保证了埃及高校中文系的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达到16小时/周,而学习英语和阿拉伯语共计4小时/周(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爱因夏姆斯大学可谓埃及汉语教学传播的航母,除了学生数量众多,遥遥领先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师资力量强大,汉语教师不仅人数多,而且都是埃及本土教师,学校设有中文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除了爱因夏姆斯大学之外,每所高校历届汉语学生人数在100人之内,其中,近两年学生数有明显增加趋势。
① 数据由开罗大学孔子学院闫国娥老师提供。
② 数据由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主任默罕默德·阿里博士提供。
③ 数据由爱资哈尔大学教师兼任阿斯旺大学中文系主任阿齐兹博士提供。
④ 数据由爱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穆赫森博士提供。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肩负孔子学院和中文系的双重教学任务。开大孔院除了向学生传授中国文化知识以外,还承担着埃及汉语学习者各种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的任务,如全埃及大学生的中文故事比赛、中文小品赛、国家汉办的汉语桥比赛、埃及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各种教研活动,各种汉语学术研讨会议等等,在埃及的中国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的组织者作用。开罗大学中文系目前在校生既有本科生,也有中文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苏伊士运河大学是一所政府主办的公立大学。尽管其所在城市Ismailia的汉语就业状况并不乐观,但学校从长远利益出发,早在2006年就设立中文系,积极发展中文教学。2008年与中国华北电力大学签约合作孔子学院,2014年与北京语言大学签订了新的合作关系。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善于利用孔院教师的中文教学资源,全部启用中文教师授课,以至于在最近几年中,名声大震,入学率不断提高。在埃及高校中,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以师资力量为全外籍教师作为显著特征和招牌,吸引了来自全国热爱汉语的学生,周边的塞得港、苏伊士、塔坦等城市的学生更是慕名来苏伊士运河大学求学。孔子学院在苏伊士运河大学除了承担孔院的教学任务外,还为中文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汉语言专业学生。
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运行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各种配置基本成熟,系主任由复旦大学毕业的默罕默德·阿里博士担任。中文系拥有中文图书资料室,中文藏书超过一万册,各种影像资料数百种。课程设置日趋合理并稳定,1-2年级的课程以汉语拼音、语法、阅读为主,主要任务是完成认读写汉字;3-4年级的课程以文学和文化历史为主,分别有中国历史文明、中国现代文明、中国诗歌、中国戏剧、中国小说等。目前,汉办给海外孔院配备的《长城汉语》、《新实用汉语教程》、《跟我学汉语》等教材多达数十种,不过,毫无例外地这些教材都属于语言类,文学方面的教材几乎没有。埃及所有高校中文系的文学类课程,都是教师自行编写讲义,这样,每一个大学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就不尽相同,且讲授内容也不相同,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通过自编讲义传授中国文学。在苏伊士运河大学,文学课的教材是教师根据学生的汉语程度和实际上课周数,编写针对该校学生的讲义。讲义有很大的灵活性, 一般提前一周编写好下次课的讲义并发给学生预习。在编写过程中,教师按照中国高校文学教材的编写体例,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逐一精挑细选,力求系统、简洁明了。重点编写作家和作品,如,古代文学必讲作家和作品有:屈原、李白、杜甫、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诗经》《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战国策》《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现当代作家有胡适、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王蒙、莫言、余华、北岛等。锁定内容之后,就是语言上的锤炼,尽量措辞简单,并富有文采,镶嵌成语和多种修辞手法于其中,便于学生在学习文学经典的同时,获得语言文本的美感。
通过音像资料直观地传播中国文学。很多现代文学已被拍成影视,教学中,教师借助影视资料,让学生对原作有更直观的了解。如分析《骆驼祥子》时,教师解释 “人力车夫”这个概念,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用图片来展示也未必有很清楚的效果,看了视频资料之后,什么叫车场,什么叫“人力车夫”,什么叫“臭拉车的”,什么叫“黄包车”,什么叫“拉包月”, 学生一目了然,然后讲解祥子“三起三落”的拉车人生和情感转折点,讲解完毕,由学生根据故事梗概复述祥子故事。看了视频的学生,理解能力明显增强,基本上能够运用手中的学习材料,复述小说内容,并能很好地把握小说情节发展的起伏变化和人物的情感变化。
综上无论是在行业政策的大背景下,还是就贵冶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具体需要来讲,编制企业定额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该厂也有能力来做此项工作。
通过学生复述故事检测所学内容。如讲解了鲁迅和他的小说之后,要求学生复述《故乡》中闰土的故事。学生复述时,教师主要观察并指导学生对小说情感的把握,对闰土形象的理解。透过学生对小说复述的熟练程度、情感表达能力,可以检测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化程度。
通过课外活动巩固所学内容。课余时间,举办诗歌朗诵、话剧改编、戏曲表演、歌唱比赛等丰富有趣的活动,巩固所学内容,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学的热爱。80%的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大胆表演,施展才华,有的学生邀请妈妈、弟妹、朋友一起参加,无形中扩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并有效地为汉办的“汉语桥”大赛、大使馆的各项活动储备和输送了人才。
二、中国文学在埃及的翻译
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和传播,离不开翻译和介绍。虽然语言不通,文化迥异,但人类的思维和感情存在着共性,有效的沟通可以达成共识,建立和谐互补的共存关系,因此,通过翻译进行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沟通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中,文化是翻译传播的内容,翻译传播则是文化的羽翼,异质文化借翻译而传播、交融和延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网络媒体每天都通过几十种语言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发布中国的最新消息。要想让更多的国家了解自己,翻译是重要的途径。
现代史上中国文学远播埃及的功臣是阿拉伯语泰斗、北京大学教授马坚(1906-1978)先生。马坚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爱资哈尔大学大学工作学习了8年,他不但培养了一批精通中文、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埃及学子,还把中国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论语》、《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译成阿拉伯语在开罗出版,给阿拉伯丰富的文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珍宝。更值得称颂的是,马坚先生研究和翻译的领域,使中阿文化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他把中国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让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他撰述和翻译阿拉伯典籍以及文学哲学为中文,不仅提高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水平,而且向中国传播了阿拉伯世界文化,他翻译的《古兰经》中文版至今依然无人超越。马坚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翻译中文作品经由英、法等语言转译的历史。但是杯水车薪,直至二十世纪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中国文学译本,基本上还是学者们通过其它语言转译而成。
埃及学者通过英译本的《道德经》《易经》《庄子》《孙子兵法》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也逐渐对这个东方国家产生兴趣,于是,唐宋诗歌、明清四大名著陆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有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有多种译本,如《道德经》的译本有6种,但大部分作品都是通过法译本、英译本甚至德译本转译。这种现象得到改观是在20世纪90年,一批当代埃及学者和翻译家出现之后。
哈齐兹(ABD ELAZIZ HAMDI)博士,埃及当代著名汉学家、现任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阿齐兹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熟知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翻译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二十余部。主要有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铁凝、艾青、余华等作家。代表译作有《鲁迅小说选》《茶馆》《日出》《边城》《艾青诗选》《永远有多远》《活着》等。他曾告诉笔者,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作品。他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选择之前要考虑各种综合性因素,要考察它是不是能透过作品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要预测它能否被埃及读者接受。阿齐兹说,很多人在读了《日出》之后被作品中人物打动,为人物的命运担忧,有读者不断地问“小东西怎样了?”阿齐兹曾三次拜访曹禺,为曹禺创作中表达的人类共性而感动。2015年2月,阿齐兹的译作《活着》在科威特出版,不到一个月,译本在埃及就销售一空。阿齐兹指出,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如果是一个穆斯林,阿拉伯人就很好理解,因为心中有信仰,所以生活有希望;可是,福贵没有宗教的寄托,他的坚韧,让阿拉伯人很佩服,阿拉伯人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精神,值得学习。哈齐兹的文学翻译为阿语国家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门。2009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及时给予哈齐兹高度评价,亲自授予他“中埃文化交流贡献奖”①笔者根据访谈译者整理。。
穆赫森 (Mohsen Sayed Fergani) 博士,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因夏姆斯大学教师。穆赫森博士擅长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古典文学则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具有独特的魅力。他是第一个用阿拉伯语把《道德经》翻译到埃及的学者。此前《道德经》在埃及已经有5种译本,但都是从其它语种转译而来,穆赫森的译本不再借助于中介语,译作出来之后,深受埃及著名小说家杰麦勒·黑托尼先生赏识,立即在权威期刊《文学消息》先行刊载。近10年来,穆赫森陆续翻译出版了《道德经》《战国策》《四书》《列子》《孙子兵法》《离骚》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近两年,穆赫森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先后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牛》《梦境与杂种》《幽默与趣味》等作品,穆赫森的译本尽可能追求莫言文本中的智慧与审美。2013年穆赫森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奖”。对于翻译,穆赫森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着多重角色:首先,译者以读者的角色研读原作;其次,译者以作者的角色再现原文。穆赫森明白,译者为了达到对原作的理解,不仅需要驾驭语言和句法的能力,而且要有一种跨越不同文化的眼界,因为,作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传播文化的职责。他的译作更注重文化内涵。
哈赛宁(Hassanein Fahmy Hussein) 博士,爱因夏姆斯大学大学讲师,现受聘沙特国王大学,2008年获得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哈赛宁求学期间,系统地梳理了中埃两国文学的发展关系。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傅谨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以及《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实验剧》等, 2013年荣获埃及国家青年翻译奖。
这三位译者是活跃在埃及翻译界的当代代表,他们都是高校的学者,熟悉汉语,精通中国文化,慧眼挑选中国文学中的精品,把握中国文学的最新动态,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文,保证了译作的质量,是沟通中埃文化的桥梁,为传播中国文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文学在埃及的接受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商贸通道,同时也建立了良好的中阿文化往来关系。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绵延数千年,至今依然散发着活力。当前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为 “21世纪的中阿商贸新通道”。
9世纪左右,阿拉伯人苏莱曼·塔吉尔在《中国印度见闻录》②1 .+里用阿拉伯语记录了他在中国和印度的见闻,详细介绍大唐帝国和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书中赞美中国人的心灵手巧,赞美中国薄如蝉翼的丝绸、 晶莹剔透的瓷器和略带苦味的茶叶……。作者满怀好奇之心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或许,苏莱曼·塔吉尔是最早向阿拉伯世界打开中国之窗的阿拉伯人。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①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从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再一次系统地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这是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至今被许多学者引用,它成为研究元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埃及现代作家马哈穆德·伊勒·巴达维(Mahmoud El Badaway,1908-1986)曾在中埃建交之后,作为第一批埃及文化代表团的作家成员访华,回去后他写出游记《梦想之城》,这本游记可以看成现代阿拉伯人对新中国的解读。书中盛赞中国物产、城市和淳朴的中国人民。中埃相似的社会背景促使巴达维经常把他看到的中国情景与埃及生活相对比。北京人的工作,北京的古老建筑,上海的现代,杭州的街景、西湖的清冷,南京中山陵的雄伟和肃穆,都让这个埃及人感慨万分。阿拉伯作者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不仅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了解外国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重要资料。
“埃及现代小说之父”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对中国文化也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很多阿语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论语》《骆驼祥子》等,他曾在自己的《开罗三部曲》(《两宫间》《思慕街》《怡心园》)中译本首卷中写过一篇《致中国读者》,文中写道:“《三部曲》译成中文,为促进思想交流与提高鉴赏力提供了良好机会。尽管彼此相距遥远,大小各异,但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于此项译介工作,我感到由衷高兴,谨向译者表示谢意。我希望这种文化交流持续不断,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我们的图书馆占有席位,以期这种相互了解更臻完善”②丁淑红:《“他对我们来说,更有亲近之感”——浅谈马哈福兹作品在中国的译介》,2012年4月16日《文艺报》。。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恳切地表达了对翻译和文化交流的渴望。
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上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都走过了曲折和漫长的帝国发展路程,经历了现代社会列强侵略的惨痛历史,太多的相似性使得这两个国家始终有一种文化上不言而喻的默契。
相似的民族历史使得埃及人很容易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共鸣。1914-1952年,埃及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952年,纳赛尔的军事政变之后,迎来了埃及的独立,但是从1953-1981年的30年时间,埃及人民历经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为独立和自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断的战火和动乱严重制约了埃及经济的发展。最近30年,埃及处于政权不断更迭中,局势动荡,社会混乱。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相对比,埃及感觉两国历史既异常相似,又发展迥异,尤其近30年,曾经多灾多难多相似的两国,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让埃及人民很是羡慕和敬佩。他们带着渴望民族发展的愿望,愿意接受一切新鲜事物,主动积极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一方面派大量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另一方面,埃及大学中文系的入学率在逐年显著增加。官方组织或出资,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在爱因夏姆斯大学,已形成翻译中文的学者团队。新闻出版总署、外文局以及中国的一些出版集团近年来和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 “图书翻译出版及文化项目合作协议”等多项合作项目。目前,国家汉办在二十二个阿拉伯国家设立了9所孔子学院,而埃及一个国家就占有2所,无论在非洲国家或是阿拉伯国家中这个比例都是很高的,孔子学院的设立当然也与当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紧密相关。
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埃及人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读到了自己的影子,从文学中关照自身,反省自我,成为很多埃及学生阅读中国文学的目的。
相似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得埃及人更愿意从中国文学中关照自己。埃及84%的人信仰伊斯兰教(16%的人信仰科普特基督教,也称正统教),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是融沙漠游牧文明与绿洲农耕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于一体的文明,地域、气候、种族、生活方式等等铸就了他们的刚毅、冒险、奋斗的精神气质,也铸就了伊斯兰人民的直率、自信、开朗、外向的性格。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具有坚韧、内敛、大度的气质;委婉含蓄、温柔敦厚的性格。看似迥然不同的两大文化圈的人民,在经济发展、民族富强、捍卫和平的观念上是一致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交汇点和契合点,有许多虽不完全相同却能够相通的地方。
中国文学里体现的民族气质和性格,虽然无法从宗教的角度阐释,但那散发着人类共通的情怀和精神同样吸引着异族异文化的阿拉伯人。“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管是笃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人,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都谨记着先知穆罕默德在创世时的圣训,这句格言至今在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广为流传,正是其中相互理解和相互默契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
埃及是非洲乃至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而且两国关系日渐笃厚。我们对埃及的传统文学和文化做了大量翻译和传播。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在埃及的传播还很薄弱。高校中的中国文学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手段,至今没有系统的教材可依;来华留学的埃及学生主要是政府间教育协议或者是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资助,仅限于少数的公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非常少;中国文学在埃及并没有形成广大的读者群,在全埃及的各大小书店,很难觅见中文图书的踪影,在埃及的各类图书馆,中文书籍微乎其微,即使有,也鲜有人问津;中国电影、电视剧极少以版权输出的方式在阿拉伯国家上映;中国电视内容,虽然有阿语和英语的国际频道,但在埃及可供选择的频道达150多个,文化和地域的差异决定了他们选择的视域;文学翻译,只限于少数人的个人行为,虽然有中埃两国的一些合作协议,翻译的中文作品也只限于少数从事研究的人阅读,并没有引起埃及大众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大部分埃及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成龙和李小龙主演的一些功夫片上。其实,这些影片往往由好莱坞制作和推广,语言、情节、价值观完全是西方风格,应该说它们只是具有中国元素的美国电影。总之,中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由于传播文化的平台和产品数量少,加之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阿拉伯受众的需求存在差异,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埃及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中国文学在埃及的传播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金一超)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Case Study in Egypt
CHU Beij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The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university lectu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gypt in recent years. Abundan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from Egyptian scholars promote the spread of our literature in the Arab world, and in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c. The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spirit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contains,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aesthetic value that it pursues, have fascinated Egyptians from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deeply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outp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 circulation in Egypt is very weak yet. Besides, owing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religious distinctions, most Egyptians do not know much about our literature. Therefore,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 it to the Arab world.
cross-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Egypt; Confucius Institute
2015-04-20
褚蓓娟(1965-),女,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I712
A
1006-4303(2015)02-01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