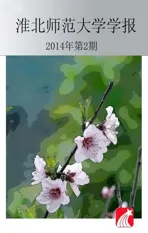朱熹审美阅读的主体论:“涤肠宽胸”说
2014-04-07洪永稳
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宋代的美学家朱熹继承了中国古代审美主体论思想的资源,强调主体的审美心胸对于审美生成的重要作用,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的实践中,提出主体的“涤肠宽胸”是审美阅读有效完成的重要前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阅读的主体论思想。这是对先秦以来中国审美心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欣赏理论的宝贵资源,对审美欣赏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朱熹的审美阅读的主体论思想来源和内涵。
一、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体论思想资源
审美的主体性来源于哲学的人学主体性。中国的人学主体论思想的兴起,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人性的觉醒和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崛起,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自觉运动。春秋末年,在社会领域,由于铁器的使用,农业的繁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物质方面的基础,在思想领域,由于奴隶制土崩瓦解,“学在官府”被私学部分取代,社会下层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产生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阶层即“士”阶层,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审美的主体性也逐渐萌芽,表现为当时艺术的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玄学的兴起,文学出现了自觉的时代,文学从服务于政治教化转向抒发个体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诗缘情”论和“文气说”分别强调文学艺术与作家的主体情感和个性精神的关系,文学对审美特征有了自觉地追求;哲学上,对人物品评风气的盛行,重视人的材质,形成了才性之学;艺术创作上,重视作家个性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促使文章风格学的形成,至此,中国的人学主体论思想最终确立。随之而来的审美主体性意识也得已确立。
审美心胸理论是审美主体论的主要表征。它是指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审美心胸理论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精华部分,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先秦的老子,老子《道德经》第十章提出了著名的“六问”之其中“一问”:“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涤除玄览”就主体的修道过程中精神上的修养而言的,属于哲学的认识论,它要求修道者面对功利的社会除去心中的功名的、物质的、生理的种种外在束缚,达到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虚静状态,方可与道为一。《道德经》第十六章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认为主体能做到虚极纯笃,不受外物的引诱而使心灵扰动,才能观物知复,认识道之本质。后来,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这个理论,提出“心斋”和“坐忘”的命题,第一次在审美的层面上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以天合天”,以自然之心观照自然,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心胸理论。战国时期,审美心胸理论也为其他学派继承,如儒学大师荀子吸收了老庄的心胸理论,站在儒家入世的角度提出“虚壹而静”的命题;韩非也讲“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1]43,“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1]15。魏晋时代,随着人性的觉醒以及文艺的独立和自觉,审美心胸理论开始进入文学艺术领域,首先是宗炳提出“澄怀观道”“澄怀味象”的命题,把庄子的审美心胸理论直接运用到绘画艺术领域;陆机和刘勰又把审美心胸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就是说文学创造要以空明的心境关照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强调虚静对于文学构思的重要性。唐宋时代,伴随着中国文学诗歌的成熟,审美心胸理论进一步扩展,唐代的刘禹锡则进一步用于诗歌创作,提出“虚而万景入”;北宋的苏东坡则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北宋著名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林泉之心”,这些都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身为南宋初期的理学大家朱熹吸收了历史上的审美心胸理论和历史上艺术理论家关于审美创造的深刻洞见,并把这一审美心胸理论直接运用于审美阅读鉴赏上。
二、“涤肠宽胸”说
朱熹认为,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一样都是审美主体心灵化的过程。对主体有同样的要求。朱熹说:“来喻所云‘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淡’,以诚极至之论。然恐亦须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此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2]卷64这里的“六艺之芳润”指艺术作品的意蕴,朱熹认为,欣赏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明理悟道,了悟“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诗》《书》《春秋》等六艺皆“只是一个理”,而艺术作品的“至理”是艺术审美的底蕴,只有获得这种底蕴才能真正地获得审美享受。如何达到这种欣赏的佳境,朱熹认为,主体必须洗涤心胸,“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这里的“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就是指审美主体的主观欲念、知识成见、谬误等,只有清除掉这些“污浊”,审美才得以进行,主体才能享受到“六艺之芳润”。心胸有遮蔽之处,“譬如一片洁净田地,若里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3]卷11。朱熹认为,这种遮蔽有两类,“一是私意,一是旧有先人之说”[3]卷11。如果有私心、欲念,便失去了本心、公心,“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3]卷11;如果只因循前人之说,便失去了真见,人云亦云,无法得到“真个道理”。因此,需要洗涤肠胃,得到虚静空明之心。朱熹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又曰“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即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
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是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3]卷11
也就是说,欣赏文学作品不要以自己的一己之见替代作品的原意,洗涤自己的心胸,除掉先有的观念,方可得正理。朱熹这样的言论很多,如“濯去旧闻,以来新见”[3]卷11,“心要精一。方静时,须湛然在此,不得困顿,如镜样明,遇事时方好。心要收拾得紧”,“读书有个法,只是刷尽了那心后去看”[3]卷11,“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会,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3]卷10。除此外,在欣赏作品时也要排除前人之成见,防止前人观点对自己心理的定势作用,影响自己的创见,他说:“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文义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以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3]卷11。除去心中的“先见”和前人的“成见”,使自己的心灵平静如水,使欣赏得以形成。
为什么要保持心灵的虚静空明呢?朱熹认为,“虚心方能接物”,“心无物,然后能应物”,他说:“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3]卷140。只有虚心,“便识好物事”,“百工技艺做得精”,艺术作品的内在底蕴才能够被把握。朱熹说:
看心有所喜怒说,曰:喜怒哀乐固欲中节,然事过后便须平了。谓如事之可喜者,固须与之喜,然别过一事,又将其意待之,便不得其正。盖心无物,然后能应物。如一量称称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称物,则轻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犹是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才有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了。盖着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荡,终不消释。设使此心如太虚,然则应接万务,各止其所,而我无所与,则便视而见,听而闻,食而知其味也。……譬如衡之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先有一物在上,则又如何称?
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象,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纲常影象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来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物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3]卷16
朱熹认为人有喜怒哀乐四者,这是天生的,但不能将个人的喜怒哀乐的私有情绪附加给我们对待的事物(也包括审美对象),心中无物,方能接物,如要在心中添加些私物,则梗在心中,便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也就失去了审美感知的灵敏,不能真确地判断其轻重得失,只能保持本心的湛然虚明,才能随物而感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
朱熹认为,洗涤肠胃后必然就得到宽胸从容的心态,这样方能取得好的鉴赏效果。“宽胸”就是求“放心胸宽闲”,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求“责效”,朱熹说:“方责效便有忧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3]卷11,而要有一种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心态;其二,要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胸怀,朱熹说:“阔着心胸,平去看,不是硬捉定一物。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人,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3]卷117,朱熹这里把审美主体心胸的广阔描述得如此精彩,“如僧家行脚”句尤其形象,僧人除了心无尘念,更在游脚四方,见识多广,八极之内,四方人事,山川之势,古今兴亡,尽在心中,但又忘之脑后,“不是硬捉定一物”。这是多么深刻的辩证法,即强调了审美主体的深厚修养,又强调审美活动中主体的胸怀若谷,不拘一物,不受任何他物的干扰,这足以和西方的思辨哲学审美论相媲美。这样既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不追求利害得失,又要有一种开放的视野,纵观古今,耳听八方,心怀天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的境界中,自然能品尝到其中的“意味”。所以朱熹说:“文字且虚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寻支蔓,旁生死穴”[2]卷4。像这样的语言在朱熹的著作中很多,如:“学者要看义理,叙事胸次放开,磊落明快,……看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著工夫也”[4],“读古人书直是要虚着心,大着肚,高着眼,方有少分相应。若左遮右拦,前捉后拽,随语生解,节上生枝,则更读万卷书亦无用处也。”[2]卷49
朱熹的审美心胸理论对后来的艺术鉴赏家有一定的影响,如:清代小说评论家金圣叹提出“澄怀格物”说,要求作家内心虚静,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深入地钻研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创作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可以看出受到朱熹审美鉴赏中“涤肠宽胸”和理学上“格物致知”的影响。
潘立勇先生说:“朱熹在审美目的论,即在审美的终极功能上,强调儒家的极端功利主义,而在审美方法论,在审美的当下境界中,却也强调类似道家的超功利或忘功利。”[5]这个判断非常准确,朱熹深得儒道文化的精髓,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人生在世建功立业,修心养性,悟道明理,审美也是一种把握人生的方式之一,其最终目的也就在于此;但他也深知艺术审美的真谛,超越儒家功利主义的局限,采取道家无功利或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吸收道家审美心胸的理论,运用于审美实践,使儒道互补,使道家的审美方法论通向儒家的审美目的论。这正是艺术审美的深刻之处,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审美就其当下来说是无功利的,但就其最终的目的来说又是有功利的,是无功利和功利的统一,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生于12世纪的朱熹就能深知此理,在西方,直到18世纪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才有这样的见解,可见,华夏民族的审美思想论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创见之功。
[1]韩非.韩非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2]朱熹.朱文公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37.
[3]黎靖徳.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8.
[5]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