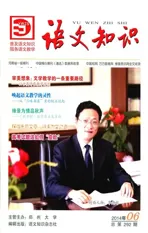论老舍文学语言的“方言化”
2014-03-11郑州大学文学院
◆ 郑州大学文学院 陈 晨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老舍的成就不仅在于他作品中文化思想的丰富与深刻,还在于他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非凡成就。他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代表了“五四”以来现代白话小说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峰。这也是老舍的经典作品成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论及老舍的文学语言,“方言化”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正如冰心所说:“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凉和辛酸,向往和希望……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1]老舍运用方言写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所使用的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尽管如此,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北京话也还是一种方言。老舍正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了自己既通俗又浅白、既朴素又活泼的文学语言风格。此外,方言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最外在的语言标记,同时又蕴涵着最底层的文化。因此,“方言化”不仅是老舍文学语言突出的特点,更是我们进入老舍文学世界的特殊路径。
一、平民精神与对方言表达的自觉追求
老舍出生于北京最底层的平民家庭,“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从小就对贫苦市民的不幸境遇有深刻了解。这使得老舍与平民之间具有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精神纽带。他熟悉他们,同情他们,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俯瞰穷人的生活,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将他们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并不强调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自称“写家”,将写作看作是极为平常的一种劳动,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这些苦人们都成了他的朋友。这种生命情感的融入正是老舍选择用北京方言来进行写作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我知道他们怎么活着,所以会写出他们的语言。”“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就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2]长期浸淫在民间文化氛围中,又使老舍形成了平民的审美心理,他明确将文学语言的“俗”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他说:“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3]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言文一致”,提倡一种方言化、口语化的写作:“我愿在纸上写的和从口中说的差不多”“而不是去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4]
如果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为老舍对“方言”的自觉追求找到更为有力的阐释。现代语言学把人的存在本质归结为语言自身,人的认识、思维都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因此,“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5]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方言与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得以呈现:“它深刻地体现了某一地域群体的成员体察世界、表达情绪感受以及群体间进行交流的方式,沉淀着这一群体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敏感地折射着群体成员现时的社会心态、文化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6]对此,研究者早有过精辟的论述。赵园指出:北京方言不仅是“北京文化中最易于感知的那一部分”,更“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而“‘说’的艺术,其条件,其心理内容,其美感效应,应该比之别的更有利于说明北京人‘审美的人生态度’。”[7]正因如此,方言不仅是老舍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展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老舍自己生命的源头,它比任何方式都更为强烈地显示着老舍自己身上的文化印记。
二、“方言化”的具体表现
老舍的文学语言具有鲜明的“方言化”特色,首先体现在大量方言词语的使用上。据统计,他在《龙须沟》里一共用了136个北京方言词,“诸如晌午、没辙、泡蘑菇、累赘、大脖拐、耽待、老梆子、紧自、得烟儿抽、多咱、挤兑、这不结啦、至不济、大八板儿、王大胆、归掇、圣明、左不是、抱脚儿、耍骨头、纳闷儿、横是、抖漏、赶碌等等。”[8]就拿我们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常收录的《骆驼祥子》等作品来说,里面的方言词也俯拾皆是,例如:
“这就是咱的榜样!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市!”(《骆驼祥子》)
“只要是自己的车,一天好歹也能拉个六七毛钱,可以够嚼谷。”(《骆驼祥子》)
其中的“行市”“嚼谷”都是来自北京市民口中的土语方言,它们质朴自然、活泼生动,具有独特的魅力。“儿话韵”是北京话里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它在老舍作品中的出现频率非常高,也充分反映出老舍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方言化特色。例如《骆驼祥子》中出现的“眼儿热”“傻大个儿”“今儿个”“大子儿”“拉晚儿”等等,它们带着轻松随意的语气,透出活生生的北京口语气息,使人读来倍感亲切。而“着”“了”等助词、“呦”“嘿”“吧”“呕”等感叹词的使用,更呈现出了人物说话时多种多样的语气和口吻,流露出北京话轻松俏皮的独特韵味。
其次是在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熟语的使用上。熟语是民间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大众智慧的结晶,它不仅简洁活泼、通俗易懂,更富含哲理,增添了语言的形象感。例如:
“修沟不是三钱儿油,俩钱儿醋的事,那得画图,预备材料,请工程师,一大堆事那!”(《龙须沟》)
“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骆驼祥子》)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儿,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骆驼祥子》)
最后是在句式的使用上,老舍将大量的具有北京地域特点的方言句式带入作品之中。这方面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方言句式在老舍小说的人物对话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但在他的散文中,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明显的例证。我们就以老舍的名篇《济南的冬天》为例,看看老舍如何将方言的句式融入写作之中。
“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北京口语中常见的一个语法现象就是“在双音节的复合词或成语中插入一个或几个词,使之成为一个短语。”[9]在双音节复合词中间插入“了”,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如“害了怕”“及了格”等等。“害了羞”就是典型的北京口语的用法。
插入语也是北京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语法现象,例如“您瞧”“我说”等等,它们的使用不仅使句子在语义的转接上自然得当,也会给读者带来平易亲和的感受。在《济南的冬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如:
“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
“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
老舍格外注重语言的“声音形象”,这也是“方言化”特色的体现。北京方言是依赖于“腔调”的语言,尤其是旗人讲究说话的艺术,在“嘣响溜脆”“甜亮脆生”的语音腔调中传递出“不缠绵粘腻,不柔靡”[7]的北京文化气质。老舍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始终把“能读”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他说:“我们写的白话文,往往不能琅琅上口,这是个缺点。”他主张挖掘语言的“声音”潜力,让它既有意思,又有响声,还有光彩,这不能不说是从北京方言中汲取的养分。
以上这几个方面,充分地体现出老舍在文学语言“方言化”上的大胆追求与探索,这使他的作品语言充满了生命力,在新鲜活泼中透着朴实醇厚,为读者展现出一个具有北京情韵的语言艺术世界。
三、语言观念变化中的方言选择
老舍重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方言化,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对“方言化”进行反思。正是这种理论的自觉性,使他的文学语言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老舍文学创作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在语言上显露出明显的“京腔”,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作品。但却在信手拈来中少了节制与筛选,不可避免地落入油腔滑调。到了《小坡的生日》,老舍逐渐形成了自己“浅明简确”的白话语言观,《离婚》《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一系列作品都显示出他对方言土语的从容调动。他努力往“细”里写,在方言的使用上精雕细琢,并非完全趋附与投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他强调语言的浅近明白,极少使用那些难懂的方言和拗口的俚语。老舍说:“白话本身并不都是金子,作家应该在大白话中找出金子来,把白话精选提炼成金子,作家的任务不是作白话的记录员,而是精打细算地写出白话文艺。”[10]他的方言写作,正是在对“俗”与“白”的追求中,呈现出语言的审美性和艺术性,这正是老舍小说雅俗共赏的原因所在。
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强调汉语规范化的大潮下,老舍的语言观念也发生了调整,他对《龙须沟》中因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而造成的演出限制进行了反思:“我们应该让语言规范化,少用方言土语。只有这句土语的确是普通话里没有的,又有表现力的,可以用一些,不一定完全不用。”[11]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深刻意识到推广普通话的时代任务,并自觉将其化为行动,他说:“我以后写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以我的作品配合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12]而这其中,无疑也显示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语言共同体的“普通话”对于方言土语的规范。《龙须沟》之后的《西望长安》《青年突击队》等剧作,虽然紧贴时代,在语言上“尽力避免用土话,几乎都是普通话”,[11]但却不再是老舍最为熟悉的关于老北京的城与人的生活,最具老舍特色的那种语言风格也无处可觅。直至《茶馆》《正红旗下》,我们才在老舍式的主题中又重新感受到京腔京韵的巨大魅力。
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就成为现代汉语变革的重要诉求之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彻底打破了文言的束缚,开辟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方言土语作为民间语言资源也被纳入到白话语言体系中,但此时的白话文学刚刚起步,欧化调突出、学生腔泛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使得“大众化”成为文学语言的明确要求,但是却停留于形式的探讨,并没有有力的文学实践。老舍的白话语言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其文学语言“方言化”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也从中凸显。老舍是真正实现了文学语言“大众化”的作家,他笔下的方言浸润着文化的底蕴,与个人生命体验紧紧相连,他坚持对“方言”的艺术创造,用心“烧”出了白话的“原味儿”,也展现出现代汉语书写的艺术魅力。老舍对于文学语言中方言的吸纳、使用和思考,永远是现代文学发展中值得珍视的宝藏。
[1]冰心.怀念老舍先生[J].人民画报,1978,(10).
[2]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A].老舍全集(第 1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A].老舍全集(第 1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老舍.我的“话”[A].老舍全集(第 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汪东如.汉语方言修辞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7]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舒乙.老舍小说语言发展的六个阶段[J].语文建设,1994,(5).
[9]马尔华.《离婚》中北京口语的运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12).
[10]老舍.怎样写通俗文艺[A].老舍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1]老舍.记者的语言修养[A].写与读[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2]老舍.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N].北京日报,195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