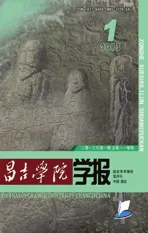《诗经》中的农耕文化
2013-04-01王开元
王开元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经》的内容丰富多彩,农耕文化也是《诗经》的核心内容。农耕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农耕文化,是指农耕民族所产生的所有文化,从广义的角度看,《诗经》305篇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狭义的农耕文化,是指与农耕生产、农耕生活直接相关的的文化。本文试图以狭义的农耕文化为视角,从《诗经》的文本出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诗经》中的农耕文化。
一、关于农耕的祭祀
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以后,仍以农业为本,要想取得农业的丰收,就必然特别重视祭祀天帝与后稷,祈求他们的保佑,故《礼记·明堂位》载:鲁公“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1]农业生产有着自己的众多规律,而关键在于春秋二季,故周人的农耕的祭祀重在春秋二季。由《诗经》中的农耕祭祀诗,可以看出周人对于农耕的重视。
我们先看春祭。西周天子有所谓耕籍田之礼,《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2]天子率领公卿诸侯躬耕籍田,固然是做样子的,并非真的要参加农业劳动,但仍可说明统治者想通过这一举动来表示自己对农业生产是极其重视的,以便调动农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诗经》中涉及春祭的诗篇有如下几篇.
《周颂·载芟》,与籍田之礼有关,“毛诗序”说它是“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社”是土神,“稷”是周人始祖后稷演变为的谷神,社稷主管百谷的丰歉,对社稷的尊崇,即是对农业的重视。
《周颂·噫嘻》,“毛诗序”称其为“春夏祈谷于上帝也。”诗歌记载了成王春祭祈谷,告诫农官率领成千上万的农奴为朝廷播种百谷,并努力开垦私田。诗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臣工》篇,“毛诗序”说它是“诸侯助祭,遣于庙也”。虽未明言祭于何时,但据诗中“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属于春祭无疑,故陈子展先生说:“《臣工》,盖王者暮春省耕之诗。”[3]可见此诗也是周天子重视农耕的证据之一。
我们再看秋祭。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之后,从周天子到臣民都要举行祭祀,回报天地神灵、社稷以及祖先的保佑与恩德。
《周颂·良耜》,“毛诗序”说它是“秋报社稷也。”可见它是西周天子秋季举行祭祀社稷典礼的诗篇。
《周颂·丰年》,“毛诗序”说它是“秋冬报也。”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周人大获丰收,在秋冬之时,举行各种祭祀,以报答各路神祇以及祖先的保佑。
另外,《周颂·思文》一诗,“毛诗序”说它是“后稷配天也”。可见它也是当时西周统治者祭祀上帝与后稷的乐歌,诗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里,在敬天的同时,也充满了对农神的尊崇与赞颂,并明确感谢上帝与后稷恩赐“来牟”,“来牟”即小麦与大麦,这就表现了周王朝对农事的依赖和极端重视。
二、关于农耕生活
最能充分反映周人农耕生活的是《豳风·七月》。《豳风·七月》是十五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共八章88句,380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此,此篇当作于西周建立之前,即公刘处豳时期,周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部落。周人虽处于部落时期,但社会运转已有一定的模式和秩序,上有公侯、公子,次有田畯,他们既是社会的统治者,又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公侯还是祭祀的主持者,“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社会最底层的农夫,才是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豳风·七月》反映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等诗句来看,农夫过着定居生活,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基本特点。
在春天,“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诗中的“一之日”指夏历十一月,“三之日”应是夏历元月,即春天的第一个月,“四之日”即春天的第二个月。春天一到,农夫们就开始整理农具,到田里耕作。老婆孩子则到田头送饭,田官见他们劳动很卖力,不由得面露喜色。在春天,男子的主要任务是耕种,但有时还要修剪桑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妇女的任务则是采桑养蚕,“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女奴不仅要从事劳作,还要时常担心遭受公子的侮辱,“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在秋天,女奴要开始纺织,为奴隶主制作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衣裳,正如诗中所说:“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农夫们则忙于收获庄稼,贮藏谷物:“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在冬天,农夫们要忙于打猎,猎取狐狸,给公子做皮裘;猎取野猪,供公侯食用。还要参加公侯组织的军事训练,就象诗中说的:“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除了这些,农夫们在冬天还要给公侯维修宫殿、凿冰将其藏入冰窖以便公侯夏天使用。“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另外,农夫们在冬天,还要维修自己的住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由此可见,农夫一年到头都在辛勤劳作,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很艰辛。“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农夫缺吃少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吃的是野果、冬葵、豆类、菜瓜、葫芦、麻子、苦菜,做饭烧火用的是难以燃烧的臭椿。
农夫除农耕业外,还有养蚕业、纺织业、饲养业、酿酒业、和狩猎等生产活动。
三、关于食物品种
《诗经》中涉及的食物品种,异常丰富,有植物类,有动物类。植物类又分粮食类和草本类、木本类。动物类又分家畜类和渔猎类。《诗经》中这些丰富的食物品种,体现了鲜明的农耕文化。现在把《诗经》中涉及的食物品种,罗列如下:
粮食类
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有所谓“五谷”之说。“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说法则不尽相同,或曰:麻、黍、稷、麦、豆(《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或曰:稻、黍、稷、麦、菽(《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歧注);或曰:稻、稷、麦、豆、麻(《楚辞·大招》:“五谷六仞”,王逸注)。不管哪种说法,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五谷的存在。
黍、稷。黍,碾成的米叫大黄米,有粘性。稷,碾成的米叫小米,《诗集传》:稷,“似黍而小,或曰粟也。”又程瑶田《九谷考》曰:“黍,今之黄米;稷,今之高粱。”《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魏风·硕鼠》:“无食我黍”。
麦。《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麦”。《魏风·硕鼠》:“无食我麦”。
稻子(稌)。《豳风·七月》:“十月获稻”。《周颂·丰年》载:“丰年多黍多稌”,“稌”是稻子。
菽(豆子)。《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荏菽(大豆),《大雅·生民》:“艺之荏菽”
麻。《豳风·七月》:“禾麻菽麦”;《大雅·生民》:“麻麦幪幪”。
禾、苗。则是百谷的通称。《魏风·伐檀》:“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无食我苗”。
草本类
荇菜。俗称金丝荷叶,叶子圆形,浮在水面,茎在水底,嫩叶可吃。《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卷耳。即苍耳子,可食用。《周南·卷耳》:“采采卷耳”。
芣苢。车前草,古人以为它的子实可以治妇人不孕。《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苹。又称藾蒿,初生可食。《召南·采苹》:“于以采苹”。
葑、菲。葑又称芜菁、大头菜。菲属于萝卜一类。《邶风·谷风》:“采葑采菲”。
荷华。荷花,其实为莲子,其根为藕。《郑风·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藚(xù)。药用植物,即泽泻草。多年生沼生草本,具地下球茎,可作蔬菜。《魏风·汾沮洳》:“言采其藚”。
苓(甘草)。《唐风·采苓》:“采苓采苓”。
苦。野菜,可食。《唐风·采苓》:“采苦采苦”。
菜瓜(瓜瓞)。《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大雅·生民》:“瓜瓞唪唪”。
葫芦。《豳风·七月》:“八月断壶”。
韭菜。《豳风·七月》:“献羔祭韭”。
唐。或曰唐蒙,菜名;或曰女萝(兔丝),草名。《邶风·桑中》:“爰采唐矣”。
葵。即冬葵,冬苋菜。《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
木本类
桃。《周南·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梅。果实味酸,立夏后熟,生者青色,叫青梅;熟者黄色,叫黄梅,古代用作调味品。《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
甘棠。果味甘美,今名棠梨。《召南·甘棠》:“蔽芾甘棠”。
木瓜。《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
桃。《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肴”。
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李”。
栗。《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栗”。《唐风·山有枢》:“山有漆,隰有栗”。
枣(棘)。《豳风·七月》:“八月剥枣”。《魏风·园有桃》:“园有棘,其实之食”。
花椒(椒聊)。《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藩衍盈升”。
杜。《说文》:“杜,甘棠也。”高亨《诗经今注》解释为:“梨属,果实红色,味涩。”《唐风·杕杜》:“有杕之杜”。
棣,梨树。《秦风·晨风》:“山有苞棣”。
榛。落叶小乔木,果实叫榛子。《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
家畜类
中国传统的农家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在《诗经》中都已出现。说明《诗经》的时代,传统的家畜都已具备。相关资料如下。
鸡、羊、牛。《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马。《秦风·车邻》:“有马白颠”。
犬。《小雅·巧言》:“躍躍毚兔,遇犬获之”。《诗经》中的犬又名“猃”、“歇骄”,“猃”,是长嘴巴的犬;“歇骄”,是短嘴巴的犬。《秦风·驷驖》:“载猃歇骄”。《诗经》中还还有猎犬,称为“卢”,《齐风·卢令》:“卢令令”。
豕(猪)。《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蹢”,豕即猪。《豳风·七月》:“言私其豵,献豜于公。”豵是六个月至一岁的小猪,豜是三岁的大猪。诗中泛指野兽。
鱼猎类
鱼。《陈风·衡门》:“岂其食鱼”。
鲤,鲤鱼。《陈风·衡门》:“必河之鲤”。
鲂、鳏。均为鱼名。《齐风·敝笱》:“其鱼鲂鳏”。
鱮。又称鲢鱼。《齐风·敝笱》:“其鱼鲂鱮”。
兔、雉。《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虎。《郑风·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献于公所。”
狼。《齐风·还》:“并驱从两狼兮”。
貆。即獾。《魏风·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特。指大野兽。《魏风·伐檀》:“胡瞻尔庭有县特兮”。
鹑。即鹌鹑《魏风·伐檀》:“胡瞻尔庭有县鹑兮”。
辰牡,高亨《诗经今注》解释为:“大公鹿”。《秦风·驷驖》:“辰牡孔硕”。
鹭,白鹭。《陈风·宛丘》:“值其鹭.翿”。
四、关于农耕劳动的场景
《周南·芣苢》,是记载妇女采摘芣苢的,诗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清人方玉润评论这首诗的劳动场景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4]
《周颂·载芟》,开头部分便描绘了规模宏大的热烈的劳动场景,诗云:“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诗的意思是,有的人在割草,有的人在砍树,一片片土壤被松散地翻掘出来,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在低洼的田地里劳作,有的在高处田地里劳作,大家一起耕田,呈现出热烈的春耕大生产的景象。他们当中,有主人、有长子、有次子等众多晚辈,另外还有许多男女奴隶。中午有人把饭食送到田头,大家都吃得很香,女人显得更加美丽,男人显得更加强壮。清人方玉润评论说:“一家叔伯以及佣工妇子,共力合作,描摹尽致,是一幅田家乐图。”[5]
《周颂·良耜》诗的开头,也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春耕的画面:“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馕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几句意思是,春天,农夫用耒耜在南亩深翻土地,尖利的耒耜发出了嚓嚓声。接着又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撒入土中,让它发芽、生长。他们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家中的妇女、孩子挑着方筐、圆筐,给他们送来了香气腾腾的黄米饭。夏天在田间锄草的时候,烈日当空,农夫们头戴用草绳编织的斗笠,把庄稼地里的荼、蓼等杂草统统锄掉。荼、蓼腐烂变成了肥料,绿油油的黍、稷长得非常茂盛。这里写了劳动场面,写了劳动与送饭的人们,还刻画了头戴斗笠的人物形象,又是一幅农业劳动的画面。正如清人方玉润评论说:“如画。”[6]
另外,《召南·采蘩》叙写宫女为诸侯采蘩,以供祭祀之用;《召南·采苹》,是叙写女奴采苹,作为贵族女儿出嫁时祭祖的祭品;《魏风·十亩之间》,是表现妇女采桑劳动的;《魏风·伐檀》,是表现农夫砍树劳动的。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细致描写劳动场景,但都足以引起读者对劳动场景的想像。
五、关于农耕生产者与生产工具
关于生产者。《周颂·臣工》篇载:“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噫嘻》篇载:“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载芟》篇载:“载芟载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这里,“众人”、“农夫”全是在王室土地上集体耕作的奴隶。我们从“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等诗句,可见成千上万的奴隶,是当时农业生产的基本劳动者。而这些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的俘虏。《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周王室大量占有殷民俘虏作为奴隶的史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从“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字样,可见西周王室占有殷民俘虏,作为生产奴隶的数量之多。
关于生产工具。《诗经》中所记载的生产工具,虽然简陋,但也能基本满足当时农耕的基本需求。主要有如下几种。《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顷筐”,斜口的筐,前高后低。《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椓之丁丁。”“罝”,是捕兔的网。《周颂·臣工》篇载:“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载芟》篇载:“有略其耜”、《周颂·良耜》篇载:“畟畟良耜”、“其镈斯赵”。“钱”是当今锹铲之类,“镈”是今天锄一类的农具,“铚”是短镰,“耜”是铁犁,而且西周时期很可能已出现了牛拉的铁犁。
有了这样的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农耕生产的成果是很大的。《周颂·载芟》和《周颂·良耜》都有“播厥百谷”的话,可见当时农作物的品种之多。另外,当时农作物的丰收景象也是很可观的,如《周颂·丰年》篇载:“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高亨先生解释周代十万为亿,“秭”具体数量未详。“万亿及秭,犹今语万石亿石”。《周颂·载芟》篇,也有“有实其积,万亿及秭”的话。《周颂·良耜》则说:“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些都足可说明当时农作物收获的数量之多。
六、关于恋土怀乡意识的表现
恋土怀乡意识,也是农耕文化的表现之一。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之初,便分封天下,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诸侯,诸侯再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说明周王朝仍然继承了以农为本的传统,把土地作为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极端重视土地,于是在《诗经》中也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土地是农夫生存的依靠,《豳风·东山》,是士兵出征三年后回乡的诗,其中第二章记士兵在回乡途中想象家园荒凉荒凉破败,不禁分外担心,诗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土地又是农夫养活父母的资本,农夫一旦失去耕种土地的机会,便不能养活父母。《唐风·鸨羽》,就是农夫因长期在外服徭伇或兵伇,而担心不能养活父母,急切希望尽快结束在外奔波的日子,回家过着安定的生活,以便耕种田地,养活父母,诗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王风·扬之水》与《小雅·小明》也是此类恋土怀乡的诗篇,《王风·扬之水》有云:“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小雅·小明》有云:“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土地是百姓生活的依靠,故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然而人们一旦无法生存,便要寻找新的安生之处,所以《诗经》便有了寻求乐土的呼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这种呼声依然是重视土地的表现。
总之,《诗经》中所表现出来的农耕祭祀;农耕生活;丰富的食物品种;农耕劳动的场景;众多的农耕生产者和生产工具;恋土怀乡意识,都强烈地说明《诗经》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
[1][2]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1488,1356.
[3]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089.
[4][5][6]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85,61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