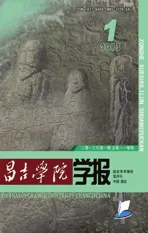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列王纪》对《玛纳斯》的影响为例
2013-04-01韩文慧
韩文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关于两部史诗
《列王纪》又名《王书》,是与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并列的世界文学巨著。它产生与10-11世纪之交的中古伊朗,全诗12万行,6万联句,时间跨度4600年,内容涉及古代伊朗四代王朝50个国王的盛衰兴亡,它纵横捭阖,卷帙浩繁,享有古代伊朗百科全书的美誉。它写的是伊朗历代国王统治时期的兴衰大事,其中可独立成篇的故事达20余个,王权的更迭和传承构成史诗的重要篇章。勇士故事占全书的一半以上篇幅,也是《列王纪》的精髓。其中英雄鲁斯塔姆是贯穿勇士部分的主要人物。他出生皇族,幼年身强力壮,胆识过人,还未成年便杀死难以对付的白象。此后,他便以波斯第一位勇士的面貌出现在与敌国交战的战场上。史诗的内容还包括四代英雄人物的悲剧故事,分别是伊拉治、苏赫拉布、夏沃什以及艾斯凡迪亚尔。
俄国杰出的民主主义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列王纪》,他说:“从有人证明《荷马史诗》不过是希腊民间诗歌的集结以后,一切有识之士终于发现民间诗歌有极高的诗学价值。菲尔多西的优美创作,伊朗的《列王纪》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是改写的民歌集。在《列王纪》里,有许多章节,它们的美甚至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都找不到”[1]英国学者珀西·赛克斯对《列王纪》评价到:“这部伟大的史诗——经过翻译,已失去了它那音韵铿锵之美。正如科威尔教授所说:‘它在亚洲所占的独特地位,正如荷马史诗在欧洲一样。’”[2]
《玛纳斯》是13-16世纪诞生在新疆柯尔克孜民族中间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歌颂了英雄玛纳斯和他的子孙后代率领柯尔克孜人民抵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黑格尔曾经说过,一部优秀的史诗能够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而《玛纳斯》正是这样一部能够显示柯尔克孜民族精神全貌的优秀史诗。史诗为我们展现了柯尔克孜人曾经经历过的重重灾难,向人民显示出柯尔克孜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纯朴忠厚、粗狂坦直的民族性格。
史诗中,当柯尔克孜人民面临灾难、危在旦夕的时刻,民族的救星——英雄玛纳斯诞生了。他有着超人的神力,却又有凡人的血肉之躯。他率领柯尔克孜人民和他的四十名勇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把侵略者追得落荒而逃。听到玛纳斯的赫赫威名,敌人胆颤心惊。只要有玛纳斯在,敌人就不敢来侵犯。玛纳斯拯救了濒于灭绝的柯尔克孜民族,使柯尔克孜民族获得了解放。在玛纳斯身上,凝聚着柯尔克孜人民的信念与希望。在柯尔克孜人的心目中,玛纳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史诗第一部中有许多中外学者所注目的名篇,如《玛纳斯的诞生和童年时代》、《卡妮凯的婚姻》、《两英雄结盟》、《阔克台依的祭奠》、《玛纳斯之死》……都是第一部的精华,也是八部中闪光的华章。
二、柯尔克孜人西迁
柯尔克孜民族最早发祥于叶尼赛河上游的山林地带。大约10世纪初,雄踞漠北高原的蒙古契丹征服柯尔克孜民族,在先汗的追击下,柯尔克孜人开始大量西迁,他们分批分期逐步迁移,先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天山南北,再向西迁到中亚塔拉斯一带。他们西迁中亚之后,长久居住在深山,但离丝绸之路很近。往返于丝绸之路的商队,也经常去柯尔克孜牧村,商队与柯尔克孜牧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商业性活动也日渐活跃。在他们返回的途中,各种商品包括文化以及文学作品都源源不断地从中亚这些著名的商业城市输入柯尔克孜地区,沿丝绸之路途各民族的文化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元朝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华夏周边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各国之间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蒙元时期,自中亚、西亚迁徙入我国新疆境内的外来民族最多的为欧洲各民族,即“蒙古三次西征以后,欧洲民族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持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这些移民中有被俘的工匠,有被遣发的百姓,也有携带前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则是自愿投奔蒙古军和经营商业的各族人士。”[3]这也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更令人惊奇的是,从新疆地区《玛纳斯》流传分布图看,新疆地区《玛纳斯》的流传全部都在西部与外国领土接壤的交界处,比如北疆的塔城、伊宁、特克斯、昭苏,南疆的阿克苏、阿合奇、阿图什、乌恰、阿克陶、莎车、塔什库尔干。这也就更能说明了它是受到波斯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在产生的年代和历史上来看,《列王纪》产生于公元10到11世纪之初,而《玛纳斯》产生在稍晚于它的13至16世纪。从历史方面看,中国主体民族在历史上缺少叙事诗或者史诗,翻遍中国所有的文学史,仅在《诗经》中搜集的有关诗句,总共加起来只有338行,这跟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如何能比?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印象就是“中国没有史诗,或者中国是一个史诗的贫国。”。黑格尔在他重要的著作《美学》里面也讲,他说中国无史诗。中国的散文很发达,诗歌很发达,但是中国没有史诗。朱光潜也在其《悲剧心理学》中说“中国没有悲剧”,中国人就不会写悲剧,只会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反观《玛纳斯》,这一民族史诗却规模宏大、卷帙浩繁,而且在内容上充满着无尽的悲剧色彩。而在波斯文学史上,史诗也只有《列王纪》以及散文体和诗歌体。并且《玛纳斯》和《列王纪》具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共同的母题,例如怪异儿诞生的母题,亲属背叛的母题等等,在结构上也采用谱系式的结构,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
三、英雄史诗《列王纪》的东渐
《列王纪》在我国新疆地区的传播远早于内地,这是由于波斯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东西方各民族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长期处于波斯文学的影响之下,因而波斯文学和各民族文学在主题、情节和人物上彼此影响,互相交融,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玛纳斯》广泛受到了《列王纪》的影响。有很多例子可以举证,比如,在史诗《玛纳斯》中,描写玛纳斯时,曾用这样的比喻:这英雄有老虎般有力的臂膀,有狮子般勇敢的心,像鲁斯塔姆一样品德高尚、英勇无畏。老虎和狮子的比喻是因为玛纳斯在出生时他母亲吃了老虎的心和豹子的胆。鲁斯塔姆的比喻则是从《列王纪》中得知的英雄鲁斯塔姆的光辉事迹才加入的。
在《玛纳斯》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狡猾的空吾尔在战场上敌不过玛纳斯,于是暗中用毒斧子砍伤了玛纳斯,玛纳斯的结义兄弟阿里曼别特赶来救护,他把玛纳斯抱到自己的骏马上,两位巨人坐在骏马上,骏马就快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候,骏马祈祷到:“鲁斯塔姆的坐骑拉赫什啊,请你赐予我力量吧!”祈祷见效,骏马顿时驮着英雄飞快奔回大营。拉赫什是《列王纪》中英雄鲁斯塔姆的坐骑,可见,在当时,《列王纪》的传说已经传到了柯尔克孜人民当中。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的语言互相非常接近。而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又将《列王纪》做过很多翻译工作。对这样的接受是自古以来在中亚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诗人中延续的“模仿创作”传统,即将一个诗人创作演唱的著名故事情节,另一个诗人按照自己的语言、风格、创作演唱方法再创作演唱。在此,我们不可否认,阿拉伯、波斯等文明古国的经典文学对柯尔克孜文学产生的影响,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是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自古以来就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
曾经横扫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也曾是波斯的统治者,1253年,成吉思汗的子孙旭烈兀受蒙古大汗蒙哥的派遣,率10余万大军越过阿姆河西征侵入波斯。1256年占领了波斯全境,建立了伊尔汗国,称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1258年,旭烈兀率军攻占巴格达,处死哈里发,消灭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蒙古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以大不里士为京都的伊尔汗国,其疆域东至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达高加索,南抵阿拉伯海。波斯高度的文明对蒙古征服者产生了融合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步波斯化,讲波斯话,并且皈依伊斯兰教。
四、两部史诗的交流与影响
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动向,而是一种揉合着多种民族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因为地理条件的不同,来淡化许多优秀文化之间的相同性。通过对两部史诗的分析,来研究两部史诗的文化原型,并非偶然的一种极为相似的文化,诞生在我们的视野中。对波斯的《列王纪》与中国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进行多角度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两部史诗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史诗《玛纳斯》与《列王纪》在结构上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都是以行为为结构中心;二是史诗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既独立,又统一的结构关系;三是内部结构上两部史诗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识。究其原因,此种外部结构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中亚时的《突厥语大词典》,它是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词汇的一部大型词典,收录古代突厥语词7500余条,诗歌片断242个,是当时波斯诗歌创作的总库。
从语言文字分类讲,波斯境内语言主要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另外还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闪含语系等。突厥语民族绝大多数英雄史诗都是以口头形式长期流传在民间的,其中,《玛纳斯》、《乌古斯汗》等许多作品早已蜚声世界。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传统的渊源可以从《词典》中找到蛛丝马迹。[4]这一点再次证明了中亚早期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中英雄诗歌在我国广泛流传的事实。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试图重构古代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传统,曾对这些诗歌片段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拼合和对接。伊明·图尔逊根据诗歌段落的内容、韵律系统特点,从《词典》中选择了36个相关段落142诗行,将它们进行有机的组合拼接,重构了一部描述喀喇汗王朝时期英雄业绩史诗雏形,这一重构方案情节与情节,段落与段落直接的衔接与连贯显得有点牵强,但从整体上完全可以看出其作为英雄史诗的诸多特征。尤其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比较生动地体现了古代人的英雄史诗特色。它与突厥语族典型的英雄史诗,比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有很多相似之处。[5]也就是说,这种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从诗歌的结构和内容上看,这部史诗雏形基本上是一首赞歌。诗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赞扬了自己的同胞的英雄功绩。一个事件按照其顺序得到符合逻辑的描述,并且这个顺序的各种因素都得到十分清晰的展现,在韵律方面,AAAB押韵形式和简短的7、8个音节的诗行结构也是典型的中亚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诗歌结构格式。
同时,两部史诗都表现出了强烈悲剧意识,史诗中的悲剧英雄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共同的悲剧意识作者认为可以归结于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遭遇。在外族的不断侵扰下,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以及他们不幸的死亡,唤起民族人民极为强烈的悲哀、痛苦及同情之感,这种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在民间,当歌手们演唱史诗时,常会出现歌手情绪哀痛、热泪盈眶,听众声泪俱下、唏嘘不止的动人场面。史诗中英雄的命运牵动着听众的心弦,英雄们不幸牺牲的悲剧结局震撼着他们的心灵。
10世纪时,伊朗陷于阿拉伯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伊朗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这次入侵甚至超过公元前亚历山大对伊朗的入侵和希腊人在伊朗的统治。亡国的波斯人在社会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如果一个波斯人骑马走路,在路上见到阿拉伯人,他得下马,把马让给阿拉伯人骑。在阿拉伯人入侵统治波斯以后,波斯全国上上下下都对外侵者强烈不满。他们心怀对故国的眷恋和怀念,痛恨外族统治者给他们带来的奴隶般的生活。所以上至国王、大臣总督,下至平民百姓都希望以自己的某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悲愤和宣扬自己祖国的光荣与辉煌。于是《列王纪》中的悲剧意识的创作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这种浓郁的悲剧意识与史诗作者菲尔多西也有一定的关系。诗人的遭遇在波斯诗人中最为不幸,然而诗人菲尔多西倾其一生奉献了这部史诗,经济的拮据,老年丧子的痛苦,以及不被统治者所承认的一系列忧愁折磨着诗人,因此史诗中表现出生活的悲惨是不难理解的。
柯尔克孜民族史诗中表现的悲剧意识,与自己民族本身的遭遇也不无关系。正如有的学者说:“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的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忍受。”[6]柯尔克孜民族从10世纪起,一直受着异族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与蹂躏,饱受战乱与被奴役之苦。但是,柯尔克孜人民对外的反抗从未停止过。这一特殊的民族经历,不幸的生存境遇,培养了柯尔克孜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在侵略者的驱使下,背井离乡、迁移漂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柯柯尔克孜人民对于自己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面对悲惨的现实柯尔克孜人民直面人生,与命运抗争,表现出了用于进取的积极精神和蕴藏于民族深层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悲剧意识的事件作为史诗的题材也是意料之中的。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是联结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的纽带,也是横跨亚、非、欧洲各大帝国―马其顿、波斯、蒙古、奥斯曼的必经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波斯英雄史诗《列王纪》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在外部结构的谱系式与内部结构的悲剧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两部史诗成为了中波文化交流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丝绸之路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与物化形态,在“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各族人民表达情感、传递文化信息,以及完成民族思维意识的超越与文化认同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流。除《列王纪》外,《蔷薇园》也流传到我国,出现在穆斯林的经院教育中。由此看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交流与传播不乏此例。正可谓:中波交流自古有,驿路梨花处处开。
[1]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62-63.
[2]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332.
[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24.
[4]突厥王书[M].和田地区文管所藏书.
[5]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突厥语大词典〉与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5.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