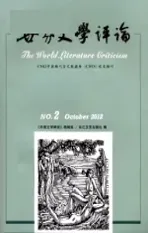爱与苦难的悖论:论王尔德童话《星孩》
2012-08-15余迎胜李华维
余迎胜 李华维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文学创作及文学观念既鲜明独特,又充满自相矛盾式的悖论。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立场出发,王尔德拒绝赞美一切具有瑕疵和尘世气息的事物,尽管这一类事物能够赢得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们的认可。对于超脱的美,王尔德持有一种极端理想化的看法:“美学则高于道德标准,它属于更高的精神范畴”①。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随着道连·格雷一次次的作恶,画像逐渐变得衰老难看。主人公宁愿死,也不肯接受自己容颜的老去,随着死亡的到来,画像恢复了它最初的完美鲜艳。戏剧《莎乐美》(1893)的女主人公更是不顾一切的追求血腥的美,哪怕以牺牲他人及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些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作品深刻反映出王尔德对于美与现实、美与死亡的看法。而在他著名的童话作品《快乐王子集》(1888-1891)中,王尔德关注的是爱与苦难的沉重话题。
王尔德的童话风格绮丽,其面貌与传统欧洲童话作品迥异。首先,他的童话作品大多以悲剧告终,如《快乐王子》、《了不起的火箭》、《星孩》:其次,他的童话颠覆了传统童话中善良正直的主人公形象,大多是或自私、或暴躁、或任性、或冷酷的形象;第三,他的童话中仅有的两个正面主人公,快乐王子与星孩,虽然给读者带来了希望,却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被这个邪恶冷酷的世界所吞噬毁灭。在这两个主人公尤其是后者身上,阐明了王尔德对于爱与苦难的悖论式立场。
一、爱的代价
爱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中应有之义,古往今来无数作家描写和讴歌它。可是,在王尔德看来,19世纪末的英国和欧洲,爱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事物,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不啻为一种奢望。《星孩》②的开局,作家通过两个樵夫的对话,指明了世界的不公平:“‘我们为什么还要高兴呢,既然生活偏向有钱人,不是向着我们这样的穷人?……’‘真的,’他的伙伴答道,‘有的人享受得很多,有的人享受得很少。不平已经把世界分掉了,可是除了忧愁以外,没有一件东西是分配得平均的’”(124)。在这样的窘困生活里,樵夫并没有失去同情怜悯的爱心。当他的妻子拒绝收养星孩时,樵夫的回答让读者倍感温暖:“可是她还不肯息怒,她却挖苦他,生气地讲话,并且嚷着:‘我们自己的小孩都吃不饱,难道还要养别人的小孩吗?谁来照应我们呢?谁又来给我们饮食吃呢?’‘不要这样,上帝连麻雀也要照应的,上帝连它们也养,’他答道。‘吹进硬心肠人家里来的风不总是冷风吗?’他反问道”(127)。
然而,慈悲浇灌出的果实并非也是慈悲。长大后的星孩,虽然美貌,却不能以爱心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可是他的美貌给他带来了祸害。因为他长成骄傲、残酷而自私了。他看不起樵夫的儿女,也看不起村子里别的小孩,说他们出身微贱……他自命为他们的主子,称他们做他的用人”(127)。他的行为暴虐而冷酷,甚至引起养父母及神父的指责:“‘我们并没有像你对待孤苦无助的人那样对待过你。为什么你对一切需要怜悯的人总是这么残酷呢?’”(128)。
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里,爱业已成为一种代价高昂的“产品”,需要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才能得到。而恨,却无需理由、无处不在。这应该是对人类日趋富足、但精神日趋功利的一种莫大讽刺。
二、苦难的不可避免
星孩终于自食其果,因其冷酷与残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这样的惩罚过于的冷酷与残暴,使他遭受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苦难。在驱逐了亲生母亲后,星孩遭到了可怕的魔咒:“他便走到水井旁边,往井里看去,啊!他的脸就跟蟾蜍的脸一样,他的身子就像毒蛇那样长了鳞”(130-131)。曾经美貌的星孩心肠狠毒,而面貌丑恶的星孩却在痛苦与自责中找回了良知:“不,我待我的母亲太残忍了,这个灾难就是给我的惩罚。所以我应当走开……得到她饶恕的时候”(131)。
这里的对比是极为鲜明的。外表美貌的星孩,内心却刻薄狠毒;外表丑陋的星孩,良知渐渐苏醒,并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愿意承受各种苦痛与磨难,以一种受难者的姿态承受命运的无情捉弄与打击。在寻找的道路上,他走的越远,越是感到自己的罪孽。那些曾被他荼毒过的小动物对他的戒备,使他羞愧难当;那些厌恶他丑陋外表的人欺负和驱逐他,他也默然承受,“没有一个人怜悯他”(132)。“三年来他走遍了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得不着爱,得不着亲切,也得不着仁慈”(132)。对于星孩苦难历程的详细描写,充分证明了这个世界里满是罪恶与倾轧,星孩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每个人都在继续犯下去,直到造成了这个冷漠可怕的局面。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人都无从逃避,甚至连星孩的亲生父母,他至亲至爱的人,也无法幸免。童话的后半部分,详细叙述了星孩为通过“考验”而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他所经历的是一个充满邪恶与阴谋的世界,抓住他并把他当做奴隶使唤的魔术家和伪装成大麻风病人的父亲,以及乔装成乞丐的母亲,组成了这种邪恶与阴谋的重要成员。在苦难的历程中,尽管星孩自顾不暇,但还是能够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那些陷入厄运的弱者。面对落入陷阱的小兔子,星孩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隶,可是我还可以给你自由罢”(134)。面对大麻风病人的乞求,“星孩又动了怜悯心,给了他那块红金,一面说:‘你的需要比我的更大’”(137)。在漫长的流浪生涯里满是病痛与悲伤,它们既是对星孩的重重考验,更是现实生活的影射。在穿越病痛与悲伤的苦难历程中,星孩的灵魂渐渐升华。
三、爱与苦难的悖论
星孩的父母无疑是爱着他的。只是这种爱是尘世的爱,有条件的爱,而非作家毕生赞美与追求的纯粹的爱。而且纯粹的爱的条件极为严苛,足以抵消这种爱能带来的正面作用。为了使星孩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冷酷,他的父母设计了圈套,使他从幸福骄傲的云端坠落到艰辛苦难的尘世,直至星孩受尽折磨、身心俱疲、心灰意冷。如果说爱是不计较得失的付出,为什么星孩要承受如此可怕的折磨?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为什么星孩要费尽周折才能求得父母的认可?王尔德以星孩父母的行为告诉读者,纯真无私的爱已不复存在,爱与苦难已经结成了相生与共的关系。就如同在人类脱离动物本性的社会初期一样,爱因苦难而生,爱也因苦难遭受摧残。星孩对母亲的愧疚令人动容:“他把头俯到尘埃,抽泣着,像一个心碎了的人一样,他对她说:‘母亲,在我得意的时候我不认你。现在在我卑屈的时候你收了我吧。母亲,我恨过你。现在请你爱我吧。母亲,我拒绝过你。现在请你收留你这个孩子吧’”(138)。
这段催人泪下的肺腑之言,直指一个残酷的事实:尘世的爱是以苦难作为交换条件的。爱与苦难,如同人性的两面,相共相伴,无法分离。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一个标准的王尔德式悖论。星孩的这番话,无疑在传达作家的观点:既然父母对子女的爱应当是无私的,那么无论受到何种践踏与伤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为人父母者都不应当拒绝或折磨子女。可惜,在这个冷酷的现实世界,谁又能做得到这一点呢?
童话的结尾是颇令人费解且耐人寻味的。星孩终于得到父母的原谅,赢得了臣民的认可,做了受人爱戴的国王。“他对所有的人都表示公正和仁慈……在他的国里充满着和平与繁荣的景象”(138)。这样的乌托邦景象无疑是历代作家心目中的美好社会图景,也是人类不懈努力的终极追求,“然而他治理的期间并不长久,他受的苦太大了,他受的磨练也太苦了,所以他只活了三年”(138)。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使人伤感。这个结局也绝不同于传统童话的大团圆结尾。苦难在继续,绝望挥之不去,“他死后继承他的却是一个很坏的国王”(138)。本该为星孩的苦难遭遇终于结束松一口气的读者,再度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苦难固然可以成就星孩纯粹的美德,可是苦难也极大地折磨着星孩,无可挽回地毁灭了星孩的生命,葬送了星孩的美德。在这个充满仇恨与暴行的世界,纯粹的美找不到立足之地,纯粹的爱难以寻求。这部童话正好验证了王尔德关于美和爱的观念:“唯有通过艺术,而不是别的,我们才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至善至美;唯有通过艺术,而不是别的,我们才能保护自己免于实际生活中的可悲的沉沦。”③爱的理想是美妙的,现实却是如此丑恶无情。《星孩》这部童话应该是王尔德对爱唱出的一首凄凉挽歌。
注解【Notes】
①③王尔德:《评论家也是艺术家》,汪培基译。参见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 年)305,277。
②王尔德:《快乐王子集》,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下文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