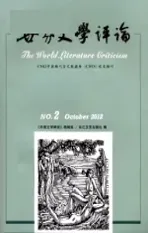杜拉斯作品中的声音世界
2012-08-15范荣
范荣
杜拉斯在1991年发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时,将它归于“小说”门类。因为在书的前言中,作者两次使用“小说”这个词指称此书:“我带着疯狂般的创作乐趣撰写此书。在这部小说中我徜徉了一年,沉湎在中国人和女孩相爱的那一年里”(前言 1)。“在这个故事里,只和他们在一起。我重又成了写小说的作家”(前言2)。虽然杜拉斯用“小说”指称此书,但是读者很容易看出,这部作品基本上采用了电影的叙事方式。尤其是作家在书中使用了大量声音来表现外部和内部世界,如音乐、歌曲歌谣、孩子们的欢闹声以及大海的波涛等等大自然的声音。用声音表情达意,显然是电影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如果说电影是一种运用活动影像和声音的写作,杜拉斯的这部小说则是用文字建构的无声的活动影像和声音的写作。
一、音乐:创造了时间与空间
音乐贯穿这本书的始终。它作为一种在场的直接关注,既是一个具有表情达意作用的独立元素,又是一种与书写文字相互作用、共同表情的互动元素。它给予了作家自由表述的无限空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开头就是音乐的场景:
“一幢房子,处在学校操场的中间,门窗洞开。仿佛过节。从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兹·雷哈尔的华尔兹舞曲声,还有《拉莫娜》和《中国之夜》…… 人们在冲洗房子,……一边洗,一边随着欧洲乐曲跳舞。他们欢笑。他们歌唱。……音乐,那是母亲,一位法国老师,在隔壁房里用钢琴弹奏出来的”。(1)
杜拉斯的读者都知道,《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与《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等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有些同样的故事素材被作家使用不同的叙事方式再表述出来,或使故事有所变形。但是某些音乐曲调,如华尔兹舞曲和《拉莫娜》乐曲在这几部作品中反复回荡,不仅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作者使用它们的用心,也激发了读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张力,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或想象,从而领悟音乐元素在建构故事中的象征意义,获得更强烈的艺术感受和审美体验。
科恩(Edward T.Cone)曾在其论著《作曲家的人格声音》中论及音乐与叙事之间的密切关注性:“音乐是有意义的,尽管对于这意义究竟是什么,没有任何两个权威可以达成一致。于是便有了大量关于音乐讲述了什么、怎样讲述的讨论——的确,音乐能够‘讲述’任何事情。”①音乐以自己特定的语法、修辞和语义结构来传达信息、表述意义、抒发情感。作家根据需要选择相关的音乐篇章,将它融入自己的文字叙述中,成为文字无法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杜拉斯在创作《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时,曾专门打电话请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为她弹奏华尔兹,然后让它出现在小说各种需要的场景之中。小说开头,华尔兹仿佛电影序曲般地开启银幕,引出书中的主人公:“跳舞的人群中,有个很年轻的英俊少年,法国人,和他共舞的是个很年轻的姑娘,也是法国人”(1)。华尔兹和《拉莫娜》不仅打开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银幕,它还是一个记忆的链条,串连起几十年间作家不断返回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电影院》和《情人》等作品:“拉莫娜,我做了一个美梦。拉莫娜,我们携手同出走。我们缓缓地行走,远离所有嫉妒的目光。没有任何情侣,享有如此温柔的夜晚”(《抵抗太平洋的堤坝》57)。四十年前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反复回荡的音乐旋律又飘转来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音乐具有令人心醉神迷的能力,它跨越时空,连接过去的梦和未来的梦。
但是如果认为出现在小说开头的音乐仅仅起到电影序曲的作用,仅仅连接过去和未来,那就不全面了。它更是一个事件,无需讲述,就说出了一切。聆听母亲弹奏华尔兹,伴随音乐跳舞,这个场景既表示当下在场的幸福,又表示对过去时刻的记忆。它打破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界限,使一切都发生在当下,发生在写作和阅读的时刻,发生在弹奏和聆听的时刻。对过去时刻的深深怀念,对未来时光的幸福期待都凝滞在现在时的聆听之中。小说结尾处仍然是音乐:“乐曲声响彻邮船,……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正十分流行,乐曲主题是初恋的狂欢和失恋后不堪回首的凄恻。……乐曲声回荡在停下的邮船上,海面上,深入女孩心中”(《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208-210)。音乐呈现出时间上的永恒性,将兄妹之间难以言表的情愫、法国女孩与中国情人之间的爱恋都幻化成在书中飘荡的永不消逝的音乐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音乐脱离了时间的束缚,不如说它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
二、画外音:超越时空的叙事者
通常画外音被运用于电影。由于杜拉斯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采用了电影的叙事方式,所以就出现了画外音叙述。无论小说或电影,叙述的关键是叙述者选择讲什么和不讲什么,以及怎样讲述。由于杜拉斯的故事经常缺乏明晰的时间线索或连续的故事情节,她的讲述也不是按照事件发生时间的线索,而是按照叙事者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动态变化跳跃式展开,因而故事的时序模糊不清,使得情节看似错综复杂、互不相连。在这种情况下,画外音作为一个看不见的叙述者参与叙事,为故事的接受者(读者或观众)提供了一条心理逻辑线,从而比较容易理解和阐释故事。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故事从音乐开始,从女孩和小哥保罗随着母亲的钢琴曲跳舞开始。还有其他一些孩子在拿水冲洗房子。整个一个欢快的场景。紧接着大哥皮埃尔跑过去抓住小哥的双肩,把他从窗口扔了出去。孩子们都吓坏了,随之散开。大哥为什么这样做?读者(观众)看到这里一定会产生疑问。紧接着女孩跑出去找小哥,没有找到。回到家里,她大声责问母亲为什么只爱大哥,而不爱她这个女儿和小哥保罗。她怕大哥会杀了小哥。这时我们才知道大哥因受母亲溺爱,经常欺负弟妹。接着女孩又出去寻找小哥。许久才找到,他靠着一堵矮墙睡着了。女孩叫醒小哥。故事叙述者是这样讲述的:“我们看到两个孩子观望这同一片天空,先是一起看,然后各看各的。然后我们看到唐从街上回来,朝两个孩子走去。……此时我们听到唐的口哨声,面对这片固定不变的蓝天,唐吹出那首名叫《绝望》的华尔兹”(《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8)。
到此为止,可以说是叙述者摄像头在述说。读者看到听到的都是摄像头展示出来的。这个摄像头以第三人称的讲述提供了一个选择性全知视角,是以主人公“女孩”的观察范围来讲述故事的。上面的场景第一次出现了另一个人物唐,而且他也吹着华尔兹。《绝望华尔兹》是小说的主旋律,吹这个曲子的人物一定与女孩相关。那么他是谁?为什么来到这本书中?下面我们听到了画外音,这个声音带给读者(观众)家庭的过去和唐的故事:
“母亲哭泣着,这时唐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唱起他在暹罗边界的童年故事,当时母亲遇到他,把他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带回家。……女孩也回想起来了,当唐唱起这首被他称作‘遥远的童年’的歌曲,随着《绝望华尔兹》陈述刚才所讲的那一切时,她就会和他一起哭泣。”(《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
读者(观众)听到的画外音也是女孩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声音,它提供了对故事的理解至关重要的信息,同时传达了某种细腻微妙的情绪。对于女孩来说,唐也是母亲的一个孩子,是她喜欢的另一个小哥哥。这一段画外音的述说可以认为是对故事发展的一种铺垫,其中华尔兹以音乐带给人的丰富想象力可以让读者比较准确地把握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试想如果删除了这一段画外音的述说,从兄妹俩看夜空的画面直接切入下面将出现的湄公河和轮渡的画面,即女孩和中国人相遇而发生故事的画面,人物情感关系的发展就会非常唐突,会使读者觉得莫名其妙,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唐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与三兄妹一同长大,女孩视他为和小哥一样英俊的青年,而唐也一直将女孩当成妹妹,俩人之间保持着既纯洁而又相当微妙复杂的感情。作家安排唐在书中的第一次出现是走向女孩和小哥保罗,并吹着《绝望华尔兹》,其中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出现的画外音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人物关系的某种解说。
画外音作为一个看不见的叙事者,有时可以穿越时空,让故事讲述者任意切换画面,传达更多的信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还有一段画外音是以回顾性的视角讲述后来发生的事。画外音之前的叙述是这样的:女孩和中国人到港口兜风,一艘正要起锚远航的邮船甲板上在举行舞会,几个白种女人和高级船员在跳舞。女人们带着笑意,身穿浅色印花连衣裙。“女孩观望着这一场面,简直入了迷”(《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32)。此时响起了画外音;“有很长一段时期,女孩和中国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这么入迷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天,她记起了这件事:她脑海间浮现出这场……甲板舞会的完好形象,它仿佛已进入一本书里,这本书,虽然她还没落笔写作,却已在她人生的每个早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酝酿成熟起来,并且要求她写出来”(132)。作家在此还加了一个注释,说这本书便是《埃米丽 L.》。《埃米丽L.》是杜拉斯1987年发表的小说,画外音提供的信息将女孩与《埃米丽 L.》一书相联系,一方面强化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一书的自传性质,另一方面又使得其中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因为作家是以“小说”指称这本书的。不过无论如何,此处画外音的运用虽然并不与故事直接相关,却提供了超出画面表现的深层信息。在空间意义上,它延展了摄像头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使读者(观众)走进人物的内部世界。
三、大海:声与画的双重叙事
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一书中,戈德罗和若斯特两位学者对于声音的运用作了这样的阐述:“电影艺术家或剪辑师正是根据声音的逼真性作出他的选择,正如电影之初就有追逐的音乐、爱情的音乐,同样存在一些办公室、警察局、街道、海滩等环境声。……声音参与单一的画面叙事的建构。我们所谈论的声与画的双重叙事因此而融合起来。”②杜拉斯的作品正是声与画的双重叙事。
杜拉斯曾在论及自己的一部影片时这样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欲望和情感”(《物质生活》144)。从她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是带有声音的,它不仅呈现活动影像,还述说情感和欲望。杜拉斯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采集各种声音用于写作。同音乐一样,大海的波涛声便是她最常使用的音响之一。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海潮涨潮落,听到浪涛翻滚,如《乌发碧眼》中的这段文字:“海的喧哗,或远或近,……风和日丽时,那厚实的墙会使它的音量减弱,但它的声音永远在那儿——和着风平浪静的大海的节奏。你从来不会弄错它的自然属性。有些风狂雨急的夜晚,你能清晰地听到海浪在拍击房间墙壁,以及和话语夹杂在一起的涛声”(188)。这段文字不是简单的对于海的描绘,而是对于爱的欲望的述说。
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一书开头,音乐序曲过后,文字呈现这样的画面:“她(女孩)正朝大河方向走去。长街尽头,昏黄的防风灯的灯光,欢腾,呼喊,歌唱,嬉笑,其实是河。湄公河”(4)。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水”——包括江河海洋溪流泉水等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形态,它时常传达与母亲、女人、爱情相关的象征意义。杜拉斯在其作品中,经常不惜用笔墨描绘大海、江河、泉水的形态、声音等等。海的声音同音乐一样,是写作的发祥地,是故事和欲望发生的地点。上面的画面让我们听到了湄公河的声音,它传达的是快乐的信息,同时以暗示的方式告诉读者(或观众),女孩走向了欲望的大河。
法国杜拉斯研究专家安娜·古索在其著述《杜拉斯作品中的童年诗意》一书中特别论及大海江河在表现女性爱欲方面的象征意义:“流向大海与之汇合的江河是产生爱情的最幸运的环境,如同杜拉斯赋予这个词的暗示的力量,它同时表达欲望、激情和性愉悦。……人们可以称之为‘情人河’。”③情人河”和大海出现在杜拉斯众多的作品中,将女性经验与爱欲以既浪漫朦胧而又真切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河海的喧哗和奔腾中,生命与自然合为一体,呈现了它的真实、原始和纯粹的面目。
“现在,她回忆往事。……她仿佛还能听到当初在那个房间里听到过的大海的呼啸声。她还记得她写到过这一点,说它像中国城街市的喧闹。她甚至记得她曽写到过大海,说它就在情人们的房间里。她曾用到过这些词:‘大海’和另两个词:‘简单极了’和‘无可比拟’”(《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62)。故事的叙述者兼主人公女孩以回顾性的画外音形式向读者诠释着故事画面——即女孩和中国情人在爱欲中的极致体验。大海和“情人河”奔腾喧闹的声音是女孩永不消失的记忆,也是杜拉斯书中永远飘荡的音乐符号。对于杜拉斯来说,即便是电影,声音远比画面重要。因为只有声音才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力。它与音乐相仿,源自叙述文本,超越直白描述,在更广阔的空间建构充满象征蕴涵的诗情画意。
综上所述,音乐、画外音和大海构成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声音世界,是这部作品——文字文本兼电影——的主要叙事方式。文字和声音创造性的组合,建立起一个叙述系统的有机整体来传达特定信息和意义,不仅使作品得以在一个多角度多维度的空间中加以表现,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和深刻内涵,同时,声音叙事有效拓展了作品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效果,获得意象神合的艺术境界。因此在杜拉斯那里,文本是电影,是戏剧,也是音乐,我们在阅读时,是观看也是倾听。
注解【Notes】
①Edward T.Cone.The Composer’s Voice.1974.转引自王旭青:“音乐叙事学的历史轨迹”,《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2010):55。
②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37。
③Anne Cousseau.Poétique de l’enfance chez Marguerite Duras(Genève:Librairie Droz S.A.,1999)342.引文为笔者译。
杜拉斯:《抵抗太平洋的堤坝》,张容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周国强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乌发碧眼》,南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物质生活》,王道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