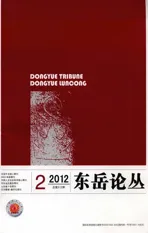论《野草》的基本意识结构
2012-03-28李玉明
李玉明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论《野草》的基本意识结构
李玉明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作为一种基本意识结构形态,《野草》是关于自我的,是自我对自我的究诘,拷问,是对自我的存在状态的探寻,而显现在这种究诘和探寻背后的精神趋向则是某种“抵抗”的行动,即鲁迅的“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凸显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或自由意志,它追求的是自我的某种超越性存在,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地位的某种建构。
鲁迅;《野草》;意识结构;反抗绝望;生命哲学
《野草》世界是一个从经验世界到超验世界的飞跃,然而鲁迅是以经验世界为根基、从来或须臾不曾离开经验世界,他是在经验世界的生存感觉中来体验、并进而把握超验世界和终极价值的。执著于自我的切身的生存感受、总是从具象的层面中挖掘并追寻形而上的意义几乎是《野草》文本的基本趋向,那么,鲁迅又是如何以自我的生存际遇为基础、在具象世界中“体味”“确证”人生和生命的终极价值的?这是《野草》的本体论和意识结构的问题。借助于《野草》意象繁复的象征性表达方式,鲁迅力图昭示出某种既注目于形而上、又联结着形而下的人生观念,人能够把握到自我的存在吗?——在自身痛苦的生命体味中诗人发出了令人揪心的“存在之问”。所以较之形而上的体系式的追问,鲁迅似乎更注重人生内部的内在的联系,注重人在经验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觉,正是执着于现实,正是执着于芸芸众生的人间的生存感觉,在《野草》中才萌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力图在自我的人生之途中即可把握人的超越性存在方式和彼岸世界的冲动,现实性(具体性)和超越性、个人性和人类性、形而下和形而上在鲁迅那里从来都是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本质,人是以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形态而存活的,并行走于世的。老托尔斯泰见到在深秋的泥泞中顽强地挺立、并开着小花的“野蓟”的惊奇和震撼的感觉,就是饱含了对生命的强韧和力量的体认,眼前的“野蓟”的迎风而立和顽强生存昭示或象征了万物——人固有的生命力量和人类本质。同样的情景也使鲁迅为之身心荡漾,他因老托尔斯泰的“感动”而沉思,并写下了《一觉》;在《一觉》中,面对着头顶上飞机炸弹的轰响和随时来袭的“死,”鲁迅反而有了生和人的感觉。《一觉》是人生的“觉悟”,到最后(《一觉》是《野草》的最后一篇)鲁迅终于觉醒了,觉悟到了什么,实质上也确证了什么,是大觉,更是自觉。
一
那么,《野草》中呈现的鲁迅的意识结构其总体特征是什么呢?换言之,鲁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将解剖的利刃刺向自身,决绝地、痛苦地开始盘诘和拷问自我的呢?下面先从《求乞者》文本的解读,具体地整体地感受并把握《野草》中所揭示的鲁迅的意识结构及其基本特征。
象征主义文本因其自身的感觉性整体性歧义性特点,它从来都是一个“结构”,具有层次性特征的结构。在《求乞者》中,它体现为自我的三个不同层次或三个不同层面上的自我,因为处在同一结构中,因此三个不同层面的自我又形成一个“张力”:消解,颠覆;构成,均衡;再消解,再颠覆,是一个矛盾、冲突和对立的结构,互为关系又互相否定,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总是处在某种运动和变化当中,总是处在某种可能性当中。《求乞者》充分地体现了其作为象征主义文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与整体性特征。第一,对“孩子求乞”这一行为,“我”的态度是烦腻,疑心,憎恶,其表现则是“不布施”,这是一种批判性态度和否定性评价;那么“求乞行为”(是否“孩子求乞”或其他人如老人求乞没有特别的意义,未揭示出某种阶级特征)揭示出什么呢?在表层意义上,这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行为,它指向某种生活情态,在其背后显现为或人的生存方式——“求乞式的生存方式”,然而它又是某种真实的社会现状,指向人的或人类的存在状态,那是一个灰暗的蒙昧的落后的奴性的现实图景,在其中只有奴性的“苟活”即“求乞”,而不见人的生存和生命的气息,一切都是灰色的,“灰土,灰土……”。因此,在深层意义上,对于“孩子求乞”,“我”的态度和表现是烦腻与憎恶,它透露出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差异,显现为其与这种社会现实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差异和冲突表明,“我”从“赋予我的现实”中脱离出来,“我”已经把“赋予我的现实”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往往预示着人的一种觉醒:“我”已与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同,“我”觉醒了,其标志是“我”获得了先进的(与落后相对)的思想和意识,被先进的思想“占有”;并在其指导下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和态度: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凭借着它,考察、审判曾经“赋予我的现实”,于是,在这种审判中现实其落后的一面被凸显出来,“我”与这样的现实显得格格不入,这种人为的差异和冲突在这一关系中被大大地强调了。所以这个从现实中觉醒的自我,实质上是一个先觉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因为不同和先进而对现实作了那样的“判断”,其态度是那么明确,决绝,“强烈的好恶,明确的是非”,在他那里一切似乎泾渭分明。明确,坚定,自尊又自信,是其基本的心理和精神特征——他以高傲的姿态对“现实”作了“判决”,审判的是与他无关的现实,并由他审判的。这就是《求乞者》第一层面的自我,是一个从现实中觉醒的先觉者。
然而,为什么“我”忽而也变成了一个“求乞者”:“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这是一个十足的讽刺和嘲弄。对于“求乞行为”,我能够鄙视、否定,坚定地予以拒斥,“求乞式的生存方式”却如影随形,是我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的,在这样的现实中生存着的就是这样的“求乞者”,我也生存于这样的现实中,我不能摆脱这样的现实,我不能断然割断它,我还在“赋予我的现实”中生活、生存,我只能背负着这样的现实生存下去,这样的现实“赋予”我以“求乞者”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求乞者”。到了这里,“我”才明确:这完全是“一种相对化了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他自己。这是多么悲惨的境遇啊。原来,我与现实的差异和距离是假想的虚幻的,是“手造的幻影”,我就生存于这样的现实中,这样的现实(首先而且从来都是)赋予了我的一切。先觉者的“我”又回到了现实的地面上或现实当中,变成了(首先是)一个现实生存者。这是第二层面的自我,——从启蒙先觉者身份又回复到了现实生存者身份,而且首先是一个现实生存者。这标志着“我”的第二次“觉醒”。这时的自我与现实是一体的,即同为“求乞者”,不再有距离和差异,就和忍受着自我的这种悲剧性生存状态一样,回到现实中的“我”更关注这个现实的状况及其改变,尤其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改变,他不再君临现实之上,或隔岸观火,他置身其中,他与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他以后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均以现实为基础,均从现实出发,均是为了现实和现实中人们合理而健全的生存和发展。制约于现实,被现实所羁绊和束缚的现实生存者,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是人的基本状态和本来面目,所以他(她)具有人的一切倾向和色彩,具有人的一切弱点和缺陷,在这个层面上的自我,实质上是对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人的历史性和局限性的体味,是人的有限的相对的存在状态,是对人的相对化有限性的一面的拷问。“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
对陷入“求乞者”地位和局限于“求乞式的生存方式”的自我,诗人是痛恨的否定的和批判的,“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显现为挣脱现实束缚的某种努力和反抗,显现为不甘于自我的局狭的现实存在状态、并力图冲破之的努力和反抗。局狭的“求乞者”角色是人的有限的现实的状态(当下或此在),而反抗则是一种“行动”,是冲破这种有限状态而追求某种无限和肯定,在这里暗示了相对向绝对、有限向无限转化的一种趋向,是力图在相对性中获得某种绝对性。更进一步,则将这种无限趋向绝对化,是对无限的绝对化趋向的揭示和呈现:“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乞讨的声音”是“有”,却是空洞的无力的(实乃一种“无”),而“沉默”(无声)则是“无”,以沉默求乞,就是“无声的抗争”(以“无”否定“无”,暗示了“有”,实乃一种肯定),“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②。求乞者——现实生存者是一种“此在”,是一副行走于人世间的“臭皮囊”,是附着于“躯体”、依存于现实的生存状态,它显现为一种“有”或“所为的状态”,即“无所为”的那个“所为”,然而这样的“此在”又是局狭的有缺陷的有限的、因而是“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无),生命在这种状态下体味到的是“束缚”和“有限”,这时候的“有”潜存着“无”,“有”指向“无”,究其实质又是一种“无”,——“有”(求乞者)等于“无”。“无所为”更是一种“无”,以“无所为”求乞,是以“无”否定“有”(指求乞者即现实生存者、指无,“有”等于“无”的“无”),就是对这种“有”(无)的不满和反抗,是以“无”反抗“无”、否定“无”,就是“有”,否定之否定——一种肯定;“得到虚无”则是以“无”证“无”,“无”就是虚妄的,虚妄的“无”则反证着或显现着“有”,即肯定,这就是所谓“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得到虚无也是一种“得到”,即是一种“有”和肯定。“有无”既互相依存,同时又显示着“无”向“有”的转化趋向,是一种相对化了的关系,是在相对中看取绝对,在有限中把握无限,从而追求一种无限的绝对的永恒的肯定。萨特在他的本体论中把存在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自在的存在”,一类是“自为的存在”。所谓“自在的存在”是指客观的事实性的存在,它只是无条件的存在着,与自身是绝对同一的,自在的存在是偶然的,荒诞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虚无,缺乏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必然性;所谓“自为的存在”是指有意识的存在。萨特说自为的存在其特点是:“是其所非而又非其所是。”意思是说,自为的存在是它现在所不是的东西,而又不是它现在所是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存在的缺乏,它永远是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自为的存在永远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不断地成为什么东西,它总是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身。在萨特看来,在宇宙中,只有人才具有意识,才能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也只有人才能称得上是自为的存在③。
这一切,暗示出一种什么趋向呢?它揭示出:这是个体的生命的“抵抗”的冲动或趋向,力图从局狭的生存状态中挣脱而出、冲破现实的羁绊和束缚的努力就是一种“抵抗”,“抵抗”这一行动本身显现为一种“有”和肯定,是某种生命力量的突击和爆发。这是第三层面的自我,一个勇于抗争和挑战的自我!而“以无非无”,多少还是一种愤激之辞,暗示出这个自我还有些游移,怀疑,不是那么有底气(弥漫于散文诗中灰暗的调子和色彩透露出了这一倾向),然而抗争的姿态是坚定的,因此这个自我又是自尊自信的,由自卑自嘲到自尊自信,预示着自我的又一次脱皮、新生、挺立,预示着自我生命的一个新的形态。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求乞者”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涵的意象,而且具有整体性和多义性的特征,属于象征主义的艺术范畴,因此以所谓客观的现实关系和逻辑关系是无法予以解析和呈现的,在这方面它们显得无能为力。这里有一个如何解读、把握象征主义文本的问题。所以在《求乞者》中“作为一种结构”至少有三个层次,是三个自我的矛盾、冲突,也是三个自我的对话和转化。
这就是《求乞者》的基本意蕴,也是《野草》的一种整体性的基本意识结构:对人的历史性和局限性的考察以及在考察基础之上的理解、宽宥,在其背后则是对“人”的基本状态的肯定,是对人及其本身和人的一切的极端的尊崇和张扬,是对人的整体性姿态的把握和呈现。这种姿态肯定人的基本生存和自然生存或生物性生存,人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哪怕是(尤其是)人的最卑微最自然的生存和欲望。缺乏主体性或主体性丧失的存在,只是如一般的生物,出于本能而选择了生存,这种生存的目的是已经麻木了的目的,因而,他并不是存在论的存在。但是,人无法摆脱这种存在,人只能在这种存在中创造自我。现代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思贝斯说过:“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仅是一个现在存在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④。在这个意义上说,《野草》的意识结构更是具体的内在的,但是它同时却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形式。
那么,《野草》的意识结构形态是如何呈现、如何构成的呢?从以上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它源自于鲁迅对自身的凝视和解剖,是诗人对爆裂为几个不同层面的自我的“揭示”,所以它不局限于某种思想的或意识的细微特征,而是指向自我及其存在的基本结构形态。这是《野草》一般的基本的意识结构。将解剖的利刃刺向自身的结果是:鲁迅孤寂悲哀地看清了自己悲剧性的现实存在和历史地位。整部《野草》所展露出的就是鲁迅的这一心态,其中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张力:意识到的悲剧性存在与力图摆脱这种悲剧性存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始终处于一种冲突对立之中。于是我们看到,鲁迅由对现实和历史的否定,走向了对整个启蒙运动及其作用的怀疑,更进一步,鲁迅又怀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走向了对整个人生的否定,对自我的否定,遗世而独立。这种全面的否定倾向造成了鲁迅的现实自我的分裂,并最终粉碎了他关于自我的一切“神话”。于是,在《野草》中出现了至少两个以上的自我:一个是困窘在社会现实中的自我,一个是力图摆脱超越这个现实自我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正走向死亡的自我,一个自省的自我,一个反抗的自我,这两个或以上的自我既对立冲突着,又互为依存互相联系着,消长起伏,互相转化。《野草》的整体性意识结构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具体而特殊的结构形态。因此,作为一个“结构形态”,构成《野草》意识结构的诸层面(自我)其内涵既是繁富的,又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这诸多层面是不均衡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排列的,有些层面,比如基础性的层面或所谓最底层,作为一个根柢性的自我或观念,是极其深厚恢廓的,它联结着诗人(鲁迅)人的基础性观念,它往往指向那个现实性自我,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只有把“人的观念”建立在人首先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认识之上,才出现了真正的“人的发现”,所以自我的这一层面是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的,因而也是根柢性的,其深湛性是其他层面上的自我所无法比拟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其上才生长出诸层面的自我,觉醒的自我,犹疑徘徊处在两难境地的自我,面临死亡的自我,反抗的自我,等等,即使这些层面的自我也并非处在同一平台的,其内涵也有或单一或丰厚之别的,有一些是观念的,思想的,有一些则是“意象”的,行动的,有一些是充分的,成型的,有一些则不过是情绪的,信息的,甚至是不过一个声音,一个暗示,一种趋向,一个动作而已。如:“一径逃走”(《狗的驳诘》);“我疾走”(《墓碣文》);梦中“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颓败线的颤动》);“我于是坐了起来”(《好的故事》);等等。但是,即使一个动作,也暗示了自我的一个新形态,显现了一种新趋向;而这一结构的最上层,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个自我,则具有方向性主导性的特征,与最底层的那个根柢性的自我相比,其往往是情绪性的,其精神指向不免朦胧模糊,还不那么确切,还不那么深厚丰满,但是它却联结着诗人的人生信念和终极关怀,昭示出自我的超越性存在,它烛照着大地之我,赋予大地之我以意义,赋予生命以价值,二者又是同构关系,内在关系。总之,这一意识结构其基础性根柢性的层面(最底层?),是极其沉厚的夯实的;其上的层面——并非一层,而是诸层——是以之为根基生发、生长出来的,是其伸向四面八方的触角,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自主特征的系统(母系统与子系统,大系统与小系统),是一个上下勾连、联系紧密的层次性结构,甚至是诸层并行于一个平台(其常态不是这样),而又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结构,是极其丰富的复杂的。它们只有一个指向:鲁迅的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如此,我们才稍微目睹了这一伟大精神世界的初步面影!
二
鲁迅又是决绝的,决绝地冲破现实世界的羁绊,以一种挑战姿态倔强地打破自我的这种悲剧性存在。于是,对于这个现实自我的死亡和消殁,鲁迅毫不可惜,相反,他急切地期望这种死亡“火速到来”。——这就是构成这一矛盾张力的另一端:鲁迅所具有的惊人的精神力量和罕有的意志力量。这个分裂着的自我还有另外的一面。虽然这另外的一面在《野草》的整体意象中并不构成主要的内容,相反,它往往是混沌模糊的,不确切,不明晰,呈现为一种感觉状态,但是,它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和倾向,因为它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是另外一种声音。它的出现和存在表明,鲁迅力图摆脱现实自我的这一悲剧性位置,虽然这种挣脱更多的时候又呈现为另一种悲剧性选择和承担,然而正是在这一新的悲剧承担中,我们捕捉到了鲁迅自我的另外一面,抓住了鲁迅自我的一种新形态,把握到了鲁迅意识结构的另一端。我们反复说过,《野草》的写作是鲁迅出于“看清我自己”的需要,那么,在《野草》中鲁迅更力图看清或体会自我的哪些方面呢?综观《野草》,可以说,鲁迅力图揭示自我所体察到的某种罕有的“力量”:像他那样的人,像他那样的先驱者才可能具有的某种殊异的意志力量和精神力量——一种“天启”的或神(耶稣)所赋予的精神品格。是这样,一定是某种“天启”或“神示”,这一点(从《野草》中来看)鲁迅甚至没有任何怀疑,鲁迅自觉地豪迈地体味着自己所承担的这一历史性悲剧性角色。在《野草》中直接暗示这一倾向的文本虽然不多,仍有三篇:《复仇(其二)》、《失掉的好地狱》、《淡淡的血痕中》。前者是很直接的,在耶稣的“受难”中或在耶稣身上,鲁迅分明体验到了某种亲缘关系,那简直在暗示鲁迅自己,——虽然文本最后归结为“人之子”,但鲁迅所体味到的是某种“神之子”的情怀,是自己身上的某种“神性”。《失掉的好地狱》则“变身为”魔鬼,在其中诗人体味到的是某种“魔性”,然而归根结底魔性还是一种神性,“有一个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这个魔鬼曾经主宰“三界”,其身心被一种罕有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所鼓胀着。后者似乎是“人”了,但是是一个能够与“造物主”及其所统驭的人间秩序相抗衡的特出的“人之子”——一个“猛士”:“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他反抗造物主即神的世界,在这种反抗中猛士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能够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那种神性,非人间所有的某种对抗力量。“非人间所有”,“伟大如石像”(石像应该是一种特指或隐喻符号),是对《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这一意象其精神状貌的揭示,这就不难理解了:不仅在上述三个文本中,不仅在直接揭示和体味某种“神示”的文本中,而且几乎在《野草》的每一首散文诗中,鲁迅都力图揭示只有他那一类先驱者才具有的某种精神品格,一种罕见的充沛的意志力量和精神力量,一种在人身上所显现的“神性力量”!“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以此“回响”回应了20世纪初自己在《摩罗诗力说》中急切的呼号。——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野草》延续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和寻找,而将其具象化的一种呈现,即只有在这时候,在《野草》中,鲁迅才能赋予其完整的形态(“完型”,完型是一个阶段或过程)。对自我“力量”的这种体味和揭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野草》文本的最强音,但是可以说,正如体味着咀嚼着自我的孤独、虚无和绝望一样,鲁迅也在体味着自我的“力量”,至少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了《野草》内在的基本精神结构形态,构成为具有一定弧度和韧性的某种“张力”。而且,可以这样说,这种“张力”所显现的某种平衡状态正在被打破(消解),出现了某种“倾斜”,或正运动在一个新的结构状态中,其标志就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这是《野草》精神结构的一种新的整体性趋向。——《野草》中所显现着的鲁迅的精神结构并非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变化而动态的精神趋向,可能性是其内质。
而且,更多的时候,这个自我是愿意牺牲的。在《死火》中,“死火”面临着两种选择:留在冰谷,将被冻灭;或者走出冰谷,重新燃烧,但可能烧完。诗人选择了后者,在生命之火的燃烧以至于烧完中,使自我之花绽放。在《过客》中,鲁迅对自我心态的各种倾向进行了层层剥离,但是整个诗剧所呈现的鲁迅心态却给人以沉重郁闷之感,因为在其中找寻不到支撑鲁迅前行的任何信息。但是即使如此,“过客”也没有停息。而且,始终有一种“前面的声音”在催促着“过客”,使他息不下,不能息,只能向前,走下去。在这里,鲁迅暗示出:生命的终点是悲剧性的死亡(坟),但是生命的过程却是内涵丰富而充实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从这里到死亡(结局)的过程。是的,《过客》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丰厚而伟大的“过程”!从这里出发,鲁迅才从忧伤和困顿中站立起来,开始了新的一轮人生探索。史铁生是深味鲁迅的。或受鲁迅的启示,在《好运设计》中他这样说,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因为只要人们眼光盯着目的,就无法走出绝境。当意义的呈现从终极目的转向实践过程的时候,当目的被消解而过程被空前地凸出的时候,终极关怀和意义终于立于不败之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身所在。这是不能被颠覆,被异化的精神乌托邦,这是经受了虚无和荒诞的洗礼,同时又超越了,战胜了它们的理想主义。这时候,理想主义不再是实在的,功利的,它被形式化、空心化和悬置起来了,悬置在最具审美价值和非功利的实践之中⑤。史铁生是一位最具荒诞感的当代作家,其文本的荒诞意味直接得之于鲁迅,所以他对《过客》等文本和鲁迅精神结构的把握最到位,也最真切。——虽然这些文字并未直接评点《过客》和鲁迅,但是显然史铁生从鲁迅那里得到了“启示”,更重要的是,他对鲁迅的某些精神特征作了最准确的诠释。鲁迅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他成了反抗虚无的第一个挑战者。
三
作为一种基本意识结构形态,《野草》是关于自我的,是自我对自我的究诘,拷问,是对自我的存在状态的探寻,而显现在这种究诘和探寻背后的精神趋向则是某种“抵抗”的行动,即鲁迅的“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凸显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或自由意志,它追求的是自我的某种超越性存在,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地位的某种建构。这是鲁迅在日本从事文艺活动之始就一直在探求的问题。
在早期,作为启蒙思想的接受者鼓吹者,鲁迅对建基于个人的西方价值及其个性、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观念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了然于心,感同身受,但鲁迅并非一味地接纳这些思想,也并非启蒙思想的完全支持者,他对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有保留的,在某些观念上甚至形成冲突,比如,鲁迅认为,对西方社会过度泛滥的社会民主倾向必须加以警惕,因为它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压制人性,灭绝个性。(实际情况正如鲁迅所揭示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多数和少数的讨论,对此也有所警惕)无差别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意味着个性的沦落。不仅如此,鲁迅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其对启蒙主义的探讨,其核心是“伦理的进化”即人的进化和发展,注重的是个体及其人格的现代化,即自主的“个人”和人的主体性建立。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承接了梁启超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及其实践问题。这些思想在鲁迅早期文献《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均有一定的论述。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了“文化偏至”的文化观:“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自此,鲁迅开始了关于人及其个性、存在的追问和寻找,并且在其所敬仰和推崇的西方哲人那里找到了回应。其中尤其是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和影响引人注目。后来,1920年鲁迅又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尼采之于鲁迅的影响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就《野草》而言主要体现在情绪性和象征性两个方面,有学者指出,“尼采哲学的象征性、情绪性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使得鲁迅能够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而赋予新的内容,鲁迅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尼采的兴趣,那种深刻的孤独感和大破坏、大愤激、大憎恶、大轻蔑的情绪方式,久久地萦绕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使人仿佛听到了尼采的遥远的回音。从这个方面说,尼采的影响远远超过施蒂纳和其他人”。鲁迅与西方思想“遭遇”,并以某种“内证式”的方式极其独到地把握到了西方价值的“精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关键在于人的个性自由,而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扼杀了这种自由,因此鲁迅的个人观建立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之上。他提倡独特的、主权的个体,这亦是鲁迅文化哲学的核心。“鲁迅把人的个体性与主观性置于他的社会历史思考的中心,从而形成了他的文化偏至的历史辩证法”⑥。在这里,鲁迅实质上开始了一个主体性的发掘和建构的过程:不仅外在地探寻,而且力图在自身中、在自我内部寻找,并建构之。这一努力,作为一种集中的和显形的状态,主要体现于《野草》中,可以说《野草》乃鲁迅第一次集中地在自身中建构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鲁迅对于西方思想的这种悖论,反映了他对传统与现代同时的怀疑。在反传统的过程中,他洞悉到自身的历史性,他是“站在传统中反传统”,这本身就需要自我否定。反传统,就是否定自己;履行旧道德,还要激烈批判旧道德对国民的危害。自己沾染着历史的遗迹,还要否定历史。“把自我纳入否定对象中加以否定,正是鲁迅反传统的最彻底体现。”“与黑暗捣乱”和“绝望的抗战”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他的反传统主义的最深刻的体现。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鲁迅对自身的“绝望”来源于自身与传统的联系,理解了鲁迅对传统的否定性判断来源于对民族新生的期望,我们才能理解鲁迅关于个体悲剧人生观为什么没有把他引向虚无哲学,而是以“反抗”为核心,以“绝望”为出发点,构建他的人生哲学。这种否定带来的分裂与矛盾,恰恰也是鲁迅不断探索、寻找历史真理和挽救国民的内在动力,是他创作的源泉。“反抗绝望”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把价值与意义的创造归结为个体的选择与创造,面对“黑暗与虚无”,人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力量承担其存在的责任,而“奴隶”则怯懦、随遇而安,没有个性,逃避责任,承认现状,不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个体,因而也无力在反抗与选择中赋予生活以意义。第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强调孤独个体的“绝望的抗战”,从而个人面对无可挽回、极端痛苦的失败反而产生了“更勇猛,更悲壮”的人生尊严,而“奴隶道德”却用“同情”来消解个人人生旅程的无法回避的艰难处境,从而泯灭了独立自强的人格⑦。因此,反抗绝望在鲁迅思想和意识结构中便构成一种根本性识别。
《野草》的写作起因于鲁迅的自剖,是鲁迅对自我及其存在(个人的现实位置和历史归宿)的究诘与拷问,在这个意义上说,《野草》是“存在主义”的。——这应该视为《野草》更内在的意识结构。作为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联系,那就是在《野草》中鲁迅意识到并强烈地体味到的自我存在的“荒诞性”,而荒诞或荒诞感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加缪的哲学中,荒诞主要指述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现代人被抛在这种环境中无处可逃,他唯一可做的只是如何面对荒诞并在荒诞中生存。在加缪看来,指述现代人基本生存处境的荒诞,意味着作为意义本源的“上帝”无可挽救地死去,从而导致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无意义或虚无。尼采宣称的“上帝之死”隐喻着西方文化信仰的根本危机,它意味着那曾经赋予事物与行为以意义的各种观念学说的解体。在此处境中,虽然一切都还存在着,但已毫无意义,因而无法理解这一切;虽然人们还行动着,但行动失去了可信赖的意义与理由,因而行动变得漫无目的而荒唐⑧。这种荒诞感也为鲁迅所经验和体味,所以几乎在《野草》的每一首散文诗中都可见出这种自我存在的荒诞感。鲁迅首先体味到自身荒诞的境遇,荒诞的现实处境和历史角色:在《秋夜》中,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凛秋的夜空”挤压着我,我被逼仄到一个局狭的角落里;在《影的告别》中,“影”来向“你”(形)告别,然而告别了的“影”却陷在一个巨大的难堪而尴尬的两难困境中,黑絮一般的暗夜或即将到来的黎明,或者“淹没”它,或者“消失”它;《过客》甚至不知从何来,到何处去,甚至没有姓和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认自己,他或者是冰封在冰谷中的“死火”(《死火》),或者是墓穴中的“死尸”(《墓碣文》),或者是死在尘土飞扬人声鼎沸的路边、只能任人摆布的尸体(《死后》)。与此相联系,进而又突然洞见了自我的荒诞的命运归宿,——一种趋于死亡、并正在走向死亡的意识趋向,宿命般的、不可逃避的死亡结局是这种荒诞性存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归宿,它并非简单的“人总有一死”的意思,而是藉由这种可预见的荒诞的悲剧性死亡,揭示了人生的无意义无价值,即引发的是一种人生虚无感。死亡的阴影死亡的趋向如影随形般弥漫于笼罩于整部《野草》中:暗夜将淹没掉影子,白天或黎明不容许影子的存在,无论怎样,“影”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就是“死亡”(《影的告别》);“过客”已经很困顿疲惫了,但是他还是走,一直在路上,一直走,向前走,然而前方是什么,愈向前走,他愈接近那个人生的终点——坟,前方是“坟”——死亡,人生的最终归宿是可预见的死亡,死亡的情绪死死地环绕着他,怎么也逃不了,一路走来的过客始终被这个揪心的问题纠缠着(《过客》);被“爱欲”和“仇欲”所蛊惑的、立于荒野之上的“一男一女”,其最后的结局是身心的由圆润而“干枯”,还是一种死亡(《复仇》);耶稣悲悯地注视着众人,那些以色列人正在钉杀他——“神之子”同时亦“人之子”,透心的大痛楚穿透了他,变成了“人之子”的耶稣目睹并咀嚼着自己的死去,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吗(《复仇(其二)》)?!所以,《野草》的死亡意识首先突出的是“当下”自我生存的荒诞性,它加重了当下生存的虚无感,进一步渲染了当下生存的绝望情绪。——既然人生无法摆脱死亡阴影的纠缠,终将化为尘土,那么,“活着”的人生其意义又将焉附?在这里,荒诞的现实境遇和历史角色源自于荒诞的命运归宿感,一种悲剧性的死亡体验。尤奈斯库指出:“荒诞是指缺乏意义……,人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先验的根基隔绝了,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无意义,荒诞,无用。”⑨概言之,荒诞首先指向“意义本源”解体后人所面临的虚无。其次,荒诞指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因为在一个对意义本源(以“上帝”为表征的各种观念体系)充满信赖的时代,一切都先行纳入了意义秩序,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在此没有意义的虚无,也没有荒诞。再次,当意义本源在现代被还原为虚构而解体之时,荒诞就不仅指述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而指述一切时代的人的本真处境了,只不过这种生存处境在古代被掩盖起来罢了⑩。
然而,在《野草》中,在鲁迅那里,这种荒诞感只能、而且从来都是体味和感觉,他无法也不可能以明确的理性的方式予以言说,是一种不可解释的存在之荒诞感(萨特试图分析,而加缪则干脆拒绝解释,所以,他只关注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存在之荒诞的这一特性——永远处在感性的状态,或曰存在之荒诞的感觉性特性,使任何关于它的“言说”都显得软弱无力力不从心,尤其是那些所谓“窥见了存在之面目”的明确的体系性的解析,其结果往往是“言诠式”的嘲弄。“存在之荒诞”始终处于整体性神秘性和感觉性的状态下,荒诞感首先是不合情理不可理喻不合逻辑的,悖谬和不可理喻乃是其实质。“不可理喻”亦即无法以理性和逻辑的形式予以表达和传达,那么要传达这种存在的荒诞感,或借助于扭曲和变形,即以一种非理性的手段揭示非理性的荒诞感,或借助于“梦境”,在一种非现实的情景中,在打乱了现实性逻辑的境况下,天马行空般地、无拘无束地掇拾似乎随意散落的意象,在意象与隐喻的“契合处”,寻找暗示的内容,亦即象征的寓意。所以,要整体性地传达存在之荒诞感,象征主义及其所谓的“应和”是最有力最切合的艺术方法。上述两种情况正是《野草》的基本抒情方式,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艺术特征的创作方法,《野草》就是纯正象征主义的文本。
四
《野草》中所揭示的鲁迅特有的意识结构,除了鲁迅从尼采等西方思想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并与西方价值“精神”构成呼应以外(海德格尔、萨特等都较鲁迅晚出),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如道家、佛教等也给予鲁迅一定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又与中国古代思想形成了沟通或接续的关系:其一、这种关系是更内在的,主要限于整体性层面上;其二、鲁迅把握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而非对道家、佛教的全盘接受,更非等同于他们;相反,比方说,鲁迅始终对道家是有所警惕的。稍作辨析,我是以竹内好的“无”的观念来解读《野草》,来界定《野草》的生存哲学的。竹内好的“无”指向鲁迅的黑暗感觉,更是指鲁迅所处的一种绝望的状态,他认为鲁迅是从黑暗和绝望当中产生的或形成的,即鲁迅不是从希望开始,而是始于绝望。只是与竹内好不同,我认为,与“无”相对,至少在《野草》中还有一个“有”的观念,二者显然是反向的对立的,然而在《野草》中、在鲁迅那里却是一体的同一的,是一个东西,一个事物。《影的告别》所呈现的就是这一精神结构趋向。在《影的告别》中,鲁迅的生存体验更是内在的:无边无际的、黑絮一般地压过来的黑暗,是一种虚无,导致了彻底的绝望;但是,选择了这样的黑暗,是否又意味着“有”呢,“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而以悲剧性的承担方式显现,因而又是悲壮的崇高的,是一种有价值有内容的肯定。换言之,体味着黑暗,体味着虚空,就是一个“无”,但是承担并选择了黑暗,选择了虚空,就是一个“有”。“充盈着光明的黑暗”,暗本身映射着光,暗向明的向度和转化。竹内好指出:“当然,鲁迅通过对痛苦的分析,不借助抽象而以个别事物的形态接近了普遍真理,从客观上来看,这是他不断成长的表现,但尽管如此,他现在的意识,却没能离开总是自己对自己不满的这种对黑暗的绝望的抵抗感”。至此,《野草》实质上完成了一个“过程”:呈现于《野草》中心的或表面的,是一个巨大的铺天盖地的“无”,绝望,黑暗,空虚,衰败的躯体,抉心自食的痛苦,等等,然而,又选择了并悲剧性地承担了这一切,只有绝望与黑暗,只有“我”在绝望与黑暗中。这种选择就是怀疑于“无”,显现为对“无”的否定性趋向,同时也就暗示了“有”,肯定了“有”。不仅如此,“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种选择不仅在自身中暗示了“有”,而且它还指向外在的世界,旧世界也将伴随着我的消失而消失,——我是旧世界的人,我消失的那一天,旧世界也将一同偕逝,在自身的否定中显现着双重的肯定(有)。《野草》自足的结构方式本身已经完成了从“无”向“有”的转化、转折。
这也可以解释《过客》里“前面的声音”等,在表面上,“前面的声音”具有一种游移的、变化的、不确定的、朦胧的特征,就是一种怀疑或“无”,是对人生价值和人生信念是否或有无的无法把握,但是内质里,我们分明感觉到涌动于其中的某种生命的感召力量,是否在其中潜藏着某种源自于心灵深处的“人生之念”呢,不容凝视无法把握,却分明能感觉到,这就是一个“有”,一种肯定,冥冥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终极价值吧,当鲁迅这样问的时候,在表面的巨大怀疑之下(无)实质上潜藏着某种积极的信念。——这应该是一种宗教的或宗教式的情绪吧!《野草》带有很浓厚的佛教色彩,鲁迅这种“有无观”与佛教的“有”、“无”、“空”(虚空)、“有所执”应该是有联系的吧,佛教语言和体格在《野草》中打下了很深的印记,佛教的某些精神如建立在生死观根柢上的终极关怀恐怕是渗透到鲁迅骨子里的吧。因此,这时的“无”并非“子虚乌有”,在“无”中鲁迅填充了最珍贵的东西——自我的生命或自我的生命过程:一种“抵抗”,一种对绝望、死亡和黑暗的反抗,一种具有行动和实践意义的“在路上”。在这一过程中,在其中,鲁迅强劲地吹进了生命的气息,只有生命才能“证实”,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什么是“黑暗”和“空虚”,鲁迅的“实有”包含了双重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分析,都是机械的简单的,甚至是人为的,也因此,它不可能完整地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和哲学观念里,鲁迅也在这一分析里被肢解了,他不再是一个具有内在自足“结构”的统一体。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154页。
②《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③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页。
④雅思贝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9页。
⑤史铁生:《好运设计》,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⑥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29页。
⑦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279页。(上述凡引文均据此,不再一一注出)
⑧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⑨转引自朱虹:《荒诞派戏剧集·前言》,见《荒诞派戏剧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12页。
⑩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I210.97
A
1003-8353(2012)02-0024-08
李玉明,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