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庆德
2011-08-20周彦涛
□周彦涛

浓烈、呛鼻的硝烟刺得孔庆德睁不开眼睛。他脸色紫红,凸出的喉结因恼怒而剧烈蠕动,额头那块血痂不住地往外渗着血珠。他刚刚经历一次战斗,国民党军队的土炮发射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一块呼啸而来的铁片削去他额头处一块食指大的肉皮。他侧脸看着押解他的士兵。剽悍、高大的孔庆德足足高出他们半个头颅。他突然顿足,大声诘问:“你们为什么抓我?”
“你是改组派!”
孔庆德浑身一颤,一脸茫然。
1931年11月的湖北红安县,躁动和悲壮浸透了这块糙红的土地。红四军与盘踞在红安县城内的国民党军第69师展开激战,史称“黄安战役”。红军将士势如破竹,破城而入,国民党军师长赵冠英仓皇之际令其秘书骑上他的战马,率众从南门突围,自己则带着几名贴身随从由西门潜逃出城。
身骑战马的秘书成为众矢之的。他被红军击伤后被擒。他跪倒在手持短枪的孔庆德脚下,一边叩首一边声称自己不是师长赵冠英。孔庆德抬脚把他踹翻,率部追击赵冠英。
当他擒获师长赵冠英时,颤悚不已的赵冠英烂若泥团。他是个“独眼龙”,张大一只独眼惊恐地盯着孔庆德,孔庆德扳过他的头,哈哈地笑了。不容分说,将其挟在腋下,直奔红军团部。
这是红军首次攻下整师设防的强固据点。战后红安城内沸腾了,“解放区的天是艳阳天”,红军战士和穷人们为改天换地沉浸在不能自禁的喜悦中。兴奋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绳索加身,正经受屈辱和死亡折磨的年轻人。
祸从天降。几天前,孔庆德率部在红安西南约10公里的高桥河击溃敌军,清扫完战场,正满载战利品班师之际,几个自称是奉鄂豫皖中央分局保卫局之命,前来逮捕他归案的人悄悄逼上他,他们蜂拥而上,将他扑倒在地。卸掉他身上的武器之后,一个瘦削的军官伸手扯掉他军服上的领章帽徽:“给我捆起来!”一根细长的麻绳瞬间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
他被押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在这里,张国焘正在实施残酷的内部“清洗”。孔庆德被押进来。他不住地翕动鼻翼,仿佛嗅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主审他的军官冷冷地望着他,冰冷的目光中充斥着仇恨。他们曾经一同经历冲锋、杀戮、跋涉和迁徒,战火中生死与共。生存的欲望和对朦胧未来的憧憬让他们无法容纳任何试图颠覆他们这种理想的“异类”。主审官双眼洇血,他很疲倦,也很恼怒。可是,他很快就显得茫然无措。他找不到孔庆德任何“反叛”的嫌疑,一时语噎,无奈地注视着他,仇视的目光中渐渐地掺杂了些暖意。
孔庆德年幼丧父。父亲因“通共”被关进国民党大牢,后惨死囹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地主逼债,饥寒交迫。1928年春隶属国民党革命军第46师北伐攻占了山东曲阜,16岁的孔庆德走投无路,从戎离家。
国民党部队的阴暗、腐败和欺凌百姓的行经,让孔庆德陷入迷惘和痛苦中。1931年2月5日,他参加中共秘密党员魏梦贤领导的“六安兵变”,在六安打死敌团长击伤敌旅长后,投奔红军。与那些直接参加红军的士兵相比,孔庆德的这段“弯路”此时成为遭受质疑和拷问的“污点”。
死神与他擦肩而过。但他并未得到赦免,他被开出党籍,与100多位像他一样侥幸逃生的人一起,在保卫局派出的人监管下,罚做苦力。
时序进入公元1932年,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亲往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向鄂豫皖发起第四次“围剿”。强敌压境,战事急促,红军伤亡惨重,鄂豫皖苏区岌岌可危,红四军方面不得不实行撤离转移。孔庆德随同罚做苦工一行人,分散编入方面军总部的各部门担任“挑夫”。孔庆德分配到电台处,负责搬运发电机。
这部电台是在黄安战役中缴获的。孔庆德他们负责搬运的电台发动机重约六七十公斤,他们一路磕磕绊绊,身上的军衣被日光和风雨剥蚀成了网状。
红四方面军走走停停,边走边打,忽而向南,忽而折向北,似无定向。孔庆德根据听到的零星消息,判断红军可能已经陷入被动的局面。几场激战,几次绝处逢生。红军沿荒野山路行进,追堵之敌沿公路和大道疾进。红军前脚刚进村,不待饭熟下肚,敌人尾随而入,饥饿,战斗,红军将士在极度困厄中生存。孔庆德脚上的鞋子完全被磨烂了,他用在沿途拾掇来的烂布包裹。生满硬茧的脚掌被锐石穿破,血肉模糊。荆棘丛生的山路上,留下了绵延不绝的血脚印。
从腥风飒飒的秋天一直走到天寒地冻的隆冬,红军在漫天风雪中翻越秦岭。这天,被饥饿、寒风和痛苦折磨得周身瘫软的孔庆德与总部人员正依着山崖小憩,一支队伍急匆匆与他们擦身而过。
猛然间,他听到有人惊喊:“这不是孔庆德吗?”
他循声望去,见是自己的老团长王宏坤。这位参加过黄麻起义的骁将此时已是红四军第10师师长,率全师担任方面军开路先锋。
“你没被杀呀?”老团长惊喜地跳下马,注视着他。
孔庆德一时语噎,泪花在眼眶中翻卷。
老团长黯然点点头,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上马离去。
孔庆德随总部继续穿行于崇山峻岭间,出秦岭,翻越川陕交界的大巴山。人困马乏,衣单鞋破,饥寒交迫。沿途虽已被先头部队清除冰雪覆盖的荆棘、杂草,但山路狭窄、溜滑。孔庆德他们负重前行,难若登天。夜里宿营,他们找一避风处点燃篝火,蜷缩着打一会儿盹,便赶紧起来活动肢体。这天夜里,疲倦至极的孔庆德一行脊背贴地,昏头睡去。寒风砭骨,当孔庆德被寒流扎醒,挣扎着站立起来,眼前情景让他头颅炸裂:和他依偎在一起的几位战士双目紧闭,身体僵硬——他们死在了一个香甜的梦乡里。
生命残若游丝,命运乖张暴戾。但被列为“另类”的孔庆德没有死去,待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四川通江后,生命的春天悄悄地不期而至了。
是年初春,在红军控制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之后,得到喘息之机的红军战士沐浴了短暂的春光。孔庆德这时接到通知:回第10师30团报到。
已是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没有遗忘孔庆德这些蒙冤的红军将士,他以部队减员严重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由,将陕川肃反中几百人组成的劳改队悉数纳入了红四军。以戴“罪”之身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了一年多的孔庆德重获新生。
已是红四军10师36团团长的孔庆德率2800余人的疲惫之旅踏进茫茫草地时,时值1935年的初秋。裸露的松潘草地广裹、粗犷,目力所及,是茫茫无际的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辨不清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成洼,淤泥和腐草浸泡出一层黑油,散发出腐臭的气息。
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求补给是不可能的。部队此前紧急作了动员,炒制了青稞粒作为干粮。
孔庆德率领部队,擦着松藩草地东部边缘地带,渐渐深入到草地腹部。脚下,杂草疏密高矮不一,深浅坑洼不平,走在上面,有时感觉像踩在软塌塌的海绵,有时踢着硬撅撅的草根子磕磕绊绊。各部队都严格遵循一定的行军路线,不能随便绕行或赶超。茫茫草地,危机四伏,不慎踩空,就有可能陷进泥沼,惨遭灭顶之灾。枪声渐渐远去,而草地气候暴戾无常,忽而暴雨如注,随后又飞雪漫卷。6天时间,他们昼夜兼程,走到草地北边的达班佑地区。这里稀稀拉拉地散落着百十户人家,是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经历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试图在这里稍作休息,然而,紧盯着他们行踪的胡宗南部早已在此布网,他的一个团抢占距此50公里的包座地区,另一个师由漳腊疾进赶赴包座,欲会同守敌堵击红军。
包座是红军北上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一场激战在所难免。守敌早已在此严阵以待,而红军仓促应战,带着饥饿和疲劳与敌浴血奋战。
孔庆德热血急涌,持枪冲入敌阵。耳畔风浪呼啸,猛地,他身子打了个趔趄,眼前一黑,一股柱状的血流从他胸口喷射而出……他右手握枪,左手撑地,试图直立胸脯。卫生队长冒弹雨冲到他身边,用手压住他胸部伤口处,遭到挤压的血流穿过指缝,四处喷溅。卫生队长急忙掏出纱布,猛地塞进伤口。血流止住,他被抬上担架。
军衣被血浸透,他昏迷过去。这一枪是致命的,斜穿肺部,从背后打了出来。这是他第四次挂彩了,长刀、炮弹和子弹在他躯体上都留下无法祛除的疤痕。
这次没有人相信他会活下来。左肺贯穿,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死亡是注定了的。他躺在担架上一直昏迷。战火接连,不断有首长身披硝烟,从他身旁匆忙而过。他们看见他脸色苍白,周身蜡黄。肉体的血似是流尽了,除了胸部微微起伏显示他一息尚存外,看上去他像个死人。他们一个个神情黯然,摇头离开。抬担架的士兵步履踉跄,满眼悲怆。
眼看他就要死去了。几天滴水未进,嘴唇干裂,呼吸日渐衰竭。抬担架的士兵把他放在了地上,静静地等待。忽地,他嘴巴大张,一团黑色的污血从他口中凌空喷出,继而,他睁开了眼睛!
周围的士兵目瞪口呆。
他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四周依旧是荒凉的草地。苍鹰低旋,高声哀鸣。灰色的长龙游动在变幻莫测的草丛中,数万双脚板一同拍打松软的草地,轰鸣震耳。逶迤前行的红军队伍在迷雾中时隐时现,他们身后,每隔半里便存有一个鲜明的路标,标志着不可更改的行进方向。
“怎么又在草地里,不是出草地了吗?”孔庆德忍着伤口剧痛紧皱眉头问。
冷雾缭绕,前景迷茫。与红一方面军刚刚会合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又分道扬镳,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几千人马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则奉命南返。张国焘为此鼓动他的麾下:回马四川,直指成都平原,那里有大米吃。
对于饥肠辘辘和被雪山、草地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红军士兵来说,晶亮的大米和无际的平原犹若一幅诱人的图画,激励他们迈动沉重的脚步。
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感到茫茫草地更加凶险了,狂风、暴雨、冰雹接踵而至,青稞制成的干粮所剩无几,草地里的野菜在部队第一次过草地时已基本挖掘干净,二进草地的先头部队对残存的野菜实行了彻底“扫荡”,待孔庆德所部沿着他们的足迹艰难行进时,草根和树皮成了他们惟一可以裹腹的食物。
草根在从水洼中舀出的浑水中烹煮,缺盐,煮出的野菜汤又苦又涩,硬邦邦的草根直刺咽喉。队伍中有人开始浮肿、便秘,头昏无力,病号与日俱增。
抬担架的那个面黄肌瘦的士兵突然双腿发软,摇摇欲倒。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伸手抓住他的手,他和那个生命耗尽的士兵一同跌落在地。
“把我的马牵过来,我自己骑马走。”他下了命令。在马背上颠簸,渗血的伤口痛若刀绞。他冷汗淋漓,嘴唇被牙齿咬烂。
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穿越了草地。当孔庆德清点他的士兵时,泪雨滔滔。没与恶敌交战,但这个团自然减员近千人!
无辜的死亡仍在继续。孔庆德率部队走出草地来到毛儿盖时,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看到了一片无数次出现在梦境中的庄稼地。那是些青绿的尚未成熟的玉米,当地人叫青包谷。部队以高价买了下来。
玉米散发着黏稠的香馥,鼓动着饥饿至极的士兵跃动起来。他们拢了些柴禾,点火烧了便狼吞虎咽。不多时,几个士兵紧捂腹部,浑身抽搐,满地打滚。团长孔庆德忽地意识到事情不妙,狂奔过去,夺掉正在狂啃不止的士兵手中的玉米。
“不要多吃!都把玉米放下!”
声若炸雷,但无法阻止饥饿的人群。他怒不可遏,朝天开了一枪。
枪声把他们震愣了。很快,他们感到腹部胀痛。庄稼地里到处滚动着呻吟不止的士兵。长时间的饥饿,他们的肠胃薄如纸,骤然大量进食,几名官兵被胀死,其中有一名营教导员。
死亡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当他们第三次穿过草地,重新北上时,胜利的曙光已近在眼前。
战斗、行军,从1935年8月到1936年10月,他们经历数不清的大小战斗,往返雪山草地,辗转川康甘青四个省,孔庆德用他那双坚实的大脚丈量了这段漫漫征程。
他仍要继续走下去:率军出师山西抗日,进军冀南,移师冀鲁间,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个革命者不断跃进的足迹清晰地嵌印在一块块红色热土上。
在宁晋地这的大地上,依然能够寻到孔庆德的功名。1939年,孔庆德率冀豫游击支队与日军周旋。驻宁晋日军出动300余人,步兵和骑兵齐头并进,拉着一门大炮,进驻大杨庄。
这天午后,孔庆德借助望远镜观察大杨庄敌人动向,猛地发现半截土围子后面露出一门大炮。他心里一动,“夜晚把它弄过来!”
孔庆德选出30余名精兵强将作为突击队,每人左臂扎一条白布巾,携手榴弹,配一把大刀。为了不惊动敌人,孔庆德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
冬夜里寒气袭人。突击队在大杨庄群众的引导下,顺利摸到大炮跟前,一个守炮的鬼子正抱着枪打瞌睡,队员一刀将他劈死。
一个突击班拖大炮,另两个突击班扑向旁边鬼子的住房,浇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点着,顿时火势冲天。
在突击队员有推拉之际,没想到炮膛还装着一发顶膛的炮弹,炮弹“轰”地一声打了出去。惊骇的敌人喊叫着往外冲,被突击队一排手榴弹炸得死伤一片,退缩回去。
秋收后的田地都是耕过耧平的,连一块石头都没有,赤脚跑路几乎一点声响也没有。但把笨重的山炮弄走却不易,一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
天亮后,日军顺着拉炮的辙印一路追赶。后来又专门派出由两辆坦克、18辆汽车组成的快速搜索部队,跟踪追击,妄图夺回大炮。
孔庆德派出部队一面阻击,一面把这门笨重的山炮不断转移。后来,从日军俘虏口中知得:这门大炮是天皇御赐。日军指挥部为此恼火万分,将该部的大队长撤职法办,并下令必须将炮追回。可后来日军连这门炮的影子都没见着。
徐向前亲自观看了大炮,激动之余派人给夺炮勇士们照了一张照片,并在大炮上写有“八路军在大杨庄战斗缴获日军之山炮”一行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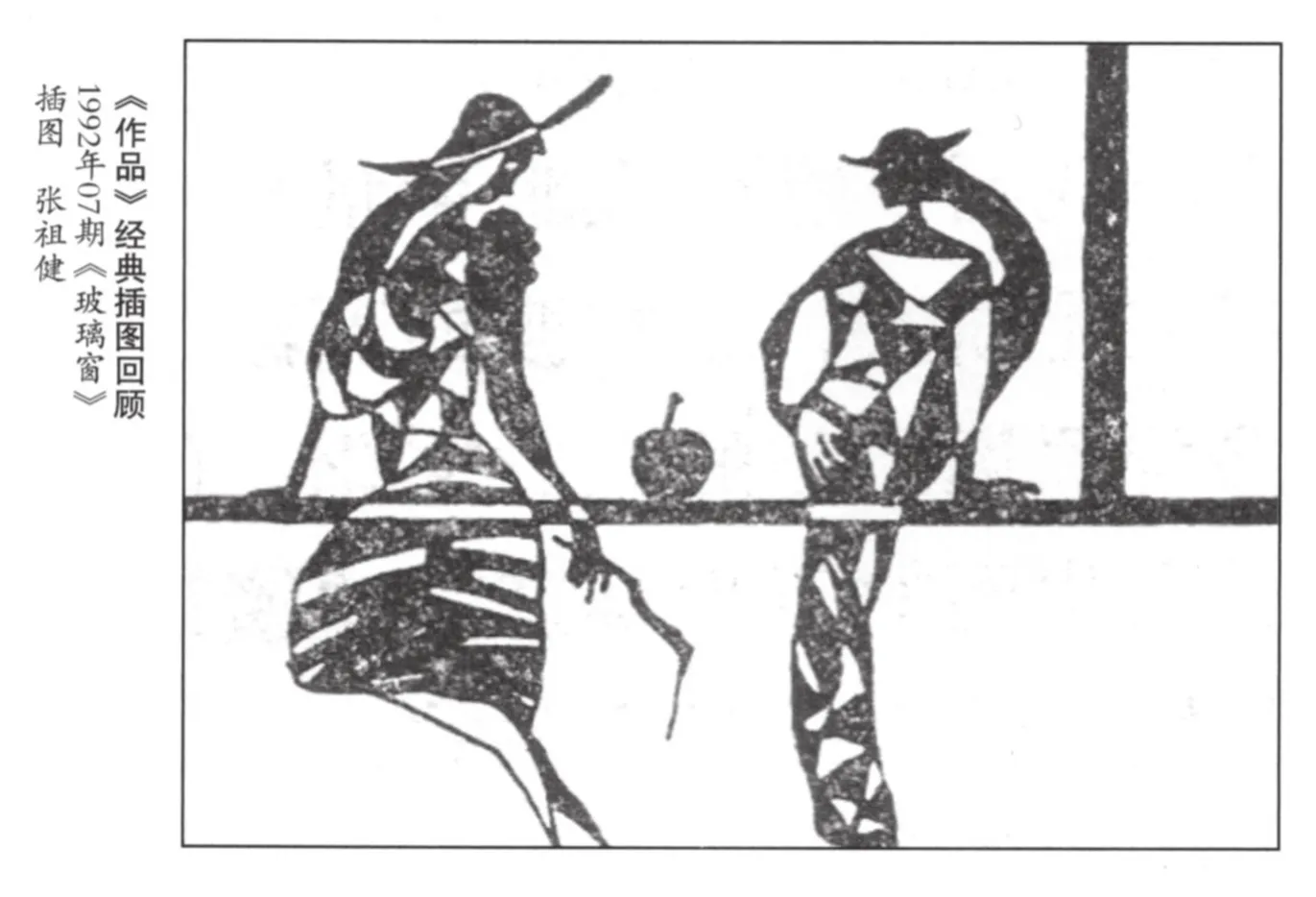
八路军夺得鬼子的大炮,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日军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提供大炮下落者,赏金不断提高却无人问津。事隔一年,宁晋县有一勇士冒着生命危险,趁日军疏忽,盗出3发炮弹,献给八路军。这3发炮弹从这门日本天皇御赐的山炮炮膛怒射而去,炸裂在日军群中。
这门大炮后跟随“刘邓大军”辗转参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展览于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
将军卸职后,曾随参观人流悄然来到这门山炮前,他仔细端详,面露微笑。峥嵘岁月已沉淀在他的记忆深处,他跋涉、迁徒的足迹也被岁月的尘埃淹没,而一种精神和情感却穿越时空,浅浅的,浸润在他这抹灿烂的笑容里。
一辆伏尔加轿车穿过躁热的火炉城市武汉,向西北方向疾驶。车上坐着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他斜依在后座上,双手微微颤抖。摇下车窗玻璃,沿街城墙上不时可见白灰写的一行“火烧孔庆德”的大字。他气鼓鼓地怒骂一句,关上车窗,默不作声。
1967年的武汉被“造反有理”的狂潮席卷,孔庆德作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犯了方向性错误”,被造反派批斗。与众多从战火中走来的将军一样,孔庆德有一副火暴脾气,敢于“放言”,但粗硬的外壳下却掩藏着斗争的韬略和艺术,周恩来总理戏谑地称他“孔大炮”。动乱之际,心力交瘁的周总理想到了他:让他出山,负责武汉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工作。
6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令,为此中央作出加紧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武汉“二汽”作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指示:“二汽”要抢在战争爆发前建成,为军队解决越野性能优良的机动工具。1964年“二汽”曾两度上马而又两度中途下马,1965年又再度开张。造反的浪潮急涌而来,“二汽”停工“闹革命”,筹建工作陷入停顿。根据中央指示,武汉军区派出一位副司令员,会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乘飞机来解决问题。飞机尚未着陆,机场就被从十堰赶来的造反组织包围,飞机只好升空返航。
一片混乱。周恩来总理忧心忡忡,他命令孔庆德:快去,一定把“二汽”搞起来!孔庆德接到命令,带着秘书和警卫员,直奔地处武汉西北方向的十堰。
烈日坠落黄龙滩。轿车驶进十堰老镇,孔庆德来不及吃晚饭就和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及国家纪委、建委的负责人聚首在芦席棚,商讨如何制止混乱,打开局面。大家说:“这乱哄哄的工地,没有半年的工作,恐怕开不了工。”
孔庆德手拍桌子大声道:“半年?半个月的时间也长了。三天,三天就得解决问题!”
大家愣住了。翌日,张湾河滩上就挤满了人群。脸庞黝黑、风纪扣紧扣的老将军,晃动高大身躯登上了土台,台下吵闹之声戛然而止。他摘下军帽,花白头颅在朝晖下熠熠生辉。他那洪钟般的山东腔开始在人群中炸响:“今天请大家来讲明一点。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建设二汽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今天来就是执行毛主席建设二汽的命令。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借口,偷懒耍滑,不干活,不施工,要离开基地,要走。这干的是什么革命呀?这里面有坏分子,坏分子在捣乱!……”
台下鸦雀无声,一个个目瞪口呆。
“革命是自愿的,”孔庆德的大手一挥,“愿意建设‘二汽’的留下,不愿意干的可以走……”
台下那些捣乱分子拉长耳朵想听听“可以走”的下文。
“但是,不开介绍信,不发路费,不发工资。”
这一着厉害,等于开除。
“还有已经离开基地的人,限十天以内返回基地,否则过期开除。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就讲这些,没来的人,你们回去给他们捎个口信。”
次日晨,孔庆德从席棚里走出来散步,惊奇地发现工地上居然有人挥锹动土干了起来,而那鼓噪“造反有理”的高声喇叭也破例哑然无声。各工地纷纷电话报告:一个人也没走。
三天后,离开的人也陆续返回工地。
孔庆德第一板斧就制止了混乱。
造反有理甚嚣尘上,造反派轻易不敢招惹。孔庆德也手捏一把冷汗。那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将孔庆德堵在了办公室。孔庆德上下打量他一番,问:“你来干啥?”
那头头脖子一梗:“夺权!”
孔庆德笑了:“凭什么?”
“我是革命造反派。”
孔庆德把手中的茶杯猛墩在桌上:“革命就要干革命工作,现在全厂职工都在山上架高压输电线,你就上山去抬铁塔,证明你是不是革命的!”
眉毛高挑,目光如炬,手腕处那块鸡蛋大的伤口明晃晃地摇动在那头头眼前,头头眼晕,憋闷半晌,离去。
“二汽”的糟乱摊子渐渐被孔庆德梳理清晰,开始蹒跚前行。1970年的9月24日,他们造出二十辆献礼车,在这年国庆节那天,簇新的车辆出现在武汉街头的游行队伍中,整个武汉为之沸腾。
孔庆德刚刚为之舒一口气,周恩来总理又紧急召见他。这天中午,孔庆德和秘书步出北京火车站,驱车直奔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早已在此等候了。
周总理说:“你们先吃饭吧。”
性急的孔庆德想尽快知道情况,解开风纪扣对着电扇吹:“不用了,我们在车上吃过面包。总理有事就交代吧。”
“急,是急呀!这次请孔老你这门‘大炮’来……”
孔庆德一听“孔老”二字慌了神,忙说:“怎么敢在总理面前称‘老’,叫我孔庆德吧!”
“在我党历史上,人过50岁就可以尊称为‘老’嘛!董老、郭老还不是50岁就喊起来了。”周总理笑着解释。
孔庆德自知自己的分量,便说:“可不能那样比,他们是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贡献大,知识又渊博。”
周恩来看着孔庆德谦恭的态度,无声地笑了。
“好了,现在就交代任务。这次请你来,是要你去指挥修建焦枝铁路。”
“修铁路?”孔庆德脱口而出,“总理,修铁路我不会,我只会扒铁路。”
战争年代为了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他带领部队扒过不少铁路,惟独修铁路没干过。
总理摆摆手,继续交代任务:“焦枝不建成,主席睡不着啊!”
孔庆德立刻感到建设焦枝铁路事关重大。
焦枝铁路穿越豫鄂两省,跨越黄河、汉水、长江,是一条战备干线。该线北部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鄂西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并经过以产粮、棉著称的南阳、襄樊、荆州地区。因此,毛泽东对这条铁路的建设极为关注。还在正式修建之前的1969年6月,他到武汉视察,就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询问:“你们那条铁路上的怎么样了?”
曾思玉回答:“我们那条进川的路已动工了。”
毛泽东忙说,不是的,不是那条川路。他叫人拿来地图,指着地图说,是与京广线平行的焦枝路,是在群山中建的一条南北走廊。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
毛泽东略停又说,万一战争打起来,京广、津沪线被打瘫痪了,南北大动脉就中断了。有了焦枝和枝柳路,就可以抗衡一下,南北交通就不会中断。
最后毛主席严肃地说,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时间,抓紧修好这条铁路。
“不会就学,边学边干。”孔庆德肃然而立。
“这就对了。”周恩来笑了,“修汽车制造厂,建设三线,你干得很好嘛。这次又多给你压一副重担,焦枝总指挥,具体如何搞,你们武汉军区和铁道部开个会研究一下。”
孔庆德激动地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斗着胆子立下军令状:“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让毛主席睡好觉。”
周恩来赞道:“很好!”
孔庆德回到武汉,发动百万军民参与铁路会战。中央要求,铁路要在1970年底,最迟于1971年5月1日前铺轨通行。而在此后不久,中央又提出工期要比原计划提前十个月。
孔庆德顿感火烧眉毛。
焦枝铁路全线800公里,有三个大型咽喉工程——“两桥一洞”。这“两桥一洞”即襄樊汉水大桥、洛阳北的黄河大桥、南阳以北的九里山隧道。九里山隧道上了6000民兵也未能加快进度,特别是汉水大桥图纸尚未完全出来,无法施工。
孔庆德一听就急了:“走!到汉水大桥看看。”
孔庆德一行心急火燎地来到汉水大桥工地。全线开工快一个月了,汉水桥还没动工,孔庆德急切地问:“为什么图纸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来?”
设计人员说:“设计一座铁路桥是很复杂的,需要多方面的资料作依据,因此设计的时间就长。况且我们接受任务也晚。”
“要多长时间?”
“半年!”
“半年图纸才出来,施工又要多长时间?”
“也需要半年。”
孔庆德一听暴跳起来:“半年不行!半个月,半个月也长了!”
“不行啊,总指挥。”
“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子,”孔庆德说,“有没有长江大桥的图纸?它的上部结构与汉水大桥的结构是不是一样?”
“两座桥的上部结构是一样的。”
“从中给我截下一段!”孔庆德的语气不容置疑。
设计人员依计讨来长江大桥的图纸,截下其中一段,略加改动,一段大桥的图纸在几天后就产生了。
197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49周年这一天,焦枝沿线大小车站张灯结彩,锣鼓喧天。800公里的焦枝铁路八个月建成,成为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
……
将军终于老了。花发渐渐袭上了他的头颅,岁月在他的额头刻满了“年轮”。1983年10月,他离开工作岗位休息。黄昏渐渐向他袭来,晚霞依旧在映照着他。淡红的霞光中,走进人生暮年的孔庆德将军常常孤坐,他微眯着眼睛,恍若看见徐徐落下的人生帷幕。此刻他的眼里含着悲凉,而嘴角却浮动着久久不逝的微笑。2010年9月29日,孔老将军驾鹤西游了,但他的微笑、他的精神却永存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