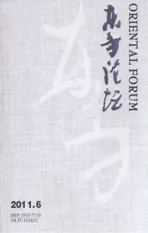租界文人视野下的空间构设与道德表达
——邹弢《海上尘天影》析论
2011-04-03李永东
李 永 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租界文人视野下的空间构设与道德表达
——邹弢《海上尘天影》析论
李 永 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邹弢的《海上尘天影》是理想主义与写实精神,政治表达与欲望释放相结合的产物。邹弢租界文人的经验视野,影响到《海上尘天影》思想观念的表达。《海上尘天影》提供了的世界性人文空间图景,得益于并且受制于作者的上海经验,小说描述的核心空间绮香园可以看做是租界生活图景的一个缩影。在道德观念上,《海上尘天影》的故事游走在西方观念和传统伦理之间,道德上举意不定,所塑造的理想女性类型亦透露出租界文人的道德不适感和迷惘感。
租界文人;上海租界; 《海上尘天影》;空间;道德
一
在晚清的狎邪小说创作潮流中,邹弢的《海上尘天影》多少显得另类,是理想主义与写实精神,政治表达与欲望释放相结合的产物。晚清狭邪小说的发展经过了“溢美”、“近真”、“溢恶”三个阶段。[1](P349)《海上尘天影》①《海上尘天影》共六十章,又名《断肠碑》,原题梁溪司香旧尉编,成书于1895年,1904年印行。梁溪,即今江苏无锡,司香旧尉是邹弢的笔名。王韬在1896年为小说作的“序”中指出,《海上尘天影》乃“门下士梁溪邹生为汪畹根女史作也”,小说可以看做邹弢的情感自传。汪畹根,名瑗,堕入风尘后改名为苏韵兰,颜其居曰“幽贞馆”,自号“幽贞馆主人”。小说中的韩秋鹤和汪畹香分别是邹弢和汪畹根的化身。属于“近真”的作品。《海上尘天影》虽然“近真”,但与《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2](P275)的风格有所不同,是一部把纪实与虚构的混合文体推向极端的小说,小说借助情天恨海的外层神话结构,从中衍生出以韩秋鹤与苏韵兰之恋为中心的上海欢场故事,最后又从神话世界回到作者的现实情感告白。与单纯的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不同,《海上尘天影》虽“大旨专事言情”,但同时“于时务一门,议论确切,如象纬、舆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等,均有涉猎,“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3](P2),“足善风俗导颛蒙”[3](P3)。《海上尘天影》也突破了《花月痕》、《青楼梦》等晚清情爱小说美人沦落名士飘零的故事格局,把富商顾士贞和洋务官阳子虚两个家族的生活遭遇糅合到情爱故事中,提供了晚清内忧外患的军事、政治、外交、商务、舆情等多方面的信息,并借助韩秋鹤的海外游历,呈现了欧美日俄的历史地理、科学技艺状况。总之,《海上尘天影》把诉私情、“导颛蒙”、论时务、输西学等多种主题混杂在一起,反映了租界文人在个人情欲与洋务时事之间编制故事的喜好,思想、文体的趣味接近《孽海花》,又比《孽海花》多了神话的色彩和理想的激情。
二
邹弢属于比较典型的租界文人。他是王韬的门生,创作《海上尘天影》之前,已在上海报界谋生十多年,主编过《益闻报》,与西方来华人士有过广泛交往,并于1898年加入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发起旨在传播西方科学的“益智会”,广泛学习西方科学并予提倡,著有《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经世实学之书,是“晚清文理兼通,科学与文学兼擅的报人作家”[4]。长期的租界生活修改了邹弢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他属于比较典型的被租界语境所塑造的洋场文人,即租界文人。租界文人的经验视野,影响到《海上尘天影》思想观念的表达,小说提供的故事面貌在诸多方面受到租界经验的制约。
邹弢的租界文人经验视野,渗透到创作中,使得《海上尘天影》突破了以往小说本土文化空间的局限,提供了一幅世界性的人文空间图景。小说的故事空间涉及天堂仙界和下界人间,涉及国内和海外。小说从天堂仙界的故事说起,交代并预设人物命运,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外层叙事框架,在仙界与尘世的生活遭遇之间进行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所构设的天堂仙界,并非纯中国式的。情天恨海相联系的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故事,固然源自中国的远古神话,但九天之尊却不是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而是西方基督教中的至高神“上帝”。小说还以《圣经》的创世纪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形成:“天地未辟之前,有亚当元沮之天父,将日月分光,水陆分位”[5](P12)。天界的组织似乎与上海租界的状况相仿佛——外侨掌控租界,华人填塞其间;神话故事和神灵谱系的中西杂糅,也类似于上海租界中西文化共时空的错杂情形。现实人间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人间故事空间亦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世界图景。上海租界作为通商大埠和新闻言论中心,有助于邹弢这样的租界文人形成全国视野和海外眼光。小说中的尘世故事涉及的空间以上海为中心,旁及扬州、苏州、天津、金陵、江阴、泰山、新疆、湖南等国内空间与日本、美国、俄国等国外空间。小说中旁及的国内地域空间,虽然其山水地理、民情风俗会被零星提及,但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并不具有多大的文化区分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人物行踪和命运遭遇的地点。小说的文化空间既濡染了浓厚传统文人趣味(如:绮香园的苏州园林风味,妓女的名士化,吟诗作画谈玄赏荷等文人雅趣),又明显受到租界文人经验视野的制约。就《海上尘天影》的文化选择和故事创意来说,海外空间和绮香园值得探究,它们也是小说中最重要、最能体现租界文人视野的空间。
海外空间的集中呈现是小说的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这三章叙述了韩秋鹤为时一年的海外游历。随着他旅行路线的延伸,世界性的地理、经济、军事和人文风情的宏阔图景,得到了粗略勾画。他先去了美国,在三佛昔司克登岸,先后游历了纽约、伦敦等城市,美国的历史地理、现代旅馆的设备、新式农业的经营方法、矿石的开采冶炼、纽约和伦敦的繁华盛况,一一有所涉及。游历了美国之后经香港去了日本,在横滨、长崎等地逗留了一阵,领略了日本妓女的风情,观看了洋人的马戏表演,亲眼目睹了每日印报三万张的印刷机器,绘制了进攻日本的路线图。随后受林友香之邀,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意大利,到达俄国圣彼得堡,参加了俄国宫廷的舞会,遇到吴冶秋,在聚会中详细地谈到俄国的炮台、炮弹的发射角度。小说提供的图景无疑是粗疏的,邹弢并无海外游历的经验,世界图景的想象与他在上海租界同外侨的交流、对租界现代文明的体察、广泛涉猎西学有很大关系。世界图景的叙述和想象,得益于他作为租界文人的知识体系和观念视野。海外场景叙述的详略处理,亦局限于租界文人的经验视野。韩秋鹤的海外游历,凡是叙述较为详细的异国状况和场景,或者可以看做作者经验的空间移位,把在上海租界体验到的新奇事物安置在海外讲述,变成海外见闻,如马戏表演和高速印报机,也是那时上海租界出现的新事物,上海的新闻、画报对之多有介绍;或者属于作者把在上海阅读西学报刊书籍所得,以及与圈子中的文人、外侨交流时所获知识,装入小说,如论美国的商务国政,介绍金银冶炼之法,谈论煤炭的形成,细讲大炮的射击技术这些内容,当是如此。与之相对的是,乘坐远洋轮船的情景体验和海外异国情调、城市景观等内容,小说叙述得极为简略,而这往往是有过出洋经历的文人所乐于详述的。小说对纽约的描述,不过以“百货纷腾,客商云集,说不尽的大邦风气,海外繁华”寥寥数语加以交代,就这几句套话,还可以当作是模仿上海租界情形描画的。对韩秋鹤海外游历的叙述,除了后来出现在绮香园里的两个外国妓女,没有略微具体地提及任何一个异国当地人,所交涉的人物群像,其实还是活跃在上海租界的洋派人物,属于在上海租界就能开列的一份类似人物名单。自然,韩秋鹤在海外交流的都是些讲究实学的洋派人物:或为在异国做买卖、办报纸的洋商,或为洋务派的青年仕子,或为驻外的参赞,就连碰到的美国妓女马利根,也是能操中国话,游历过日本,对“机器测量格致化学”颇懂行,置备了几间屋的仪器,造过不少东西。韩秋鹤的海外交游,不过是与上海租界人物的海外重逢。由于缺乏海外经历,作者只有把洋场人物影像搬到国外,配合韩秋鹤完成海外游历故事。总之,小说提供的海外见闻和世界图景,得益于并且受制于作者的上海租界经验。
小说所建构的海外游历故事和观念体系,是丰富而芜杂的,亦可以看到租界文人经验视野的规约作用。小说提供的海外游历故事所包含的兴奋焦点不是异国情调,而是政治与情欲相纠缠的芜杂观感。政治和情欲是晚清租界文人乐此不疲的两大叙事主题。对政治主题的热衷,源于晚清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处境和租界殖民语境所激发、强化的民族意识;情欲主题的泛滥,则与租界传统伦理道德的消淡和情欲消费空间的扩张有关,租界提供的淫冶风气与个体对自由情欲的追求混合在一起,为租界文人身陷花界恋情、书写花界情欲故事制造了机遇和兴致。二者的同步推进,使得租界作家沉醉于政治与欲望混合的叙事模式。韩秋鹤一方面扮演着军事间谍与民族大势的阐述者的角色,收集邻国日本、俄罗斯的地舆形势的资料,纵论国际局势和民族处境;另一方面在国外亦不忘寻花问柳,交接洋妓,并不断担忧、怀想旧相好汪畹香和金翠梧。小说刚叙述了韩秋鹤与日本妓女玉田生缱倦半月有余的情节,旋即抒写韩秋鹤念及“身世之交多险,国家之虑正长”,感叹“老天你生我这个人,应该给我一个称心施展的境遇”;刚向朋友吴冶秋倾诉过对汪畹香的一往情深,紧接着转向谈论报纸上日本入侵高丽而引发中日战争的新闻,表白对中国战事的忧虑。就这样,民族忧患感与儿女情长如影相随般交织在一起。
《海上尘天影》故事延展的主要空间为绮香园,苏韵兰与众多沦落风尘的佳人聚集于此,阳子虚和吴冶秋也借园中房屋做公馆,各路名流才俊、仕宦子弟慕名往访,在这里演绎才子佳人恋情,游园赏景、论诗联句、行酒令、办女学、诉衷情、闹别扭、伤离别、叹飘零,上演了上海版的风尘女子与才子名士的大观园故事。绮香园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封闭空间,带有浪漫理想的色彩。绮香园位于闸北脱空桥西头,原是乌有先生的遗业,后卖给西陵无是乡人武官莫须友。“脱空桥”、“乌有先生”、“无是乡人”、“莫须友”都属于对绮香园踪迹的虚无规约。一座绮香园,作者有意把它的来头和具体位置虚化,并且让莫须友很快消失在人间,苏韵兰拥有了这座园子,引领一大群风尘女子开始了风流繁华的生活。绮香园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但大观园翻版为上海的绮香园之后,就打上了鲜明的租界文化的精神烙印。小说虽然虚化绮香园的来头和具体位置,让它模糊在上海的城市空间中,但没有忘记把它定位在特殊的文化区域空间——“租界地方”[5](P358)。这一空间归位也意味着文化观念的归位,对于表达人物、生发故事、制造观念来说,显得至关重要,为之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绮香园中违背传统伦常的人物关系和新奇开化的观念,如果不是依附于上海租界的文化空间,而把绮香园嵌入北京、西安、奉天,甚至杭州、苏州、广州的城市空间中,那么,在晚清社会的文化逻辑中,小说的故事和观念都将因过于离经叛道而接近天方夜谭,遗留下大量不可信叙事。《上海闲话》证明了亦中亦西、“非驴非马之上海社会”在道德评判方面,能够规避传统礼法的驯化和惩罚,“每见上海社会中发现一伤风败俗之事,一般舆论则必曰:此幸在上海耳,若在内地,即使幸逃法网,亦不免为社会所不齿”[6](P104)。由于小说的故事和观念有了“上海租界”作为文化空间注脚,就变成得见怪不怪、顺理成章了。
绮香园不是单纯的风月场所,它是上海租界生态图景的一个缩影。上海海关道阳子虚借绮香园一角做公馆,仕宦吴冶秋也把家眷迁到绮香园,与当红妓女比邻而居,他们如此行事实属相当“西法”。绮香园容纳了洋派官宦、中外妓女、落魄名士、得意才子、尼姑女道等各色人等。园中建有花神祠,还凭空降下一座断肠碑,同时又办了一所女塾,教授中外语言和技艺,神道迷信与新式教育并行不悖。绮香园还像租界其他娱乐消费场所一样,出售门票,供人参观游览。绮香园的娱乐生活丰富芜杂,交流的话题五花八门,“冯姑献技”、“谢女谈元”、“公子送巾”、“校书鼓瑟”、“雅士谈兵”、“娇娃论画”、“碧霄舞剑”、“湘君谈禅”、“赏荷花”、“闹红社”、“试气球”、“遇私情”、“媚知己”,不一而足,仿佛一锅新旧、中西文化的大杂烩。就连园中女塾的礼仪以及所开设的课程和考试的内容,也是如此。学堂院主、教习与学生见面的礼节有着中西合璧的怪诞,在中西乐器的合奏声中,两跪一叩的封建大礼与见面握手的西方礼仪在同一场面中出现,英国书与中国书同样讲授,针线、画图与算术皆为修学内容。女塾秋季考课包括对对子,背诵《女四书》(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女德教育所用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四本书汇集的总称),中英文互译(把德国《伯灵京考略》中的一段英文翻译成华文,把《三国演义》中的十几句话翻译成英文),再加上格致和算学考题。绮香园女学的教育方式似乎表明邹弢认同“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观念,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三
《海上尘天影》的道德观念态度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没有一以贯之留在旧道德的堡垒里。实际上,小说证明了作者在道德上举意不定。小说灌输忠孝节义观念的人物故事为数不少,无论域外空间还是国内空间,作者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宣讲。在韩秋鹤的海外旅途中,作者没有忘记以中国道德楷模的故事补充海外阅历的匮乏:韩秋鹤与吴冶秋在俄国谈论中国的忠孝节烈之事;吴冶秋给韩秋鹤详细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玉蓉的妇女守节尽孝后自杀的故事,令韩秋鹤对之顶礼膜拜。在国内空间中,借汪家仆人秦成护主的事迹表现了“忠”,借汪畹香割臂当药为母亲治病的事件表现了“孝”,借苏韵兰为未婚夫贾倚玉守身(虽然是不值得守的杳无音信的一个浪荡子)的苦衷表现了“节”,借绮香园的姐妹交情以及韩秋鹤割胸肉为汪畹香治病等情节表现了“义”,而吴冶秋与冯碧霄之子英毓为父报仇、为君解忧而奔赴疆场建奇功则属于“忠孝两全”之举了。这些“忠孝节义”的例子,有的甚至属于极端的例子,把“忠孝节义”观念的布道推向了极致。
如果说整本小说都宣传旧道德旧伦理,尚能表白作者伦理道德观的保守性与纯粹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第十七章“荡春心淫尼污三宝 施妙计智女宝千金”对尼姑庵污秽淫欲故事的展示,接近了“三言二拍”赏玩离奇淫欲的态度。绮香园排座次的故事则颠覆了作为封建“忠孝”基础的等级观念。作者既试图贴近现实的生活逻辑,又把个人情愿与租界风尚结合起来,构设臆想中的身份等级谱系,使得绮香园中人物的“座次”发生了逆转,妓女与贵族太太平分秋色。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等差关系自然不容僭越,由道德、知识所划分的“士农工商”的职业身份内含地位的差等,“倡优皂卒”更为世人所不齿。但是在妓女苏韵兰掌管的绮香园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颠倒混乱的伦理等差图景。在晚清上海租界,妓女确实具有身份区分的功能,有脸面的人以狎高级妓女为荣,以狎身份较低的妓女为耻。但是高级妓女本身并不因此而跻身上流社会,她们只是权势人物的装饰品。作者心仪的妓女苏韵兰的参与,使得仕宦眷属与绮香园的妓女在身份地位上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排座次的情节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三十三章中的排座次还大致遵守文化常态。苏韵兰做东请贵族太太小姐来绮香园赏桃花,官宦妇女打破闺阁不能涉足风月场所的界限,纡尊降贵进入绮香园,与风尘姑娘一同赏花游乐,不过,作者通过宴会席位的排定,多少保留了世俗权力被绮香园的妓女们所认可,时任上海海关道的阳子虚的太太程夫人坐了东席首位,吴冶秋的夫人坐了西席首位,其余座次的排列均有定规,遵守的是现实社会礼仪,主流社会的身份等级认定在绮香园仍然有效。而在第四十章,借助上天旨意和莲因的道法,对上海姑娘的身份等次进行重新洗牌,以抽签的方式排出了花神祠的座次。给英雄排座次的情节,《水浒传》开了先例,晚清民初的上海小报则热衷于选花,邹弢受英雄榜与花榜的双重启发,给绮香园的姑娘拟了这份“座次表”。“座次”意味着名分、威望、生命价值的差序判定。邹弢提供的座次表,令人惊异之处是打破了世俗社会的价值秩序,把贵族小姐与风尘小姐等量齐观,外国妓女与中国妓女同场竞位,双琼、珩坚、萱宜、雪贞、素秋、霞裳、喜珍等良家女子与风尘女子同刻断肠碑,而且现实社会“世人所不齿”的妓女还占了上风,贵族小姐则屈居其后。现实中不可僭越的身份等级被颠覆了,主持拈位的莲因还强调此次排座“不可僭的”,小说实际上以绮香园的道义秩序替代了现实社会的秩序。究其根据,邹弢对上海妓女汪畹根的痴情拔高、美化了苏韵兰形象,司香旧尉亦坦承:“书中极意销张,皆说他的好处。”[5](P1044)对苏韵兰形象的钟爱扩展到了对其他风尘姐妹,这是其一;上海滩“笑贫不笑娼”,提升妓女形象也就是提升作者自我形象,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韩秋鹤认定“访艳寻芳本是风流雅事”,这也是绝大部分晚清上海文人的一种生活情态,这是其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体系在上海租界受到外侨观念的挑战,上海租界是以商业、金钱、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传统道德、仪式和禁忌因无权力机构的约束变得松弛,门第、出生不是保证个人名望的必须条件,邹弢就在观念混乱的上海租界以自定的个人品貌才情作为标准,把“仕女班头”苏韵兰推向了贵族女子与风尘女子混杂群体的首座。排座次具有强大的观念冲击意义,以租界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颠覆了中国农业专制社会的等级观念,把个人从世袭的深度社会结构中抽离出来,置于同一平面社会来评定。
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小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禁锢、压制、歧视的不满。邹弢在《海上尘天影缘根》中表明过自己的女性观,他反对“抑女尊男”,对男女情欲持自然态度,认为中国对女子施以礼教禁锢,“遂生乱阶”,不如学“无节孝贞烈之说”的西方各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7](P11-12)。在小说中邹弢借女娲之口亦表达了对裹脚陋习、多妻制、歧视女性的不满和对男女平等的向往:“下界中国地方看我们女子太轻,不令读书,但令裹足,且一妻数妾,最是不好,你下去可立一女塾,教导国中,男女并重;且女子读书明理,所教的孩子也易开风气的。”小说道德观念的矛盾芜杂与租界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租界文化语境熏陶有关。在晚清上海租界,西化观念与守旧思想混杂并存。姚公鹤在《上海闲话》(1917)阐释了上海租界中西道德观念交错的情形:
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以与吾华习尚之不同,故士大夫既尽力致其攻诘之词,……而一二不理于舆论之人,见世界中尚有上海一隅之足以逃避吾众弃之身也,则群习而安之,其实中国旧伦理,以范围于专制政治之下,诚不免束缚之太甚,而此辈横决藩篱之士,苦旧伦理之束缚而思逃则有之,若其对于新伦理之原理,彼亦何尝梦见之也。摈斥旧学说,未尝取新学理以代之。例如公德私德,旧学说混为一谈,误矣。然以自身私德之为人诟病,因力折私德无关公德之说,以破旧伦理之范围。破之诚是也,试问新伦理果一任私德之堕落为无伤乎?[6](P103)
《上海闲话》所分析的上海租界的道德伦理中西混杂的状况,也应该是邹弢身同感受的。对于晚清租界文人来说,国与君、公德与私德、贞节与自由、个人价值与家族观念的对峙与分野,一时还难以清晰把握,上海租界中西文化的错杂并置,容易形成租界文人道德上的混杂感和迷惘感。《海上尘天影》的思想体系,正表明了租界文人道德上的举意不定,既留恋老祖宗流传的“忠孝节义”观念,把寻芳访艳当做文人的风流雅事,又想利用小说“善风俗”“导颛蒙”,提倡男女平等、僭越传统等级制度。如果说笼统意义上的晚清开明文人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达成了道德上的共识,那么,对于租界文人来说,伦理道德的一致性正遭到肢解,上海租界就地形成的中西道德混杂状况,使得他们一时还难以形成新的道德体系,只能对固有的体系进行适当删减改造,增删组合之后的道德体系难免歧义丛生、自相矛盾。
道德观念的芜杂从苏韵兰形象塑造中也可感受到。《海上尘天影》既然是“邹生为汪畹根女史作也”,小说中的苏韵兰(汪瑗)形象当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想。作为人物原型的汪瑗,邹弢认为是青楼女子中少有的“超出风尘,自树一帜者”[8](P917),王韬亦赞扬她“性既聪颖,又喜浏览群编”[3](P1),“所折节者,多读书长厚之人,浮华子弟望而却步。”[3](P2)最难得的是汪瑗身陷风尘却胸怀时政,1894年给邹弢的信中表达了她关心战事、忧患时艰的胸襟:“自君行后,殊觉无聊,兼之时事日非,更深愁闷。北洋军务,不堪问矣。旅顺于十月二十二失守,诸将皆望风先遁,以天然之险要,而拱手让人,若辈之肉,其足食乎!使碗根易巾帼为须眉, 当仗剑从戎, 灭此而朝食。”[9](P5)由此可见,汪瑗是一个风雅美丽、情志高超、洁身自好的妓女。邹弢对汪瑗的痴情,进一步拔高、美化了苏韵兰形象。那么,现实中的汪瑗进入小说之后,到底承载了作者怎样的理念呢?上天招回苏韵兰的诏书中下的评语为:“青楼历劫,肯留干净之身,红粉培才,不蹈虚浮之习。洵褒贞之德望,开化之功臣,笃志堪嘉,前因不昧。”[5](P1036)概括起来就是守贞节赢得德望,办女学开化风气。上天的评语亦可当做作者对苏韵兰的赞许,表明风流而西化的租界文人试图在妓女身上同时寄托自己的佳人梦想和时务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维护心中偶像的道德纯洁性,把她置于烟花之地,使之出淤泥而不染,所处空间是妓院,却又要做良家小姐。韩秋鹤对一班文人雅士朋友说:“以后到这里玩也不过借他的地方,文酒聚会,倘然当他风月场似的,我秋鹤就不能领命了。”实际上,苏韵兰洁身自好,为自己保留“纯洁”身体,是以牺牲其他女子的身体做代价的。她在绮香园也扮演了万花总主的角色,与天界不同,她是绮香园众多校书风尘经营的万花总主。她既入风尘,又不愿承担“俗累”,得其利而不愿付其实。碧霄的建议吻合了苏韵兰的这种心思,于是“如法炮制起来”[5](P357-358)。苏韵兰固然“人品、学问、应酬”出类拔萃,但她把这些当做一种商业资本,筛选客人,乐得在冠盖如云商贾云集的上海租界捞上一笔。她深谙青楼经营秘诀,既维持自己的脱俗习性作为招牌,又借“体面姑娘”满足“附腥逐臭”的需要。因此,绮香园的生意并不冷清。苏韵兰与韩秋鹤分别属于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两人的恋情本来是逾越礼法的,作者只好以“发乎情止乎礼”来控制他们的关系,既不敢挑战传统婚姻伦理和贞节观念,又想借此表达对两情相悦婚恋的向往。作者只想在名分许可的情形下撮合这一对有情男女。苏韵兰自困名教规定的名分,不敢进一步发展与韩秋鹤的关系。最后提出让韩秋鹤远去新疆探问贾倚玉的生死下落,想了断后再与韩秋鹤结为夫妻,无奈秋鹤途中为匪所害。即使韩秋鹤不死,两人的关系也是个难题,因为苏韵兰仍将执着于名分。雪贞的一席话说中了她的心思:“我看你心里头,不过不肯做如夫人,但你现在光景,充充畅畅,你肯招秋鹤,他必然待你胜过大夫人。况且你有这个场面,仍旧你自己作主,要怎样便怎样,人家大夫人哪里能及得你”。所以,苏韵兰想要挣的不光是如意郎君,还有大夫人的名分和权威。说到底,邹弢笔下的苏韵兰是住着莫须友的花园,做着贾倚玉名义上的妻子,同时与韩秋鹤谈情说爱;一面混迹花界为生计,一面以洁身自好相标榜。晚清租界文人所拥有的关于女性解放的有限观念,混杂在新旧道德伦理的纠缠中难以清理,体现出租界文人在中西古今杂糅的租界文化语境中探索理想女性类型的道德迷惘感和不适感。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王韬.海上尘天影叙[A].邹弢.海上尘天影[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4]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J].明清小说研究,2004,(2).
[5]邹弢.海上尘天影[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6]姚公鹤.上海闲话[M].吴德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邹弢.海上尘天影缘根[A].海上尘天影[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8]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9]邹弢.海上尘天影珍锦[A].海上尘天影[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Spatial Design and Moral Expression in the Eyes of Men of Letters in the Concession: an Analysis ofMy Life In Shanghaiby Zou Tao
LI Yong-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My Life in Shanghai by Zou Tao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idealism and realistic writing,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desire release.Zou’s experience and vision as a man of letters in the Concession influenced his expression of thoughts and ideas in My Life in Shanghai.This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Shanghai experience, so that the space depicted in it is just a miniature of the life in the Concession.The story told lingers between west moral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ethics.The females characters revealed their moral unfitness and loss characterizing people of letters in the Concession.
man of letters in the Concession; Shanghai Concession;My Life in Shanghai; space; moral
I207
A
1005-7110(2011)06-0077-06
2011-07-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08XZW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SWU0909406)的研究成果。
李永东(1973-),男,湖南郴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