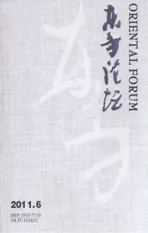“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2011-04-03雷定安
雷定安 逯 进 陈 阳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雷定安 逯 进 陈 阳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黄宗羲定律;周期率;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黄宗羲定律”是由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发现,后由我国学者秦晖总结的一种经济现象。黄宗羲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中国许多朝代每进行一次减轻人民负担的税赋改革,过了不久,民众的税赋不是减轻了反而是加重了。于是,人们把这种经济现象命名为“黄宗曦定律”。2000年秦晖在研究了浙江省兰溪县陈家村村民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自己世代居住的居宅基地时,认为这是黄宗曦定律的现代版。他的研究曾引起了我国高层的注意和重视。但总的来说,学界对这个关系到我国农民切身利益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研究极为不足。
而“中国社会周期率”这一概念,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于上世纪4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黄先生在访问延安期间,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谈到了这一问题。黄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周期率”,是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种朝代由盛到衰、由衰到盛、再由盛到衰的重复更替现象。由于它与数学上的正弦波相类似,故黄先生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社会周期率”。黄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将如何防止中国社会周期率的再现?”毛泽东的回答很简洁:“民主”。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战事频繁、社会动荡、政治问题紧迫,这个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就此搁置起来。
以前述为背景,我们认为,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上述两个规律的研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求得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康,创建永恒的太平盛世,既是中国亿万民众所殷殷期盼之愿景,也是国家领导人所孜孜追求之伟业;既关乎我国人民的现实利益,也关系到我国人民的长远福利。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类问题较为忽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一段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我们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的夸大症和长期行为的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长远发展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1]虽然我们不敢说,学界对当前所有短期问题的研究都有夸大的趋向,但人们对长期问题的思考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探讨的“黄宗曦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应该说都属于这种长期现象。当然,对这类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全加以解决,因此,本文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二、“黄宗羲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曦指出了明末清初的“三害”——“田土无等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2](P54)黄说的“田地无等之害”,是指官方在征收田赋时,不论土地的肥力等级,征收同样的赋税。这种征收方法,必然使耕种差地的农民负担更重。即越贫者,税赋越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的是农民所缴非实物地租,而是货币地租。因此农民必须把生产出的粮食在市场上换成货币。这一过程使农民不得不经受一次商业的盘剥。“积重难返之害”,说的是每一次赋税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繁重,故有积重难返之势。正由于此,很多农民辛勤耕作一年,但“一年所产尽输于官,然且不足”。即不但不能拥有净收入,反而还有亏损。这就是所谓“吾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的原因。也就是,赋税的增加使农民生活困顿、无着。
黄炎培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周期率”,无疑是中国历史演变的真实写照。中国曾有多个王朝兴盛更迭,就是明证。那么,何以会发生这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和民间收入分配关系失衡所致,即国家在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民间份额则不断下降。其机理是:国家通过税收等方式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占有,人民不堪忍受,大量逃亡,而国家为了满足其统治者的消费需求和镇压起义之需,又继续加大税费的征收,采取更残酷的方法对民间财富进行剥夺,于是人民继续逃亡,国家又继续加强掠夺,最后,难以生存下去的人民揭竿而起,这就直接表现为封建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摧毁。于是,又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再重复以前的历史。这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率。
从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三个王朝——秦、新、隋——的迅速覆灭,完全可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
秦朝一建立,统治者就大兴土木,各项土木工程耗费甚巨,使民不堪命。如为了自己生前死后的享受,秦统治者仅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动用了70余万人,耗费钱财不计其数。秦二世时赋敛愈来愈重,人民饱受赋吏之苦。正如董仲舒所说: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三十倍于古”。[3]通过这种方式,财富大量集中于国家,而民间穷困至极,秦民无法生存,只能揭竿而起。
我国的另一个短命王朝——王莽所创立的新朝也是这样加重人民负担的。王莽当时进行了币值改革,其实质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每改革一次,新朝统治者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王莽实行了“五均赊贷法”,后来发展为六管(分别针对于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些法律和管制之执行,为政府官员聚敛财富和搜刮民脂民膏提供了便利。当时,“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繁剧。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克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贼盗”。[3](P183)所以,短命的新朝,“王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饕餮者,他手下的官僚是大小不等的中小型饕餮者,他们对人民群起劫掠,锱铢必尽,而给劳动人民的只能是日甚一日的苦难”。[4]
隋朝也是一个横征暴敛的封建王朝。隋文帝时,对民间的剥夺已经暴露出来,筑宫殿、造龙舟、纵物欲等活动劳民伤财。隋朝末年,农民的负担已经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隋炀帝南北游玩恣意挥霍:“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租赋之外,一切征敛。”[5](P34)正是隋朝统治阶级的无尽贪婪,使人民不堪忍受,从而加速了隋的灭亡。
此外,我国明代学者王夫之还考察了唐朝覆灭的原因。他说:“皆当年尽耕夜织,供县官之箕敛者也。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也。王仙芝、唐巢一呼而天下鼎沸”。[6](P217)唐朝诗人对当时的情形做了极为生动的描绘:“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反映的就是唐国家机器对人民征税之多、征税之酷。
我们再来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及其最高统治者是怎样从民间和地方剥夺社会财富的:“乙戌至戊戌间,凡借外债五千万两,除偿债外,所余尚一千二百万两有奇。辛丑之后,各省每年解一千八百万两于北京政府,每年所余者七百万两有奇。及会三年,亦有二千万两有奇矣。此等羡款,用诸何途?乙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三百余万两。皇太后晚年吉地工程,每年百万余万两。戊戌秋间,皇太后欲望天京阅操,命荣禄修行宫,提‘昭信股票’余款百万余两,辛丑銮费,据各报所记,二千余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佛照楼(即后来的居仁堂)工程五百万两。今年(1903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一千二百万两。另各省大员报效,一千三百万两。即此荦荦数端,专为一人身上之用,我辈所能知者其数达九千万两!未知者复何限。国民乎!国民乎!公等每年缴四千三百万两之膏丘,为北京城内一人(那拉氏)无用之私费,公等节衣缩食,抛妻鬻子,以献纳于北京,为彼一人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之需也!”[7](P24)清朝统治阶级及其最高统治者为满足无穷欲壑,从地方和民间巧取豪夺,安得不亡?1903年的8年之后(1911年),清帝国被辛亥革命的洪流所埋葬。
从经济角度看,封建政府对民间的无尽剥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强制引导社会财富向官方流动。当这一过程达到极限,人民无法忍受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就会最终烧毁封建王朝。
总之,“黄宗羲定律”说明,封建国家不断对民间加重赋税,实行横征暴敛,不仅使中国历史上的每次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税制改革都归于失败,而且还使封建国家与民间收入分配结构和比例出现恶化,而这种分配结构的恶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中国发生“社会周期率”,并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冲突和流血悲剧。因此,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就是关心此问题的学人之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黄宗曦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发生的深层原因
那么,中国历史上,为何会发生“黄宗曦定律”和“社会周期率”,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所决定。封建社会“天下财富皆归于王权”的制度设计,是财富从民间流向政府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黄宗羲说:“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者,为君也”。君主竭力“敲剥天下之骨髓”,从而导致民怨沸腾。[8](P8)也就是说,这种封建的产权制度将天下财富视为封建君王的财富,而非人民的财富。显然,这种制度使整个社会的财富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向国家流动,就具有了必然性。
第二,封建政府及其官员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封建国家的官员对民间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且这种权力没有强有力的制约,这是封建官府能够横征暴敛、一些官员能够中饱私囊的原因之一。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作为整体的官僚阶层巨额俸禄收入是有保障的,但是个别官员地位极不稳定,获得一官半职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学费、买官费、礼品费、‘规定费用’)”,往往要背上一身债,所以,当了官,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量地捞上一把。由于没有固定的估价和保障,所以,他们便使出浑身解数来搜刮。当官就能赚钱,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该指责。[9](P111)他注意到这样一个消息:“大量文告披露了这类事实。1882年3月28日《京报》载:广东的一个官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超常地搜刮了10万两白银。”韦伯所说的是“个别”官员有这种受贿的倾向,其实,在王朝的后期,这种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像细菌和病毒一样蔓延开来。
第三,私人财产保障制度的缺失。财产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说,与人权有关。因为财产的保障根本上就是人权保障的体现,保障财产权实际上就是保障人权。但中国古代私人财产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封建国家及其官员在向民间无度掠夺时,民众没有保障自身财产的武器,这也就更加重和促进了封建国家及其官僚向民间掠夺的力度和速度,加速了财富向国家及其官员的流动。
第四,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官贵民贱、官大民小、官强民弱的观念在文化思想中占有主要地位。时至今日,“官本位”在我国家还有强大影响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这些思想文化观念,必定要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进而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即出现有利于政府、不利于民间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结果。
四、“黄宗羲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留给我们的警示
首先,对“黄宗曦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由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共和政体。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文化基因和制度惯性仍然会发生作用,仍然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文化基因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它不会因为政体的改变而彻底消亡。我国社会的文化基因有:官贵民贱、以人代法、“官本位”观念、权力大于法律、国家至上、国家权威主义、国家专制主义,等等。这些文化基因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活动,甚至制度等方面。此外,封建制度和任何制度一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一些封建制度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基因和制度惯性双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财富仍然会向国家及其官员集聚和流动。对这种可能性我们绝不可忽视,而应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第二,重点要防止“官”、“民”之间分配比例的失衡。黄宗曦定律表明每一次改革之后,政府赋税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而农民赋税负担的增加就是政府和民间分配关系的失衡,即社会财富不断从民间向官方流动。当民间承担的赋税达到极限而不能承受时,社会不稳和动荡就在所难免。因此,为对抗社会周期率发生,就必须在经济上防止“官”、“民”之间分配比例的失调,防止社会财富由民间向政府的无限流动。政府、政府官员占有了和享受了过多的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却处于底层,处于被剥夺、被边缘化的境地。这种状况是极为最危险的。从现实看,我国近些年来确实已经出现了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份额逐渐增加,而民间收入份额不断减少的现象。因此,必须解决政府与民间分配失衡的问题,这是防止中国社会周期率继续发生,在经济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只有防止政府与民间分配结构的失衡,才能真正建立杜绝社会动荡的经济基础。
第三,加速相关制度设计和观念转变。民间财富向国家及其官员流动,表面上是个经济现象,但其实质反映的是制度问题和观念问题。很显然,我们的社会只有建立起一套国家权力制衡制度、官员权力约束制度、私人产权保障制度,只有清除国大于民、权大于法、官优与民的封建思想毒素,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流动与聚集的思想与政治基础,才能建立国与民、官与民、权与法的和谐平衡关系,并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最后,应全面从“黄宗羲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中吸取历史教训。对王朝兴盛问题,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有深刻的分析:“这些帝国与王朝在其兴起之后,必然会出现两个阶级的对立:一个是位居于少数的统治阶级,志得意满,骄奢淫逸,保守落伍,颓废懒惰,逐渐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基本权利被剥夺的被统治阶级,生活条件被压抑至最低水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对社会、对政府怨深仇重,一旦爆发,便形成残酷的动乱与革命,使帝国王朝不是亡于外患,便是亡于内乱。”[10](P4)应该说,加氏的分析对我们仍有一定的警示意义,这也与上述两大定律相吻合。以上对黄宗羲定律和中国社会周期率的分析与研究,其目的也就在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寻找历史运行的规律,铲除导致帝国和王朝衰败的根基,建设和谐永固的社会。
[1] 孙立平.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J].领导文萃,2010,(2).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秦贞兰,雷定安.无限政府和王朝衰微[J].兰州学刊,2007,(9).
[5] 魏徵等.隋书:卷24[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M].湖南:岳麓书社,2011.
[7] 董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4.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 加尔布雷斯.自满年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潘文竹
"Rule of Huang Zongxi" and "Chinese Social Periodicity"
LEI Ding-an, LU Jin, CHEN 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The Rule of Huang Zongxi and Chinese Social Periodicity reveal the general laws of relationship among country, bureaucrats and the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polit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excessive encroachment on social wealth directly results in economic recession, social unrest, and even the government’s closedown. This can provide much experience and a strong war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when our economy is in such a bottleneck period with evid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us we should learn more from history.
Rule of Huang Zongxi; periodicity; government
F091
A
1005-7110(2011)06-0018-04
2011-09-05
雷定安(1950-),男,甘肃成县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逯进(1974-),男,甘肃天水人,经济学博士,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陈阳(1987-),女,江苏无锡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福利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