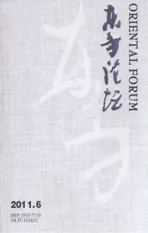黄裳书话:隽永凌厉间的书写
2011-04-03徐敏
徐 敏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黄裳书话:隽永凌厉间的书写
徐 敏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黄裳是当代书话创作大家。在他的书话作品中,或用现代随笔式的写法,或用承接传统流绪的题跋之法,为读者讲述了他和书、书友之间的情谊,展示了他所寓目的书籍的风采。在这些文字中,不仅体现出他强烈的书话文体意识和创作理路,即话古籍谈往事不离现实;而且彰显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即通达之中满蕴凌厉之锋,书卷气中传达隽永温情。
黄裳;书话;文体意识;隽永;凌厉
黄裳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他于20世纪40年代展露于文坛,在其后多年的创作中,发表、出版了众多的游记、杂文、随笔、书话等,在不同层次的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关于黄裳的创作及个性,姜德明曾评论道:“黄裳究竟算个什么家呢?新闻工作的特点往往要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黄裳为报纸写了不少辛辣的评论和杂文,这个职业造就他成为一个思想活跃、观察事物特别敏锐的杂家。直到现在,他对世事仍不是漠不关心的。应该说他走的正是杂家的路子。”[1](P28)而李辉则说黄裳是“性情风流,文字风流。在世事纷繁人声喧嚣的闹市里,在一己选择的书香阁楼里,在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小巷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2](P6)杂家、名士如此不同的界定统一在黄裳身上,笔者认为其书话作品正是这种结合统一的最好表征。
黄裳最初创作书话可以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唐弢在《文汇报》的副刊“文化街”上发表书话,“因故告假缺席”,黄裳就出来代作几日,是“晦庵先生‘书话’续稿未到,试拟一题以寄延贮之意”。[3](P320)于是他写了《先知》、《佛家哲学通论》、《百喻经》三则,发表于1946年11月4日、9日的《文汇报》上。而其大规模创作、发表书话则要推到近40年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
裳先后出版了《榆下说书》、《银鱼集》、《珠还记幸》、《翠墨集》、《榆下杂说》、《春夜随笔》、《黄裳书话》、《书之归去来》、《来燕榭读书记》、《梦雨斋读书记》等书话集。
一
“书话”是关于“书”的话语。就书话创作来讲,“书”不仅是谈论的内容同时也是其得以存在的根源,正如唐弢所说:书话的“着眼在‘书’的本身上”。[4](P5)正因此,书话这一文体对作者有独特的要求,即书话作者必须是一个爱书者、藏书者,很难想象一个不爱书的人会写出书话作品来。
早在读中学期间,黄裳就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购买新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他就总是把家里给的一点点心钱花费在购买书籍上。他最早收集新文学作品,后来渐渐地转为收集线装的旧书、残本、刻本、抄本、校本等。在书籍的选择方面,黄裳有独特的眼光。在他的藏书中,比例最大的是明清人的集部。黄裳认为“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记录与素材。”[5](P10)如果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黄裳的这种观点在现代的一批作家、学者那里可以找到同好,鲁迅、周作人、阿英、郑振铎等都非常重视收集史料,注重原始的记录与素材,因为从这些资料中往往能见到人所未见,从而道人所未道。
黄裳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他与书的故事,如《书的故事》、《书之归去来》、《书祭》等。与现代很多爱书者不同,黄裳对待书籍的态度更通达一些。他回想当年书籍被没收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时,自己感觉“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6](P3)这段话虽有作者的激愤之情,但也是对当时心情的真实描述。也许正是这种坚忍、通达让他少了物的羁绊,在行文时才能更自由、灵动,完全传达出自己的真性情。
二
1948年,唐弢在给黄裳的《旧戏新谈》作跋时就“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7]文体家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就书话而言,黄裳不仅有大量的实践,而且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文体意识。“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作家、读者在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不同文体模式的一种自觉理解、独特感受和熟练的心理把握。”[8](P56)黄裳对书话有非常明确的解说。他认为“书话其实是一种散文”[9](P55)“是一种随笔,一种很有文学性、很有情趣的文字。”[10](P83-84)这类文字述说的是与书有关联的事情。在写作时可以“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11](P295)这与唐弢对书话的认识颇为相通。但黄裳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在写作时的重要性和意义。应该说,在任何文学性的创作中,作者的思想、意见、观点总会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来。书话作为散文的一支,对作者个人的展示会更直接、鲜明一些。黄裳指出书话“从一本书讲起,却又并不限于书,往往引申开去,谈到别的,发点感慨和牢骚,很随意,包含面很广,但又不是漫无边际。”[10](P83-84)这首先体现在一篇书话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对于书话作家来说,寓目的书籍非常之多,为何谈这本书而不谈那本书,即选择什么材料,在哪个角度、层次上使用材料,其中就折射出作者眼界、学识的高低来。所以说,书话作家不仅是藏书者、爱书者,还要独具识见。正是这种识见使得书话在散文艺苑中脱颖而出,也被一些论者命名为“学者散文”。
在强调书话有思想、有观点的同时,黄裳还提出所选材料、观点应该与时代结合起来:“要把书中的材料和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结合起来,不写无病呻吟之作,所记事实,所发感慨,应带有时代的声音和痕迹,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9](P55)谈古书不停留在历史的回忆与怅惘中,而是要直指当下现实,这不仅是黄裳学习鲁迅的结果,也是他自己对书话一体的强烈认识。他认为:“散文与杂文的分界是困难的,特别是面对现实发抒愤懑的时候。”[12](P3)在给李辉的信中,他也说到:“其实我所写只是散文,只是因时地之异,采取不同方法而已。又我不信散文杂文之间有不可逾越之鸿沟,亦是一因。”[13](P178)这种意识在他1980年代的一些读书记中体现的尤其明显。这一点使得黄裳的书话创作不拘泥于单纯版本、作家经历等相关知识的介绍,而是直接和作文的当下连接起来,显示了黄裳杂文家的本色。
谈到书话文体时,黄裳还触及到的一个问题是“抄书”。 抄书是书话创作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早在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就出现了抄书的端倪。到了现代书话作家手中,抄书不仅是惯用的手段,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周作人就有“文抄公”之称。可见,抄书并不少见,关键是抄什么,怎么抄。正如黄裳所说:“写书话有时不免要抄书,其实抄书也不容易,往往读一大部古书,值得抄的就那么几行。为什么抄这段不抄那段,其实是反映了作者的眼光、识见和学养的。”[10](P84)也就是说,所抄的书不过是材料,是内容,其后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做指挥棒,这样才不会只是材料的堆积。
三
对于自己的书话创作,黄裳加诸过不同的名称,如“读书记”、“书札”、“读书杂记”等等。笔者觉得从具体的写作体例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现代随笔式的书话
黄裳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爱好,对古籍的搜集、阅读,对历史问题的探求,使得他具有了深厚的学养。故谈书时,能够从一点切入,联系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相互对照品评;行文时,又摆脱了学术论文通常的严肃和枯燥,而是笔姿摇曳、娓娓谈来,在不温不火中传达出他的意见,把散文的境界发挥到极致。
用这种笔法写作的成文,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谈与书相关的知识。如《书的故事》、《谈“善本”》、《谈“题跋”》、《谈“集部”》、《谈禁书》、《再谈禁书》、《残本·复本》、《插图》、《谈“全集”》、《关于“提要”》、《谈影印本》、《插图》、《清刻之美》、《四库全书的老帐》等等。二是谈具体的一部书。这类文章的篇幅多较长,充分体现出黄裳丰厚的学养。通过他的介绍和说明,读者不仅可以一睹古代典籍,而且也在作家的评述中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如《谈题跋》一文中,黄裳谈到祁俊佳写的跋文后评述到:“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14](P25)这可谓是确评。面对家国的沦落、个人的复杂处境,文字往往并不能充当发泄的工具,所以有所谓曲笔、反语。知识分子更不能表现出对现实的关照和评议,那满腔的情绪只能在两句“淡话”中让其随风而去。黄裳简单的两句品评却涵盖了历史上多少的事实,这事实不仅在古代有,我们在现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黄裳自己的经历中不都可以看到、体会出吗?这是一个老人历经磨难之后的感慨,也是一位资深学者才能有的视野。
黄裳在谈论一部书籍时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不局限于所谈书本身,而是用古籍中所记载的内容来参照历史和现实。在《黄裳书话》的编选后记中他谈到:“这本读书记中所收有些是或因禁毁,或因避忌而幸存下来的东西,倒往往是并非无病呻吟之作,所记的事实、所发的感慨也都带有时代的声音与遗痕。这就使它们在成堆的朽骨中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15](P292-293)
在这类文章中,常出现的一种写作模式就是抄书。“写读书记免不了要抄书,而抄书实在是艰苦的工作,往往看了十册八册也找不到一句半句值得抄下的字句。写读书记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想尽力介绍一些有用的资料,这有些近于‘提要’,是节省读者时间精力的好方法。”[16](P353-354)故黄裳抄书的范围极广,不仅限于题跋,只要是和所谈题目有关的材料,他都能引入自己的文章。在《关于祁承——读〈澹生堂文集〉》一文中,黄裳引了祁氏的一封信——《上赵明宇、高莹塘》作为例证,说明清初那可怕的禁书风波对书籍的影响。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夷狄”、“虏骑”、“老酋”等字样都被涂去了。当后人翻阅此书时,映入眼帘的到处是墨丁,“我们彷佛依然可以摸到祁氏子孙翻阅先人遗著时惴惴的心。”[17](P3)《关于周亮工》[18](P24-31)中摘引了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关于周亮工的小传,还引了周的学生汪楫对老师的评价,还有曹寅的《楝亭文钞》中对周亮工“好士”的介绍和曹氏两代的交情的文字。这样做,一方面是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了历史资料中的周亮工形象,另一方面也为读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寻觅的资料。
二是传统题跋式书话
在1991年5月10日写的《榆下杂说》“后记”中,黄裳解释到:“把几年来写下的读书记收集起来,编成一册小书,取名《榆下杂说》。这是因为过去曾印过一本《榆下说书》,也是同类性质的杂文。所不同的,这里所收,更多偏重旧书的题跋而已。”[15](P291)《前尘梦影新录》的缘起为:“二十多年前,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经过、书林琐事,颇近于传统的题跋。”[16](P351)
黄裳的这类书话创作是中国传统题跋的直接延续。在创作中,他常以黄荛圃自期。如在《梦雨斋读书记》的序中他就写到:“以视荛圃之题跋,不知何如。”[19](P1)在《翠墨集·后记》中又说“多年来的习惯,一书入手,总是要在书前卷尾写一点题跋之类的话……这是受了《荛圃藏书题识》一类书影响的结果。”[20](P263)
关于这类题跋的写法,黄裳也多次表述过自己的意见:
在尽可能收罗完备的基础上,根据实物考察(目验)的结果详尽地记录每一书的雕版时代、版式行格、序跋牌记、雕手风格、写刻姓名、纸墨刷印、藏书印记、流传始末、作者事迹、内容提要、著作特色、优点缺误……这只是一种理想,目前还没有一种著作可以达到这要求。[21](P93-94)
我一直梦想能读到一种详尽而有好见解的读书记,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撰作的时代背景、书籍本身的得失、优点和缺点之外,还能记下版刻源流、流传端绪,旁及纸墨雕工,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15](P292)
在实践创作上,这类题跋被结集为《来燕榭读书记》和《梦雨斋读书记》两种,其基本的写作路向比较接近。往往是先谈书籍的来源、流传端绪、时代背景、作家身世、自己的观感等等,之后详细录下版本、版式等说明,其中还涉及到很多书事。仅举《录鬼簿》一则来看:
庚子春三月,归自奉贤。偶过博物馆观画,见吴梅村《南湖春雨图》,绝得意。后更过古书店,见此书新刊,遂得之归。夜饮归寓,煮茗阅此,见西谛、斐云二跋,不仅感慨系之。印行此书,固可为西谛之最好纪念,非徒夸古籍孤本已也。此本抚印亦佳,虽非珂罗版印,亦非俗滥,殆近时佳制矣。余收天一阁书之有蜗寄庐抱经楼印记者亦颇多,然皆不如此本之秘。其足相颉颃者,或《远山堂曲品》稿乎。他日印行,当更识之。三月十一日夜。
——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一九六○年二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原本影印。[22](P100)
此则所谈书籍为1960年出的影印本。在文章中,黄裳记述了自己买书的经过,对书籍纸墨刻印的品评,对此书出版意义的认识。读此则可以联想起当年郑振铎为《录鬼簿》写的题跋:“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一书。……予见此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示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痴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23](P227-228)两段题跋对读,更可想见黄裳睹物思人的慨叹。
除了上述两种写作模式外,黄裳还有多篇谈论书人、书事的文章。在书话中记录下卖书的书友,“这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16](P353)黄裳为读者塑造了很多生动的卖书人形象。
如《上海的旧书铺》一文中,记下了修文堂的孙实君、修绠堂的孙助廉兄弟二人。“实君温文尔雅,一袭长袍,满口京西风味的北京话,是地道北京书店掌柜风度。”[24](P169)这位卖书人善谈“眼光好,也有魄力,跟藏书家很熟,常能找到好书,不过要的价也真贵。”[24](P169)他“选书之精,可当稳准狠三字”。[24](P170)对于古旧书籍的把握能力之强连黄裳也是佩服不已。而且在孙实君的身上,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商人的本质,他既懂得图书的质,同时又能估定图书的价,对于被贱卖的图书总是耿耿于怀。这分明是一个传统的商人的形象。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其弟“极喜交际”,而“收书的本领不下于乃兄”。[24](P170)在他的劝说下,九峰旧庐藏书的部分精本摆在了“温知楼(孙助廉的店名——笔者注)上的长案”[24](P171)上。以书人为内容的书话,还有《老板》、《记徐绍樵》等篇。在写作中,黄裳纯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与这些书人的交往,于平淡中蕴含着真情。
除了写书人,黄裳还有不少写访书的文章。这些文章传达出的知识含量多并且表现出作家的通脱。如《西泠访书记》中黄裳讲述了他到坐落于西湖的浙江图书馆访柳如是的《戊寅草》,经过多番波折,“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对于一个学问家、爱书家来讲,其不能见书的失落及遭受挫折的愤怒,可想而知其内心活动是多么的激烈。可是作者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不是向郑西谛那样常不禁地写出心情,而是笔锋自然一转:“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25](P13)接着作家回顾了“四人帮”时期对待善本的问题并对目前保存善本提出了个人的意见。这样的叙述手法,真是得了周作人的真传。文字无比的通脱后面浮现出的是作家严肃的思考。
《访书》更象是篇回忆性的散文,黄裳记下了当年在苏州与西谛、叶圣陶一起访书的故事。文章中不仅勾画出西谛豪爽的举止和神情,而且满蕴着朋友之间的深情。回忆和现实穿插,增添的是岁月流逝、好景不再、物非人非、世事苍茫的感慨:过去相从的老友“墓前白杨堪作柱”,过去满街满眼的旧书、好书也渐渐乌有。作者的沉痛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此文惟在结尾添了一丝亮色,歌颂新的时代、社会。笔者觉得就整篇文章的情绪和气势来讲有狗尾续貂之嫌,当然这种写法可能是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回忆同样一件事情的还有《苏州的书市》一文,在文中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矛盾,一方面他在哀叹“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一方面又说“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但是“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26](P342)从这篇文章看出,黄裳行文之笔表面看来是很散的,但是在“散”的背后往往是作家对历史深入的思考和对现实问题深刻的揭示。
四
黄裳从1980年代开始集中创作书话。有论者评述他的“说书散文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书卷气,这类文章,或说一个主题,或记一段轶事,或以某一历史人物为中心,说书评史,都写得酣畅淋漓,舒卷自如,显现出作者丰富的知识、学养。”[27](P284)书话历史感的由来与他所谈书籍多为古籍有关。黄裳耽于古籍,但是并不沉溺于对古籍的赏玩之中,更确切地说,他是通过古籍来关照现实。如他自述:“新时代开始以来,被抄去的书册少少归来,摩挲旧物,往往别有兴会,像看待旧戏似的谈旧书,多有感触,于是就写些读书记,采用的仍是写‘新谈’的方法,谈往事却不脱离现实,努力不作新时代的遗少。”[28](P266)
谈往事而瞩目于现实,使得黄裳的书话表现出一种奇妙的融合,即隽永与凌厉杂糅的风格特征。隽永体现在他谈古书时,由一点生发开去,勾连起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字、事实,纵横捭阖,传达出意味无穷的效果。如他的《谈禁书》一文。由“雪夜闭门读禁书”说起,溯本穷源,从秦始皇到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虽修成若干册“禁毁书目”,但是“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29](P26)接着黄裳就开始从历史上寻找禁而不绝的图书:韦庄的《秦妇吟》、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城守筹略》、《今乐府》、清代汪景祺的《西征随笔》、三十年代马列主义等等。种种鲜为人知的禁书书目、种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史实被黄裳信手拈来,不温不火地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读者在频频点头之际能够清楚地体会到禁书不绝,感受到作家于其中传达的意味。隽永的笔调带来了余味无穷的阅读效果,视线中依稀出现的黄裳似是一位老名士在历数家常,有白头宫女话当年的感觉。
但是在轻声细语、娓娓而谈的同时,我们又常能遇到如火一样激烈的文字。在《不死英雄——关于张缙彦》一文中,黄裳在文章开篇初就自杀和气节的问题直接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残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30](P12)
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危害也不小。[30](P13)
以上两段文字直指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出现大变动时的选择,指出持守气节的重要性。文字激越、气势逼人,充满了杂文具有的凌厉之气。对此,黄裳曾谈到:“鲁迅先生的有些文字,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真是嘻笑怒骂,各极其致,如此写来才顺手。因而悟到,散文与杂文之间,其实并无一条分明的鸿沟。我一直坚持着这看法,直到写《榆下说书》那样的读书记时,也还使用着同样的手法。从此,我笔下的文字是散文还是杂文就很不容易分别了。”[31](P4)在细读了黄裳的书话类作品后,笔者感到黄裳骨子里是杂家,而在表面上又是一个闲家。这是黄裳自己的风格。
书话文学性的表现之一是情感。与抒情性的散文不同,书话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叙事,因此作家所抒发的感情常常是通过相关的书籍掌故和书籍知识传达出来的。黄裳的书话之所以耐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弥漫着浓厚的书卷气和学者气,在书卷气和学者气之间他所传递的情感通过一本本书渗透出来。可以说,在黄裳的书话中,没有感情的直接宣泄,而资料本身和对资料的组合运用为情感的抒发承载起极大的空间。在黄裳讲述的一个个与书相关的故事中,在他掌握了充分资料之后展示的历史真实中,读者的情绪会不由自主地随着黄裳情感的起伏而起伏,尽情体会到散文的魅力。所以有论者认为黄裳的文章“深情而不抒情,从文章本身来说,就构成一种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很能够打动人的。”[32](P99)
参考文献:
[1] 姜德明.从《旧戏新谈》说起[A].爱黄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 李辉.看那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代序)[A].来燕榭书札[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3] 黄裳.拟书话三则[A].来燕榭集外文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 唐弢.序[A].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5] 黄裳.谈“集部”[A].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6] 黄裳.书的故事[A].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7] 唐弢.黄裳作《旧戏新谈》跋[A].唐弢文集5:序跋 书话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8] 王充闾.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A].爱黄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9] 何倩.腹有诗书气自华——访黄裳先生[A].识荆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 黄裳.书林漫步——与刘绪源对谈录[A].春夜随笔[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 黄裳.后记[A].榆下说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 黄裳.周作人的三本散文[J].读书,1988,(2).
[13] 黄裳.黄裳致李辉的信(2002年7月28日)[A].来燕榭书札[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14] 黄裳.谈“题跋”[A].榆下说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 黄裳.后记[A].榆下杂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6] 黄裳.选编后记[A].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7] 黄裳.关于祁承 ——读《澹生堂文集》[A].榆下杂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8] 黄裳.关于周亮工[A].榆下杂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9] 黄裳.梦雨斋读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0] 黄裳.后记[A]翠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 黄裳.榆下杂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2] 黄裳.录鬼簿[A].梦雨斋读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3] 郑振铎.录鬼簿[A].郑振铎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4] 黄裳.上海的旧书铺[A].书之归去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5] 黄裳.西泠读书记[A].榆下说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6] 黄裳.苏州的书市[A].黄裳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7] 陈惠芬.《黄裳散文选集》序言[A].爱黄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8] 黄裳.后记[A].拾落红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9] 黄裳.谈禁书[A].书之归去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0] 黄裳.不死英雄——关于张缙彦[A].榆下杂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1] 黄裳.寻找自我[A].海上乱弹[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32] 张新颖.黄裳文章[A].爱黄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冯济平
Huang Shang on Books: Pleasant and Sharp Writings
XU 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Huang Shang is a contemporary famous writer on books. In his works, he uses modern essay style or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writing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alk abou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im and books or book friends and to introduce what is good about the books he reads. In these works, he talks about the past by relating it to the reality, displaying his distinctive creative features: sharp, warm and pleasant.
Huang Shang; essay on books; stylistic consciousness; pleasant; sharp
I207
A
1005-7110(2011)06-0065-06
2011-08-20
徐敏(1973-),女,山西大同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