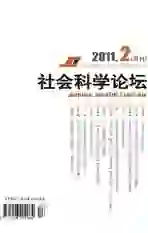龙虫并雕 雅俗共赏 追求创意 功在拓荒
2011-03-17谭汝为
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李世瑜先生于2010年12月29日上午7时30分因病不幸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谨撰此文,概要评述先生的学术生涯,缅怀先生的道德风范。
李世瑜先生1922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和研究院人类学部,1948年获硕士学位。从1940年起,他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旁及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社会学、方志学、戏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另外,在民间文学、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地方史、文物、地名、昆曲、曲艺、相声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而饶有成果的探讨。其勤奋治学七十载,都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
李世瑜先生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贯通中西,涵盖古今;龙虫并雕,善于打通;追求创意,功在拓荒。他曾应邀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英、法、俄、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讲学。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及终身路斯学者称号。代表著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宝卷综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
一、关于天津方言研究
李世瑜先生于1941-1948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著名方言学专家比利时人贺楼登崧(Grootaers)研习语言学理论。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天津方言进行了深入的开创性研究。方言研究虽然只是先生科研大厦的一个楼层,但其四大贡献令人瞩目——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确定“天津方言岛”成因,寻觅到“天津方言”的根,推出天津方言研究的力作。
1.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李世瑜生长在天津梁家嘴一个封建大家庭,主仆一百多口,分别住在九道院子里。他从小发现:家中佣人、街市商贩、送水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他们或说杨柳青、静海话,或说咸水沽话,或说武清、白洋淀那边的话,而天津方言与附近地区方言的差别很大。在上世纪50年代,李世瑜以天津方言的语调特点为主要区分标志,对天津周边地区的方言状况进行实地调查。他骑自行车跑遍近郊近两百个村庄,找到近一百位发音人,记录下他们的语音。终于查清天津方言的“等语线”,天津方言区域以天津旧城为中心,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包围,北面则是北京方言和冀东方言的过渡区,在此基础上绘出《天津方言区域图》。
李世瑜试图用方言岛理论对天津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所谓方言岛,指历史上大批移民,使外来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方言区内的一片地域,形成被原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犹如孤岛的新方言区。说天津话的地区就属于典型方言岛,呈倒置的等边三角形:底边距旧城北约1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22公里。李世瑜确定了天津方言区周边的方言分界线,绘制了《天津方言区域图》,使“天津方言岛”的观点得以确立。
2.确定“天津方言岛”的成因。天津方言岛是怎样形成的?民间流传着“燕王扫北”的说法。明代朱元璋称帝后,分封藩王。四子朱棣握重兵,且建战功,故遭忌惮。为削弱其实力,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燕王朱棣扫北得胜,把从家乡安徽带来的官兵按军队建制安置在今天津一带戍边屯垦。朱棣夺取帝位后,设天津卫并为天津赐名。史书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汪来传》)“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卫志·毛恺德政碑》)——这说明:明初天津人口的主要构成是“军事移民”。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聚居,“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平调的皖北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燕王扫北前后,不断有苏皖移民在天津定居,天津方言岛因以形成。
3.寻觅“天津方言”的根。为弄清天津话“母方言”来自何方,上世纪80年代,年逾花甲的李世瑜先后来到苏北和皖北二十三个市县和村镇,进行方言考察。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途中,车厢拥挤,很多人都是“站票”。火车过宿州后,李世瑜身边两人因抢座争吵,而说纯正的天津话。李世瑜以为碰到天津老乡,便劝解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的。”天津话的腔调使李世瑜大喜过望,就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
下车的那个站是固镇,位于蚌埠北48公里处。到了固镇车站,李世瑜似乎回到天津,因为满耳听到的都是天津话。因操同种方言,车站茶摊老掌柜和李世瑜相谈甚欢。录音带记录——“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人?”老人迟疑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往人群都经过这个车站,老掌柜对本地人几乎都认识。固镇属宿州市管辖,两地相距45公里。李世瑜立即赶回宿州,历经数月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浮出水面——天津话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皖北平原。
4.推出天津方言研究力作。2004年,李世瑜先生《天津方言俚语》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部分由十篇专题论文组成,将方言理论和实际语用相结合,涉及天津方言定义、方言岛、语源考察、比较研究、后缀方言词、有音无字问题、方言成语的借字、谐音和借用、方言创新、特殊读音等内容,几乎囊括了天津方言研究的基本方面。开掘深入,语料详实,结论中肯。该书第二部分是“天津方言俚语选辑”分别选辑天津方言词汇、成语、谚语、歇后语一千多条。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当之无愧成为天津方言研究的代表性专著。
著名语言学家马庆株教授为拙著《这是天津话》(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所写序言指出:“老辈学者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研究有开创之功。”在天津方言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研究成就之最高,贡献之最大者,当属领军人物李世瑜先生。
二、关于天津贝壳堤的发现和研究
李世瑜先生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主攻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连续两年师从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教授学习考古学。裴教授曾一再引导李世瑜跟自己专攻考古学,但李世瑜性格外向好动,认为自身不适合从事长期潜身深山的考古工作,虽未回应裴教授的栽培美意,但这段学习经历毕竟为李世瑜日后的考古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史学界曾认为,天津在一千年以前是海,再往前的历史则无古可考,而李世瑜的考古发现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观点。1956年到1957年,李世瑜在无经费、无助手的情况下,单人单车,历时十一个月,行程五千里,对天津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田野调查中,李先生先后发现战国、秦汉古迹三十多处,摸清了天津地区的退海线,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贝壳堤的存在及其与古海岸的密切关系。第一道:天津东郊白沙岭—军粮城—泥沽,年代为战国至唐代;第二道:宁河县赵学庄—白塘口—黄骅县苗庄子,年代应晚于商殷时期;第三道:天津市区育婴堂—静海四小屯,年代不晚于商殷时期。
考察之后,李世瑜撰写了五万字的调查报告,得到裴文中先生的赞赏。报告详细描述了渤海的退海规律和贝壳堤的研究情况,将天津陆地形成的历史向前推前了四五千年。该报告在《考古》1962年12期上发表后,震动了考古界,并开启了渤海退海规律和贝壳堤研究的热潮。
此后,在李世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贝壳堤的研究逐渐深入: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进与海退的时间和范围,贝壳堤的数量、分布和年代,提出贝壳堤形成的机理;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古遗址和古墓葬分布情况,探讨了考古遺存的时间、空间分布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总结了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规律;确定和公布了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加强并推动了自然遗产的保护。
关于李世瑜对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调查方法,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考古学家陈雍先生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刻认识:一是从事研究活动必备的识、学、才,识即敏锐的学术眼光,学即深厚的学术素养,才即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二是坚持田野调查,强调实证研究,一切结论都立足实地勘察,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不演绎,也不假说;三是注意研究对象的相关性,能够联系地看问题,发现并准确把握现象与现象、时间与空间、陆与海、人与环境、学科与学科、专业调查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为现实服务。
三、关于宝卷及秘密宗教研究
1944年,李世瑜先生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选题“中国秘密宗教研究”,获得历史学教授赵卫邦先生的重视,将他引荐给比利时籍教授贺登崧。贺登崧治学严谨,以其自创的“方言地理学方法”——以地理学为中心,以特定地理环境为基础,对当地的历史、民俗、方言、宗教等进行多方多层次的调查研究——而闻名学界。这种治学方法对李世瑜的人文科研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研究生,李世瑜曾两次随贺登崧去察哈尔南部地区进行地理民俗考察,在那里发现“黄天道”等秘密宗教组织。师生二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合著《万全县的庙宇与历史》《宣化县的庙宇》两部书稿及多篇论文。在贺登崧与德籍教授雷冕的共同指导下,李世瑜于1948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对一贯道、皈一道、黄天道和吕祖道这四大秘密宗教,进行了具有拓荒意义的全面考察与深入研究。
为什么李世瑜对秘密宗教这个冷门课题情有独钟呢?他生长在四世同堂百余人的大家族内,宗教信仰五花八门,诸如天地门、圣贤道、在理教、蓝万字会等,在其家族内各行其道。李世瑜的父亲李彩轩在教会学堂——新学书院读书,后赴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工科肄业,接受文明思想熏陶,对封建家庭种种弊端尤其对五花八门的迷信活动深恶痛绝。李彩轩曾教导李世瑜:“这些东西一定要取缔,不然可能导致亡国灭种。但是取缔一件事情,必须彻底了解它,看它使人那么迷信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番话对青年李世瑜影响很大。他在上高中时就开始对流行的多种民间秘密宗教进行调查,常装扮成虔诚教友,深入会道门内部,以获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李世瑜硕士论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一书的出版,差点儿引来大祸。当时,因一贯道势力很大,这部以研究一贯道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在北平难以印行,只得安排在成都的华西大学出版。但因华西大学不能制铜版,无法印插图,只得将插图拿回北平辅仁大学印制。辅仁大学印刷厂一个印刷工是一贯道教徒,偷着多印一份交给一贯道“总佛堂”。一贯道道长一看,他们的“三宝”——点玄关、手诀和五字真言,以及祖师张天然及其老婆的尊容,全都清晰地印在纸上。于是道长向警察局告发,而警察局长又是“道亲”,就派人秘密抓捕李世瑜。幸亏辅仁一位校工报信,李世瑜才得连夜逃出北平,躲过一劫。后来,李世瑜听说学校后身的德胜门大街59号大杂院里,住着“混元门”教首李抱一。李世瑜了解到这个教派不忌烟酒,便买了好烟好酒登门造访。在多次密切接触中,李世瑜从李抱一处获得其收藏多年的“天书”—— 珍贵的《家谱宝卷》,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史书和文献资料都不曾记载的内容。
这部“偶然得之”的宝卷,为李世瑜的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开拓了新天地。所谓“宝卷”,就是从白莲教开始,各种各类秘密宗教的经卷。几十年时间,李世瑜统搜集明清以来“宝卷”四百余种(包括善本、孤本五十余种),各种秘密宗教的“坛训”“鸾书”数千篇,数量远超郑振铎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李世瑜先生是我国民间宗教研究最早的奠基者之一,天津理工大学李正中教授总结了李老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
(1)建立了民间宗教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以佛、道、儒三教为正统的宗教信仰。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中国下层民间社会,出于信仰和期盼的需要,不断地创造着自己信仰的宗教,与正统的信仰有着很大分野。对于民间宗教的研究,学术界都以各自宗教或会道门的名称来进行阐述,而把这些民间宗教综合称为“民间秘密宗教”,则始于李世瑜先生的奠基。他1988年主编“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时,就提出了这一课题的论证。
(2)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李世瑜先生1978年首次提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他认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就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对某些人物进行调查访问,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变化、社会的结构以致自然环境进行观察了解,对一些文物资料进行搜集,然后如实地、准确地、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然可以使用文獻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使所得结论更为完美”。李世瑜先生以身作则,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进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为后学树立了成功典范,提供了科学方法。
(3)推进了民间宗教宝卷学的建立。“宝卷”是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将宝卷归属于“民间文学”体系。对此,李世瑜先生根据自藏四百余种宝卷及有关馆藏宝卷,经历十几年的研究认为:从宝卷的体制,特别是内容方面分析,宝卷在形式上虽然与变文有关,但内容与变文全然不同,宝卷不仅有宗教的形式,还有各教派各自崇拜的“佛祖”“佛堂”及“坛训”等。由此李世瑜先生第一次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此后,李世瑜先生又出版了《宝卷宗录》(1961年),在国内外学界引起震动。
四、关于社会历史学开创历程
李世瑜先生在辅仁大学毕业后,到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教历史,不久即调入天津史编纂室编天津史。后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历史研究所,李世瑜调到该所《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工作。《历史教学》编辑部几经辗转,最后附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直至先生退休。在单位供职的四十年中,除在天津史编纂室有十个月时间奉公进行过一项田野调查工作(渤海湾古代海岸遗迹贝壳堤)外,李世瑜先生其他全部学术成果都是在八小时之外完成的。
李世瑜先生社会历史学研究代表作有以下四篇:
其一,《顺天保明寺考》(载《北京史苑》1985年第3期),此文把西大乘教的来龙去脉理清,弥补了民间秘密宗教史上的缺环。为此他曾先后九次从天津来到保明寺旧址,动员当地八位解放军官兵翻转己被用做建筑物料的巨大石碑,来考察抄写碑文。其二,《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该文系李世瑜先生研究民间宗教几十年的重要成果,可视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纲。其三,《义和团源流试探》(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和《义和团源流答问》(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这是学界首次从民间秘密宗教角度追溯义和团源流的学术文章,此后不少学者循此思路推出佳作,被日本学者小林一分析为义和团研究中的“源流派”。其四,《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载《文学遗产》1957年第4辑)和《江浙诸省的宣卷》(载《文学遗产》1959年增刊第7辑),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使宝卷从“民间文学”体系回归到民间秘密宗教行列。
五、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从1940年开始,李世瑜先生以田野调查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为开端而走向学术殿堂,学术生涯长达七十年。其学术研究时间之长,研究条件之艰难——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极为罕见。究其原因,除先生天资聪颖,勤奋治学之外,更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路径。其社会历史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范围广博。李老堪称“学术杂家”。其学术研究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的多种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戏曲学、版本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另外,在民间文学、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地方史、文物、地名、昆曲、曲艺、相声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而饶有成果的探讨。
2.研究成果厚重。李老著有《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专著,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在海内外学界颇有影响。
3.研究经历奇特。李世瑜先生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如此艰难的研究条件,却取得令人瞩目的科研硕果——这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可谓凤毛麟角。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经历,可谓“传奇教授”。
4.研究方法创新。李世瑜先生学人类学出身,人类学属于综合性学科,其学科性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冶于一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现在:其一,擅长“打通”的综合性——李老在以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把西方学界的社会学、考古学、方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交叉起来,综合运用。其二,求真务实的实证性——李老在注重历史文本(典籍、档案、文献)的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社会考察和民间采风,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从而获取丰富、鲜活、典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论的依据。其三,重视强调方法论——李老十分重视方法论,他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列为第一栏目的,就是阐述方法论的七篇重头论文。李老撰写的文史资料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他主张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走近“下层社会”,对于散落民间的资料、记忆,要善于挖掘、寻找、访问,就是善于“挖宝”。其四,求真务实不盲从——1945年到1948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从语言学家、比国神父贺登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李世瑜先后两次随贺登崧教授赴万全、宣化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经过反复思考,李世瑜认为:贺登崧教授那套办法是外国人研究另一国方言的办法,但中国人在研究本国方言时用不上。为此,师生二人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分道扬镳,各行各是。
李老探求真理重实践,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为人先求开拓——这种求真务实精神,难能可贵!李老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的结尾,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历史学这套方法论是不胫而走、势在必行的,许多人已经在走着,行着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这样做,诚如斯,‘史学危急于我何有哉!”我们总结李世瑜先生七十年来的学术成就,探研并总结其倡导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加以推广和弘扬,必将嘉惠学林,垂范后昆。
六、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
2010年5月31日,由天津文史研究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天津市语言学会共同主办的“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在天津文史研究馆会议厅举行。天津市地方史研究者、李世瑜先生亲属和在津友好,以及主办方代表等三十余人参加会议。与会者针对李世瑜先生在“城市考古”“天津方言”“民间宗教”等三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著名学者陈雍、谭汝为和李正中,分别以《距今一万到二百年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及方法论问题》《李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贡献及其宝卷学的建立》为题,做了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与会者回顾李世瑜先生六十余年治学生涯所取得的成就。最后,李世瑜先生回忆自己求学、治学中的经历以及创设社会历史学的历程。会议同时印行了《天津记忆·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和“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藏书票”。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先生的学术成就及贡献,得到学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
在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马庆株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词。他简要回顾了李世瑜先生的学术经历,认为其从1940年开始,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又旁及人类学范畴内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学科,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召开会议总结其学术成就,探研其治学方法及特点,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澍伟认为,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方言岛”概念的提出。经过李世瑜等人的调查,现在的天津话,大约源自以安徽宿县为中心的皖北一带,而且在天津市区形成三角形的“方言岛”;“岛”内的天津方言,几百年来保持得相当稳定。罗澍伟先生由此提出,由于“岛”内方言的稳定,天津话里的一些语汇,至今还保存着现代汉语已经不用的历史语文,并列举“大冰”“瓯”“下街”“囫囵”“袷帙”“鬊”“飥”等实例加以说明。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宋金来认为,李世瑜先生的天津方言岛学说,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历史和文化坐标。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绝不能忽视天津方言岛的存在,这一学术成果是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点。如果基点问题不解决,天津地域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难以形成共识。
参加会议的民俗学者王和平与郭文杰两先生,会后分别写下《大儒大雅李世瑜》和《悲天悯人的李老爷子》两篇文章。王和平认为,李世瑜先生七十年的学术生涯,有三点值得后学身体力行:一是注重实践,以实际考察为支点,汲取民间历史,比如对会道门随时随地进行观察研究,即便在国外也不放过实地考察的机会;二是注重科学,客观地看待文献,尽量找到资料背后的真实,比如针对“贫农宋文成”由来进行的调查研究;三是注重方法,如利用地图作为社会学的考证工具,又如对天津理教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对娘娘宫、泰山娘娘和王三奶奶關系溯源的研究等,这些都为考证历史提供了借鉴。郭文杰认为,李世瑜之所以从事民间宗教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与其一生“重情”性格有关。因为家里很多人受各种会道门邪说的伤害,李世瑜先生遂抱着挽救家人乃至拯救国人的志愿,开始研究民间秘密宗教,他认为对这些东西只有充分了解才能彻底破除。由于对家乡和人生的挚爱,使得李世瑜先生的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深刻而独特。
七、学术大家的传奇人生
李世瑜先生斋名“穿月”,其书斋门额悬篆书横幅“穿月斋”,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长孙、福建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刘蕙孙手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象征着智慧和光明。正如王振良先生所言:“今先生已归诸道山,与永恒之月华和凝重之土地融为一体,而其学问之博大精深,我辈庶几永远瞻望也哉!”
李世瑜先生至八十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思维敏捷,言谈风趣。在天津《今晚报》和《中老年时报》常能读到李老脍炙人口的文史短文。李老身高1.80米,体重90公斤。他自幼习武健身,大家族内常年雇用两位武术师傅,一个传授长拳门,另一教练六合门。李老回忆:“我从10岁开始就跟六合门的师傅练武术,先学一套弹腿,后学六合拳、六合刀、六合枪,还有一趟对打。”这套拳术奠定了李世瑜锻炼健身的基础。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后,李世瑜周日都爬香山。骑车到香山后,跑步上山,直到最高峰鬼见愁,当日往返,持续两年。寒暑假回天津,多骑车往还。从颐和园“云辉玉宇”下水,游到对面龙王庙上岸。多年长跑、游泳、滑冰、打球等锻炼,使他在奔走南北的田野作业和社会调查时精力充沛,游刃有余。
先生读小学时就学昆曲,向白云生、王益友等名家学艺,曾登台彩唱昆曲《夜奔》,饰演林冲。天津现有甲子曲社、芗兰昆曲社、昆曲艺术研究会三家昆曲社团,皆聘李先生任名誉社长或顾问。先生喜好曲艺,曾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业余曲艺创作组”成员身份,创作出几十篇曲艺段子。李老酷爱相声,与相声大师马三立在高中阶段即结为好友,多年来情谊深厚。他不仅会说相声,还为马三立创作过多段相声作品。不久前,天津举办“全国相声新作品大赛”,八十八岁高龄的李先生提交三件作品,使主办方大为感动。数十年风雨人生的社会历练和天津地域文化的长期熏染,使李老形成幽默达观、淡泊名利、荣辱不惊的霁月情怀,对其持续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大有助益!
先生在民俗学研究领域,如对于高跷、法鼓、天后崇拜、泰山娘娘崇拜、父老传闻、红白喜事、烹饪名吃等研究文章,都颇受读者欢迎。李世瑜先生尚未收入文集的作品数量很多,如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所写词条,曲艺创作集和诗词集等。李世瑜先生近年来着力撰写回忆录书稿——《我的三亲》,即把亲历、亲见、亲闻的有价值的人和事写下来,已写出七十多段,包括到国内外各地讲学经历见闻,内容非常丰富。唯望早日出版,以飨读者。
李世瑜先生在辅仁大学攻读社会学院人类学专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但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已被取消。他被安排到《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工作。这种无奈的“改行”,却成就了一位社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先生这些深受海内外学界赞誉的成就,既是他坚持田野工作的结果,又是他打通不同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结果。而这些“田野工作”和研究开拓,都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先生在介绍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我请读者注意其中两个关键词语,即‘八小时之外和‘田野工作。前者是指上班的时间之外,包括节假日和晚上的四个小时左右以至通宵达旦。后者是指到社会上、下层组织内部、田野间进行调查访问。”
柳士同先生在《李世瑜和他的社会历史学》一文中指出:“田野工作”的方法,使李世瑜的研究交叉、跨越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语言学、地质学等学科,他一方面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从而创立了社会历史学。李世瑜的本职工作是看稿、改稿和审稿,而他的研究工作只能放到“八小時之外”,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其治学艰辛可想而知。直到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成立“民间宗教研究中心”, 六十六岁的李世瑜先生出任主任,这才名正言顺地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他在荣获亨利·路斯奖,应邀到美国宾州大学任客座教授时,他花了半年时间,考察了费城大学区一百六十多所民间教堂的情况。作为中国学者在异国进行这项调研工作,堪为破天荒第一人。
八、奖掖后进的慈祥老人
李世瑜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师辈,多年交往,爷俩儿成为忘年交。多年前,我与李老,以及民俗学家张仲老、历史学家罗澍伟等先生一起,多次参与天津市地名管理办公室召集的天津地名命名审议工作。李世瑜老先生对天津地名如数家珍,对天津各地方言惟妙惟肖的模仿,洋溢着睿智幽默的谈吐,高尚纯真的人格魅力。这位宽厚而慈祥的老人,给后辈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2004年,我在撰写《天津地名文化》书稿时,多次拜访李老。每有疑难问题向老人请教时,总能得到三言五语解惑性的指导,切中肯綮,醍醐灌顶。老先生冒着酷暑,欣然为拙著赐写序言。2005年夏天,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制作“天津建城600年”系列专题节目时,我们爷俩儿作为嘉宾密切配合,使拍摄录制顺利成功。2008年,我在撰写《这是天津话》书稿时,又多次向李老请教,得到悉心指导。李老为该书撰写序言,对我的天津方言研究方法给予充分肯定。李老将其代表作《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赠送给我,这种奖掖后学的隆情高谊令我感铭。
2010年上半年,我和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穆森、王振良先后三次拜访李老,商议文稿编辑和研讨会会务。每次交谈皆涉及天津方言、地名、民俗、地域文化等诸多学术问题。6月12日,李世瑜先生请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穆森先生给我送来一批资料,供研究天津地域文化和方言时参考。其中有《天津通志·民俗志》《中国民俗大系·天津民俗》《天津文化通览·民俗文化谭》《天津方言语汇》《北京土语》《北京方言词典》《十三辙实用词语手册》等十来本。不久后,又嘱穆森先生捎话:“带给谭汝为先生的书,不必归还了,是送给他的。我手头还有一些图书资料,都是谭先生用得着的,让他来我家选取。”当时,我深受感动,但悲愧交加!年近九旬且重病缠身的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仍满怀热情地对后辈学者寄予厚望,令人钦敬,但悲从中来。李老之学术嗣响早已播誉于海外,但遗憾的是津门故里似仍乏继其衣钵者,令吾侪赧颜惭愧!但李世瑜先生金针度人,薪火相传的愿望,终应焕发卓荦光华。
2007年,李世瑜先生出版《社会历史学文集》时,学界三位老人为之撰写贺联。傅学玉撰联:“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侯振鹏先生撰联:“民间教门,独辟蹊径;社会历史,别出心裁。”任秉鉴撰联:“天津卫六百载,粮鹾懋迁,乃成都市,谁当拓荒者?端看一片方言岛;渤海湾五千年,沧桑演变,终是良田,全归造化工,赖有三条贝壳堤。”对李老学术贡献之总结,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如何对李老的七十年学术活动进行总结呢?思忖良久,写出四句话:“龙虫并雕,雅俗共赏,追求创意,功在拓荒”——这十六个字和上述联语,可视为李世瑜先生治学特点与学术贡献的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