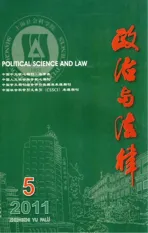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是如何确立基本法审查权的
2011-02-19李纬华
李纬华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可诉性。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法院已经就基本法一百六十个条文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条文作过裁判。这在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都获得了高度评价。例如,我国内地有学者评价道,基本法迄今为止已经成为我国整体宪法规范系统中“最活泼、最有实效性的一个规范体”。2香港特区更有法律职业者将香港特区法院阐释基本法涵义的判决比喻为基本法这株“活树”生长出来的根和枝。3可以说,香港特区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基本法诉讼制度。
通过基本法诉讼制度,香港特区法院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乎基本法进行审查,贯彻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了基本法作为法律规范体的效用,实现了基本法确定的价值。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我国内地,还是在香港特区,已经没有人会质疑,更没有人去挑战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审查权。4不过,无论是在我国内地,还是在香港特区,人们依然认为,基本法在法律规范层面没有确立周延的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合乎基本法进行审查的制度,更没有明确赋予香港特区法院享有这项权力。也就是说,基本法对基本法诉讼的这一前提性问题未置一词。
香港特区法院是如何确立基本法审查权的?5难道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6案又在香港特区上演、香港特区法院通过一场“伟大的篡权”7而抢占了这一权力?这是个饶有趣味的宪法学问题。笔者拟系统梳理回归前香港法院依据宪法性文件对香港本地立法的审查权、基本法中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回归后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对立法会立法的审查等问题,以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初步的解析。笔者认为,回望相关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不但有利于中央与香港特区在历史发展中对特区法院进行定位、完善基本法诉讼制度,而且可作为香港法治未来发展的借鉴,有利于香港特区的持久繁荣与稳定。
二、回归前香港法院依据宪法性文件对本地立法的审查权
回归之前,香港本地的宪政秩序是由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于1843年以英皇特权立法形式颁布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确立的。《英皇制诰》共二十四条。其主要内容是确立总督一职及其权力、权威,设立行政局、立法局,两局成员的职责及其与总督的关系,法官的任命与退休等。关于香港本地立法权的范围,《英皇制诰》第7条第1款规定:“总督,经咨询立法局并取得其同意,可为了殖民地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管治而立法。”关于香港本地立法权行使的要求,《英皇制诰》第12条规定:“总督与立法局在制定任何法律时,应当遵守并服从任何‘训令’所规定的制度、规则与指令。”共有三十七条的《皇室训令》则是为了执行《英皇制诰》而颁布的。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行政局、立法局运行的具体细则、立法程序,以及明确指出和规范总督的权力。鉴于《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所规定内容在宪制层面上的根本性,这两个法律文件被称为香港本地的宪法性文件。
香港特区有学者认为,在殖民体制下,香港法院在法理上享有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其主要依据是《英皇制诰》。不过,由于《英皇制诰》赋予总督与立法局的立法权非常广泛,对立法权行使的约束比较松散,基本上不存在有章可循的规范性条款,所以这种主张仅仅在观念层面具有意义,表明了司法权所可能触及的范围。在《英皇制诰》颁行后的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中,香港法院鲜有依据《英皇制诰》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案例。8
面对日益临近的回归压力,为了对那些无论愿意与否都将留在香港的人给予“道义”上的保护,香港立法机关于1991年制定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9。位列于该条例的第8条即是《香港人权法案》。该法案以香港本地立法的形式完全移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的规定。10
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第2条第3款、第3条的第1款与第2款、第4条等四个条款最为紧要。第2条规定了“释义”问题,其第3款规定:“在解释及应用本条例时,须考虑本条例的目的是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的规定收纳入香港法律,并对附带及有关联的事项作出规定。”第3条规定了“对先前法例产生的影响”问题,其第1款规定:“所有先前法例,凡可作出与本条例没有抵触的解释,须作如是解释。”其第2款规定:“所有先前法例,凡不可作出与本条例没有抵触的解释的,其与本条例抵触的部分现予废除。”第四条规定了“日后的法例的释义”问题,即“在生效日期或其后制定的所有法例,凡可解释为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的规定没有抵触的,须作如是解释”。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对香港本地与人权有关的立法以及宪政秩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基于英国普通法中的“后法优于前法”原则,《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第1款与第2款,使它具备了对其生效之前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的效力。这也就促使香港立法局不得不对以前通过的与人权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正,以使它们符合该条例的要求。这样,对于在其施行之前通过的香港本地立法而言,《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就取得了凌驾性地位。同时,《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打破了法院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原有平衡,使权力向法院倾斜。11
由于受英国“议会至上”法治传统的影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在法律位阶上只是香港本地的普通立法,根本不是宪法性文件,故同样是基于“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它对在其施行之后制定的立法没有优越效力,其第4条只能规定日后制定的法例应当如何解释。因此,它存在着被立法机关后续立法废除的潜在危险。
为了配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实施,彻底消除它被后续立法废除的潜在危险,专门为管治香港而颁布的宪法性文件《英皇制诰》也于1991年被修正,并于6月8日与该条例同时生效。《英皇制诰》第7条新增加的第5款规定:“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适用于香港,应当通过香港法律予以实施。在1991年《英皇制诰》(第2号)施行之后,任何法律不得以与适用于香港的该公约不相一致的方式限制在香港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综合上述两个法律文件,显而易见,在法律规范层面,《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成为对1991年6月8日之前生效的香港本地与人权相关的立法进行审查的规范性依据,《英皇制诰》则成为对1991年6月8日之后生效的香港本地与人权相关的立法进行审查的规范性依据。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制定和《英皇制诰》的修正,使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行使有了根本改观,有四个案例可恰当说明这种根本性改变。
第一个案例是香港上诉法院于1991年9月30日判决的R v.Sin Yau Ming案。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大体是,施行于1969年的《危险药物条例》12的第46条中的部分规定与第47条中的部分规定是否抵触《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前者是两种关于以贩运为目的管有危险药物的推定与关于管有及知悉危险药物的推定,后者则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即“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其无罪”。具体而言,依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第1款,《危险药物条例》第46条中的部分规定与第47条中的部分规定是否允许作出与《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相一致的解释?若不能做如是解释,便与《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相抵触,那么依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第2款,《危险药物条例》第46条与第47条中的哪些部分已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废除?香港上诉法院最后在判决中宣告《危险药物条例》的第46条中的部分规定与第47条中的部分规定抵触《香港人权法案》第11条第1款,自1991年6月8日起被废除。13香港上诉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中还有两点主张值得注意。一是,他们认为,香港上诉法院及任何其他法院的唯一职责是,为了确定某部立法是否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不相一致而审查该法。香港上诉法院或任何其他法院不废除立法,废除立法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完成。14二是,根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第3条与第4条规定,香港所有现存及所有新制定的立法须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持一致,这就使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变得至高无上,立法机构不再至高无上。15这就突破了英国“议会至上”的法治传统,使得香港本地的立法处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下。
第二个案例是香港高等法院于1992年7月27日判决的R v.Lum Wai Ming案。本案是在香港上诉法院于1991年9月30日对R v.Sin Yau Ming案的判决之后、香港立法局随之于1992年6月26日对《危险药物条例》第46条与第47条修正之后发生的。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大体是,1992年6月26日修正后的《危险药物条例》第47条第1款中的部分规定能否允许作出与适用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相一致的解释?如果不能,则它便抵触《英皇制诰》第7条第5款而应当被废除。香港高等法院最后在判决中宣告《危险药物条例》的第47条中的部分规定因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而被废除。16
第三个案例是香港上诉法院于1994年3月17日判决的The Queen v.Chan Chak Fan案。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大体是,施行于1972年的《入境条例》17第37K条第1款关于“未获授权进境者”的推定是否因抵触《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而违宪。香港上诉法院判决,尽管《入境条例》第37K条第1款偏离了《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但这种偏离是合理的,因而不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最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上诉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发表的这种观点,即由于《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1条第1款“逐字照录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18“《英皇制诰》通过禁止任何立法抵触适用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方式巩固了《香港人权法案》。该法案是适用于此地的该公约的化身。任何抵触该法案的立法因而都是违宪的,并都将被身为宪法守护者的法院推翻。合宪性测试等同于是否合乎该法案的测试”。19这就把香港上诉法院在对R v.Sin Yau Ming案判决中所发表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一步,促使《香港人权法案》成为审查香港本地立法是否违宪的标准。
第四个案例是香港上诉法院于1995年11月24日判决的Lee Miu Ling v.At torney General案。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大体是,《香港人权法案》第21条(乙)项规定了平等选举权利,施行于1994年的《立法局(选举规定)条例》20附表二确定的功能团体是否因抵触《英皇制诰》第7条的第3款与第5款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第2款而应废除。香港上诉法院在判决中重新确认了其在the Queen v.Chan Chak Fan案中所发表的关于《香港人权法案》的立场。不过,就本案而言,香港上诉法院认为,尽管《立法局(选举规定)条例》附表二确定的功能团体表面上不符合《英皇制诰》第7条第5款确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第2款以及《香港人权法案》第21条第2款关于平等选举的规定,但功能团体完全规定于《英皇制诰》第7条第3款之中,因而不违宪。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上诉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还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在上诉法院对本案的审理中,包括法官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将本案涉及的问题视为被挑战的那些条款是否已被废除,但由于本案所涉及的条款是在《香港人权法案》施行之后制定的,故本案的法律问题是这些条款是否违宪。21二是,正是因为《英皇制诰》第7条第5款致使在《香港人权法案》施行之后制定、与《香港人权法案》不相一致的立法违宪。22这就具体细化了《英皇制诰》第7条第5款的规定,使《香港人权法案》成为对其施行之前与其施行之后制定的立法进行审查的标准,并使这样的案件成为违宪审查案件。
综合观之,R v.Sin Yau Ming案和the Queen v.Chan Chak Fan案都是依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对该条例施行之前的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案例,由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并非是香港的宪法性文件,故这两个案件不是违宪审查案件;R v.Lum Wai Ming案和Lee Miu Ling v.Attorney General案则是依据《英皇制诰》第7条的第3款或第5款对《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施行之后的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案例。由于《英皇制诰》是香港的宪法性文件,故这两个案件是典型的违宪审查案件。由于香港上诉法院在港英时期是香港本地的最高审级法院,故香港上诉法院于1995年11月24日对Lee Miu Ling v.At torney General案的判决被普遍视为是确立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权的案件。23这种看法亦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于1997年7月29日对HKSAR v Ma Wai-Kwan David and Others案的判决中。24
三、从基本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看基本法审查权
“从法学观点来看,革命的决定性标准就是现行秩序已由新秩序在以前一个秩序本身所不曾料到的方式下加以推翻和代替。”25中国于1997年7月1日零时以和平方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无疑就是一场革命。对于香港的法律秩序而言,这一革命时刻带来了香港宪政秩序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即“回归前,香港的最高‘基本规范’是英国的法统,其法律表现形式是《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回归后香港的基本规范是中国宪法,其法律表现形式就是中国全国人大为香港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26
按照法律秩序理论,在一个法律秩序内部,低层级的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抵触高层级法律规范的问题,尤其是法律与宪法的抵触问题。如何解决法律与宪法的抵触问题便涉及宪法的保障。27就香港特区的法律秩序而言,也可能发生香港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立法与基本法的抵触问题,尤其是香港特区立法机构就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立法与基本法抵触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宪法保障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基本法审查权的问题。
香港法院在回归之前确立的违宪审查权能否在回归后直接过渡到基本法审查权?依照法律规范理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革命所改变的绝不仅是宪法而却总是整个法律秩序”。28因此,在法律规范层面上,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审查权在基本法上的规范依据只有两种可能性,即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特区法院这种权力,或是基本法确认了香港法院在回归之前根据宪法性文件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能够在回归之后嫁接到基本法之上。
显而易见,基本法没有明确赋予香港特区法院基本法审查权。但是,与《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松散宽泛相比,基本法显得更为周详与细密。或许基本法所确立的宪政秩序能为香港特区法院享有基本法审查权产生某种影响。
香港特区享有立法权,29但不享有独立的立法权。从立法事项所涉及的内容看,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立法;另一类是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的立法。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不影响法律的生效。30按照对“备案”一词的通常理解,香港特区立法机关负有将其制定的所有立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义务,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享有对其报送备案的所有立法进行形式审查的权力,不享有实质审查的权力。但这种一般性的形式审查权力存在例外,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果认为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31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进行实质审查的范围只限于香港特区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涉及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条款的立法,而不能对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立法进行实质审查,更不能对自治范围内立法的效力作出否定性举措。基本法规定的其他中央机关,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则更无权对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立法进行实质审查。那么,对香港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立法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权力只能由香港特区内的机构来行使。
香港特区的立法权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共同行使,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都可能承担对立法会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责任。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方能生效。32如果行政长官认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区的整体利益,可在三个月内将法案发回立法会重议,立法会如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在一个月内签署公布或者与立法会进行协商,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在征询行政会议的意见后,可解散立法会。33这里的“整体利益”一词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以涵盖立法会的立法必须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行政长官因而承担一定的实质审查权。
不过,基本法又规定,行政长官在其一任任期内只能解散立法会一次,34如果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原案,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则行政长官必须辞职。35可见,即使行政长官认为立法会的立法因为不合乎基本法而不符合香港特区的整体利益,只要他的反对不能彻底终结立法会的一项法案,那么他也就不能独立地承担起实质性地审查立法会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责任。
香港特区立法会作为专门的立法机关,负有使自身的立法不得抵触基本法的责任。对于自身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的问题,立法会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而它也可能承担起对自身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的责任。从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看,立法会可以冒着可能被行政长官解散的风险,使本机构的意志压过行政长官,从而通过被行政长官反对但本机构认为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另外,立法会可以利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在发现先前立法不符合基本法时,进行后续立法,使相关立法规定符合基本法。但是,在这个深受“自己不能担任自己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影响的普通法地区,由立法会行使对自己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很难被认可及接受。
作为一个法律执行机构,法院的典型职能特征之一便是享有对法律的选择适用权。从法理上讲,由于基本法在香港特区法律秩序中的优越地位,香港特区法院有权选择适用与基本法相符合的立法,而拒绝适用与基本法相抵触的立法,并在无下位法时,直接适用基本法裁判案件。既然是对法律的选择适用,那就不可避免地隐含着香港特区法院有权对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实质性审查。
“违宪审查权往往与宪法性规范的解释权不可分离。”36显然,这里的解释权并非指一般性解释权力,而是指作出有拘束力的解释决定的权力。拥有宪法性规范的解释权往往意味着拥有违宪审查权。依照中国整体的宪制模式,基本法解释权被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37基本法相应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涉及基本法规定的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立法进行审查。38这一点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基本法解释权与基本法审查权的关系。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39如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类比,那么推理的结果便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香港特区法院可以根据自己对基本法的解释,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就自治范围内事项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进而作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裁判结论。
这种类比推理似乎也可以从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40的规定找到支持。香港特区法院作出的裁判结论是最终的,即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都认为立法机关就自治范围内事项的立法合乎基本法,也无法将之推翻。可见,在基本法的法律规范层面,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相比,香港特区法院处于更为有利、更为独立的地位。但是,这仍不足以断定香港特区法院就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自治范围内的立法享有基本法审查权,因为即使是就同样属于成文法性质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言,人们也曾由于该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哪个联邦部门享有宪法的最终解释权,而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就当然享有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即使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作出判决之后,这种论战仍旧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香港法院在回归之前根据宪法性文件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属于普通法的范畴,这种权力能否在回归之后嫁接到基本法之上的问题就将我们带入了对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进行解释的问题,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了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41在香港特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区的法律。42
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专门研究了香港哪些原有法律抵触基本法的问题。但由于对香港普通法、衡平法和习惯法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的任务过于繁重,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放弃了对这三种香港原有法律的审查,而仅仅对属于成文法性质的条例和附属立法进行了审查。43依据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7年2月23日作出的《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宣布“《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2条第(3)款有关该条例的解释及应用目的的规定,第3条有关‘对先前法例的影响’和第4条有关‘日后的法例的释义’的规定”不采用为香港特区的法律,从法律规范层面上废除了《香港人权法案》的凌驾性地位,但该决定没有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区如何适用的问题,也没有处理香港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和习惯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的问题,更没有对香港法院在回归前根据发展出的普通法而享有的依据宪法性文件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予以评论及决定。
那么,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的截止日期(cut-of f date)该如何界定、其参考标准是中英两国政府互换《联合声明》批准书时的1985年5月27日还是《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英皇制诰》生效实施时的1991年6月8日或者是基本法通过时的1990年4月4日或者是基本法生效实施时的1997年7月1日,或者还有其他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该决定中所规定的“采用”,是自动采用,还是必须有一个正式的采用行为?这些关涉香港特区法院基本法审查权的问题在当时都是无法解答的。
四、回归后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对本地立法的审查权
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涉及基本法的诉讼是HKSAR v Ma Wai-Kwan David and Others案。该案的关键法律争议大体是,包括普通法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是否存活过了香港主权行使者的变更。具体而言,该案的法律争议是,包括普通法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是否会在香港特区于1997年7月1日成立之际自动被采用而在香港特区得以继续有效,还是有必要采取一个正式的采用这些法律的行为,否则就不能继续有效。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于1997年7月29日对该案判决,认定香港原有法律在香港特区成立之际自动被采用为香港特区的法律,没有必要采取一个正式的采用这些法律的行为。44普通法已经成为香港特区法律的一部分。另外,对于“香港原有法律”的截止日期问题,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认为,该截止日期不可能是《联合声明》的日期,因为《联合声明》仅仅是一个条约和意向的宣示;亦不可能是《基本法》通过之日,因为《基本法》规定其将于未来的1997年7月1日生效施行;唯一合乎逻辑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恰当可行的结论是1997年6月30日。45历史地看,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在该案中对普通法自动采用问题以及“香港原有法律”截止日期问题的判决为香港特区法院日后行使基本法审查权埋下了伏笔。
Ng Ka Ling and 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案正式确立了香港特区法院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法的基本法审查权。在该案的判决中,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不但宣示了香港特区法院享有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审查权,而且宣布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中的部分条款因抵触基本法而无效。
这宗案件涉及的多项法律争议中有两项与本文研究的主旨相关。这两项法律争议涉及香港特区立法机构就自治范围内事项制定的法律是否抵触基本法。第一项法律争议是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于1997年7月10日制定的《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中规定该条例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的第1(2)条46是否抵触《基本法》;第二项法律争议是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于1997年7月1日制定的《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新附表一中规定父母子女关系的第1(2)条(b)项47是否抵触《基本法》。
第一项法律争议涉及该案中的所有申请人。这些申请人都是通常居住在内地的、希望凭借血缘关系而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人。在这些人出生时,他们的父亲都已经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他们都是在1997年7月10日之前非法进入香港,或者是在合法进入香港后非法逾期居留。尽管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承认,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意义上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但由于《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第2(c)条(a)项48规定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只能通过中国内地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单程证与在其上附贴的有效的居留权证明书来确定,并且这种规定将视为自1997年7月1日起生效,故认为他们在香港特区没有居留权。
这宗案件申请人从两个方面主张《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的第1(2)条违反基本法。一方面,这些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于1997年7月1日就被基本法第24条第3款无条件地赋予了香港居留权,而《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则于1997年7月10日生效时回溯性地剥夺了他们已经取得的香港居留权;另一方面,这些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在香港入境后将会因《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的有关规定而被视为不享有香港居留权,不享有香港居留权而未经入境处许可入境将会依据《入境条例》第38(1)条(a)项49构成刑事犯罪,这就抵触因基本法第39条第1款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有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5条第1款50以及为在香港本地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制定的《香港人权法案》的第12(1)条,而后两者均禁止这种立法。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判决《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第1(2)条不违反基本法,且不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15条第1款以及《香港人权法案》第12(1)条;51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多数意见支持了原讼法庭的判决,少数意见则认为《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第1(2)条违反基本法,且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以及《香港人权法案》第12(1)条;52终审法院则判决《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第1(2)条因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以及《香港人权法案》第12(1)条而无效。53
第二项法律争议仅仅涉及张丽华一人。她属于非婚生子女,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天便去世。她于1994年12月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到达香港。她所持通行证的有效期于1995年1月届满,此后便一直在香港非法逾期逗留。她于1997年7月15日向入境事务处报告,坚持声称自己是属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权。入境事务处处长则认为,根据《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新附表一第1(2)条(b)项的规定,张丽华由于是非婚生子女而不属于她的父亲所生,也就不属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永久性居民,不享有居留权。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判决《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新附表一第1(2)条(b)项的规定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54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支持了原讼法庭的判决;55终审法院则首先依据基本法第39条考虑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条款,即第3条和第26条,然后将上述考虑纳入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之中,最后得出了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上诉法庭一致的结论。56
这两项关于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抵触基本法的争议历经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一审、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二审和终审法院三审,走过了香港特区法院系统中的全部审级。尽管对具体的法律争议存在不同的判决结论,但在本案三个审级的判决中,没有显示出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在内的本案当事人对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表示过异议,也丝毫没有显示审理此案的法官对此问题犹疑不决。同时,从香港特区法院对这两项法律争议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特区法院法官依据基本法第39条进而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香港人权法案》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审查的裁判思维,与香港法院依据《英皇制诰》进而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香港人权法案》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裁判思维如出一辙。这也难怪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本案的终审判决中宣布:“在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司法权时,特区的法院有责任执行及解释基本法。毫无疑问,香港法院有权审核特区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机关之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发现有抵触基本法的情况出现,则法院有权裁定有关法例或行为无效。法院行使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乃责无旁贷,没有酌情余地。因此,若确实有抵触之情况,则法院最低限度必须就该抵触部分,裁定某法例或某行政行为无效。虽然这点未受质疑,但我等愿藉此机会毫不含糊地予以阐明。行使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时,法院是按基本法执行宪法上的职务,以宪法制衡政府的行政及立法机构,确保他们依基本法行事。”57
对于这两项法律争议的裁判结论,香港特区政府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对于第二项法律争议的裁判结论,香港特区政府甚至宣称他们将会采取适当措施,落实终审法院关于非婚生子女问题的判决,不寻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58
五、结 论
尽管至少自《最高法院条例》于1844年在香港施行开始,香港逐渐继受了包括普通法在内的英国法律,但由于英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所以香港地区的法院和法官在漫长的100多年中并没有积累多少依据宪法性文件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审查的经验。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也仅仅是香港上诉法院于1995年对Lee Miu Ling v.Attorney General案判决之后到1997年7月1日之前短短不足两年的时间。尽管时间短促,但这一点没有弱化对依据宪法性文件所作的香港本地立法行使的违宪审查权对回归之后的香港特区法院产生深远影响。
在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对Ng Ka Ling and 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案作出判决之后,香港特区法院就一直高调地、积极地行使基本法审查权,宣布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诸多法律因违反基本法而无效。人们也许会认为,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审查权是回归之前对依据宪法性文件所作的本地立法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继续。这种观念尤其可以从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对HKSAR v Ma Wai-Kwan David and Others案判决中的以下论述中找到支持,即“基本法——源自《联合声明》——的全部要旨即在于确定继续性,除非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所带来的那些必要变化。这个原则贯穿于基本法的全部条款,并涉及到香港特区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59
确实,在香港回归之后,除了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而取得香港宪政秩序中根本法的地位以及少数原有条例和附属立法被修改或废止之外,原来适用于香港地区的普通法、衡平法、习惯法以及大量的条例和附属立法得以继续;60除了新设立的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取代英国枢密院以及部分法院变更名称之外,香港原有的法院体系最大限度地得以留存;61除了因退休或离职而不再担任法官之外,香港原有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得以留用。62可以说,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基本上没有变革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基本上没有变更和废除在原有司法体制中运行的原有的法律制度,更没有替换运行司法体制、适用法律制度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进而,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63就更加巩固了上述因素的继续性。
或许是香港原有法律秩序中大部分要素都在回归之后得以继续,被香港特区法院作为直接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基础的基本法第39条的文字也与《英皇制诰》第7条第5款的文字极为类似,由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而带来的“基本规范”的变更对原有法律秩序的影响很小,致使“基本规范”的变更对原有法律秩序的革命性影响遭到忽视。“旧法律秩序的大部分在新秩序的体制内还是‘继续’有效力的。但是‘它们继续有效力’这句话并没有充分地说明问题。继续一样的只是这些规范的内容,而不是其效力理由……如果在旧宪法下所推行的法律在新宪法下‘继续有效力’,这只是因为新宪法以明示地或默示地以效力赋予它们,所以才有可能。”64对香港的法律秩序而言,在1997年7月1日零时这一革命性的时刻,基本法作为香港法律秩序的“基本规范”,陡然地终止了香港原有的法律秩序,但马上又采用了香港原有法律秩序的大部分要素。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革命性变革,微妙得可以使人难以察觉,微妙得可以使人视而不见。
或许是未曾察觉到这种“基本规范”的变更,或许是有意回避这种“基本规范”的变更,也或许是二者兼有,再加上香港特区法院在维护香港法律秩序统一中所处的优越地位,以及普通法在回归之后能够得以继续,使得香港法院在回归之前根据宪法性文件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能够在回归之后嫁接到基本法之上。当然,这种嫁接的顺利完成不能由香港特区法院单独承担,还需要其他机构浑然不觉的配合。在Ng Ka Ling and 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案的审理中,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没有丝毫抵抗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上诉法庭与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本地立法行使基本法审查权;在香港终审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就自治范围内事项的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也没有表示任何立场。在这种双重默认之下,香港法院在回归之前确立的依据宪法性文件行使的违宪审查权就在基本法所确立的宪政框架之下成功地蜕变成了基本法审查权。这种蜕变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中机巧地抢占违宪审查权,之后遭到联邦政府、国会和法律学者多重谴责,50多年后才敢鼓起勇气在“斯科特诉桑弗特”65案的判决中重新宣布国会的一项立法违宪截然不同。
注:
1邓小平:《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载《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7页。
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3参见罗沛然:《一株活树》,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自序。
4尽管基本法被香港法律界人士称为宪法、小宪法、本地的最高法,被内地法学界称为宪法性法律、宪制性法律、宪法特别法、宪法性特别法,香港特区和内地也有学者将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力称为违宪审查权,但笔者认为用“基本法审查权”这个术语更为恰当。
5笔者在本文中仅探讨香港特区法院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基本法审查权,而不探讨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香港特区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香港特区立法的基本法审查权。当然,即使探讨后一个问题,亦不可绕过这种基本法审查权是如何确立的问题。
6Marbury v.Madison,5 U.S.137(1803).
7See Wi l l iam Tricket t,The Great Usurpation,American Law Review,Vol.40,p356~376.
8See Yash Ghai,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2nd edn.1999),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305。
9香港法例第383章。
10[英]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香港史》,王皖强、黄亚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页。
11See Yash Ghai,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2nd edn.1999),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376.
12香港法例第134章。
13See R v.Sin Yau Ming,CACC 289/1990,at paragraph 164.
14、15、19、22、45Ibid,at para 54,at para 63,at para 48,at para 43,at para 35.
16See R v.Lum Wai Ming,HCCC 75/1991,at paragraph 50.
17香港法例第115章。
18The Queen v.Chan Chak Fan,CACC 328/1993,at paragraph 47.
20香港法例第381章。
21See Lee Miu Ling v.Attorney General,CACV 145/1995,at paragraph 2.
23参见陈弘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载陈弘毅:《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邵善波:《成文宪法对香港原有司法体制的影响》,载《香港回归十周年——“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201页。
24See HKSAR v Ma Wai-Kwan David,Chan Kok-Wai Donny and Tam Kim-Yuen,CAQL1/1997,at paragraph 130.
25、28、6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第133页,第133页。
26王振民:《回归后香港法制的“不变”与宪制的“变”——原有法制与新宪制的衔接》,载《香港回归十周年——“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18页。
27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7页。
29、30、31、32、33、34、35、37、38、39、40、41、60、61、62、6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第1款,第17条第2款,第17条第3款,第76条,第49条、第50条,第50条第2款,第52条第2项,第158条第1款,第17条第3款,第158条第2款,第19条第1款,第8条,第160条第1款,第8条、第160条,第81条,第93条,第19条第1款。36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43See Yash Ghai,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2nd edn.1999),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379.
44See HKSAR v Ma Wai-Kwan David,Chan Kok-Wai Donny and Tam Kim-Yuen,CAQL 1/1997,at paragraphs 18&226.
46该条规定:“本条例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
47该条例第1(2)条规定:“在以下的情况下,视为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存在——(a)任何女子与其婚生或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关系,为母亲与子女的关系;(b)任何男子与其婚生子女之间的关系,为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如子女属非婚生子女,只有当该子女其后因父母结婚而获确立婚生地位,该男子与该子女之间才存在有父亲与子女的关系;(c)只有父亲或母亲与其在香港根据法院命令领养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方为父亲或母亲与领养子女的关系,而该法院命令是指香港法院根据《领养条例》(第290章)作出的命令。”
48该项规定:“任何人作为附表1第2(c)段所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只可藉其持有以下文件确立——(a)发予他的有效旅行证件,和同样是发予他并且附贴于该旅行证件上的有效居留权证明书。”
49该项规定:“(1)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如——(a)属根据第7条在未得入境事务主任或入境事务助理员准许下不可在香港入境的人,但却未有该项准许而在香港入境;或(b)在香港非法入境后未得处长授权而留在香港,即属犯罪,经定罪后,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3年……”
50该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
51、52、54、55See Cheung Lai Wah and others v.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HCAL 68,70,71,73/1997,at para 43,at para 154,at para 141,at para 48,at para 154.
53、56、57See Ng Ka Ling and others v.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5,16/1998,at para 141, at para 155,at para 61.
58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
59HKSAR v Ma Wai-Kwan David,Chan Kok-Wai Donny and Tam Kim-Yuen,CAQL1/1997,at para 175.
65Dred Scott v.Sanford,60 U.S.393(1857).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政治与法律的其它文章
- 涉及第三者的防卫行为探析
-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立法若干问题思考*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与近代英国宪政研究”(项目编号:09FXC010)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论英国宪政与城市化对我国的启示”(项目编号:V0857-10)的阶段性成果。
- 难办案件中立法过时的认定主体*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YJC820055)的阶段性成果。
- 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820157)的阶段性成果。
- 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宪政原理*本文系中南大学前沿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服务型政府法制化研究”的研究成果。
-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措施:新型的贸易壁垒*本文是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新型贸易壁垒及江苏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0FXC009)以及江苏省教育厅201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国际环境条约不遵守情事程序研究”(项目编号:2010SJD820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