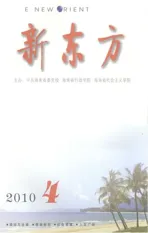海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培育
2010-12-26彭其
彭其
海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培育
彭其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当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培育何种民族精神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理性和健康发展,既有“拿来主义”的主张,也有立足于本土的考量。但是民族精神的产生并不是无根的浮萍,任意的跨文化和跨时空移植都可能使得民族精神复杂要素组合起来的“文本”更加杂乱无章。因此,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在民族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既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又不失其开放性与现代性,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并保持文化生生不息的必由路径。
海洋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曾经引导和鼓舞中华民族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又由于后来在“闭关锁国”的影响下走向内敛,而使中华民族在现代西方海洋文明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备受凌辱。“丧海辱国”的近代经历与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壮举记忆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和民族精神中二元悖反的矛盾图景,不断建构又解构着国人的“海洋梦”。从海洋资源的角度分析,中国无疑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人又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个海洋弱国。这其中的原因除去国力的不足、技术的落后等因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和现代海洋文化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精神还没有被完整地建构起来有关。
一、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条件之中的。以海洋为质介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造就的民族精神与以内陆或草原为质介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造就的民族精神在精神活力、价值取向、民族意识、民族性格乃至个性特征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1]文化环境和文化模式不同,这种“一般的精神”也随之不同。黑格尔曾经把海洋文化当作区别中西方文明的一道界限,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说,中国、印度、巴比伦等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占有耕地的人民封闭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2]。应该说,黑格尔的这种论断看到了东西方在海洋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就此否认东方文化中富含的海洋文化因子和东方民族精神中的海洋意识,就犯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中国作为世界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和文献可以证明。石器时代居住于河姆渡、壳丘头、龙山、大湾、良诸等沿海地区的远古先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实践所创造出的区域性文化就已经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如河姆渡遗址除出土大量淡水鱼遗骨外,还发现鳖鱼、鲸鱼及鳍鱼等海洋鱼类和生物的遗骨,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捕捞范围已扩展到滨海的河口并进而延伸到海上[3]。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早已经成了远古先民天然的生存智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族体上对沿海族群的吸纳、疆域上对沿海地区的拓展、物质上沿海与内陆的互通有无,海洋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并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丰富的传统海洋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渔猎和海耕互补的农业性海洋文化,指的是沿海地区的渔民在进行捕鱼业的同时,同时垦殖和发展海岸或海上种植业作为食物来源。中国是世界海洋农牧化的先驱,是世界海洋农业文化的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古人就“以海为田”,创造了“雒田”(架田)技术,开始海耕。以后,又陆续发明“蚝田”“蜡田”“蛙田”“种蛤”“养挑”“珠池”“鲻池”“盐田”等一系列技术,并在宋代、明清时期先后形成两次耕海热潮[4]。这些传统的海耕技术及其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农业性特征。(2)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航海文化,以郑和下西洋为其高潮标志。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创造出一套中外关系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制度,也叫封贡制度,费正清称其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5]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朝贡贸易的发展,使得朝贡成了中华帝国向海外输出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壮举也是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千古绝唱。(3)体制外的民间贸易、海外移民以及海盗文化。在重农轻商以及严防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下,中国海产品以及海外贸易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官方手中。但是,在商业利益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之下,以海洋为质介的底层的体制外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中叶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社会动荡,海防式微,政府的社会控制力下降,以民间性、地方性形式出现的海洋社会经济孕育发展起来[6]。以民间贸易、海盗走私、海外移民开发等为代表的民间海洋活动可以称为中国海洋文化中的“小传统”,但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像现在海外华侨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4)民俗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海洋文化,即反映在人们知识、思想以及信仰世界中的狭义的海洋文化。对生活在海洋文化背景里的民族来说,海和海岸带既是重要的地理环境,也是他们重要的劳动对象和认识对象。从中国古代第一部写海洋的经典《山海经》到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知识逐步累积和加深的过程。而面对大海的变幻莫测和经常发生的海难,民间和官方也举行一系列的祭海和造神活动,具有中国沿海特色的妈祖信仰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文化符号。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带有历史性和行动一致性的价值秩序,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的主旋律。上述丰富的海洋文化在与不同族群或地区的诸文化特征长期相互联系、磨合后,必然反映、融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反映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首先就是铸就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和包容性格。一方面,中国文化借助海洋向四海传播;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也不断接纳来自海上的异邦文明和族体。唐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中国将丝绸和陶瓷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播给世界的同时,也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和文明传播给了世界。唐宋时期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又经海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这些当时被称为蕃客的穆斯林与本土不断融合后至元代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此外,海洋文化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面不断自我反省的镜子,支撑和平衡着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支撑、平衡民族行为的过程,也就是民族精神发挥激励和心理调节功能的过程[7]。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相互交往和互融的过程中,一方面从物质上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支撑着中原农业民族的探险和开拓欲望,这对中华民族农业为本所导致的内敛倾向是一种很好的平衡。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敛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审视
在充分肯定和发掘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丰富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与西方海洋文化相比,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是迟缓的,尤其是明清以后,还走向了一个内敛化的过程。海洋文化的内敛化,使得近代中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对外经济互动、文化互往以及社会交往的主动权,也使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重创。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走向内敛?“最终迈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一些文明?”[8]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如果追溯起来,实际上都和15世纪郑和远航后中国丧失了历史机遇有关。
600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不仅发展了明朝同海外的贸易,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海洋知识,在世界航海史和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这一事件仍然是我们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范本。但是此后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郑和下西洋又恰恰成为中国海洋文化从开放走向内敛的一个分水岭,而郑和下西洋也没能够像哥伦布、麦哲伦等欧洲航海家那样给中华民族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抛却当时封闭保守的社会制度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朝贡”目的不谈,从中华民族精神中固有的保守性出发,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海洋文化之所以发展迟缓并走向落后的原因。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一些固有因子是束缚海洋文化发展的内因。首先,中华民族内在地以道德标准为衡量事物或行为好坏的首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选择的原则是“义然后取”,即凡是符合仁义道德的就是有价值的,应当选择,否则就无价值,应该舍弃[9]。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在对外开拓方面以输出为主,而轻视“拿来”;以宣化炫耀为主,而轻视贸易技术。郑和下西洋也同样带有“耀兵异域”“宣教化”“以示中国富强”的目的,这个目的一是向海外诸国展示中国的强大,告诫海外诸邦,不要与中国为敌,要“恪守朕言,循理安分”;二是向海外诸国显示中国的富有[10]。尽管郑和下西洋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但是“科技”在天朝政体之下被称之为“雕虫小技”“淫技”等。这种体制内的航海文化缺乏经济理性的驱动,势必不能造就和培育出新生的社会因素。其次,中国古代“大一统”“攘外必先安内”等治国理念导致了历朝历代重视内陆、轻视海洋的国土安全理念,这又使得中国传统的“海疆”观念长期迷失。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均以“大一统”的思维定式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西方外来势力的关系。这在古代封建政权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大一统的思想为主体的海疆观念阻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11]。最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观念重视生命与乡土的联系和延续,这也使得民众向海外进取创业的动力不足。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在海洋文化发展中起着最根本的作用。中国早期海岛移民的主体如迁到海南岛的人口绝大部分是苦工、难民、流放的“罪人”,等等,而明清时期的海外移民也多是迫于生计所致,这就造成了海洋开发中人口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的局面,中国海洋文化发展迟缓也就在所难免了。
郑和有一句名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也来自于海……”[12]但是出自实践的这句真知并没有给后来的统治者和国民带来深刻的启迪。郑和与他所代表的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在当时的远航竞赛中占尽了风流,却在历史长河的文明竞赛中终成输家,竟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失去了命运之神的眷顾[13]。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以其特有的宏大视野,从地理环境和海上活动的不同,解释了中国和西方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不同,认为海上经商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14]。但是,抱持着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置自身海洋优势于不顾而行闭关锁国之政策,失去的不仅是财富,迎来的更是来自海上的“亘古未有之变局”和整个民族的屈辱史。中华民族唯有以爱国主义之精神来抵抗西方海洋文化的冲击,以自强不息之精神来重新反思和重构自己的海洋意识。
三、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培育
从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下西洋,再到近代西方列强携船坚炮利之势肆虐中国领海,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历经了几多坎坷和几多觉醒。一方面,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内向性特征使我们的祖先始终难以大幅度超越土地的限制而走向海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也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在面临外侮时又特别能激发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加快发展,海洋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已经被世界各个民族认识得更加清楚。民族文化是可塑的,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有利于海洋意识的培育。但是受传统海洋意识的影响,中国海洋文化仍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面貌。在当今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过程中,培育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更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发展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培育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必须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丢失了传统的现代化,并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整体的提升,也不能使中国以平等的姿态与西方对话。中国走向海洋,需要对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了解它的源头、发展过程及其利弊,才能正确把握今后的发展趋向,进而取得适应新的历史挑战的自主地位。没有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便没有当代海洋发展的行动自觉[15]。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自觉,一方面要挖掘和肯定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看到其开放、包容和自强不息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反省我们的不足,“运用科学的理性和文化自觉精神,准确地把握中国海洋文化价值取向转换的现代精神方向”[16],以适应新的世界性海洋文化的发展。
培育中华民族海洋意识,还必须以开放的精神学习近现代西方海洋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民族精神是在发现“他者”的时候和地方出现的,即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形成自己族群的历史故事和民族性格的叙述系统[17]。近现代以来西方强国之所以能够兴起,都是与其高度重视海洋以及积极指导本国开发利用海洋,建设强大海上力量分不开的。如夺取出海口、争夺海上霸权,就是历代俄国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一条主线。日本则自丰臣秀吉时代起,就制定了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进而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而后以此为基地和跳板,吞并全中国、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最终称霸世界的海洋发展战略。而美国在二战后逐步走向世界超级大国的宝座也是以其海权思想为指导的。反观中国,海洋在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体系中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地位,这深深束缚了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向外发展。在此,我们并不是要鼓励中国也培育侵略性的海洋意识,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海洋经济价值取向、法律取向以及知识理性取向等现代海洋文化,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海洋发展战略对话。
培育中华民族海洋意识,还应该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参与和谐世界和谐海洋建设。21世纪是海洋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开发、利用、争夺海洋资源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中华民族传统的海洋文化对海洋开发采取的是一种平等亲和的道德取向。这种道德取向表述为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实施海洋开发战略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而坚持走和平、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的正确选择。全球化时代人类对海洋资源的索取不能以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也应该避免世界各国之间的海上冲突。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观念有助于维系人海之间的平衡、和谐状态。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05.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三联书店,1956:146.
[3]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J].文物,1980(5).
[4]孙关龙,孙永.古代海耕与今日海洋农牧化[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5]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M].林海、符致兴,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76.
[6]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
[7]王克千.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功能[J].开放时代,1996(6).
[8]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6.
[9]周大鸣.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J].广西民族研究,1996(4).
[10]闫亚平,纪宗安.郑和下西洋未能带动中国发展原因探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6).
[11]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2]罗宗真.郑和论丛:第一辑[G].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13]郑一均.论郑和下西洋[M].海洋出版社,1985:7.
[14]吴继陆.论海洋文化研究的内容、定位及视角[J].宁夏社会科学,2008(4).
[15]杨国枢.中国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C]//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4—5合卷.海洋出版社,2005:6.
[16]叶世明.“文化自觉”与中国现实海洋文化价值取向的思索[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7]韩震.论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J],理论月刊,2007(1).
中国(海南)南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