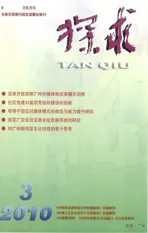对广州都市亚文化特性的若干思考
2010-03-22吴武林
吴武林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32)
对广州都市亚文化特性的若干思考
吴武林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32)
都市文化的魅力来源对于多元性的外来文化的包容、吸收与改造,从而呈现出自身文化的丰富性。酒吧,作为都市文化多面性的“夜色”一面,折射出广州亚文化的“半国际化”特点,其实也是这座城市主文化的特性。“自由支配性收入”和“自由支配性时间”使目前中国都市还不成熟的“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应的变化。在目前中国社会人的精神生存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下,求得“生存缓和”的生活方式有其现实的伦理意义。
亚文化;酒吧;自由支配性收入;自由支配性时间;中间阶层
英国学者史蒂文·康纳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提到,近年来,人们对文化文本和文化实践的整个领域的兴趣激增。当代文化批评家们在罗兰·巴特和斯图尔特·霍尔等思想大师的引导下,将体育、时装、发式、购物、游戏和社会仪式等作为其社会文化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以对待任何高雅文化艺术品的方式,毫无愧色地在这些领域中形成同样高深的理论。在这样的文化研究疆域的扩张中,文化、社会和经济这三个方面不再可以轻易分辨。美容院、健身房、摇滚乐、广场文化等等城市文化形象,甚至小到封面女郎、口香糖、广告词等,为大众文化或社会文化批评提供了最为形象和鲜活的素材。
当然,诸如酒吧这些连接、牵动和释放着都市人最真实的欲望神经的场所和空间自然也被纳入社会文化研究者的慧眼之中了。透过夜色下的酒吧灯光,从夜场的歌声与音乐,还有啤酒香中来观照广州这个城市的特性,不失为一个独特而真实的视角。
一、“半国际化”:广州亚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
丹尼尔·贝尔说:“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一个城市也表现出一种使想囊括它的意义的任何努力相形见拙的规模感。要认识一个城市,人们必须在它的街道上行走。然而,要‘看见’一个城市,人们只有站在外面方可观其全貌。”[1]近两年,在广州街道上行走,能“看见”这座城市什么全貌呢?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座城市正在动用所有的行政资源,举全市之力而进行的各种工程,来迎接2010年亚运会。为此,正在紧张而全面地铺开大型体育场馆、市政配套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着手城市旧建筑外观的装饰与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解放与异化、秩序与混乱、紧张与盲目、激进与浮躁、接触与陌生、铺张与悭吝、稳定与难测、开放与保守,带来的有政府的紧张与期待,来自民间的淡漠和批评,所以这些现象共同呈现出广州近两年来特有的都市文化现象。
有批评者认为,由于广州亚运会从申报到筹备的整个过程都呈现为过于浓厚的、单一的政府行为,所以到目前为止,广州市民缺少参与的热情和荣誉感,亚运会几乎成为了政府与体育界的自娱自乐。在大街上,关于亚运文化的一切都简单地退化为随处可见的异口同声的标语、整齐划一的宣传招贴、毫无创意的广告等,使得我们的的确确看出这又是一座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城市。“城市是才智。大都市是‘自由的’才智,”[2]“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城镇的心灵的诞生”。[3]就广州目前的这种精神状况,我们很难判断,亚运这种“半国际化”的体育文化交流会催生出新的城市心灵和城市风格。
笔者认为,和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最大的不同是,亚运会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际性的体育文化活动,准确地说,应该是“半国际化”或区域性的体育赛事,它对广州的国际形象并不能起到一个根本性的提升作用,对广州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所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
大多论者一再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强调广州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这种观点几乎成为了定论。持这种观点大致有几个主要的立论标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十三行、华侨、外向型经济等等,但在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的文化上,除了广州原住民外,源源不断的是来自于内地的“新客家”,他们带来内地不同地域的文化,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广府本土文化,因此在文化上更显示了它的倾内陆化。归结起来,从广州城市文化的现实来看,作为珠江三角洲都市中心的广州,并没有完全成熟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主文化的特征显示的是这还是一座倾内陆化、半国际化的大都市。
何谓主文化?主文化(“主导文化”或“统治文化”)是针对亚文化(次文化、副文化或潜文化等)而言的,这组概念反映了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文化价值差异和社会分化状况。主文化是在共同体内依靠权力的捍卫,被赋予了绝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主导和制约着社会思想潮流和生活风尚,如亚运会所有的标语口号、吉祥物等都是由政府统一发布的。主文化还包括三个子概念:一是侧重权力支配关系来划分的主文化是主导文化,如政府可以动用所有的行政资源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宣传和灌输广州亚运会的理念;二是强调占据文化整体的主要部分的主文化是主体文化,如亚运会贯穿的“和谐”观念,就是现实政治要求的反映,成为此次亚运的政治主体文化;三是表示一个时期产生主要影响、代表时代主要趋势的主文化是主流文化,和奥运会之于北京、世博会之于上海一样,亚运之于广州,成为了广州近年来大力宣扬的主流文化。主文化往往会因为它的主题先行和时效性而缺乏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昙花一现,如由政府征集的以亚运为题材的歌曲和音乐这样的应景之作,即便是用行政力量硬性推广,但也很可能随着亚运的闭幕而成为“绝响”,不再会有人传唱或演奏。
广州目前的主文化的特性如此,那么亚文化又如何呢?都市文化的魅力来源对多元性的外来文化的包容、吸收与改造,从而呈现出自身文化的丰富性。酒吧,对应于“白日”的都市,作为都市文化多面性的“夜色”一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它们折射出广州亚文化的“半国际化”特点,其实也是这座城市主文化的特性。下面我们以广州酒吧文化为切片,来透析从广州酒吧折射出这座城市的亚文化特质。
亚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化整体里占据潜在、地下或附属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讲,亚文化比主文化更具创造性和爆发力。亚文化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文化,它是当一种亚文化壮大成一种足够的力量与主文化形成对立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反文化,不过从目前的广州亚文化缺乏原创力量和向心力这点来看,还远不足以与主导文化形成明显的对立,反而是亚文化在主文化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如有名的花街90酒吧,在亚运整顿市容与秩序的强势下被拆除了,被拆的原址贴满了有关亚运的宣传画和口号。
斯宾格勒说:“唯有城市的命运和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才会以具有可见形式的逻辑诉诸于眼睛。”[4]的确如此,现实中的城市文化特质来自于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与遗传,城里人的生活经验、观念与方式都会以各种形式和内容呈现出来。
大体而言,上海酒吧由于凭借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租界”气息和民国旧情,所以天然有着洋派情调的遗绪和“国际性”的根底;北京酒吧由于依靠的是这座城市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所有北京酒吧的“联合国”特性是天然形成的。这两座城市共同的特点是外籍人士众多,所以各种“国际性”的酒吧就应运而生。
相比而言,广州酒吧的“国际性”要逊色得多,酒吧的装潢相对来说也没有北京和上海的那种情调,驻场知名歌手更是少见。具体而言,与异域风情有关的酒吧并不多见,如墨西哥餐厅酒吧、大篷车酒吧、Hooley's爱尔兰西餐酒廊、印斯味餐馆酒廊、特洛伊酒吧、舢舨泰国餐厅酒廊、纳斯达克吧等。墨西哥餐厅酒吧的南美风情、拉丁风情舞、沙滩PARTY,大篷车酒吧的吉普赛风情、花街90酒吧聚集了泰、葡、法、日、南美洲美食,Hooley's爱尔兰西餐酒廊给广州带来了真正的爱尔兰文化、印斯味餐馆酒廊的正宗印度风味、舢舨泰国餐厅酒廊芭堤雅热带雨林气息、纳斯达克吧是华南IT主题酒吧等,无意中丰富了广州以及来客的“生活经验”。一座城市,需要这种生活经验,也许这样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品味、心态、容量,更能激发和碰撞出新的想象,诞生新的心灵。
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原创的酒吧文化,或者说由酒吧文化演绎出来的新的创意文化元素并不多,甚至说是贫乏。严格说来,西方酒吧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历史也只是20多年,所以中国目前的酒吧文化大多还是以模仿为主,从酒吧审美趣味、酒吧音乐、消费方式、装饰风格等无不充满西方文化想象,仅以吧名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大都市中有类似的吧名,如威尼斯酒吧、夏威夷酒吧、法兰西酒吧、巴黎左岸酒吧、香榭丽舍酒吧、好莱坞酒吧、爵士酒吧、诺亚方舟酒吧、苏格兰酒吧、圣保罗酒吧、爱尔兰酒吧、鸡尾酒酒吧等等。再以广州的新觉青年公馆旗下西方文化主题区——公馆咖啡·西餐为例,它分森林狩猎、乡村田园、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文明五种空间,意在浓缩西方文明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虽然这种西方文化想象从文化模仿开始,但只要我们提供足够的文化自由空间,定能创造中国新的非主流文化的因子。
以音乐而论,欧美许多最精彩、最能体现人类精神与心灵的创造性的文学艺术,不乏来自于酒吧文化的例子。典型的如美国爵士,这种从底层酒吧中诞生出来的伟大音乐最终“成为世界奇观”,“一些西方古典音乐在世界各地演奏,但古典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尚不及爵士音乐。”[5]另外如电音、摇滚、hop-hop、香颂、环境音乐(Ambient)、沙发音乐(LoungeMusic)、伊比萨(Libiza)、Chill Out、雷鬼(Reggae)、Dub、Acid Techno、Bassa Nova、World Beat、原音音乐(Acoustic)、电子原音音乐(Electroacoustic Music)等无不与西方的酒吧文化有着血缘关系。这样的流行文化需要国际文化交流的环境才能得以形成,酒吧作为一种方式,所激发的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正是包括广州在内的内地酒吧今后着力追求的。
二、酒吧“乐趣”:催生广州本土亚文化力量的酵母
另类音乐、价格不菲的酒水、情色男女、藏污纳垢、酗酒狂欢等等,大概这些形容词还是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对酒吧的一种既定的看法与妖魔化的想象。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一语道破了通俗文化的秘密:“通俗文化之所以通俗,是由于它的消费者从其标准化中获得了各种乐趣。”[6]“乐趣”让所有的凡夫俗子砰然心动,因为它真的可以做到释放人所有的欲望,酒吧自然可以成为满足他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一个纵情空间,或是一个自由“场”。借用布尔迪厄“场”的概念,在于这个概念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其中就包括“对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的研究。”[7]
与传统的酒店、餐馆的公共交往不同,酒吧作为一种公共交空间,它以“乐趣”为唯一目的。“泡”在这些最能展示一个城市夜晚魅力“场”中的群落,他们的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和“乐趣”是什么?
夜幕下的广州在酒吧中醉眼朦胧,外企职员、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传媒、演艺界、明星大腕等是目前中国社会公众经验中的“中间阶层”,他们构成泡吧群落中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有来自不同阶层中向往“另类生活”、“个性生活”或“小资情调”的所谓“另类”,他们汇流到一起,成为酒吧中最IN最YEA的“蒲友一族”。
关于“中间阶层”,由我国学者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这个阶层有所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一些新型的社会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类似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白领’职业群体”,“一般而言,公众是将‘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与中间阶层联系在一起的。”[8]由于这个阶层属于新兴的阶层,从精神到物质尚不成熟和稳定,易于形成精神上的困惑和空白,酒吧对他们有一种更为亲和的诱惑力。
对于“另类”,不像“中间阶层”那样,有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样系统而有组织的社会学调查。他们更属于一个游离而不成熟的群体,从心智到行为的随意性、反叛性较强,但还远远不能形成一个社会主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拥有我们想要的朋友”。由于这个群体的叛逆性和自由性,酒吧对他们自然也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中提到“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并引用了汤姆森的诗来说明夜晚对于城市的特殊意义:“城属于夜,却不属于睡眠。”[9]
都市的夜晚充满着被“白天”压抑了的诱惑和自由的空气,酒吧、咖啡厅、KTV等,这些释放心灵的消费空间,是与“白天”主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呈现的场所,它们容纳着具有创新和潮流意识的群落,也体现了都市城市的品位。
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的开篇提到乔纳森·拉邦一部高度概括上个世纪70年代初伦敦生活的著作《柔软的城市》,并评论道:“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话语,这种话语后来产生了通常描述都市生活的各种词语,如‘向日趋破败的城市移民的中产阶级’和‘雅皮士’”。[10]同样,都市里的酒吧也在衍生出鲜活的词语,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如从“蒲”(玩)到最IN最YEA的“蒲家”,再到“蒲友一族”。语言、词汇与某种文化形成对应关系,它们为文化批判和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词源,不熟悉这个群体的“黑话”,是难以切入这个文化最核心的地方。酒吧在创造着与日常生活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影响和改变着一定范围群落和阶层的交往方式,它成为时尚文化、身体文化、大众流行文化展示和宣泄的场所。它具备着在总体上与各种文化形式进行组合的能力,例如,青年文化、时装、时尚和街头文化,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中,可以无顾忌地倾诉欲望,可以随意交换减肥心得,自如地传播服饰潮流等时尚信息。诸如情感和性这样的绝对隐私,可以成为这里最主要的话题。对于都市中的人群,德国著名思想家本雅明认为“人群是一层帷幕,从这层帷幕的后面,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游手好闲者招手。在梦幻中,城市变成风景,时而变成房屋。”[11]将这句话引用到这些消费群体身上,也恰当不过。广州的夜晚变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风景,把酒吧变成逃离日常俗世生活的自由空间。
分散在广州角角落落的酒吧、酒廊算起来不下千家,以各自的特色、情调、个性和风格向“蒲家”招手示意,就算一晚泡三家也足够人们泡上一年了。
东面的天河、环市东路到环市中路华侨新村别墅群一带,是广州一个典型的高级国际商务区,也是广州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消费人群以外籍人士居多,这里的酒吧自然也就带有城市新贵和遗少式的奢华和颓废,依次有大篷车酒吧、万紫千红吧、特洛伊酒吧、风之花、大象堡酒吧、墨西哥酒吧、小山酒吧、BARCITYB·BOSS、TANG、红馆、CHINABOX、酒晶、INHOUSE、KEVIN’S……相对而言,这里的外籍人士,尤其是黑人居多,如大篷车酒吧。华侨新村路段依次有和平吧、CHINABOX、路点吧、星吧、枕木西餐吧、闪动领域等,这里的酒吧虽然既不靠山,也不临水,但近商,几乎所有酒吧都是一幢幢独立的花园式别墅,因为多为老城建筑,所以空间有限,在小巧精致上显示自己的特色。此外,或许是因为这里外籍人士居多,又有几家五星级酒店,所以相对而言,这一带的消费者层次较高,酒水价格也比较高,啤酒价格基本维持在300元/打。
沿江路和长堤大马路酒吧街虽也多设在民国老建筑里,但不像华侨新村那样的旧式花园式别墅,而多是民国时期商业性建筑,加之临水,所以这里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以花街90为例,它正好位于解放南路的拐角处,多年以前是一座闲置的电厂,后来经过简单的规划,就改成了可以欣赏夜景的露天酒吧;咆哮吧则是由一座五层楼高的中空发电厂改建而成。粗粗列举,从仁济路口往东数,有滚石俱乐部、爱群大厦的爵士吧,到解放南的夜樱吧、花街90,再到原德国发电厂旧址位置的咆哮、Happy吧、Cafe1920、正点吧、Babyface等。因为这里的消费人群大致以本地时尚青少年及中年成功人士聚集地,所以相对而言比华侨新村一带更新锐,更新潮一些。
荔湾(芳村)白鹅潭酒吧街,严格说来,这个酒吧街是规划出来的,像双指吧、夜景吧、本色、飞帆吧、风车伴、开心吧、威特斯、红树林、绝世好吧、夜未央、赢吧、亚米高、喝采吧、拉菲吧、金锁匙、蓝堡吧这些酒吧是一家接着一家的空间布置,不像上述两个那样分散,所以这里更像酒吧街。这里是珠江夜游的一个重要景点,酒吧街在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彩中成为夜游过程中最闪亮的一景,也成为展示这座城市夜景魅力的重要题材,所以在外观上,这里以灯光显其特色。这里的消费人群大致以当地人及珠三角经济收入稳定人士为主,消费价格算最低的,每打啤酒仅100元左右。
以191SPACE作为个案来分析,191SPACE是艺术交流为主题的艺术酒吧,这里聚集了广州独立音乐各流派的原创音乐人才,也是国内外乐队来穗交流的场地。191SPACE以音乐为主打,同时也支持其他门类的原创艺术,如画展、摄影展、DV、独立电影、诗歌、戏剧等。综合它2009年5月和7月的演出节目单,可以读出这个文本的都市流行文化意义:
5月:“RockX HongKong”CD发布会广州站、沙漠乐队新专辑《永远没有终点》全国巡演首发、北京硬核金属——堕天、TOM VS光头“重出江湖”纯器乐演奏会、“夜上海”怀旧老歌演唱会、重庆后朋克——愚人船、沼泽与朋友们“变形的N种方式”、北美当红摇滚乐团Protest the Hero、加拿大顶级萨克斯Yannick爵士四重奏。
7月:Loser乐队(中英文老摇滚和原创)、沙漠抗洪义演、法国电音大师Opra Hashimo中国巡演广州站、《你——搁浅的马儿》法国科拉琴实验民谣中国巡演广州站、Loser乐队(中、英文老摇滚和原创)、达达乐队主唱彭坦“夏天以南”巡演、惘闻2008年新专辑《IV》发行巡演with“沼泽”&“Elf Fatima”、澳洲及菲律宾著名金属乐队Intolerant中国巡演广州站、黄金力量修行者音乐会、“沧浪星·古琴和吉他的交响”沼泽乐队08广州音乐会、北京山地摇滚DEFY-Rockabilly中国巡演广州站、30Marqido(日本)+itta(韩国)女子实验电子+嗓音+诗歌音乐会、零壹乐队全国巡演广州站。
这个文本包含了较为丰富的西方酒吧音乐:重金属、摇滚、爵士、电音等,这些都是西方原创的音乐,在酒吧这种丰富、多元、轻松、前卫的演出形式和乐趣中,无疑既丰富了人们的视听经验,也成为催生广州本土亚文化力量的酵母,但目前要滋生出广州本土具有全国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新的亚文化元素,确实还有非常艰辛而漫长的路。
三、“限度自由”:作为都市生存的一种酒精
有秩序的、开放的宽容的城市绝不会限制自由,而是“限度自由”。一个城市凭借什么能涌动起一个如此巨大的欲流和消费?
答曰:“自由支配性收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于“生存缓和”的需求。
丹尼尔·贝尔解释西方社会的休闲文化时说,“在经济领域,被社会学家称之为‘自由支配性收入’——即满足人基本需要以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得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消费方式的种种开销(如建设游泳池、购置游艇、出门旅行等)。”[12]丹尼尔·贝尔的论断虽然不是针对酒吧文化而言的,但其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自由支配性收入”,对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依据,应该说,“中间阶层”最具这方面的消费实力。
以酒吧中酒的价钱和喝酒的人群来分析这个消费圈的特点。看一看一个名叫唐会(Tang Club)的酒吧的酒价:啤酒300元/打;红酒300—39999元/瓶;洋酒300~800元/瓶;鸡尾酒30—60元/杯。再看一看一个名叫BAR CITY B·BOSS的酒吧的消费:啤酒400元左右/打;洋酒在450元—1800元左右。它们适合的人群都是白领、成熟人士和外国人。酒吧这个可以把人的所有口感、视界、听觉、触须调动到极至的“场”,就是这样像磁石一样让这些中间阶层和一个以追求新锐为乐趣的群落心甘情愿将一部分收入投入酒吧的啤酒桶中。相当的消费能力,就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如购房、私家车、旅游和相应的文化、社交消费等,酒吧可以为他们的文化或社交消费提供一个其他生活方式所不能达到的另一个理想的纵情舞台。
另外,还需要“自由支配性时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成另一主体。”[13]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多少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参数。在这里,笔者理解,“变成另一主体”是将人格的多重性分解出来,将真善美、假恶丑都在不同的“场”中表露出来。自然,酒吧可以使那些有着自由支配收入的群落毫无顾忌地“变成另一主体”。白天道貌岸然的人士在这里可以纵情欢乐,日常笑不露齿的淑女可以在这里与影共醉。酒吧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暧昧、幽秘和暗示,他们需要的不是酒吧本身,而是需要一个“场”让深藏的欲望在劲歌热物中沸腾起来,在觥筹交错中流淌出来。
“自由支配性收入”和“自由支配性时间”同样重要。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中国现阶段中间阶层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14]除最后一点值得商榷外,这种界定有相当的科学性。一是“一份较高收入”,二是“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为城市的酒吧文化和消费提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根据。但也不断有外国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社会架构目前还欠缺中产阶层,原因是中产阶层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和催生新生文化的消费群,如new age音乐通常被看做是中产阶级的音乐。也有专家以中国的中产阶层消费量逐年提高的趋势预言,中产阶层将于二十年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成为社会经济稳定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比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更能有效扩大内需,提升经济效益。同样,被人们称为“另类”这个特殊群落也只能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态下的亚文化圈,虽然如此,我们又不能小觑这个群落的存在。
还有一点,这个群落跑到酒吧当中来,为的是得到一种“生存的缓和”。马尔库塞为解释“生存的缓和”,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傍晚高峰期的地铁。我看见的,是人们疲惫不堪、气忿满怀。我感到,有人随时都要拔出刀子来——仅仅如此。他们在阅读,或确切地说,他们沉浸在报纸、杂志或书本之中。两三个小时后,这些人身上的臭味被去掉、被冲洗干净了,穿戴整洁或随和,或许很幸福、亲切,忘记(或记得)一切。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家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异常家庭聚会或独居。”[15]敏锐的思想大师洞察人间芸芸众生干的所有勾当,但忘记提到,都市中自然还有一小部分人跑到酒吧这个自由场中去了,要在这里寻找快乐的光阴和虚拟的肯定,让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完全出轨,让白天夹着尾巴做人的退化人性回到原始野性中。生存的缓和在这里具有一种直接意义,是用消费和时间可以交换得到的一种虚拟自由。
马尔库塞提到了“艺术的异化便是非升华。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他们就变得可以容忍,甚至变得既有启发性又有效益,现在,这种形象已经失效。它就结合到了厨房、咖啡厅、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非升华——以直接满足为中介的替代。”[16]生活的异化同样是一种“非升华”,它需要种种替代物来提供松弛与快乐,酒吧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种。“替代”在这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词,它可以转换为现实意义的词汇,如酒吧为生活的非升华提供了承接空间和迷宫,“替代”了日常社会世界的压抑、扭曲和变态,为人提供了欲望的平台。在这个美女、美酒和音乐混合的疯狂天堂里,你有机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为心灵挡住炎炎烈日、飒飒寒风,包括生产恋爱,预谋爱情,制造艳遇,消费轻松,享受自由。
美国一个学者在他的《宴饮的年代》中用四个特点概括了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崇尚童年;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便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关心幻觉。”[17]这种文化情绪在酒吧中都能找到,只不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文化情绪。
对酒吧这种消费和行为是持批判还是宽容的态度?是否仅以道德价值来衡量这样一种欲望的释放和自由的追求?又以什么样的道德观来看待夜幕下的都市自由?是否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松弛成了个人自由的定义的本身目的。”[18]看来,在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道德价值观的时候,“生存的缓和”是一个可以用来应急的道德概念。
在这种场合,“生存的缓和”是否意味着一种享乐主义?这绝不能简单地划一个等号。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19]享乐主义可能违反道德价值,可能以“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根本的‘我向主义’,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就是缺乏一个扎下根子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是对这个社会生存的最深刻的挑战。”[20]但生存的缓和是对社会世界的精神和心理压抑的反抗。在人的精神生存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下,生存缓和有其现实的伦理意义,以价值论而言,它对社会和他人是无害的。
在这种场所,“生存的缓和”是否又意味着一种颓废主义?是否一如克罗齐所认为的,颓废主义是“奢侈放佚的精美”和“动物性感官享乐”[21]?或者如尼采所认为的,颓废是说谎者的策略,在它对生活的憎恨中,颓废伪装成一种较高层次生活的崇奉者?我们曾经对于颓废主义给予了过多的批评,我们需要转化这种将颓废主义等同于腐朽没落的观点,要像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颓废主义是对灵魂中的危机感的拯救,而且这种拯救不仅仅是美学上的,它感兴趣的主要是经验着危机的自我和内心生活。生存缓和是人对自己精神的按摩,对于出入于酒吧这个自由场的人来讲,有醉生梦死般的感官享乐,但不是动物性的感官享乐。有对高层次生活的崇奉,但是一种合理无害的崇奉,这是自己对自己精神生活的一种松弛。
在酒吧,有洗涤听者心灵、令人心平气和的nesage音乐,也有充满反叛精神的朋克摇滚,这是人类精神的两极,也是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与心灵元素。卡尔·雅斯贝斯的话很有意义,“当前的阶段对人提出了广泛的要求,提出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被这种危机夺去了自己的世界的人,必须以他所能运用的材料和前提条件从头再造自己的世界。……否则的话,他就会陷入空无之中。如果他不走向自我实存之路,那么他就只可能执著于生活的享乐而陷入机器的种种驱迫力之中。”[22]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自我实存之路越来越窄,我们的精神世界又将在哪里呢?生存的缓和成了我们目前最重要的生存伦理。透过酒吧,我们能看到,以“夜晚”为隐喻的都市亚文化的真实面目:在自由的状态中放松心灵,激发都市的创意、引领城市的潮流、提高都市的品位。它成为以“白天”为隐喻的主文化的一个补充,白天与夜晚在一起,才能真正构成完整的“24小时”都市文化。
[注释]
[1][12][17][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5.84.170.118.
[2][3][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85.79.81.
[5]罗伯特·拉姆.西方人文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498.
[6]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9.
[7]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39.
[8][1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48.252.
[9]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6.
[10]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
[11]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9.18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
[15][16]马尔库塞.单面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93.62.
[18][2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525.528.
[2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5.
[22]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68.
责任编辑:温朝霞
G124
A
1003—8744(2010)03—0055—08
2010—1—10
吴武林(1965—),男,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