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新疆
2009-08-27田磊
田 磊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战略观察家几乎一致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因此,如果恐怖与反恐成为了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从来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从未间断,放在历史的视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稳定和繁华,对外没有了边境战争,对内没有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大规模对抗。
然而2009年的夏天,注定将写入中国的边疆史。7月5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活动袭击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700多人受伤,近200人死亡,这样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过去10年新疆民族冲突中伤亡人数的总和。
“7·5”事件之后半个月,当记者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上,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叫卖和田玉、英吉沙小刀和吐鲁番干果的商人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比肩而过。这是今日新疆最典型的镜像:一面是开放而通达的新疆,扩建中的机场直通中西亚各国,27个对外口岸繁忙如昔;一面是紧张而脆弱的新疆,互联网断网,手机短信屏蔽,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对武警的依赖前所未有。
复杂的西北边疆
7月底,记者一路采访,来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尔津等地时,当地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最为热衷的话题是开矿、旅游、以及如何卖东西给哈萨克人、蒙古人和俄国人。
从清朝后期以来,在西北边境,一直都是中国人害怕俄国人,俄国人的骑兵不断地越过阿尔泰山脉,侵扰新疆,边境线一退再退,大片国土被蚕食,历史上诸如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地名,如今都已不在国境之内。即使到了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判断新疆形势时,还称“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最靠近前苏联边境的哈巴河县的一个乡一直都叫“反修公社”。
但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反修公社”早已更名,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跟俄国人频繁的战争已经极少有人感兴趣,做生意才是最重要的,新疆一口气开放了27个对外口岸,为中国各省区之最,廉价的服装、食物等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中西亚各国,反倒是俄国人害怕起来,严格限制着中国人和中国货物的流入。
经过60年的边疆建设,尤其是最近10多年的发展,民间的西北边陲,经济交往压倒了一切成为主要议题,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新疆却远不止是贸易通道这么简单。新疆占去了中国1/6的国土面积,相当于6个英国,4个日本,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印度等8个国家接壤。2000万人口中,除了约800万汉族之外,有12个民族,其中大都是全民信仰伊斯兰,且有4个民族跨境存在,国界之外就是本民族的独立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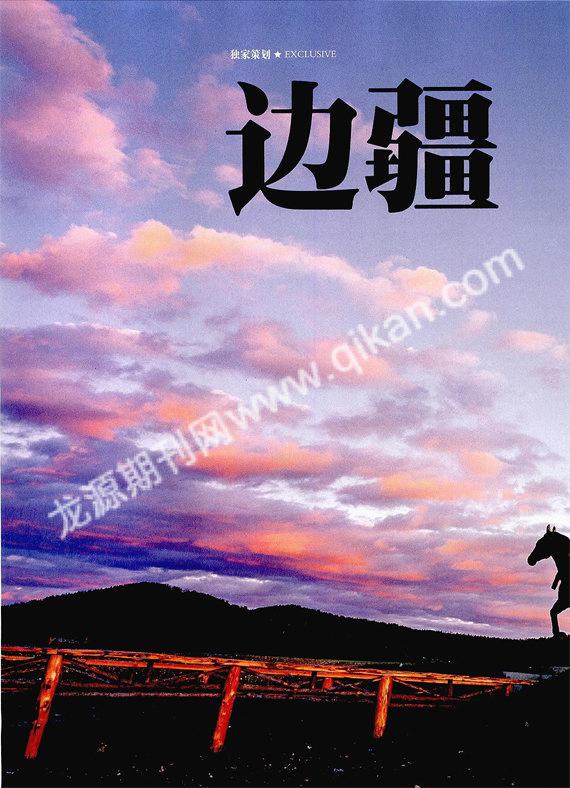

如此复杂的民族宗教成分和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让新疆历来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即使是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各省区开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经济建设之后也没有改变。在官方表述中,反对分裂主义运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历来都是新疆的主要议题。但60年来,无论是民族结构、关系,还是分裂主义运动的形式和烈度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跟历朝历代一样,新中国建国初期,反分裂最重要的手段是屯垦戍边。王震将军建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为解决军人婚姻,而从山东、湖南等地迁徙大批汉族女性,是第一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新疆。1960年前后开始的“三线建设”运动,内地大量企业整体搬迁新疆,带去了大批工人,以及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又涌入了大量的上海知青。
“这三批人构成了‘文革前汉人涌入新疆的主体,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大规模政府组织动员的汉人迁徙入疆。”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告诉记者,真正自然的人口流动始于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内地的打工者,比如拾棉花的、做小生意的、捡垃圾的等等都在新疆经过多年的打拼买了房子,定居下来,据有关资料统计,这样的人超过200万。
也因此,今天的新疆早已不是那个汉族人生活在兵团、机关,而少数民族则居住在乡村、市井,二者相对隔离的时代。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这些维族人的营生,汉族人也开始经营起来,在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乌鲁木齐传统的旅游商业圈里,汉族人和维族人比邻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为日常景象,甚至维汉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频繁而不可避免的交往、竞争中有着不同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几乎不可避免。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非流动社会的诸多传统的治边之策和自治操作模式,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适应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今日中国西北边疆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问题,也不只是贸易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多民族高度杂居社会里的民生问题。
“7·5”之痛
尽管分裂主义运动是否真的是新疆社会的头号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近年来,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新疆却往往与暴力和恐怖相伴,“7·5”事件更是将此印象推向了极致。在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公共场所,一夜之间,暴徒杀死了近200人,行凶者大多来自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而受害者则多为汉族平民。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个城市出现过如此惨烈的种族仇杀。
半个月后,当地的电视台、报纸等各类媒体播报的几乎只有两件事,一是对“7·5”事件暴徒的追击令,二是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官方在追击歹徒的同时,也在尽一切办法希望弥补事件造成的不同民族间的裂痕。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维族人又绑架了小孩,警察在一个卖馍的老头家里搜出了几颗人头”诸如此类的谣言在市民间铺天盖地,以至于警方不得不每天公布乌市的治安数据,媒体拿出专门的版面辟谣。
“你想想,如果是你的亲人被暴徒当街砍死,会没有仇恨吗?”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经退休在家的哈德斯·贾那布尔直言不讳,抚平民族隔阂将会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新疆当局的处理措施,哈德斯也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情说明我们的警惕性放松了安全部门、警察部门都负有责任,当看到暴徒行凶的时候,不管他是什么民族,都应该果断出手,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遭遇的挑战就比其他几个自治区要大。数十年来,新疆境内的爆炸、暗杀、纵火、袭击等恐怖活动从未停止过,打的旗号大都是“东突厥斯坦”,意在分疆裂土,建立独立国家。
“以前多是在乡村,针对汉族干部,可是这次却在城市中大肆杀害平民。”苗普生向记者介绍称,从1990年的巴仁乡暴乱开始,一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一共有162个干部被杀害,可是这一次7·5事件,一天死亡数字就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对于边疆的统治总是在怀柔与高压之间徘徊。1949年之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摇摆。建国初期,经过大规模的剿匪之后,新疆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文革”的到来,使得整个国家秩序大乱,新疆也不例外,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破坏。“文革”结束之后,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政策做了相当大的调整,大批的汉族干部纷纷撤回内地,甚至连工程技术人员都撤了不少,但随后的巴仁乡暴乱和1986年因司马义·艾买提上调中央而引起的新疆大学生静坐示威,让这些短暂的改革都被中止了。
1990年代以来,新疆跟整个国家一样,转而开始经济建设。“7·5”之后的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矛盾与希望的交汇点,一边是蓬勃的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有着宏伟志向的城市,新疆资源丰富、疆土辽阔,且处于亚洲地理中心,邻国众多,四通八达,完全有实力成为整个中亚的中心城市,但另一边,却在民族纠葛的泥潭里难以自拔。暴力事件留下的阴影,仍将笼罩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
失业的一代
“7·5”事件之后,在政府出动大批警力抓捕暴徒的同时,当地学者们更多的是反思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但不同民族的学者却对事件原因有着不同认知。苗普生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分裂分子的内外勾结,但深层原因则是这么多年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民族是个文化的分界,而不是政治分界。”苗普生说,过去我们的种种制度设计和文化宣传太过强调民族文化的个性,而忽略了共性。
在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教授迪木拉提·奥迈尔看来,“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更不是宗教问题。“事情一出,很多内地朋友都打电话询问我,新疆怎么了,是不是民族关系出了问题,是不是宗教冲突?”迪木拉提说,整个事件乌鲁木齐本市居民极少参加,宗教人士更是几乎没有,在他看来,这更应该被看作是社会问题,除了境外分裂分子的煽动之外,新疆内部能够有人呼应,很大一部分直接原因在于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问题。
近3年来,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源的过剩,让就业问题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负担,这一代大学生被称为“失业的一代”。新疆也不例外,但是,当失业问题遭遇民族因素,情况更为复杂。
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的要求不如汉族严格,在汉族地区,被称为80后的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女,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代人仍然多非独生子女,这也让最近几年来,适龄的各级院校民族毕业生迎来了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新疆本地不像广东、江浙等内陆省区有足够多的民营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而对于民族生来说,语言上的障碍以及学历的劣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到疆外就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一直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一对于少数民族的就业,国家都有标准不同的照顾,以前是硬性分配,但最近几年各种各样人事制度改革,让这些分配指标越来越少,党政机关还能保障硬性的民族指标,而企事业单位则完全是双向选择,虽然对企业选择民族学生就业有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之举。
在新疆采访期间,记者并没有得到全疆具体的就业率统计,事实上,官方公布的就业率,其一不会分别按照民族来统计,二则统计数据很难避免水分,这在国内任何一个省区都存在,新疆也不例外。人们对就业状况的感知往往都来自生活经验总结,而非官方数据。但这种经验更容易让人深信不疑。
在记者走访的多个少数民族家庭中,对于就业困难的抱怨几乎是共通的。但在苗普生看来,就业是个社会问题,是个自由竞争、市场淘汰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装入民族的框架里”。迪木拉提也认为,就业是社会问题,但不同民族间的失业率反差太大,确实是酿成社会不满情绪的隐患,而这些不满情绪则很容易被境外分裂分子煽动利用,在某些特定区域内,应该平衡这些因素。
敏感的公平
在新疆的采访,如果谈到民族问题,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会跟你提起不公平,无论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每个人都能举出一大串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对于政府而言,在不同群体间,不同种族间维护公平,新疆显得比任何一个省区都更难。
对于个体的汉族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处处的不公平竞争,诸如就业、进修、提拔机会,甚至计划生育,从来都是先以民族划界,而不是公平竞争,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国家为了维护民族关系而被牺牲掉的群体。但同时,他们却享受着作为汉族整体优势带来的好处,他们天生具备流畅的汉语,与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种外来政策、资源的对接有着天然优势。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则往往认为中央政府给予的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本民族的手里,这更加催生了他们的不公平感。
民间议论最多的是司法的不公。同样的犯罪,维汉之间往往会遭遇不同的判刑标准。“不管涉及哪个民族,都应该依法处理法律事件。这样的观念,提了10多年,现在大家终于都接受了。”苗普生说,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但在以前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同民族量刑不同的现象。
事实上,这一次的“7·5”事件处理过程中,当地政府被各方认为最为进步的措施就是法律的归法律。事发后没几天,整个乌市大街小巷贴得最多的一条标语是“维护法律尊严打击违法犯罪”,而不是以前遭遇此类事件后,带有强烈民族区格意味的宣传标语。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材料也被分发到几乎每一个小区。
但是,另外一个关于教育不公平感的消除,却比司法问题更复杂。双语教学一直是新疆教育领域争论不断的一个议题,新疆的学校分为两种,有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民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汉校则用汉语教学,报考大学时也分两种,“民考民”和“民考汉”,几十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游移,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分分合合。
对于民族学生来说,在高考、就业等等方面的劣势几乎都源自于语言,所以,最近几年来,民汉合校慢慢成为主流,汉语教学也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不少民族学者看来,本民族语言的被边缘化,对于民族主体性而言是一种根本上的消解,因此,对于汉语教学的抵制相当强烈。
对此,迪木拉提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是工具就有使用范围大小、使用率高低的问题,汉语的使用者有13亿,汉语的杂志、学术期刊那么多,且影响更大,自然
应该加强汉语教学。“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是支持双语教学的。”迪木拉提说。
隔阂与融合
7月26日,记者前往哈德斯家采访时,一见面,这位哈萨克老人就介绍他的小孙女:“她从小上的就是汉校,现在在天津一所名校读书,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汉语,但我要求她们这一代不仅要学习哈萨克语,还要掌握汉语、英语和俄语。”
哈德斯曾任阿勒泰地区专员,阿勒泰是哈萨克自治区,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共十三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称得上是哈萨克族人在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于自己的民族,哈德斯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一个世居边疆的草原民族,只有以开放的心态,面向整个国家和世界,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但对于普通的少数民族而言,面对强势的汉族文明,真正的融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阿勒泰采访期间,记者认识了一个哈萨克朋友。他在市政府工作,是个主任科员,他的父母仍然在阿尔泰山的草场里放牧,而他那个聪明的小女儿,从小就被送去了汉语学校,放学后再送去英语培训班上课,只有回到自己家中,见到母亲时,才会讲起他们的哈萨克语。
对他们来说,要想在汉族占据绝对主流的国家获得上升通道,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他希望女儿将来能去北京、甚至美国读书。
而他那些哈萨克族朋友,也有人去了哈萨克斯坦,再也没有回来。事实上,1991年哈萨克斯坦脱离苏联,独立建国以来,一直在广泛招募哈萨克人建设国家,俄罗斯的哈萨克、蒙古的哈萨克和中国的哈萨克人都有应召回去的。一族一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虽然在现实的国际关系实践中难以实现,但不可否认,千百年来,对于族群的认同,却是人类心灵深处最深刻的情感。
“7·5”之后,新疆的民族政策将会迎来怎样的调整,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苗普生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文化宣传教育上应该全面强调共性,培育国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他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的态度。
但在迪木拉提看来,国民意识的培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矛盾,一个政府,首先要保证国家统一,这就必须将国家意识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但同时还要保证各个地区的平衡发展、平等发展,而文化自有其发展规律,适应现代社会的元素必定会发扬,反之则会被自行淘汰。
哈德斯对此更是有着深切的体验,早在1980年代,他担任阿勒泰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就千方百计希望改变哈萨克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别人都说要保持游牧文明,可是看到哈萨克族的孩子们常年跟着父母游荡在草原上,没有办法读书,提高文化素质,这样的民族怎么会有未来?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告别。”
最终,他于1987年,争取到了一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援助,在阿勒泰草原开展了一项名为“2817”的定居工程计划,这一计划也彻底地改变了哈萨克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今,当年的茫茫戈壁早已经变成了3万多公顷的绿洲。
新疆的未来
事实上,民族矛盾不独中国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无论政体,为了消化民族矛盾,都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谓的民族同化就是少数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几个成功的例子,相反,经常导致更加剧烈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哪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边境线,而且,比邻的都是拥有丰富资源、辽阔疆土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与远赴非洲做生意的风险和艰辛相比,跟中亚邻国的生意显然更加便利,这些都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足够的缓冲。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几乎所有的战略观察家都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让恐怖与反恐成为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7·5”事件之后半个月,中央政府迅速调拨了40亿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项目的建设,据新疆发改委透露,40亿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区文化室、兴边富民工程、贫困乡村生产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乡镇干部周转用房等7个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众的专项规划。此次暴力事件的歹徒大多来自于南疆各地,一直以来南疆三地州都是新疆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
但在哈德斯看来,安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新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黄金等自然资源,近年来,资源开发如火如荼。但是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当地民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资源都在新疆境内,应该先让新疆人享受到开发的好处,矿区所在地的就业、教育等等方面都应该得到财政上的优先照顾。”哈德斯说,但在照顾原住民利益过程中,绝不能按照民族来区分'不管是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所有的族群都应该被一视同仁,而不是谁闹得凶就给谁更多的好处。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治理思路,在西北边疆内部紧张局面的缓和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是显然靠此一招已经不够用。追求怎样的发展?发展如何真正惠及民众,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命题,在西北边疆显得尤为紧迫。从某种程度上讲,新疆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交织,能否在民族问题剧烈爆发前,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关乎新疆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
作为哈萨克族人的领导者,哈德斯曾不止一次前往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在他看来,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中国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无论是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服装、食品等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科学、教育的发展,哈萨克斯坦都与中国差距巨大,但是,他们也有比我国做得好的,那就是社会保障程度,在哈萨克斯坦,每一个国民,即使是农民,只要到了退休年龄,都会得到国家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读书、看病都是免费的。”
自古以来,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强大,都是消除边患最大的保障。今天也不例外,强大而开放的中国保障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相较于中亚各个邻国,中国工业化、商业化的高度发达,让中国的西北边境到目前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的优势地位。这些因素注定了新疆的分裂主义难成气候,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求解的时候,否则,随着邻国的强大和崛起,内外因素将使西北边疆再次陷入复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