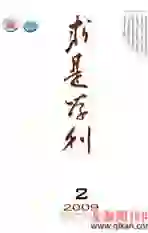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2009-04-13李德锋
摘要: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词:唐顺之;《两晋解疑》;《两汉解疑》
作者简介: 李德锋(1980—),男,安徽萧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139-06收稿日期:2008-08-05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江苏武进人,明嘉靖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入“南中王门学案”,作为明代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予以记述。于明代史学而言,唐顺之一生治学勤恳,著作颇丰。除《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儒编》、《稗编》等所谓“六编”外,亦有《广右战功录》、《左氏始末》、《策海正传》、《精选〈史记〉、〈汉书〉》、《两晋解疑》、《两汉解疑》等,共达数百卷之多。其中两部《解疑》是唐顺之的史论著作。今笔者试论之,庶几有裨于对明代中叶史学与思想的认识。
一、两部《解疑》史学思想的表现
两部《解疑》的卷帙均不大,其中《两汉解疑》二卷,《两晋解疑》一卷,“盖摘取汉、晋两代人物,论其事迹,设为问难而以己意解之”[1](《序》)。值得指出的是,两部《解疑》论述所及,并不仅仅以汉、晋的时限为断,而是在分析评议汉、晋人物或事件时,积极联系历史上其他时代相类似的人或事进行分析比较。如《两晋解疑》“贾充”条,就兼论宋代秦桧和五代时期冯道。《两汉解疑》的“韩生”条,也兼论宋金时期的兀术受困之事。如是,则更加凸显它们的史论色彩及史学思想。
历史上对两部《解疑》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持批评意见最典型的代表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四库馆臣,他们认为:《两汉解疑》“摘两汉人物论其行事,设为问难,而以己意解之,大抵好为异同,务与前人相左。如以纪信之代死为不足训,以汉高之斩丁公为悖恩欺世之类,皆乖平允,不足为训也”。同时,还认为《两晋解疑》除与《两汉解疑》同样悖谬外,更因它所涉及的是晋朝这一民族矛盾和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而对其的抨击尤为激烈,称其“持论与所作《两汉解疑》相类而乖舛尤多。如贾充一条称秦桧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终;冯道和蔼温柔,故有长乐老子之荣,悖理殊甚”[2](卷90)。
与批判意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张,评价历史就当各出心裁,不应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由此认为唐顺之的评论是合乎情理的,并褒扬道:“譬诸老吏断狱,准情酌理,均能抉擿其微,剖析至当,即起古人于九原而问之,恐亦莫可置喙。顾或以其驱骋词锋,好与古人立异为讥者,殊不知论古之作本宜各出心裁,若第知人云亦云,又何贵此操觚者哉!”[1](《序》)
上述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论都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两部《解疑》中所蕴涵的“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这里的“己意”在一定程度上是游离于古代主流意识形态束缚之外的,是唐顺之在明中叶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①。综观两部《解疑》,它们对传统史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评价历史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国家统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三个大方面。
“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在一定程度上有突破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具体则体现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不以理学伦理观念的是非为是非,从强调历史活动的目的到关注历史活动的结果,即以强调历史行为的“事功”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如《两晋解疑》“贾充”条认为:历代正史冠以“酷吏”、“奸臣”名号的张汤、秦桧、冯道等人所以会有“有后、善终”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均有“一善之长”的事功。“人有一善之长,犹可以享无妄之福。张汤之有后,廉清为之基也;秦桧之善终,息民之可颂也;冯道和蔼温柔,故有长乐老子之荣;胡广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寿。”[3](《贾充》)在《两汉解疑》“严尤三策五难”条中,关于“史谓(严)尤献策助桀(指王莽),亦逆贼之党耳,虽意在息兵,亦奚足贵”的道德诘问,唐顺之也是以“息争宁民”和错生当世为解的。“解曰,正不必深责严尤也。当莽之世,颂上功德者,四十八万人,汉诸侯稽首奉玺,惟恐在后,亦相与颂功德者而鲜有怨恶者,不特此也。一时大儒如孔光为王嘉所称赏者,始终成莽之事。刘歆为五经典领书集七略,而亦为莽用。杨子云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称莽功德。以是观之,莽之智诚足以欺一世而有余也,况严尤乎!使三策五难之说见于汉武之时,则足以息争宁民,即见于哀平之际,亦不失为忠臣嘉谟,何不幸而陈于王莽之朝也噫。”[4](《严尤三策五难》)由此可见,在唐顺之的历史价值观中,实实在在的善的结果,其历史价值远远要超过了善的目的。
唐顺之重视历史人物评价的“事功”标准,就是把历史史实投放到历史的“时”与“势”背景下加以考索,即“论人者当衡其时事,不可执己见以相绳也”[4](《李固杜乔》)。在《两晋解疑》“羊祜劝伐吴”条中,针对苏颍滨指责羊祜积极建言灭吴之计而终致晋朝灭亡之事,唐顺之解释为:“智者能见理而不能见事。苏之责祜,于理是矣。使晋世有贤君,励精图治,平吴之后,君明臣良,复有何虑?若晋无人,而吴立令主,安见长江之险,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时而灭之,以大一统之业,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谓当劳圣虑,正劝之以保治之道也。励志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岂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机不可失,晏安不可怀,羊祜之言是也。”[3](《羊祜劝伐吴》)这段话表明,唐顺之立足于权衡晋、吴双方政治修为所导致的力量变化以及时势的发展,肯定了羊祜所劝是合乎“时”、“势”的正确选择。在其后的“杜预”条中唐顺之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时”、“势”观,认为杜预作为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必定能够认识到“附会太子之短丧”所需承担的道德风险,之所以不可为而为之,实为“盖当晋新承汉祚,人情汹扰,吴蜀未平,正拮据不遑之时也。使谅阴不言,置国事于不问,吴蜀之境,其孰与底定哉”的时势所迫。至于司马温公对杜预的指责则是从“谈理道者,不倖功以顺非”的名教立场出发,“温公故深责之,以扶名教于万世也”[3](《杜预》)。可见,唐顺之坚持从杜预和司马光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去分析二者间产生差异的原因。这种多角度分析本身也是唐顺之不离事以言理的时势观的反映。
与当时主流史学更多地从道德的视阈对历史予以价值的判定不同,唐顺之从客观史实所处的“时”、“势”出发,强调历史活动的历史性,从而对同一历史现象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如在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的认识方面,唐顺之认为皇帝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一个皇朝的存在是包括君臣在内的多方力量运作的结果。对此,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唐顺之对晋惠帝的记述。晋惠帝在历代史学中都是以“戆”著称的,其中最为人说道的有两件事:一为问蛙鸣为公为私;一为问人饿死何不食肉糜。但晋惠帝也做了一些令人称道的事。如侍中稽绍在护卫晋惠帝时,血溅帝衣,左右欲为帝洗除身上血迹,晋惠帝为了表彰稽绍的忠心,更为了讥讽百官的临阵脱逃,拒绝洗除身上稽绍的血迹,而这显然与其一贯的“戆”形象相左。如何评价这些呢?对此,唐顺之从“见举朝人士,皆图自私”和“惜政出多门,权不由己”的时势出发,认为晋惠帝是“以戆自晦。至稽绍之血,则义感于中,不能自已,曰稽侍中血不可浣,见当年百官散去者,死有余辜矣。其知重贤臣也如是”。由此,进一步引发出对国家统治的思考:“苟得伊周之臣,以为之辅,则晋祚安如磐石也。何也?戆者不知为善,亦不知为恶,浑浑默默,寂然无为,较刚愎自用,残暴嗜杀者,不犹愈乎。惜晋庭无人,骨肉惨毒,自取灭亡,与惠帝何尤?”[3](《晋惠帝》)
唐顺之对皇朝统治的深刻认识同样也反映在其民族观上。唐顺之虽然也承认华夷之分,但其判断标准并不是脱离时势的种族秉性,而是“惟以才德为尚”和“气运使然”的文化认可。他认为:“所谓族类者,非必以华夷为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犬马不与我同类也。至于人久居中国,有何华夷之分,惟以才德为尚耳。(刘)渊以文武全才,久冒刘姓,生长中华,其贤不贤,当与中国等伦可也。如金日为汉贤相,岂不美乎,奚必以族类而出之哉?族类之辨,春秋之防微也。如止以华夷论,帝王之胄,流于蛮夷者,不可胜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伤为圣帝明王哉?如五胡之乱,亦气运使然耳,渊即不帅五胡,宁不乱哉?如必曰中华之人,则同类也,操、莽辈岂皆夷乎?”[3](《刘渊》)其中的“气运使然”也即时势观的体现,西晋之亡不在“五胡”,而在其政,在其政所致之“气运”。在这里,唐顺之的时势观和民族观是交相融会的,而其“惟以才德为尚”,不以血缘论夷夏的民族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对于史实理解的误差,唐顺之除运用建立在“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上的事功观、时势观、民族观等认识加以处理外,还意识到春秋笔法于其中的影响。如在《两汉解疑·彭城围》一节中,唐顺之就史书中关于项羽以三万精兵破五十六万汉兵并围汉兵三匝的记载提出疑义,并且认为造成以上疑惑的原因除了汉统治者的虚伪外,春秋笔法于其中的运用也是一个因素。“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汉以来,惟恃权谋兵力而已。汉□为义帝发丧,岂真尊王哉?亦诸臣假大义之权谋也。天下其谁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真情流露矣,故五十万人解体而俟之。平勃辈亦相与共为逸乐,初不计项羽之来,故一败而几不可支。史氏恶之,故侈陈其兵之多,而乐书其败之速云尔。迨其后,楚失之而汉得之,何也?汉犹知假仁义,楚惟有杀戮也,此得失之机也。至律以春秋之义则可断之曰:汉刘季谲而不正,项羽正而不谲。”[4](《彭城围》)在《两汉解疑》“赵壁夺符”条中唐顺之更认识到春秋笔法与客观史实的差距。“作史者欲神人之功,则必神其事以夸之;欲抑人之能,则必易其事而卑之。”[4](《赵壁夺符》)即撰史者的夸饰影响到史实的处理。
二、关于两部《解疑》史学思想产生原因的分析
两部《解疑》史学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唐顺之主要生活于明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正德、嘉靖时期,这一时期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政治腐败和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导致的思想活跃,影响整个明代后期的王阳明心学,正是从这一时期盛行全国。而王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个体的肯定。可以说,唐顺之的两部《解疑》“以己意解之”的历史评价就深深地植根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
于此,我们必须面对两部《解疑》的成书时间这一问题。因为唐顺之的性格和学术思想都经过多次变化,因此确定两部《解疑》处于其为学的哪一阶段是我们从何种角度入手来分析其史学思想产生原因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史料的阙如,两部《解疑》的具体纂写时间已无从稽考。关于这一命题,只有民国时人唐鼎元在《明唐荆川先生年谱》中论及两部《解疑》是唐顺之青年时代的游戏之作。“公素不祈以文传世。《两汉解疑》、《两晋解疑》等文当是窗下游戏之作,然名高之士下笔即为人传钞,杜甫之恶诗与我公此类文字皆偶然下笔为人传钞,虽欲收回而不可得者也。”[5](《两晋解疑》)考虑到唐鼎元是为护惜先辈,驳四库馆臣之论,因此它的说服力也是大打折扣的。这就迫使我们从性格和思想的角度来分析两部《解疑》史学思想产生原因时,必须兼顾到唐顺之学术思想以及性格于不同阶段的变化对其史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性格上来看,依照唐鼎元的“早期说”,我们可以找到两部《解疑》史学思想的立论根据。唐顺之早期就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苟同于社会主流,“早岁狷介孑特,有怀公谓为不近人情”[6](卷6)。这一点从其坎坷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亦可得到验证,如在他二十三岁廷试时,他就以“年少筮仕,守己当严”为借口而严拒主考官有利于其仕途发展、“欲首擢之”的私下之请[7](卷114)。二十七岁时又因校历朝《实录》而获得一次升迁的机会,但因避时相张璁偏爱之嫌而告归,致使其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叙用[8](卷205)。从唐顺之对这两件与其仕途攸关的事情的处理态度上,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其性格上“不近人情”的一面,这也为两部《解疑》“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提供了性格方面的注脚。
其次,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分析,其中最为直接和最具影响的就是有着深刻王学背景的“本色论”。唐顺之的“本色论”认为文章虽然也讲求外在的技巧,但文章的真正精髓则要求作者摆脱世俗的羁绊,保持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独特见解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绷缚龈龊,涡卷累赎,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9](卷7,《答茅鹿门知县》)唐顺之不仅主张以“真精神”、“直据胸臆,信手写出”本色之文,而且还致力于对“真”的追求,“言也,宁触乎人而不肯遗乎心;貌也,宁野于文而不色乎庄”[9](卷5,《与两湖书》)。正是唐顺之于思想上能够“洗涤心源,独立物表”,才会写出两部《解疑》中那些“出奇胜人”的文章。
但这一立论的前提是唐顺之已发生了由程朱理学向王学的思想转变,因此也存在着一定的两部《解疑》产生于唐顺之晚岁的理论诱导倾向,因为唐顺之比较集中地接触和研习王学大致在四十岁以后。唐顺之曾自言:“仆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谓有志于学也。自年近四十,则心益苦,盖尝参之闭门静坐之中,参之应接纷扰之中,参来参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虽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隐约之间若或有一罅之见焉,则亦不敢自昧也。”[9](卷6,《与聂双江司马》)唐鼎元更是把唐顺之一生学术思想演变概括为:“公二十以前专精制艺之文,故负海内盛名,为场屋圭臬。三十左右为诗古文辞,甲兵、钱谷、象纬、历算、击剑、挽强,无不习之。四十以后,专研理学。”[6](卷6)这里的“理学”多就王阳明心学而言。唐顺之在二十岁以前热衷于科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此时的科考指导思想是程朱理学,因此其学术思想是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此时的程朱理学生存的时代背景,即明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自身的理论缺陷并对它经过一定的改造,以外在“天理”压抑了个体道德践履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道德修养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失去了其初始存在的社会批判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两部《解疑》“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断难从已经官方化的程朱理学中吸取到营养。而王学则把外在天理融入主体之心,消解了外在天理对主体的压迫,赋予主体无比的自主性,从而使个体性的“吾心”成为历史判断、评价的根本依据。显然,唐顺之“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深受其四十以后所集中研习和体悟的王学的影响。因此,我们从唐顺之王学思想的高度来探讨两部《解疑》史学思想的产生原因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两部《解疑》的“晚期说”。
即便两部《解疑》产生于其晚岁,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其早期性格对两部《解疑》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随着唐顺之社会历练和学术素养的积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正如巡抚舒汀向朝廷推荐他时所称:“学以圣学为本,道以经济自期,立朝著謇谔正直之风,居乡有廉静无求之节。”[6](卷2)左东岭先生更是把此性格转向归结为“由气节到中行”①,但在深具王学背景“本色论”的鼓动下,唐顺之依然保有早期独立的人格和不同于世俗的性格色彩,于晚岁也并未改变其早期的行事风格。如关于其“晚岁之出”就是在冒着攀附严嵩党羽的压力、力排众议的背景下而毅然作出的决定,以至左东岭先生对此事进行分析时,也不得不跳过王学思想的羁绊而归为其“勇于自信的性格”[10](P474)。“尽管他通过阳明心学的悟解而使自我有了更为通达的心胸,在一定程度改变了早年往往意气用事的气节之士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丧失起码的做人原则。”[10](P477)对于“以己意解之”撰述旨趣的形成上,唐顺之的早期性格应存在相似的功用。
同时,忽略时代背景和性格方面的多重因素,单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失之片面的,如关于对秦桧的评价,我们无论是从王学或是从程朱理学的立场来分析,并不能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功者直以为有功,颂者世人有是颂耳。孰颂之秦桧?同时有孙觌辈,前乎荆川数十年有琼山丘濬。是数子者,皆以秦桧为有息民之可颂也……朱子尝云秦会(桧)之也有才。”[5](《两晋解疑》)从朱子、丘濬等程朱理学家对秦桧有“息民之功”和“有才”的肯定态度,我们更能看出偶然因素(性格)对必然逻辑(学术思想)的影响。
总之,正是明中后期关注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与唐顺之性格上的“狷介孑特”、学术思想上的“本色说”相桴鼓,从而造就两部《解疑》“以己意解之”的撰述旨趣,而不是某一因素的片面结果。
三、两部《解疑》史学思想的影响
两部《解疑》中对明中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在唐顺之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体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左编》。从四库馆臣对该著作“殆与李贽之《藏书》狂诞相等”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顺之《左编》对“时代抗议精神”的表达。“是书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纂集成编,别立义例,分君、相、名臣、谋臣、后、公主、戚、储、宗、宦、幸、奸、篡、乱、莽、镇、夷、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凡二十四门。其意欲取千古兴衰治乱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故其体与他史稍异,然其间详略去取,实有不可解者。如君纪只列汉、唐、宋三朝,偏安者皆不得与,而隗嚣、公孙述、李筠、李重进诸人乃反附入。于列代宦官、酷吏叙之极详,固将以垂鉴戒,而唐之杨复恭、来俊臣、周兴等,尤为元恶巨憝,乃反见遗。又以房琯为中兴之相,高骈为平乱之将,褒贬既已失平;以纥石烈为人名,姓氏几于莫辨。其他妄为升降,颠倒乖错之处,不可胜言。殆与李贽之《藏书》狂诞相等,乃贽书多相诟病,而是编独未有纠其失者,殆震于顺之之名,不敢轻议欤。”[2](卷65)同样,从“其意欲取千古兴衰治乱之大者”、“ 固将以垂鉴戒”等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左编》的编纂是为了有利于现实借鉴,对此,唐顺之亦坦言:“《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11](《荆川先生自序》)
并且与对“时代抗议精神”表达这一特点相比较,《左编》带有对现实的忧虑、为现实寻求历史借鉴的特点更为鲜明,这就使此著作所呈现的“己意”必然要和现实主流意识相妥协,不能一味张扬下去。当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在《左编》中亦予以运用。显然,处于明朝中期的唐顺之并没有十分恰当地处理好事功和道德这两套历史评判标准的共存状态,其生硬掺杂之处随处可见。如唐顺之关于冯道、秦桧的评价,在文章的前半段,都是在叙述冯道、秦桧的“和蔼温柔”和“息民之功”,这与两部《解疑》的观点是一致的;后半段则取喻于妇人之尚知羞耻而对冯道大加讥讽,并给以合乎时风的道德判断。唐鼎元也注意到这一矛盾现象:“荆川《左编·秦桧传》于桧前半截之美者,如辞附张邦昌为割地使,如金入请立赵氏状,仅隐括数语而削其词,而搜罗桧之恶迹则较《宋史》桧传为详。”①虽服务于不尽相同的撰述目的,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等思想直接作用于《左编》则是有目共睹的。
与两部《解疑》相比,虽然《左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这一撰述旨趣体现得并非十分突出,但在明中后期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和激化,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以应对现实问题的史学经世思潮也逐渐兴盛起来,而《左编》“为治法而纂”的撰述旨趣迎合了这一思潮,因此得以大量刊布,明人吴用先论曰:“嗟乎!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经世之学少而经生多,则《左编》者,何可一日不置之座右哉!”[5](《史纂左编》)正是由于《左编》的大量刊布和其中所蕴藏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这一特点,引起了李贽的强烈关注,他在编纂《藏书》时就直接地参考了《左编》,这种关系早于明朝就引起了注意。明人陈懿典论曰:“然《左编》有义例而无议论,《藏书》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骘。”[12](卷首,《天佚草堂史书纂略序》)又“李愚公曰宏甫之有《藏书》,以《左编》为之稿也”[5](《文编》)。但与《左编》相比较,《藏书》的反传统史论色彩确实更加浓厚,不存在前后的矛盾,是一以贯之的,这与两部《解疑》的史论色彩是非常相似。如在关于冯道的评价中,《藏书》也充分肯定了冯道的“安民”的事功。“卓吾曰,冯道自谓长乐老子,盖真长乐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13](卷68,《冯道》)这不免使我们作一推断:两部《解疑》在撰述旨趣上直接影响了《藏书》之立旨,从而成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之“椎轮”和“积水”②。
正是由于两部《解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令它们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如处于清皇朝统治末期、主张变法的洋务大臣张之洞,在经历了清朝日趋衰败,列强觊觎的现实境况后,在编写《书目答问补正》时亦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现实的反思和忧患,盖两部《解疑》也因此而进入张之洞的视阈。张之洞一反四库馆臣的正统认识,在所选不多的几部史评著作中,赫然将原四库馆臣摈之于“存目”中的两部《解疑》,分别列于“史评”类“论史事”条之下,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史论最忌空谈苛论,略举博通者数种。”[14](P142)同样,民国吴佩孚、柳诒徵等人也是在“(日人)卒起而攘我东北三省,旋又进窥淞沪”[6](《序一》)、“列强环伺”[6](《序四》)的时代背景下而关注唐顺之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唐顺之两部《解疑》对于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其对中国史学突破传统的认识框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值得我们重新重视和深入发掘。
参 考 文 献
[1]唐顺之. 两汉解疑[M]. 光绪十一年(1885)山阴宋氏忏花盦刻本.
[2]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唐顺之. 两晋解疑[M]. 丛书集成初编本.
[4]唐顺之. 两汉解疑[M]. 丛书集成初编本.
[5]唐鼎元. 荆川先生著述考[M]. 民国铅刻本.
[6]唐鼎元. 明唐荆川先生年谱[M]. 民国二十八年(1939)武进唐氏刻本.
[7]傅维麟. 明书[M].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诚堂本.
[8]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唐顺之. 荆川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本.
[10]左东岭.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唐顺之. 历代史纂左编[M]. 明嘉靖四十年(1561)胡宗宪刻本.
[12]马维铭. 史书纂略[M].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
[13]李贽. 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张之洞,范希增. 书目答问补正[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雪萍]
View of Historiography of TANG Shun-zhis two Jie Yi
LI De-feng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to the two books entitled Jie Yi by TANG Shun-zhi, which should be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radical social changes after mid-Ming Dynasty by TANG with great consideration. Its evalua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situa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officials, profound realiza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positive reflection on narrative features represented by Spring and Autumn contribute to a breakthrough of mainstream ideology represented by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books lies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cademic character and thought as well as a combination of all the factors.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them influences directly TANG Shun-zhis Zuo Bian, which in turn leaves trace on LI Zhis Cang Shu concerning some historical comment. In this sense, it ushers in the social critical thought in the wave of enlightenment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Key words:TANG Shun-zhi;Liang Jin Jie Yi; Liang Han Jie 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