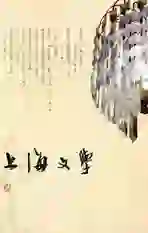点火
2009-01-12孙未
孙 未
星期二,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下班高峰已经过去。五个内部会议,两次国际电话,加上跟三个不得力的下属谈话,这些垃圾在他脑袋里晃荡。他的车钥匙在丰田的仪表盘前晃荡。他的胃在空空如也的腹腔里晃荡。
从恒隆回虹桥,遍地是餐厅的霓虹灯,他庆幸可以漠视它们的喧哗,肚子是空的,脑袋里却实在装不下更多东西了。他开进地下停车场,熄了火。在电梯里他听到胃响了一声,很清晰。他抻了一下西装的前襟,略微抬起下巴,然后他扭过头,尽量不看镜子里的自己。
他让自己想那些饺子。她在厨房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偷偷走进去看。速冻饺子扔进开水里,每个都会引起小小的巨响,她扔一个就缩一下手。这让他想起儿时过春节,点小鞭炮,每扔出一个,就飞快往后躲。也许今晚还有番茄炒蛋,他记得昨晚下楼拿啤酒,看见冰箱里除了新买的牛奶,还有两只番茄,包在贴着标价的保鲜膜里。
推开门,复式公寓。底楼厨房的灯亮着,客厅却暗着,电视也没有开。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套装别扭地裹在身上,手提包和她挤在一起。
她睁开眼,有些惊恐地辨认他。很快彻底醒了,坐起来,揉着头发说:“煤气灶坏了。”
“怎么会的?”他把肩上的皮包扔在地上,自己也坐到沙发上。
“回来就这样了,光点火,就是烧不起来。”
“怎么会的?”他皱起眉毛,只是皱起眉毛而已。
她推了他一把:“你去看看呀。”
他慢吞吞站起来,左右看了一下,迷失方向一样。她拉着他往厨房走,走到煤气灶边,她往后退,倚在微波炉边看着他。他伸出手指,犹豫地捏住旋钮,没扭动。
“按下去再转,对,就是像这样。”她看着他。
旋钮在他手里发出清脆的一响,火星闪了,又灭了,围着圈的蓝色火苗没有蹿起来。又试了一遍。第三遍时,他用了一点力。还是只有火星。
“哪里出了问题?”她问他。
他忽然有些恼火,为什么要问他?“我怎么知道!”他硬邦邦地说。他还站在煤气灶前,上下打量,沉思了一番。他克制自己没有再试,他觉得在她面前怎么也点不上火,是件丢脸的事情。
他走出厨房,打开客厅的灯,顺着墙在找什么。她跟在他背后。他摸到楼梯下的一个门把手,用力,矮门开了,一股铁锈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是个储藏柜。柜子里横着煤气开关,紧贴管道,下方是一只新秀丽中号行李箱,墨绿色,顶部都是开关落下的锈屑。他骂骂咧咧,抓起箱子的把手,单手拉出来,面朝下扔在地上。
她忽然觉得,是她被他提起头发,拉出来,扔出门去。而且完全不顾她摔得很难看。
怎么会忘了有这个柜子呢?她问自己,真是件奇怪的事情,何况那还是她的箱子,她自己放进去的。搬来这里的前两个月,这只箱子放在楼上的衣帽间,那里足够大。后来不知怎的就找到这个柜子,放进这里。然后她就忘了,连同这个柜子。她每周还打扫整套公寓来着。
扔出箱子,他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扳动开关了。两手抓住红色圆环,憋足一口气,往左。开关松动了。“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厨房试!”他喊她。
她板着脸走去厨房。
他往左拧到不能再动的位置,说:“好了,点吧。”
“还是不行。”她的声音传过来。
他向右拧到不能再动的位置,说:“再试一下?”
“点不着!”
“好吧。”他在腿上擦了擦手,意识到这是西装裤,低骂一声,往卫生间去。“看来不是总开关的问题。”他自言自语。本来就不可能是总开关的问题,她总不见得每天半夜起床关上那个吧?他只是想显得自己在做什么。
等她从厨房出来,看见柜子的门依然开着,箱子还躺在地上。他从卫生间出来,拿着毛巾擦手。看见她,他耸耸肩说:“我真的没办法了。”
她说:“总得想办法修好吧?”
“我没办法了。”他把脱下的西装外套扔在沙发座椅上,呼出一口气,重重坐下,占了沙发的另一侧。
她饿了,下班前就饿了。靠在沙发上睡着前,她就是打算在厨房弄些什么吃的,结果点不上火,好像这套公寓不再回应她的需要。现在她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她抱着胳膊,叉开两条腿站在他面前,裙子勒着她的大腿,套装外套勒着她的背。她提高嗓门说:“你坐在我的手提包上了。”
他抬了抬眼皮,用一只手把靠在背后的手提包挖出来,没有收起西装,没有给她留出并排坐下的地方。她打算就这么站着,在他没有给她留出地方之前,她不会替他收拾起西装,主动坐在他身边。
“我们得把煤气灶修好!”她这么宣布,站着没动。他拿起遥控器,信号也许是穿过了她的胳肢窝,或者大腿中间,总之,电视在她背后亮起来了。
她又站得离他近了一步:“你听见没有,我们得把煤气灶修好!”她感觉到电视频道在她背后飞快地转换。随着她在他面前移动,他的脖子向左、向右,绕开她的遮挡,只有这些细小的动作证明她不是透明的。
“你不打算修了是不是?让它这么坏着?永远这么坏着?”她觉得脑袋里有个螺丝卡住了,齿轮转不过去,正在一次次撞,朝一个方向撞。
“我说,给我做点吃的好吗?我快饿死了。”他终于说话了。他语气温和而恳切,假装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怎么做?煤气灶坏了!”齿轮还卡在那个地方。
“也许,可以用微波炉什么的?”
“我没这个本事。”
他叹了口气。她看到他叹了口气,抢着说:“所以要把煤气灶修好呀!”
他说:“不谈这个了,我们出去吃吧。我饿得血糖都低了。”他是个离过婚的男人,知道跟女人讨论问题,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他关上电视,飞快地站起来,穿上西装,从皮包里拿出钱包和钥匙。他看见她还站着不动,两手从背后揽住她僵硬的肩膀,推着她走。
关上客厅的吊灯之前,她指着那盏灯说:“吊灯也坏了,跟你说了不知多少次了,你就是不管。”是一盏花瓣形状的古铜色吊灯,六片花瓣里镶着六个灯泡,两个灯泡不再亮了。
“让它去吧,反正坏了也没什么影响。”
他关上灯,打开房门前,她又抢先说:“门链也坏了。”从几个月前,他们就不用先打开门链,再开房门了。她曾经很喜欢这条黄铜门链,像古老的旅店那样。
“我说过了。让它去,反正没什么影响。”他有些不耐烦。
他让她走在前面,自己走在后面,以免她又生出什么枝节来。在之前很长一段日子里,都是他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典型中国式的老夫老妻。今天这么一来,她感觉好像他正在送她出门,像两个礼貌而生疏的人。
车绕过公寓门前,开上另一条岔路。没等她开口,就选定了一家餐厅,停车。
这是一家新开没多久的餐厅。门口的花篮凋谢了大半。水族箱里没几条鱼。簇新的领位台,四个穿着高领旗袍的年轻女人,开衩到腿根,互相说笑嬉闹着。
他翻了翻菜单,递给她。当班经理马上转到她身边,手上拿着点菜卡纸,问:“今晚想吃点什么,姐?”
她被这甜腻的男声叫得有点难受,手在菜单上翻不动了。经理是个小巧的男人,头发乱蓬蓬的,白衬衣的领子里露出微凸的锁骨。细眉小眼,眼睛不安地左顾右盼,看见她侧过脸来,他刻意摆出一脸热忱。
“你们做的是什么菜式?”她问。
“姐,我们这儿是正宗的本帮菜,不过您爱吃湘菜、川菜、杭州菜、东北菜什么的,我们这儿也都能做。”他的脖子随着说话左右扭动,好像每说一句都是用了真正的力气。
她只能故意不看他,低头看菜单,“太晚了,我们就吃一点点心。”她把菜单翻到最后一页,“菜肉大馄饨……”
“馄饨,今天已经卖完了。”
“雪菜肉丝面……”
“面也没有了,姐,您看要不要来一斤虾?”
她有点恨这个经理,奸诈都写在脸上。她宁愿面对冰冻的饺子,出了办公室,她不再想跟任何人用脑子。她喜欢煤气灶上蓝色火苗的呼之即来,当然这是今天以前的事情。她喜欢饺子扔进开水里那一声热烈的响。她喜欢他埋头吃饺子的样子,她喂饱了他,他满意甚至有点感激地推开盘子,陷进沙发看电视。
他坐在对面打断了他们,“算了,我来点吧。”她看着他把菜单拿过去,经理立刻转到对面去,弯腰躬背地,做好记录的姿势。
他指着菜单一个个往下点:“糟黄鱼、南瓜百合、糖糯莲藕、鸭舌头。”
他停顿了一下。“四个凉菜呐,先生。”经理扭头瞟了她一眼,眉毛动了动。她觉得这是示威的表现。
“红烧肉、油焖笋……”
“我们吃得了那么多吗?”这次是她打断了他。她瞪着他,指甲在桌布上划来划去。
他抬起眼睛,完全不理解她为什么生气。他很温和地对她说:“平时每天饺子饺子的,今天正好有机会吃得好一点。我可是真的饿坏了。”
“你们要不要来条鱼?活的鱼?”
“你刚才说你们还有虾?”他合拢两只手掌,居然也很温和地对经理说话。
“是……当然。”
“可是我看不出来这儿哪里养着虾呀?”他从鼻孔里笑了一声。
“您放心,只要您想吃虾,我们就能办妥,一定是最新鲜的。”
“那好吧,油爆虾,半斤就够了。快点。”
经理走了,桌上忽然静下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把手指交叉起来,捏紧,又松开。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她看着他。他从报架上挑了两本报纸走回来,坐下翻看。她也站起来,朝报架走去,上下打量。小格里插着很多广告明信片,她咬着指甲,随手抽了五六张,走回位子。
她把其中一张一直推到他眼睛下,盖住他正看的某块报纸。明信片上印着四季酒店的标志。“你看,我要不要去上个厨艺班?”她问,她觉得自己的语调听上去像是在挖苦他。
他没抬头,喉咙里发出两个音节:“不用。”
“你刚才不是说,每天饺子饺子的,想吃得好一点?”她压低了声音,弓起背,手指敲了敲他面前的报纸,“你不喜欢吃,完全可以早说!”
“我没说。”他抬起头,目光有点茫然,随即
改口说:“是的,可以吃得好一点。你不用自己做,可以请个保姆嘛。”
“保姆?”她瞪着他,他又把脑袋沉到报纸里。
“嘿!”她说,“你请还是我请?挑一个合适的保姆有多麻烦,管理一个人有多麻烦,尤其是没文化的,你知道吗?”
他知道,可是他说:“有什么麻烦的?你在公司不是管着十几号人吗,你学的又是工商管理,把这套用在保姆身上还不是绰绰有余?”
“买菜你也让她去吗?”
“挺好的。”
“她买了不干净的原料,或者乱算钱呢?”
“你就让她去嘛。”
“保姆什么时候来?我们下班都没个准,至少,谁给她开门?”
“你把钥匙交给她嘛。”他依然在看报,声音轻飘飘的,像梦话。
“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能放心吗?”
“我无所谓。”
她觉得有什么噎在喉咙里,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一口气,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中止了,或许他根本忘了她坐在对面。她又深吸了一口气,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像在办公室跟下属开会时那样:
“我想过了。我不喜欢保姆。我不喜欢公寓里有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我不喜欢下班了还要跟保姆斗智斗勇。我不喜欢把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
他没有反应。
“再说,我们怎么请保姆呢?我们的煤气灶是坏的。”
他依然无动于衷。
“你听见没有!我们得先把煤气灶修好!”她觉得那个齿轮在太阳穴上来回敲击,就是转不过去。
“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他猛地一挥手。刚才有什么碰在手背上,他猜想是她拿着明信片敲他的手背,其实只是一本报纸的角落被风吹起来。他的手碰倒了茶水。她抱着手提包跳起来。他也迅速地站起来,拎着湿淋淋的报纸。
这时候,菜上来了。传菜员端着托盘站在一边。经理忙乱地擦着桌椅上的水,敏捷而滑稽。拖把碰到了她的丝袜,她没有生气,还有什么可以让她生气呢。
冷盆看上去蜡块一样,吃到嘴里,她才明白自己饿了。过一会,热腾腾的红烧肉和油焖笋也上来了。他夹给她。他们就埋头吃着。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从北京调任上海。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同居,一个人住了两年。他们讨厌每天透过霓虹灯和玻璃,判断哪家餐厅美味公道。他们讨厌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找车位停车。还有,他们讨厌一个人坐在诺大的餐桌前,接受服务生刻意亲切的眼神。他们也讨厌参加附近办公楼的“饭搭子团”,陌生人,还总得相互说些应酬的话。然而两者他们必选其一。那时候他们还没认识。
“饭搭子团”聚得快,散得更快,人人都找到了一起吃饭的人,最后就剩下他们两个。他上班在恒隆,她在梅龙镇广场。
他们在下班前约好时间一起吃饭,去过锦亭、彩蝶轩、新元素,试过大食代里几乎每家的味道,去过江宁路附近的永和豆浆、桂林米粉、佳比馒头、老鸭粉丝,还在吴江路美食街上排队买过生煎馒头。吃得饱到不担心半夜饿,最后各付各的,分头开车回家。
后来她的办公室搬到了瑞安广场。他不想换人一起吃饭。她也不想。淮海路与南京路之间实在太堵,他建议说,可以到他和她家中间的什么地方吃饭。他住虹桥。她住南丹路。其实不远。
他们在味千拉面固定出入几个月之久。某天她收到一个邮件,她说可以把图片发给他看,太恶心了。她说,总之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他们有过更满意的据点,是一家广式茶餐厅。他们一直吃到它关门歇业的那天。他们有一阵每天到同一家湘菜馆去吃烤鱼。之后不知道是他说吃多了致癌,还是她说,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有那种味道了。他们热爱过本帮菜的红烧肉,入夏的一个阶段,两个人各自发现夏装的裤腰紧了。有家川菜馆搞了三个月的特价,麻辣鱼片三十八元一大盆。他们连吃了两个月,口舌生疮才作罢。他们很偶然地试过一家火锅店,正好是买一百送五十的活动,他们得了五十元券。又得了五十元,每次去都为了前一个五十元。终于他们放弃了第六次获得的券。
他们经常跟服务生和经理什么的吵架。有一次,肥牛锅仔里的金针菇比话梅还酸。有一次,他们眼睁睁看着上错了菜,松仁玉米那桌都吃了两筷子了,服务生又给端过来。有一次,清蒸的鱼自己改了红烧,而且咸极了,隐隐有变质的气味。每次总是一个人脾气火爆,另一个反常地温和,不是她,就是他。
她嫌他总是点菜过量。眼睛大,肚子小。晚上吃得太多没好处,影响睡眠。桌上吃不完,她又觉得浪费,还是吃得过量。除了某一回,他们去一家泰国餐厅。他点了一份美极大虾,五十八元,结果上来一个大盘子,里面孤零零六只开片油炸的基围虾。
他嫌她吃饭太挑剔。对着灯光看骨瓷碗碟,像个鉴赏家,看到一点沉淀和斑点就要求换。她从不吃起酥的点心和甜品,说是有反式脂肪酸。她总是对服务生反复地强调,你跟厨师说,不要放味精,千万不要放,我吃了以后晚上就一直想喝水,怎么喝都渴。还有,要是有服务生惹她讨厌了,这辈子都别想劝她再进这家餐厅。
现在他们又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在少许谦让之后,他们依然吃得沉默而迅速,暗自较劲,就像以前。以前的规则是,饭钱平摊,饱饿勿论,谁让谁吃亏。
她忽然有一种错觉,吃完饭以后,他们将各自打开钱包,分摊这餐的费用。然后互道晚安。他开他的丰田回去,她开她的尼桑回去,回去不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她得抽两个小时的时间,把公寓里属于她的东西塞进那只中号箱子,再打开后车盖,放进去。这设想起来并不比煮一包速冻饺子更难。这个想法让她害怕。
“真是的,我们应该尽快把煤气灶修好。”她自言自语。
“唔。”他含着一嘴食物,居然抬头应了一声。
她忘记了,以前他是好声好气跟她说话的,对一位陌生的、堪称吃饭伴侣的女士。
她放下筷子,手从耳朵后面滑过去,直到她的后脑完全支撑在手臂上。她靠了一会,她觉得累坏了。“你可不可以想想办法,想想怎么修好它?”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又细又弱,带着哭腔似的。
他放下筷子,打了个哈欠,两只手的大拇指揉着太阳穴。他说:“我都快睡着了,天哪,非得今天讨论吗?”
她点点头,又郑重地点点头。她问:“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
他们之前最后一次在外面吃饭,是在一家东北餐厅。他那天到郊区跑了个来回,累得吃不下东西。他说,吃饺子吧,快一点。她说,好,正好也想早点回去睡。
她的位置在厨房边上,扭头能看见门背后下饺子的锅。她推了推他,说,饺子不是他们自家包的,是超市里买来速冻的。饺子端上来,四五个是破的。她说,她要是自己下,肯定比这强。
他说,听说速冻饺子是所有速冻食品中最不像“尸体”的。他吃了一个,觉得味道不错。她也觉得还行。他说,不如下次你到我家下饺子得了。饺子我来买。
她到他家煮了饺子。两个人吃得又饱又安宁。她喜欢煮饺子的过程,简单有序,一切尽在掌握。虽然她有点畏惧饺子扔进开水的一刹那。她喜欢那个煤气灶,全进口的西式煤气灶,点火轻巧,架子纤细高挑,灶眼舒展,像是女人中的芭蕾舞演员。
她还喜欢他这套公寓,复式的单身公寓,楼下是厨房、客卫、高敞的客厅、液晶电视和一个靠窗的电脑桌,楼上是安逸的卧室、带浴缸的主卫和宽大明亮的衣帽间。每个家具、家电、窗帘的细节设计都非常别致,甚至包括客卫的一个毛巾架、一只装洗漱用具的分类盒。她曾经想,她幸亏有这样的机会看见他的内心世界。这个男人竟然是很有品位的,内心静谧深沉,对生活又懂得细心咀嚼。他原来并不像平时看起来那么蠢。
那个晚上,她还看见了他皱巴巴的床单、团在一起扔到衣帽间凳子下的脏衬衣、主卫地砖上的泥脚印。她忽然很心疼他,看起来他近来有些颓废,他需要有个人来关心才是。
他们的饭搭地点从此转入他的公寓。尽管两个收入都是五位数的家伙,每天晚上吃二十四元的一包饺子,这听上去有点蠢。
她下饺子,他们天亮才分手。她赶回自己公寓换装,然后才去公司。双休除外。他们从来不在双休一起吃饭,这是延续了以前办公室附近“饭搭子团”的习惯。直到有一个周六下午,他打电话来说:“我刚去了一趟家乐福,买了十四盒饺子,塞满了冰箱……你就住到我这儿来下饺子吧。”
“见鬼的煤气灶。”她又咬着指甲。
“你可以找一下煤气灶的保修厂家,上网查一查,很容易的。”他放下筷子,打了个饱嗝。他想尽快地完成什么,然后回去睡觉。
她很高兴他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她说:“这个煤气灶恐怕很难找到保修单位了,就算在国外的网站上找到了,他们也没法过来修。”
“怎么会这样的……”他皱起眉毛,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子,看上去不是焦虑,只是无聊。
“这是一只全进口的煤气灶。”她解释说。
“啊,真糟糕。要不你找物业看看?”
“物业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先生。”
“物业也不知道有我存在,我上班太早,下班太晚。”他笑笑岔开话题。
“那现在怎么办呢?”她觉得自己已经没力气再问下去。
“我们还是在外面吃吧。”他摸了摸下巴。
事实上他不喜欢自己这个建议。很长一段日子了,他们再也没有换过地点,客厅里的饺子是他们吃过的最久的东西。这段日子匀实平坦,像一条无止境的路,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让他们踩下刹车,也许会永远开下去也说不定。
“煤气灶会不会永远也修不好了?”她叹了口气。
他忽然有些辛酸,他想安慰她。
“也许……我可以问一下房东。可是,”可是他想起来了,“这套公寓是公司替我租的,我不认识房东。而且这里可能再过两个月就要到期了,然后公司会给我安排其他公寓。你知道,我太忙了,这些都是他们替我安排的。我自己没法办妥这么些麻烦事。”说完这些以后,他觉得气喘吁吁。他觉得他活得气喘吁吁,像个傻子。
传菜员端着托盘过来了,走得畏畏缩缩。经理张着嘴,做着让她快点上前来的手势。“先生,你们的菜齐了。”经理小心翼翼在桌子中间摆下一个盘子,对右侧的他笑,对左侧的她笑,笑得一张小脸都皱起来了。
盘子里金灿灿的,是干煎带鱼。
“我点的不是油爆虾吗?”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盘子在上面嗡嗡作响。
“是这样的,我们的采购员看见带鱼更新鲜,就替你们买了这种。带鱼的营养不比油爆虾差,而且这道菜是我们餐厅的特色。你们喜欢油爆虾,可以明天再过来品尝,就是要稍微早一些来,否则菜场都关门了。”经理流利地说了一大堆,脖子扭动得厉害,他说完之后,脖子还惯性地扭了几下。然后闭上嘴,眨巴着眼睛。
他站起来,没说一句话,抬手掀翻了桌子。桌布和着金灿灿的、洁白的、绛红的什么,一瞬间变成一团废墟。
回到公寓,黄铜门链还是断的,客厅吊灯的六分之二还是暗着的。反正两个月以后,他们就要离开这里。也许她会更早些。
他坐在沙发上摁着遥控器,电视频道飞快地切换,比镜头本身还快。
她问:“你要不要我去参加厨艺班?”
他的喉咙里发出几个奇怪的音节,然后从她身边站起来,到厨房倒水喝。他想走到书架那里,不小心绊到了她的箱子,发出沉闷的声响,然后膝盖又撞到了打开的柜门上。她听见他又使劲踢了什么一脚,闷响一声之后,发出畅快的喘息。
他从书架上找到了安眠药的瓶子,吞了两颗,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杯冰水。他走回沙发前,放下杯子,含糊地说了声“先睡了”,就脚步跌撞地上楼去。电视也没有关。
她坐在电视机前,酸痛的肩颈陷在沙发里,看着偶尔停下的频道。
一只大鸟在给窝里的小鸟们喂食。
两只松鼠面对面嚼着果子。
几个丛林里的族人在用树枝搭建房屋,用凿子建造水渠。
他们堆起柴火,点燃,随后围坐祈祷。
她站起身,往厨房里去。她站在黑暗里握住煤气灶的旋钮,按下去,轻轻一扭,一圈蓝色的火苗亮了起来,像节日夜空的烟花。她又一扭,火光灭了。
她沿着墙来到柜子门前,双手握住红色的圆环开关。她向左拧,感觉到开关松动了。她用尽全身力气向左,直到拧到了底,直到拧得不能再拧。再拧紧一点也没关系,反正不再需要再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