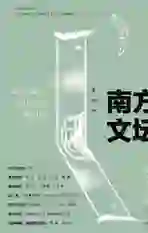反思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的拯救
2024-03-12张丽华
黄子平老师提出的“同时代人”概念出自阿甘本。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通常从字面引起的联想——作为代际关系的“同代人”的意涵十分不同。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指向人文学者对自我与时代以及对一种新的时间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所谓的同时代性,指的是一种自我与时代既依附又保持距离的奇特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通过疏离、脱节乃至时代错位而让自己与时代产生关联的辩证法;换言之,“同时代人”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说是时代的“异乡人”。这位时代的“异乡人”,既深陷时代之中,又能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凝视时代的黑暗,并蘸取这一黑暗之光进行写作与批评。
在我看来,黄子平老师提出“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一议题,其实是想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来为当下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文学批评找到一个出路。黄老师提到,他曾经被一位70后作家问到,为什么不写当代作家评论?他的回答是:我和你不是同时代人。不过,后来读到阿甘本这篇文章,让他反省他的自我辩护是否将这个概念狭窄化了——将同时代人窄化为了同龄人。借用阿甘本的定义,黄老师不仅大大拓展了“同时代人”的意涵,也十分巧妙地化解了他在70后作家那里遭遇的当代批评的危机。在很长时间里,批评与研究被认为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模式;但“同时代人”的批评,召唤着批评者将各自的“古代”带入当代,这就将历史的维度和文学研究的维度引入了文学批评。历史维度的引入,使得黄老师成功地将狭义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推向了广义的文学批评。在这种广义的批评视野里,就包含了一种新的时间哲学,用黄老师写在讨论会提要里的话说,即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糅合的历史性装置”。这种新的时间哲学,在根本上挑战了将“时代”或者说“代际”作为一种实体来理解的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
“同时代人”批评视野里所内含的这种对历史主义的挑战,令我特别心有戚戚。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即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来做一些回应。与文学批评的境遇相似,文学史或者说关于文学的历史研究,在今天其实也充满了困境与危机。黄老师在周三的讲座中用谱系学的方法,对从《史记》到当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荆轲刺秦”故事进行了一个主题学的分析。讲座的最后,黄老师对当代文化提出了一个激烈的批评,就是历史主义消解了历史叙述中的伦理关怀,其实也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道德承担,这里内含着一种“结构”对“个人”的压抑。我觉得这个批评十分切中肯綮。不仅是当代文化中的戏剧、电影,我们当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仍然回荡着这一历史主义的幽灵。黄老师的批评对我特别有启发,它精准地击中了我在文学研究中所感到的困扰和困惑。
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特别重视文学史或者说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我自己就成长于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中。文学史其实就是典型的将“时代”作为实体来理解的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对于文学史为何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主要形式,陈平原老师很早就进行了反思(《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这学期在北大也开了一门题为“文学史与现代文本校勘”的研究生课程,目的是想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反省文学史,并尝试打开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课程中我带领学生读了美国学者帕金斯(David Perkins)的《文学史是可能的吗?》(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一书的部分章节。帕金斯在这本书第6章对文学史研究所内含的语境批评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能够作用于文本阐释的语境在理论上是无限的,选择这一个语境还是那一个语境,其实存在很大的偶然性。这就在根本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中的历史主义/语境批评,提出了质疑。在帕金斯著作的延长线上,我还和学生一起阅读了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个出现在德国1874年的文本,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典型了。这篇文章虽是一百多年前的文献,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知识状况,却与尼采所批判的19世纪中后期德国知识界沉重的“历史感”非常相似。当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越来越深入细致乃至琐碎的历史考证,也生产出了一堆难以消化的、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大部分可能都是冗余而无用的。在课堂上我让学生列举出五位至今仍留在记忆中、喜欢阅读的现代文学作家,本来以为很容易,结果大部分列到第四、五位就很勉强了。那么,现代文学怎么办?还有研究前途吗?
很显然,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语境批评范式,早已陷入了困境和危机。危机当然也意味着转机,我想也许有两种方式来应对。一种我称之为“以毒攻毒”式,就是文献学的视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学和史料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我自己对文献学的兴趣是从谱系学接引过来的。文献学不是作为文学史的基础,而是视为一种挑战:通过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的手段,可以观察到文学史书写中的断裂以及被折叠和遮蔽的历史,以此可以挑战固有的、主流的文学史论述。这背后有一种对于多样性的强调。如果说已有的文学史书写的是一种意愿记忆,那么,文献学则致力于对碎片式的非意愿记忆的发掘。这种让沉默的、碎片化的“过去”来说话的方式,我称之为对文学史模式的“以毒攻毒”。
另一种应对方式我称之为“拯救”式,这就是文学批评。如姜涛老师所说,回到历史现场,不是平安的,而是要带着“当代性”去进入的。我想在文学史研究或者说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引入的文学批评,不是狭义的当代作家评论,而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是带着“当代性”进入的“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在这种批评视野中,过去与现在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的关系,而是如本雅明所说,在意象中,“曾经与当下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表征”(本雅明《〈拱廊计划〉之N》)。引入这一“同时代人”的批评视野,对于陷入漫无边际、冗余琐碎的历史还原式的文学史研究,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拯救方案。为了这个讨论会,我还特意学习了阿甘本。在收入《何谓同时代人?》一文的阿甘本文集《裸体》中,第一篇文章题为《创造与救赎》,也特别有启发。阿甘本说,救赎其实是先于创造的。我们可以将创造与救赎类比于文学与批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就是先于文学而存在的;而一种更有创造性的解读是,将“创造”理解为迄今为止的过去,而“救赎”则是我们当下的位置,那么,救赎先于创造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由当下的位置出发去理解和拯救迄今为止的过去。我想,这就是将“当代性”或者说“同时代人”的批评视野引入文学研究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我在现代文学学科中遭遇的困惑,也指示出可能的道路。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才黄子平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都提到,在当下,文学和批评某种程度上其实都被边缘化了。那么,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学者如何介入时代?如何去保持一種“当代性”?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可以作为思想资源带入的“古人”,就是鲁迅。鲁迅显然非常符合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人”的定义:他非常深地卷入时代,同时又和时代格格不入,并且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之光并蘸取着黑暗之光来写作。然而,将鲁迅带入当代,他那种有机知识分子式的介入时代的方式,我想在今天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不可复制的。今年9月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了“犹在二周之间:周氏兄弟与中国新文学”的研讨会,陈思和老师在会议致辞中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认为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氏兄弟是有遗憾的,因为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知识上的建设其实十分有限。这让我想到鲁迅和《国学季刊》的关系。鲁迅仅仅为《国学季刊》设计了封面,没有在上面写过文章。我们知道,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倡导的就是对国故进行“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历史还原式的研究。鲁迅对胡适的这种历史主义其实是有异议的,他的历史观和胡适有很大不同。我不禁拟想,如果鲁迅和王国维一样,给《国学季刊》写稿、写学术性的文章,会写成什么样子呢?这当然是我的一种想象。我想引申出来说的是,鲁迅的历史观其实和章太炎有相通之处,在他们那里,历史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一种记忆,历史从来都是切关当下之物,这是鲁迅与胡适之间深刻的不同,也是他作为一个“同时代人”的特质所在。刚刚吴晓东老师在发言中指出,黄子平老师对历史的理解,是将历史视为一种在今天仍然植入人心的记忆。我觉得这种对于历史的看法,正好是处于章太炎和鲁迅的延长线上的。那么,黄子平老师提出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我而言就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启示我将批评的眼光植入文学的历史研究之中,同时也通过对文学进行历史的、不人云亦云的研究,切实地找到自己回应时代的方式。这对于重新恢复我们对文学、对批评以及对文学研究的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