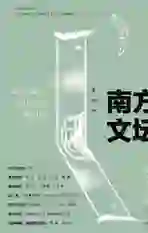门外说戏
2024-03-12莫言
二十二年前,我去苏州大学参加王尧教授办的小说家论坛,当时我们之间语言交流还有点障碍,但是我们创造了作家和批评家交谈最长的纪录,谈了三天三夜,后来整理出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对话录。
最近这两年王尧摇身变成了小说家,他的《民谣》写得很好。现在流行跨界,我写诗、写剧本是跨界,王尧写小说也是跨界。
2023年10月,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我的话剧新作《鳄鱼》研讨会,有四十多人发言,每人限定五分钟,都未能畅所欲言,很是遗憾。大家给予《鳄鱼》较高评价,我知道当着我的面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没有表达出来。任何一个作品都有不完美之处,任何一个作品也都是遗憾的作品。但话剧、舞台剧最大的长处是可以不断地修改。今天晚上感觉这个地方不好,明天晚上就可以调整。这一段不好明天就可以删掉,这一段感觉到没有尽兴,下一场就可以加上几句。有很多的戏,演几十年,演上万场次,千锤百炼,过去所讲的十年磨一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从小就是戏迷,还有过粉墨登场的经历,当然演的都是跑龙套的角色。我学习写作时写的第一篇作品是话剧,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山东黄县当兵的时候。当时有一部话剧《于无声处》影响很大,我就模仿着写了一部。动笔之前我还是有所准备,一是在童年时期,从我大哥的语文教材上读过曹禺、郭沫若的话剧片段;二是当兵后,沾一个未婚妻在黄县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战友的光,借阅过曹禺、郭沫若、莎士比亚的剧本集。这个剧本写好后,四处投递,自然不可能发表和上演。后来就开始写小说。到了1998年,在部队几位搞话剧的战友鼓励下,我写了话剧《霸王别姬》。为写这个戏,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可惜当时没能来徐州考察一下,否则也许写得更好一点。
写历史剧,便利之处就是故事是现成的,京剧、地方戏曲、话剧、电影,有很多的版本可以参考。当然最根本的源头还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这部戏由空军的蓝天话剧团在北京演了很长时间,后来到东南亚、德国的国际戏剧节演出过。
肖雄扮演吕雉,获得了梅花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重排《霸王别姬》,我很高兴,回京后我要重读一遍这个剧本,然后找他们聊一聊,估计会有新的认识。
因为《霸王别姬》演出获得成功,空军话剧团的导演邀请我再给他们写一个。这时候他手里面有一个剧本,是西安的一个老编剧写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看了这个剧本,觉得不是很满意,他们希望我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改编,我说还不如我重新给你写一遍。我用七天的时间就拿出了初稿。这就是《我们的荆轲》。这个戏沈阳话剧团演过几场,后来由北京人艺的任鸣导演搬上舞台。这个戏现在已经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还有一部戏《锅炉工的妻子》,现在还没有演。这部戏原来是《霸王别姬》的一部分,当时设置了古代和现代两组人物,交替着写,后来一是因为篇幅太长,二是两部分捏合不到一起,就把它剔了出来。这部戏比较简单,人物只有三个:一个音乐指挥、一个钢琴女教师、一个烧锅炉的农民工。这个烧铜炉的农民工是女钢琴教师的丈夫。他之所以能跟她成为夫妻是当年知青下乡的时候,女青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小伙子跟他的母亲帮助了女知青,后来她就嫁给他了。这个戏稍加扩展可以在小剧场演出。
《我们的荆轲》在北京人艺演出后,他们希望我能够继续写戏,我也有继续写戏的愿望,但因为有小说要写,写戏的事就拖延下来。2021年的春节,北京人艺的老院长张和平先生,带着北京人艺的几个领导,上门找我,要我给他们写戏。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工作时,接触过很多检察官,旁听过审讯,请检察官给我们介绍过案情,当然也接触过贪官,掌握了大量的素材。我对逃到海外的贪官比较感兴趣,后来的“天网行动”也了解一些。我一直就想,贪官跑到国外,他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比如他通过电视了解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他通过电视或者其他的媒体,看到了当年工作的城市的巨大变化,心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我觉得大有戏可做。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但要真的变成一个剧本,中间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个时候鳄鱼出现了。
我家邻居有个小伙子,他喜欢养爬虫,他告诉了我鳄鱼的特性。他说把鳄鱼放在很小的盒子里面,它的食欲很小,吃不了多少东西,所以是长不大的;给它提供的空间越大,他吃得越多,长得越大。如果把它放归大自然,它就按照物种本身的特性生长。我觉得鳄鱼的天性很像人类的欲望,也很像权力。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无限膨胀,欲望如果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也会疯狂膨胀,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也。
当然对欲望要客观分析,没有欲望人类社会不可能繁衍,没有欲望,科学、文学、艺术、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所以欲望既是社会发展、人类繁衍最基本的动力,这是合理的、正常的、正当的,但是一旦过度,一旦不受控制,任意地泛滥膨胀,就会带来灾祸。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鳄鱼跟封闭在美国独立别墅里的贪官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比较丰富、比较有张力的艺术空间。
这就是我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穿插着写的几部话剧的基本情况。四年前在英国莎士比亚的旧居前,我的确说过要用余生实现当一个剧作家的梦想,是当着余华、苏童的面半开玩笑地说的。不久前我又去了一次莎士比亚的故居,感受依然很多。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在我所知道的中国当代作家里面,十年之内,去过三次莎士比亚故居的人,大概就我一个人。
2012年春天,我去参加伦敦书展期间去了莎士比亚故居,这是第一次。2019年我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几位同事去牛津大学,顺便去了莎士比亚故居,这是第二次。那天下着大雨,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一个剧作家的戏演了四百年,依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让我既羡慕又感慨。我想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戏剧的力量,当然也是文学的力量。我看到在莎士比亚故居的院子里面有一尊汤显祖的雕像,让我感到自豪又亲切。
上个月,我去非洲,然后转到英国,又去了莎士比亚故居,这是第三次。朋友说我是去还愿,因为我写出了《鳄鱼》。我说可以说去还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感觉我的戏剧意识还没有完全打开,应该再次去寻找灵感和力量。这次看得更加仔细。我看到在小城的街心公园里,新修建了一个牡丹亭,非常漂亮的亭子。这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也是中国人的光荣。我们中国剧团演过很多外国的话剧,外国的剧团也演过中国的话剧。戏曲的翻译移植比较麻烦,因为除了语言,还涉及音乐、唱腔、服装等许多元素。前几年意大利一个学校演过我的《蛙》,2023年俄罗斯的正式的剧团在普希金剧院也演过《蛙》,他们把长篇小说《蛙》最后的话剧部分剔出来搬上舞台,这让我感到高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剧团也能把《蛙》搬上话剧舞台。
除了写话剧,我还写过戏曲剧本,《锦衣》《高粱酒》《檀香刑》。《檀香刑》是歌剧,与我的一个老乡合作,他是音乐家。《檀香刑》参加过中国歌剧节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也演过两场。歌剧在中国有一点水土不服,但20世纪60年代那批走民族化道路的歌剧还是大获成功的。民间戏曲是俗文化,它的唱词对白都是乡音土语,是土得掉渣的语言,当然是押韵的,但韵押的是地方话的韵。这样一种东西,对老百姓的语言训练很起作用。当年村子里面有很多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出口成章,合辙押韵,这就是看戏看出来的。老一代的作家,在这方面也是有很深的素养的,如赵树理,一人可以唱完一台戏。还有汪曾祺先生、老舍先生,他们对戏曲非常熟悉。戏曲根在民间,是文学艺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艺术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艺术的最重要和最鲜明的标志。
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歌舞,听到的是他们的说唱,这里面既有历史又有神话,也包括了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从远古继承下来的文化基因。民族艺术的戏曲这一块,大家有空的时候稍微接触一下,江苏也是戏曲大省,有淮剧、锡剧、昆曲。戏曲一方面在舞台演出,另外它是一个文本。汤显祖的《牡丹亭》要演全本,一天是演不完的,因為节奏特别缓慢,一句话可以咿咿呀呀唱三分钟。我觉得《牡丹亭》首先是供人阅读的文本,从某种意识上,演出反而是次要的。他的文字十分典雅,大量的出场诗、定场诗,全是集的唐诗,第一句李白,第二句杜甫,第三句白居易,第四句李商隐……难度很大。要成为像汤显祖那样的剧作家,必须将古典文学诗词烂熟于心,要有非常广博的文史知识,还要熟悉下层民众的生活和语言。像《牡丹亭》《西厢记》,首先是作为一个非常优美的文本存在,阅读这样的文本就会得到很高级的审美享受。
(莫言,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