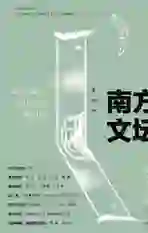大时代的影响与焦虑
2024-03-12陈平原
在我学术成长的旅程上,三十八年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至关重要。此后关于“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广泛流传,作为小弟的我,获益最大。近年好几次与錢、黄两位兄长同台表演,我都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致谢。比如,2018年10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落花时节读华章——‘漫说文化三十年”暨《漫说文化丛书》出版纪念分享会,或者2019年10月27日由北京活字文化组织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论坛,有相关报道及对话实录为证。《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推出“黄子平学术思想评论专辑”,则收录钱理群的《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赵园的《我所知子平与枚珊》以及我的《在边缘处策马扬鞭——关于黄子平的学术姿态》等八篇文章。
2020年春季学期,因新冠疫情肆虐,北京大学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个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这当中,就有专论黄子平的《文本、灰阑与意识形态——关于〈灰阑中的叙述〉及其他》,此文初刊《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后收入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2月)。
四年前,在黄子平新书座谈会上,夏晓虹提醒我不要太早进入怀旧状态。因为,岁月本就催人老,你再开口二十年前,闭口三十年前,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心态很容易老去。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今天的发言,没办法,我还是需要先叙一下旧,因在座的大多年轻,不知道过去的故事。
四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作为一个有志进京发展的外省青年,前来北京大学踩点。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唯一认识的北大人就是黄子平。到子平兄那里聊天,送上我刚完成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看完觉得不错,推荐给老钱;老钱看过了,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王先生于是决定第二年招收博士生,并让老钱通知我来报考。所以,我进北京大学,他们两位是引路人,最为关键。现在的学生们很难想象,当年我们聚在一起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时候,我还是个博士生。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出道较早,全靠他们两位提携。
这里还得穿插一件逸事。2000年4月,去国多年的子平兄第一次回北京大学做讲座,就在我们今天的理科教学楼一楼。那天晚上,场面甚为壮观,因开讲不久就停电,我赶紧让学生买蜡烛,大教室里点了几十根蜡烛,子平讲得很开心,说从来没这么浪漫过。可惜不久又来电了,这让他很伤心——若能在烛光中讲完这一课,不说进入历史,起码可以吹一辈子牛。
刚才提到2018年我们为《漫说文化丛书》重刊,在北京大学畅谈“三十年落花梦”;而后又有一系列围绕子平兄的活动,那都是老钱建议的。老钱认为,子平去国多年,目前的中国学界对他不是很熟悉,我们得为他捧捧场。于是,围绕他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举办座谈会,还有在《文艺争鸣》组织评论专辑,再加上我的课程讲述,都是基于这一思路。当然,首先是子平兄学术实力雄厚,这才可能迅速吸引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多年轻人。
在《文本及其不满》的座谈会上,我谈及批评家的同代感与史学家的异代感,相关论述已见《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实录》(李浴洋整理,《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某次接受专访,我引述日本明治维新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一句话:“一生而历二世。”正因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生活过,很自然产生观察角度的差异。我开玩笑说,这是一种“照花前后镜”的效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观察上一个时代的人物,或者用上一个时代的尺度来衡量今天的事态,都让你时刻保持疏离感以及超越的冲动。我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有较多的了解与认同,因此,当我做五四研究时,明显带有80年代的眼光和趣味;反过来也一样。这种两个时代的对峙、对照与对话,既是人生经验,也是学术立场。我以为,这比固定单一的评价标准好,起码具备自我反省、互相质疑的可能性。
时代与世代不同,这里先说什么叫做“代”?记得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的说法,也就是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文革”红卫兵的一代。关于代的划分,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30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10年。最夸张的是北大学生,他们喜欢说军训的一代、昌平的一代、万柳的一代等,也就是说,以更具体的居住地及生活经历作为标志。应该承认,作为群体,共同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容易凝聚思想、形成共识,并影响日后的成长与发挥。可见“代”的尺度,可大可小,可宽可严,就看论述需要。
今天谈这个话题,夹杂时代转移与世代更迭。我同意刚才老钱的说法,现在可能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也可以说是“新一代”的起点。最近两三年,我在好几次学术活动中,重温冷战时代的学问与人生。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2020年,恰好是三十年。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的基本判断是,中美的强烈对抗以及三年全球疫情,使得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一下子说不清,我猜想,不会完全回到全面冷战,但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了。以前我们开口闭口“地球村”,现在已告别那个玫瑰色的梦想。若真如是,我可算是一生而历三世了。
对于冷战时代,年轻一代印象朦胧,我则有切身体会。因此,当我面对某些熟悉的口号或场景时,马上明白什么东西回来了。若是小的鸿沟,你我努努力,很容易跨过去;但如果是一堵很厚很厚且无边无际的“高墙”,单凭个人能力,是跨不过去的。这几年我谈王瑶,谈普实克,谈夏志清,还谈了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一大批我的师长们,看他们的经历,深有感触。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一句很睿智的话:毫无疑问,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就怕人生有限,因而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人的一生,能尽情挥洒才华的时间并不长,若在关键时刻停顿十年二十年,那是很可怕的事。记得程千帆先生曾叹惜自己精力最好的中年时光白白浪费了,反右后放下教鞭,改为养猪放牛,1978年才重返大学。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丢失二十年意味着什么,闭着眼睛都能想得到。
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大时代的影响与制约无远弗届。同样中断学业,但断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影响迥异。历史按下暫停键时,你风华正茂,还是蹒跚学步,抑或已经功成名就,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老钱、子平和我这一代是幸运的,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大学校园,得以从容读书四十年。我观察20世纪中国学者,很少能有平静读书、安心治学三十年的。我一直感叹,下一代治学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将来成绩不可限量。现在看来,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与阴影。大概每代人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规避陷阱,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前进的道路。
路总是有的,只是你能否及时踏上,得看运气。追述冷战时代我们的长辈如何在困境中挣扎,以及他们取得的业绩、留下的遗憾,那只是一种提醒,并不意味着会重来一遍。我举一个例子,诸位听了,马上明白时代的差异。我第一次出国是在博士毕业两年之后,而我的学生大都念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就有出国交换学习的机会。那天偶然提及此事,好多学生举手,说上小学时就跟随父母出国旅游了。因此,不同世代的人,对“出国”的记忆是很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出国,有明显的“文化震撼”;年轻一代不会有,他们觉得很平常。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反正目前出国进修、访学、合作研究,比前些年难很多。不是成绩好或国家需要,你就能走出去的。这种局面若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学术生态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这一代基本谢幕了,在座的年轻教师大体定型,关键是正念硕士、博士的,日后的路该怎么走,选择何种求学路径与治学方法,必须有很认真的思考。
2023年10月12日,我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系列讲座之一《“割让”“香港”——鸦片战争前期中英谈判的翻译问题》,因王教授的学术生涯及贡献,第一讲已经介绍过了,我选择说开去,类似小说戏曲的“楔子”,或宋元说书的“得胜头回”。我提及自己过去一年先后为三个老学生的新书写序——林峥副教授的第一本书《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张丽华副教授的第二本书《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以及彭春凌教授的第三本书《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三书各具特色,都是优秀的专业著作。我的感慨是:这三位“全北大”,博士在读期间都曾在外访学一年以上(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东京大学),毕业后也都有在国外名校继续研究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她们的根底及趣味是在北大打下的,但国外访学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也改良了研究方法。北大的人文学很不错,但这远远不够,尽可能转益多师,广采博收,才能走得更远。
疫情三年,中外学术交流明显受阻。我再三强调,当下中国学界,确实需要有自信,但也得有自醒——我指的是清醒的自我认识,以及持续的自我反省。2023年2月北大开战略研讨会,确定2023年的目标是国际交流年,尽最大努力走出去、请进来,打破那些有形或无形的禁忌,摆脱自觉或不自觉的封闭状态,跟国内国外众多有真知且能坦承相见的学者沟通、对话、请教。以小小的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为例,这半年多时间,先后前来讲学的有美国学者胡志德,日本学者滨田麻矢、铃木将久,香港学者王宏志、黄子平,以及马上要来的王德威教授等。如此频繁的学术交流,有点忙乱,但机会难得,希望能保持这个状态。
近日,在一次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学术对话中,主持人要求我们各选一个关键词展开论述,我选择了“开放”,理由是:“我们更希望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心态,来面对人类的未来。相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大学的特点正是源于其能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容纳各种各样的文化乃至各种各样的立场。在这里我们讨论甚至争辩,最后找出比较好的方案往前走。”(《第二届“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评选结果揭晓》,澎湃新闻客户端:掌上青岛2023年11月16日)
每个人都深深嵌入自己的时代,只不过有的跃马扬鞭,有的采菊东篱,有的热血沸腾,有的冷眼旁观。不管你采取什么姿态,大时代的魅力与阴影,挥之不去。今天的中国大学,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内部竞争又过分激烈,我能理解年轻一辈的郁闷与惶惑,但无论如何请不要躺平。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必须有人顶住,咬紧牙关闯过去。至于年长一辈,我们有义务帮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文化环境与学术氛围,就像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做的那样——当初“三人谈”之所以能破土而出,正是得益于长辈们的宽容与扶持。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