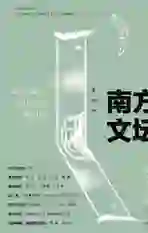赛先生:当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2024-03-12钱理群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我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满怀焦虑的同时,又充满好奇心:在后疫情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中,和我们每个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与研究,在面对危机的同时,又迎来什么新的机遇,拥有哪些“历史再出发”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困惑和期待下,我读到了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眼睛为之一亮:我欣喜地发现,在年轻一代学者中,还有人在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现状”,来寻求、思考、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研究(背后更有当代中国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未来”之路。尽管由于时代与知识结构的距离,我对她的论述,还有许多不懂之处,但仍愿意如实写下我的关注与思考。
我想从2022年所写的《商金林学术研究的“现代中国人文史”视野》一文说起。文章谈及商先生发现的关于鲁迅的一个重要史料:1930年代,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在所拟广告词里给予鲁迅两个重要评价。一是明确提出,要关注和研究“现实的活的中国”:它对于世界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钥匙,就是这部《大鲁迅全集》”。二是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作出新的概括:不仅研究“从古代到近代支那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这就“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人文史的顶峰”。正当我为商老师的新发现兴奋不已时,又注意到,也就在2022年9月,在陈平原老师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我立即敏感到,这绝非偶然。其所提出的是一个“解开‘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的学术使命,以及相应的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它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初历史大变动中,为陷于困境的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至新方向。我因此在文章里响应商金林、陈平原二位的倡议,明确提出要“接着鲁迅往下想,往下写,往下做”,突破“重传统,轻现、当代研究”的学术现状,重振“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研究,认真总结20世纪、21世纪初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以解析“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
此刻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李静的新著,就是我所期待的,解析“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的“人文学”著作。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自觉于此,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视野:以“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为突破口。本来“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样,都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主题词;现在作者将其延伸到当下,研究“赛先生在当代”,讨论“现代社会与现代中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探究科学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叙事系統”,从而将“科学”与“文学”,及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政治、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这本身即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色与贡献。
书中包含了独特的“科学观”:“在中国语境中,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现代化转型中,科学一直是高度人文化与道德化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密切互动。”正是从这样的科学观出发,“本书关注的不是思想史和制度史里的‘科学”,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不同阶段中”。于是,李静又有了一个独特发现:在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中的两个关键时刻,“赛先生”都是一个核心性存在,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也是以这两个历史时刻,结构成“上”“下”两篇。
上篇题为“历史转轨中的‘赛先生”。她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正处于“由‘文革向‘改革过渡”的历史时期。1988年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于是,就出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以陈景润为代表的“科学家(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诞生。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退场,科技人才成为更有价值的新人代表”。这标志着价值观念、人生理想、选择的巨大变化。正如本书引述的北京大学教授的自述,彼时他还是年轻学子:“陈景润对专业研究的认真勤奋,对时事政治的冷漠态度,对日常生活的毫不讲究,都与‘文革时代形成强烈反差,我们狂热地崇拜他。他的生活观念或者说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的许多人。”陈景润“由科学怪人转变为美的化身”,表征着新时期“对于‘人的理解方式正悄然转变”,“为理性而生”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被“高度道德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即明确宣布:“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邓小平还同时还“定位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真可谓“石破天惊”。这样的“知识(科学技术)”的新定位,“知识人”的诞生,为此后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成为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显然奠定了基础。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下篇”关于“2016年以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了“当代文明转型”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李静的另一个重要概括。她指出,“2016年是所谓人工智能元年。伴随着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与应用,科学技术重构了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生活系统。在数码文明转型的时代中,科技已融入身体经验,作用于环境本身,科技、资本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这样一个新时代、新文明,与高科技的新结合,其本身就是高科技(人工智能)的产物。而如她所强调,“数码文明时代前所未有地为大众带来参与文化的渠道,带来各种联接的可能性”。高科技也为国家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管控,提供技术的支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早已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而是拥有了深入社会、进入年轻一代生活中的可能,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在网络找到了施展空间,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机器人挑战了人的功能与作用,由此更是不可回避地提出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既引发关于人的未来的好奇与想象,更导致人的精神的焦虑与绝望。如本书中所写:“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甚至新蒙昧,新迷信正在上演。而情绪极化,普遍性失落与反智倾向正在蚕食着我们的文化土壤。”数码文明带来的“历史巨变”才刚刚开始,一切有待于我们的持续观察与思考。
这样,李静通过抓住两个时代:“由‘文革向改革过渡的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2016年以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把1978—2023年四十余年的当代中国巨变拎了起来。开拓了一个极为广阔、丰富的人文学研究空间。
李静不仅自觉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开拓了独特的研究空间,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或许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特别关注的,有三个方面:
其一,她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不仅注意科学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形态,还牢牢把握其“叙事系统”,即科学的建构与叙述。她是从“科学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来展开自己的科学人文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就是进行“科学故事的个案研究”。而文学书写中的科学故事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情境化、经验性与差异化”,以及高度个体化,对细节的着意关注,等等。这就避免了科学理论与科学史研究对科学的概括叙述可能带来的抽象化、简单化、单一化等问题,从而有助于复原实际生活中科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与个体性。文学修辞书写的科学故事,也更便于发挥“文学在预示、警示、反思等方面的能动作用”,以及“想象力与创造力”带来的文学魅力。
我读李静这本专著,最感惊异的是,全书只讲了七个“科学—文学故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叶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来》,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创作的机器拟人与人拟机器”,“四大名著的接受”,以及鲁迅代表的“现代经典的后现代命运”,但我却从中看到了改革以降四十余年间的历史巨变,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比如,从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老干部上任、老工人退出,“知识分子英雄”登场,中国教育的新阶段开启,这些真让我浮想联翩。而2016年以来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巨大变化,对“未来”的想象,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自我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的选择,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这正是我所欣赏与追求的学术境界:不仅给读者提供相关的知识、文化与研究者的思考,而且能够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经验和生命体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其二,关于学术研究的“历史性”,李静也别有见地。她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要“进入历史情境”,对当事人的选择怀有理解与同情;二是要正视选择的“后果”,展开当下的反思。她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历史”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当事人在不知后果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所面对的,却是当年的选择带来的后果。研究者所要坚持的“历史性”,就是要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又置身于“当下”的历史情境。这就产生了研究者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反思性。我因此注意到,她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英雄化”的出场故事的讲述,不仅谈到当时从“文革”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淡化政治,转向专业化的历史合理性与正面作用;也不回避这样的“急转弯”带来的深远影响:“‘政治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专属‘政党的事情,进而逐渐从个人的生活世界中退出。照此逻辑发展下去,人民参与现实政治的意愿、能力与渠道逐渐缩减,难以成为国家事务的能动参与者。”而“伴随市场经济以来的阶层分化,寒门难出贵子,‘脱不掉的长衫等网络热词出现时,证明我们已经置身于难以逆转的后果之中了”:“知识与学历不再是阶层上升的有效渠道。”这样的“知识降格”就必然出现我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正视后果”的历史叙述,不仅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更能凸显历史研究的反思、批判功能。
其三,李静在导论里宣布:“本书的主旨,是去追究科学何以社会化,以至其原理、方法、观念甚至成为每个现代中国人的人生律令。”这是她的另一个自觉追求:追寻学术研究与自我个体生命的联接,把自己的“生命难题变成研究课题”,追问“自己投身的研究与批判”,与自己生活的社会、时代,更与自身的生命,到底有着什么关系与“意义”连接?她坦言:“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照见自己成长与生活的过程。”这样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相互融合的研究,使我想起了自己在《商金林学术研究的“现代中国人文史”视野》里的一个论断:人文史研究的“人”,既包括作品所描写的“人”,创作者自身,也包括研究者其“人”,读者其“人”。人文,人文,就是“人物—作者—学者—读者”四位一体的生命,因“文(文学形态)”而融合,发生精神的共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静既追求这样的“融合”和“共振”,又清醒于其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她在后记里自嘲为“半新半旧之人”,“既不甘传统,又怀疑潮流”。对于自己所关注,相关作品所描述的时代“科技故事”,其所显现的“人”以及作者其“人”的观察、选择,是既产生共鸣,又有所怀疑的,因而“注定只能在持续焦灼中艰难地写下心声。而这心声的价值或许不久便将消失殆尽”。这样地对研究对象及自身的双重怀疑,同时又共鸣的矛盾,就使得本书的研究与叙述,充斥一种焦虑与不安的氛围:这恰恰是我最为看重的。
2023年10月31日—11月3日陆续写成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