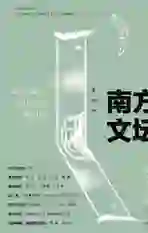“赛先生也成了赛同志”
2024-03-12李静
一、走出实验室:“科学”的社会化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①
大兴的努力,正直,热诚,使自己到处碰壁。他所接触到的人,会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视的“科学家”三个字变成一种嘲笑。他们要喝酒去,或是要办一件不正当的事,就老躲开“科学家”。等“科学家”天天成为大家开玩笑的用语,大兴便不能不带着太太另找吃饭的地方去了!
——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1943)②
今天的文学家与科学家有着相同的使命。科学家在发现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规律;文学家则应该努力发现新的人、新的生活准则。
——靳凡《公开的情书》后记(1981)③
20世纪以来,“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日渐普及,并强力重塑着民众的生活世界。开篇所引三则,便显示出“科学”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复杂影响。第一则,出自胡适为1923年“科玄论战”所撰总结,强调“科学”作为现代西方文明之精粹,逐渐占据至尊地位。文中虽也提及梁启超在一战后反思“科学万能”论,但颠扑不破的前提仍是科学权威的确立;第二则,取自老舍在战时重庆所作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小说描写了在美国学成归来的园艺学家尤大兴来到“树华农场”,满心希冀“科学救国”,却因不通人情世故而四处碰壁,直至“科学家”三个字沦为嘲讽之语;第三则,选自靳凡(刘青峰)为自己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所作后记,道出时代语境下年轻人的思想取向,对他们而言,科学与文学无不孕育着新价值、新生活与新信仰,这一除旧立新的文化选择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仅凭这三则文字,便可一窥“科学”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深广影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关头,在“文明等级秩序”的压力下,在救亡图存、追求富强、抗战建国的一系列紧急任务面前,“科学”不仅意味着先进知识与实用技术,更负载众人之幸福、社会之进化的艰巨使命。它既落实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又承载了从宇宙观到社会观、政治观进而到人生观、道德观的全方位变革,最终发展为一种最为权威的文化范式与超级能指。
大体来说,科学堪称封建社会的挑战者、现代文明的推动者与新信仰的提供者的三位一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科学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正因为它存在着中国特有的、用现代常识理性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隐形模式”④,这意味着在中国语境中,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科学一直都是高度人文化与道德化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密切互动。正如巴里·巴恩斯指出:“科学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础”,“鉴于科学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础,那就必须把它看做是文化的产物”⑤。由此,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成为,“科学”到底是如何走出“知识黑箱”,演化为新生活方式与新文化的“地基”的?“科学”是如何完成其社会化进程的,仅靠科学知识的传承扩散吗?
谈及“科学”的人文化与社会化,有一个文化符号绕不过去,那便是著名的“赛先生”。一般认为,“赛先生”诞生于陈独秀为《新青年》杂志辩护的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中认定只有“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⑥。瞿秋白评价道:“二十余年来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 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⑦,科学才真正进入并搅动古老中国文化的深层根基。沿此思路,不妨继续调用“赛先生”这一文化形象,站在科学与文化的交叉地带,考察“科学”走出教科书与实验室之后,渗透进中国的社会化进程。以“赛先生”为视角,可以观察科学观念在确立与普及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及其包含的伦理导向与意识形态内涵。
比方说,当科学观念由精英群体扩散至更广大的基层社会后,到底带来哪些变与不变?再比如,那些独属中国语境的时空维度,像是老舍小说描写的“树华农场”这类基层社群/关系网络,又或是靳凡所描写的身处特定情境的一代人,这些要素的加入到底令“科学”演绎出哪些故事,造成何种后果,又萌生了哪些影响至今的重要思想文化议题?要面对这些丰富切实的问题,或许可以借力于“赛先生”闯入中国社会之后经历的种种故事,以此为中介,去谛听现代中国文化生成的内在节奏。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科学故事的三重讲述
当“科学”概念与社会结构深入互动时,会激发出一套套故事/叙事,亦即以艺术形式重述与再现发生之物,使之变得可以理解与共享,并负载着特定的意义。关于科学知识的叙事性与建构性,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堪称经典。两位作者在实验室近距离观察科学家的日常工作,深入阐释了科学知识是如何在实验室内部的互动与协商,以及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建构起来的。这类理论考察了科学知识的专业化/职业化生产过程,还可以继续去探究的是,“科学”的社会形象又是如何被生产的?“科学”是如何传播,并转化为可被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大多数人阅读与感知的修辞系统/形象符号的呢?科学观念如何在中國社会运转起来,并被赋予无穷的“魅力”/“权力”的?科学观念只有转化为一套面向公众的情动机制与主体召唤术,被注入温度与价值,以及强烈的道德感,才有可能搅动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旧有价值系统,有机参与进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科学”完成自我的叙事化,才有可能入脑入心,化作现代价值谱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故而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倡导“文学革命”的杂志《新青年》上,会诞生“赛先生”这样尽人皆知的宣扬科学精神的文化符号,二者实则统一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之中。正是在陈独秀的激烈辩词中,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两面鲜明的旗帜,象征着革命的力量与前进之方向。相比起直接音译为“赛因斯”,“赛先生”的说法形象地展示了以西方文明为师长的学习姿态,且更便于民众理解、使用与记忆,加速了其普及传播的效率。
在20世纪文化变革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文学,在打造“科学”形象的过程中同样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已形成若干认知模式:其一,以英国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于1959年提出的“两种文化”论为代表,强调二者的分隔与差异,激起广泛共鸣与持久回响。其二,研究文学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进程,具体表现为研究文学学科的建立,研究古老的文学如何转变为一门现代“知识”,以及文学研究如何获取方法上的科学性。这主要集中于制度史、学科史、学术史等领域。又或以“影响论”“机制论”的方式,讨论科学如何全面再造了文学的生产、创作与传播等过程,这在近年来的新媒体文艺研究中尤为常见。其三,强调文学在预示、警示、反思等方面的能动作用,揭示其守护人文精神、省思科技后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后两种论述模式,其实也是在“两种文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在科学霸权作用的支配下探讨两种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
站在目前已有的学科分类体系而言,上述讨论方式是合理且重要的。但如果回到文明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在文化现代性的诉求下,科学与文学虽是各具自律性的两种知识类型,却也扭结为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体。科学与文学,在革命的世纪里被彼此深深影响,科学性内置于文学学科的形构之中,而科学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文化影响,也仰仗于文学叙事,文学拥有不容忽视的能动力量。
在此意义上,面向大众读者的科学故事,便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记录了大众对于科学的认知与理解过程,承载了大众对自我的期许与规划,进而以各种形式参与构建了公共认同与现实生活。科学故事所讲述的三重内涵与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科学故事承载了中国本土经验的复杂性。科学观念是被有机结构进整个社会文本中的,而非一个孤零零的观念。科学故事是高度情境化、经验性与差异化的,故而也可被看作“准民族志书写”,记录了所谓“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的“挤压”之下,如何“紧急变身”的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需要身处这一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加以总结。
其二,科学故事具备揭示文化生成逻辑的理论价值,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客观性”?相比起社会调研、数据统计、田野考察,文学文本的细读看似不够客观。但如开篇所引三则文字所示,科学社会化所衍生出的“故事家族”实际上构成连贯的、可追踪的文本脉络,本身便构成文本的“田野”。讲述动力、故事主体、行为方式与历史后果,也可被视作“文本田野考察”的若干“参数”与“座标”,并借此勾勒社会结构与历史逻辑的变化过程,其中的微妙分寸或许不是因果律与实证统计能简单拿捏的。
其三,科学故事最大程度地展现了科学观念所产生的情感效能。这点并不难理解,但以往的关注程度还不够。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文本,凝结了时代中人对科学迸发的极度热情与重塑自我的极致渴望,留存了这一特殊阶段的情感势能。在这类科学故事的指引下,我们可以获取在知识、概念、实证性事实之外的某种具体情境,有可能借此激活自身的切实感知,提升对于历史的理解能力。换句话说,正因为这些科学故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才令过去与现在变得可以理解,变成与我们有关的“记忆”,而且仍在形塑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三、“现代文化的不安定层”:一种文学生存论
回到“赛先生”的故事里,我们会发现,“凡‘赛先生出场时,大多时候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概念围绕着他试图搭建起诸如朋友、敌人、家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身处其中的‘赛先生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⑧,他与德先生、费小姐(freedom)、穆女士(moral)、“爱先生”、“美先生”等人格化譬喻,交织组合成建设现代文明的各式方案。“赛先生”与其他人格化概念之间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们各自地位升降浮沉的背后,乃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该如何选择价值排序?”⑨以“赛先生”为代表的人格化概念群参与了思想重构与现实解放的过程,人们借助这些概念范畴与叙述框架来不断重新表述自己的生活世界。
而在特定语境与阶段下,概念也会在与现实的交互中裂解出不同的理解方式与发展形态,掀起思想与实践的巨流或微澜。即便是在“科玄论战”中主张科学有限性的张君劢,在目睹科学技术对二战的巨大影响后,转而站在了主张科学救国的一方,而且尤其看重先进武器的力量,“赛先生”的形象亦随之有所变化,更偏重于物质层面。“赛先生”既可以是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同时也可以代表强调物质、工艺的科学,其间的思想差异不可谓不大⑩。那么,“赛先生”闯入现代中国之后,到底有着何种命运,又是如何持续在场,成为一种有效的表达呢?这是必须借助具体文学文本来思考的问题。
在文学文本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观察有关科学的叙述是如何发动的,这些叙述又是如何与其他社会力量联动,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后果?其中,“动力”与“结果”正是文本细读时尤其值得注意的两个维度。“动力”关涉历史上下文的具体脉络,而“结果”则是如今展开反思的立足点,同时也构成我们已有的认知框架。在科学故事中,关于“动力”与“结果”的讲述,往往是以一种高度混沌暧昧甚至是情绪化的方式呈现的。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实证性学科的特殊之处,它是反概括、反还原的,總是死死地盯着那些幽暗未明、无法简单作答的地带。当然,在科学故事家族中,同样不乏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的文本,但难免仍会有意或无意地纠缠着将明未明之际的思索,制造着超越于常规之上的某种“奇观”。
王汎森曾特别关注到傅斯年所提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一语。傅斯年所言,意在指出儒家经典对于下层百姓的精神与思想缺乏引导,因而产生“不安定层”,下层百姓很容易被新兴宗教俘获11。不妨借用这个说法,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与合法性来源,但它果真能够全然渗透进基层社会的生活伦理之中吗?它能够“武装”普通人的思想与情感世界使之免受其他思想的诱惑吗?对此,文学自有答案。在鲁迅的《祝福》里,武装了科学知识的“我”,难以解答“祥林嫂之问”: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12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连同“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一系列问句构成“祥林嫂之问”。在此,文学书写标示出科学在民间社会中的局限,展现了先进观念及其传播者在具体生活情境与民间伦理世界中遭遇的挑战,这些挑战看似微弱实则举足轻重。正因身处末路,“像阿Q、祥林嫂这样的非历史性存在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历史学家们观察历史的视角——一种近于鬼神的视角。祥林嫂失去了一切身份,只是天地间的一个活物,也因此获得从‘外部追问这个世界的能力,一种能够想象非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潜能”13。
在此意义上,鲁迅式的文学拥有接近鬼神的视角,因而能从“外部”追问现实世界。文学也由此构成现代理性文化的“不安定层”,徘徊于那些难以归纳/概括/推理的灰色地带。文学无法在理性化的现代世界背道而驰,它本身也需要遵循所谓科学理性的法则,却也不得不负载着许多“科学”之外的剩余物,记录着那些无法被客观语言定型、命名的东西。关涉魂灵的文学书写,并非全然想象,亦非仅是对科学的补充,它与科学共存于现代生活世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理性化与祛魅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指标,那么借助文學文本可以看到,这一“祛魅”终将是不彻底的。在社会组织、经济管理、权力运转的层面,理性化的渗透相对深入,但在主体性的层面,理性化是不彻底的。一方面,主体不得不以效率与实用为导向组织/优化自己的行为,逐渐结成当前的绩效社会或优绩社会(Meritocratic Society);但另一方面,科层系统、异化劳动与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倦怠与虚无构成我们时代的生命难题,同时也是孕育新文化形态的“不安定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人在极度异化与疏离的状态下会模仿机器写诗,在嘲弄或自嘲之间,“信息坟场”里升起的诡异诗意,圈定出科学尚未触及的、属于内在身心的文学领地。
如此立论,并非要秉持某种神秘主义,或是停留于对文学价值的辩护,而是意在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固然深受科学霸权的影响,但它依然以相对独立的姿态记录了那些难以用数理逻辑、因果关系、计算实证来命名的“诗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它真正触及“存在的难题”——人如何适应现代世界,如何在其中安顿自我?“科玄论战”的余音,仍回荡在每个现代人的体内。而文学相当于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它赋予普通人反思种种霸权的空间与媒介,它尊重偶然性、矛盾性与末路人的苦恼,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普通人的主体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
四、赛先生升格运动与文学转型
对“赛先生”命运的学术追踪,集中于其诞生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如樊洪业的《“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史的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汪晖的《“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学人》第1辑),等等。20世纪30年代以降,科学大众化运动展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逐渐占据主流,“赛先生”开始被化约为胡适一派的实验主义哲学与科学方法论,进而逐渐边缘化14。但实际上,赛先生所代表的追求无限进步的现代精神,始终贯穿于之后的发展进程中,正如研究者指出:“无论成功与否,‘赛先生作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遗迹,在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辩论中始终在场,发生于30年代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与‘文艺自由论辩,发生在4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赛先生无不参与其中。”而“时至40年代,有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称呼‘科学为‘赛小姐,还有儿童读物衷心祝福‘德先生与‘赛小姐能够百年好合,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先生甚至没有了师道尊严”15。“赛先生”或隐或显地始终在场,其地位的升降浮沉,以及与其他价值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变动关系,构成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窗口之一。但遗憾的是,对于“赛先生”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相关研究还不是特别充分,而这正构成我的主要关注领域。
提出“赛先生在当代”的话题,意在探讨社会主义体制下文学如何表述“科学”。之所以强调“当代”,是想说明“赛先生”置身于全新的历史参数之中:现代民族国家、无产阶级先锋政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冷战、现代化,等等。正如于光远1979年在报告中指出:“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说要请来两位先生,一位叫德先生,一位叫赛先生,现在这两位先生都已经入党了,德先生成了德同志,赛先生也成了赛同志。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结果,随着历史的前进,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也前进了。”16
在“赛先生”成了“赛同志”之后的种种境遇中,能够挖掘出更多贴近本土文化语境的思想议题,特别是实践难题。具体而言,“赛先生”在当代继续自身的文学叙述,一方面文学生产与研究需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指导;另一方面,“赛先生”也需要文学叙事去抵达更多的人民群众,亦即所谓的“科普”,从而发挥其塑造新人,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又红又专”,坚持走“群众路线”,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在社会主义总路线与总方向下展开,具备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与应用导向,并依靠运动、动员、竞赛等方式来加速科技发展与应用的速度。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一批关于毛泽东时代群众科学的研究,研究范畴涉及科学种田运动、汉字检字法与排字法改革、防治血吸虫病、赤脚医生运动、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农业气象学调查、地震群防群测、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的发掘17,可谓切中了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在当代科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曾强调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自觉抵制“技术自主”与科学主义的倾向。而对科学主义的集中反思,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与其时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它主要地不是有关‘知识的检讨,而是关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思。这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的历史变动的时期,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制度形式的反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汉学家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在1965年即已出版,为何会在1989年翻译为中文并产生很大影响。同年,张灏也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总结了五四思想的悖论性,亦即在理性与浪漫、问题与主义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令他们找到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而‘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他们的心目中已常常不自觉地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19。在这类研究中,科学主义开始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清理,科学主义与权力形式、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的密切关系成为重要论域。
“赛先生”诞生后,无论是“赛小姐”的祛魅,“赛同志”的变身,还是“赛菩萨”的反思,延展出丰富的问题谱系。我重点关注的则是科学技术摆脱“又红又专”的框架之后,迅速“升格”(即地位升级)的两个时期,分别是由“文革”向“改革”过渡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2016年以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两个时段当然有着诸多不同,但之所以能并置在一起,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科學技术不再完全受到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紧身衣的制约,反而因其被制约的历史获取了更高的合法性与自主性。其发展路径恢复了常态化积累的方式,越来越职业化,将绝大多数普通人摒除于专业领域之外。科技如出笼猛兽,在这四五十年间快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科学技术逐渐上升为第一生产力(1988年由邓小平明确提出),此时的文学叙事参与了科学/改革合法性的建构。就我重点关注的“科学故事”而言,在蒋子龙的工业题材书写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化、人情社会与管理科学之间的内在张力,见证了科学话语在工厂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效应。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以陈景润为代表的“科学家英雄”形象诞生,意味着前一时代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退场,科技人才成为更有价值的新人代表,以陈景润为人生榜样的发展轨迹也直接开启了对精英阶级/专家集团的成功拜物教。也正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救救孩子”的呼吁再度响起,片面追求科学知识与唯分数论,在彼时掀起了关于成长、道德的广泛讨论,但很快又被回收进关于进步主义的想象之中。这类充斥着进步主义的未来想象,完美地呈现于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之中。这本“文革”结束之后首部出版的科幻作品成为现象级畅销书,直接形塑了科技主导的未来想象,也意味着对于社会关系改造的乌托邦式想象暂时停止。以《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科幻文类,正是在科技升格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独立文体,摆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科普目的,借助创作自由与文本自律的诉求,参与了时代政治感的重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一历史时段,文学叙事充当了科学合法性的“说服者”。在发展主义的理念之下,科技与文学共同促成这一时期的历史转型,各领域的自律性得到一定恢复,改革开放的国家规划也借此获取更多大众的理解与支持。与此同时,其时的文学叙事也触及一些反思性范畴(比如社会主义规定性与科技自主性的张力、成功与道德的关系、竞争与友谊的关系),显示出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若干思考。在游说与游离之间,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学特质得以更多彰显。这也是由该时期文学生产的总体环境与历史逻辑孕育而出的。
按照华世平的研究,1978—1984年间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反拨了唯意志论与人道主义思潮,进而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生成新的社会科学原理,尤其是重新思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20,以此实现所谓的“‘意识形态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 of ideology),即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功能要求联系起来”21。通过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竞争、现代化发展、人民实际利益结合起来,破除了“群众科学”的发展模式,重塑了大众对何为科学的理解。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共识”下,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世界加速巨变。
这就要说到我关注的第二个时段。2016年是所谓人工智能元年,伴随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与应用,科学技术重构了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生活系统。在数码文明转型的时代中,科技的重要性已不再需要文学的“游说”,科技已融入身体经验,作用于环境本身,科技、资本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更多时候,文学扮演着适应者与质疑者的角色。在上一时期获取独立地位的科幻文类,在这一时期逐渐代表了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22。中国科幻创作与研究渐成新显学,与纯文学相比,更能够为公众提供面向当下的认知媒介与思考平台,并由此塑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想象力政治。与此同时,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正在发生全方位的变化。我曾借诗歌微信公众号的分析总结当代诗意生活的“生产原理”与传播特点,也曾借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分析,探讨人与机器的双向互拟,由此延伸出当代精神生活的相关议题。曾经的文学经典改换面孔,作为文化内容填充进互联网的生产逻辑中,四大名著在弹幕评点下生产新的含义与读写机制,而作为现代经典的鲁迅文学则贡献了一套互联网化的批评语汇,在网络争论与言说里焕发出重要的文化价值,正如钱理群所发现的鲁迅杂文的当代性:“它直通今天的网络文体和网络作者与网民,不仅提供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启迪,更提供了一种未经规范化的、足以天马行空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的自由文体,为今天的网络写作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写法。”23在这些进行中的文学经验里,“赛先生”敞开为人文研究的重要对象。
“赛先生”在变身“赛同志”之后,经历了革命的全方位洗礼,继而又融入国家意志、资本驱动、发展主义的逻辑链条之中,见证了当下的文明转型。在数码文明时代,赛先生迎来深刻而广泛的质疑,曾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越来越窄化为种种实用技术,且似乎走入“后真相”的怪圈。虚无主义与认识论危机随之而来,信息茧房与同温层、大数据算法陷阱、极端化舆论表达等,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有机性被极大损耗,真实性渐行渐远。真相,仿佛只是随机涌现的信息组合。比起尊崇科学家英雄的时代,近几年舆论场中对“专家”的信任近乎破产,人文知识的价值更是备受质疑。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甚至新蒙昧、新迷信正在上演。而情绪极化、普遍性失落与反智倾向正在蚕食着我们的文化土壤。与此同时,赛先生背后所关联的强力逻辑、赶超逻辑、效率至上、发展主义又未曾改变,从未得到深入的清理,遑论应对之道。当然,不得不补充的是,数码文明时代前所未有地为大众带来了参与文化的渠道,带来了各种联结的可能性。
身处巨变之中,思考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在文学经验与语言的创造性表达中,在文化与科技交互的视野中,在经验的反思与重构中,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得以真正涌现,我们拥有了言说与参与现实的某种可能。文学应时而变,不变的则是它的创造力与反思精神,以及向多数人敞开的参与权。在此意义上,讲述科学故事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事项,当代文学的科学叙事中不只凝结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更关联着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难题。
【注释】
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0页。
②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载《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56页。
③靳凡:《彷徨·思考·创造——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载《公开的情书》,北京出版社,1981,第169页。初稿完成于1972年。
④金观涛:《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载《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第359页。
⑤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第22页。
⑥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2页。
⑦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30页。
⑧⑨1415张帆:《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⑩参见罗志田:《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载《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華书局,2009。
11参见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7页。
13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文史哲》2023年第2期。
16于光远:《谈谈科学和民主》,载《论社会科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300-301页。
17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18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03页。
19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载《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233页。
20Hua Shiping:Scientism and Humanism: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1978—1989),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21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42页。
22Seo-Young Chu: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A Science-Fic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3钱理群编《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第110页。
(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