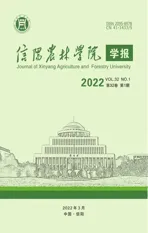“中间社会”视域下宗亲社会组织的功能及治理
——以桂西南X镇周氏宗亲联谊会为例
2022-11-26周培栋韩琪
周培栋,韩琪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 引言
当今中国乡村正处在从传统社会转向市场社会的中间社会形态,有学者将其称为“中间社会”。带来这种转型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博弈规则和社会结构[1],同时,也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绝大部分乡村居民长期处于一个相对传统的封闭社会,国家宏观政策对其引导成效相对有限,且相对外部的政府“硬法”的管理,乡村群众更倾向于认同传统礼法这种“软法”形式,因此,基层政府在乡村动员上往往遇到认同困境,乡村发展也面临着内生动力匮乏及群众动员困境的难题。
然而,在此期间兴起的诸如宗亲联谊会这样一些宗亲组织,由于植根于一定的宗族血缘社会认同基础之上,其在乡村社会的民众动员性明显强于基层政府,乡村民众对于宗亲组织的文化认同及对其领导人的“新乡贤”身份认同使得该组织在处理乡村社会民间纠纷、推动乡村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处在“中间社会”转型中的宗亲组织,在一定意义上破解了政府以往所担纲的全能主义的社会包袱以及在民间事务治理上权威弱化的困境,在“国家”与“个人”间成为有效的动员桥梁,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今学界对宗亲组织的认识,基本上局限于它是宗族组织在现代的一种形式。在乡村地区,人们基于宗族情感、祖先崇拜,对宗族组织进行了重建,成立起以地缘、血缘及姓氏为基础的诸如宗亲联谊会等宗亲组织。与以往受到国家政策限制的传统宗族组织不同,现代宗亲组织的核心人物一般是新乡贤,他们往往得到国家的认可,同时又受到熟人社会及宗族文化的熏染[2],乡村民众对这些传统“士绅”型乡村精英人物认同度极高[3],宗亲组织的民众基础比较深厚。当今不少对宗亲组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层面,认为城市一级的宗亲联谊会虽然是依宗族文化建立,但其实质目的是获取社会资源,取得个人利益。本文聚焦的是宗亲文化的发源地乡村地区,与城市不同,乡村地区对传统宗族文化不仅有强烈的情感,且传统祖先祭祀礼仪已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及社会交往中,因此,相较于城市宗亲联谊会的经济目的,乡镇宗亲联谊会对民间社会事务更为关注,宗亲联谊会在乡村地区发挥的社会治理效能也比城市宗亲联谊会高。
本文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将宗亲组织放置在“中间社会”视域下进行审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状态逐渐由建国初期的“单位社会”向“中间社会”转型[4],政府对宗亲组织的政策已发生极大变化。宗亲组织作为民众文化认同度高的社会组织,在“国家”与“个体”间扮演着桥梁的作用,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利用传统“礼法”调和政府“硬法”的民众不适性,弥补当前乡村社会传统习俗法治的不足[5]。宗亲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动员作用也能推动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进程,同时,有利于推动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6]。
2 田野调查情况
2.1 调研概况
本次田野调查对象为桂西南X镇周氏宗亲联谊会,访谈了H县周氏宗亲联谊会核心人员兼X镇的分管会长,并对其他成员进行了线上线下访谈调查。联谊会成立于2014年,当时X镇迎来中国经济发展大好契机,乡镇农业加工产业得到发展,社会层面的活力也随之提高,各大姓氏的宗亲联谊会在H县先后成立。在各大姓氏弘扬传统宗族文化的社会背景下,H县周氏宗亲联谊会于2014年成立,会议上周氏宗亲推举周焕洪作为县联谊会会长并兼分管X镇,并在各乡镇推选出各位常任副会长及常任理事,分管各乡镇周氏宗亲的事务。H县周氏联谊会成立时得到了县内诸多社会人士的关注和参与,在县城大酒店举办了连续几日的创立仪式,吸引了众多目光,市级周氏联谊会也对H县周氏联谊会的成立提供了资金支持及管理经验建议。由于本地的宗族理念深厚,宗亲联谊会这一社会组织在当地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周氏联谊会成立至今已吸纳了近2万人加入。不仅当地周氏人士加入,一些祖籍在H县但已在省外定居的周氏人士也纷纷返乡加入周氏联谊会,并参与捐款重建及祭拜周氏宗亲祖坟等公共活动。这些现象既体现了桂西南群众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认同度极高,又体现了宗亲联谊会在社会吸纳和民众动员上具有巨大的能量。
2.2 从“宗族”到“宗亲”
“宗亲”尽管与“宗族”相关联,却与之性质不同。“宗族”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将宗族组织定位为一种与“国家”相对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强烈的维护自身在当地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性。宗族组织往往具有族田、族规,在邻里发生纠纷时具有裁决权威的往往不是官方政府而是族长或族内长老,因此,传统乡村社会中民众对族内精英的权威认同往往会强于当地政府,权威的偏差也不利于政府在当地的有效动员。传统宗族组织对族田土地的维护本能不仅与国家的土地政策冲突,不同宗族间对土地的争夺经常造成双方或多方的社会纠纷甚至演变成械斗。虽然历史上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产生有其特有的历史地缘因素[7],也在稳定地区社会政治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近现代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及政府对宗族势力的压制,将其归为与现代化建设相背的传统糟粕,宗族组织在近现代渐渐淡出乡村社会的视野。但是长期以来的宗族文化已经深深印在乡村群众的文化价值观中,人们对认祖归宗、光宗耀祖等思想认同感极高,虽然宗族组织对现代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人们怀着对宗族或是家族姓氏的自豪感,由传统的基于固定血缘关系组建的“宗族”发展至一种基于血缘及同姓氏相联合的“宗亲”[8]。虽然宗亲组织也是以宗族文化吸纳成员加入,但其组织性质与传统宗族组织并不一样,其发挥的社会政治效应也大不相同。
在田野调研中发现,宗亲不同于传统的宗族组织,不在当地谋取政治性利益。在对周焕洪会长访谈时,他表示宗亲联谊会是个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其宗旨为弘扬传统宗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宗亲联谊会作为一个社会平台服务于同姓宗亲在当地的传统公共事务,如组织集体祭祖、修缮祠堂、解决邻里纠纷等;同姓宗亲间互帮互助、共同发展、敬老助学;在重大传统节日组织联谊活动,发扬本姓氏优秀“家风”。宗亲联谊会追求的是“家族”壮大的荣誉感以及为同姓氏宗亲发展服务的使命感。虽然其组织的核心人员及普通成员在组织活动中也会带有获取自身隐性社会政治及经济收益的目的,但与传统宗族组织强烈维护土地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目的已形成鲜明对比。“宗亲”文化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宗亲组织的传统性与普世的现代性可以形成一种“互以为力的双元体”,体现出乡村治理多元化趋势下的兼容性和中国社会历史的传统特质[9]。
3 宗亲组织中间社会性构建
3.1 参与社会多元治理
乡村普通居民对能人式领导较为崇拜,在传统事务的处理中对社会权威人物的依赖性高,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反而不高甚至较为排斥。由于现代法律体系与传统礼法之间存在张力,基层政府在传统事务处理上显得力不从心。如近年来X镇居民坟山纠纷及土地所有权争端中,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物证材料,乡镇政府难以有效处理此类争端。且上世纪乡村民众土地所有权意识并不明显,在访谈中,民众表示以往老人去世后,大多只与附近居民口头协商或立字据即可下葬,双方本着传统习俗,农业种植时避开坟山即可。然而如今乡镇土地开发利用规模化及坟山增多导致土地紧缺,乡村居民不侵犯坟地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传统事务的纠纷矛盾逐渐凸显。这些争端由于具有历史因素,基层政府难以有效解决,即使强硬做出裁决也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不满,反而加剧了乡村居民与官方权威之间的冲突。传统事务处理更需要借助一个社会性的中间组织来有效解决。
传统争端解决缺乏一个社会权威,而宗亲组织在传统宗族文化的天然优势则更易为社会纠纷提供一个解决的平台,更能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宗亲联谊会的属性使得其在乡村社会的传统事务处理上有一定的公信力,加之联谊会核心成员在乡村社会威望较高,在处理当地本宗亲纠纷上较有公信力,联谊会对宗族史及宗亲史的资料参考使其能更好地处理传统纠纷。在调研期间,X镇联谊会便在当地政府的推荐下,解决了一桩政府难以解决的本宗亲之间的纠纷。当时镇上某村的几个家族因为传统祖坟产生较大争议,甚至发展到需要县公安部门介入,但官方介入后案情变得更为复杂。双方当事人都认为家族的事让官方介入,“有辱家风”,认为家族的事应该以家族礼俗为标准。在宗亲联谊会介入后,双方觉得由联谊会负责人做裁定权威更合“礼仪”。当地村的分管理事是位年长的退休干部,乡村社会中尊老的礼俗使其在当地有较好的风评。分管理事以自身记忆作为依据,并以乡村社会中人情世交为依托,表示邻里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是传统美德,先以传统礼俗安抚好两家情绪,随后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并且圆满解决。此次案例不仅体现了宗亲联谊会在传统事务处理上的优势,也表明了宗亲社会组织在乡村多元治理中的有效性。
3.2 进行乡村社会动员
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上更具有效率,社会组织动员性的优势也正好可以弥补官方动员的不足。宗亲组织便是建立于人们对传统宗族情感的认同之上,乡村居民对宗亲联谊会的认同使得宗亲联谊会在乡村社会的号召力更强,在公共事务政策推广中群众抵触感更弱。
宗亲联谊会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往往会在乡村中组织一些公益活动,除了传统习俗外,在助学扶贫、敬老防疫上同样为社会作出了贡献。H县周氏联谊会每年都会组织各种公益性活动,每年暑假期间联谊会为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也组织扶贫、志愿活动等公益活动。在扩大联谊会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展现了联谊会在社会动员上的优越性,有助于推动乡村居民参与公共生活。在调研过程中,X镇的联谊会成员普遍对联谊会会长高度认同,认为其充当着类似族长的角色,在乡村有喜庆事时不会忘记乡亲们,经常主动请宗亲们到其公司参与活动及宣讲当前政府在传统公共事务上的政策。在乡村熟人社会的情境下,以联谊会为载体进行政策传达,往往比政府单方面宣传更有效果,如外省宗亲返乡防疫政策或疫情期间文明祭祖政策等方面[10]。联谊会在乡村社会的动员性有助于乡村社会活力的提升,也能作为中间性的社会组织为政府传达政策,为民众提供助力。
3.3 克服乡村社会原子化
在“中间社会”理论中,有学者认为中间社会的崛起有助于克服社会原子化及极权主义。建国初期国家为摆脱无序、混乱的社会状态而建立一种“国家—单位—个人”的联结体制,改革开放后中间社会开始崛起,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开始重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逐渐由“中间社会”取代“单位社会”,宗亲联谊会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
宗亲联谊会的兴起与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是市场机制导向的产物。周焕洪会长表示在2010年前后H县的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政府对民间宗族文化的管制也开始变松,依托于宗族文化的宗亲联谊会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联谊会的发展使国家与个体的联结得以依托于社会组织,在“单位社会”逐渐褪去,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缺乏载体时,宗亲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克服乡村社会原子化。相较于政府的“强措施、硬治理”,宗亲联谊会更加有弹性,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充当调停平台[11]。
3.4 吸引社会资本和人才回流
人们对宗亲文化的认同已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从社会层面推动乡村振兴。宗亲联谊会虽是以文化传承为主要功能,然而基于人们对宗亲文化的认同,已使联谊会当前的文化功能往经济政治上延展。
宗亲联谊会的核心成员具有新乡贤的特征,成员不仅有退休干部,也有当地的商业精英,这些人加入宗亲联谊会后,整合了当地社会资源,对当地的现代化建设有着较强的推动作用。周焕洪会长谈到,联谊会建设过程中,得到省城周氏联谊会总部及外省宗亲的鼎力支持,一些经济能力较好的宗亲不仅返乡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而且捐赠巨资给联谊会,同时,他们对家乡发展也很关心。因此,联谊会在社会效应上能整合社会资本,推动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农村地区的精英回流,以及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返乡、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在离乡打工的周氏宗亲中,不少人看到联谊会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基于乡村居民对祖宗土地的情感,十分愿意返乡工作,且他们都希望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有一位像“族长”一样的领袖为其工作生活创造有利的条件。近年来周焕洪会长的产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在X镇建设了茉莉花旅游工业园等项目,项目开张时也宴请了家乡的宗亲们,以便联络感情和进行宣传,不少外省打工的乡亲知情后,返乡务工的热情很高。
4 结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
宗亲联谊会基于传统宗亲文化,又处于城镇化加快、中间社会崛起的大背景下,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宗亲组织成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的产物。从文化功能上看,宗亲组织可以弘扬优秀家风、纪念祖先等传统文化;从社会功能上看,宗亲组织能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充当中间角色,能增强乡村居民的群众动员性及成为国家与个人间的联结载体。宗亲组织若在官方的有效引导下,也能成为乡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然而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仍会有偏差,其亦有组织性弱、管理难度大、容易导致人治等弊端。若想发挥好宗亲组织的积极作用,仍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平衡。
4.1 礼治与法治的平衡
乡村社会治理是法治、礼治与自治的有机结合,这三者治理的主体又有不同,法治是最基础的保障,然而群众对礼治的情感认同普遍较高。虽然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已经得到不断完善,但在传统文化方面仍有欠缺的地方。如上文提到的桂西南地区因上世纪中期至末期乡村坟葬制度的缺失,使得至今该地区的坟山争议不断。因此,在法治的基础上难以解决的传统争议,在以新乡贤群体为核心人员的宗亲组织以礼治的方式介入后,会更容易被群众接受。
与规范的法治相比,礼治的基础是约定俗成的“软法”性质,始终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且乡村居民对礼治方式的认同有一部分原因是对法治的抵触,乡村治理过度依赖礼治也会削弱法治的权威性。而礼治的解释权难以有明确的标准,其裁定更多依赖于乡村社会中德高望重的新乡贤群体,可能最终造成偏向于人治的局面。因此,宗亲联谊会在发挥其礼治功能时,需要做好与法治的平衡。
4.2 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
宗亲联谊会是一个在现代体制下创立,需要在民政部门注册监管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具有会长、常任理事等组织结构,核心人员也是在推选中产生的,本质上是为本姓氏宗亲服务的公益性组织。虽然其核心理念为传统宗族文化,但与传统宗族组织那种以道德礼法、血缘关系为依托,具有与国家对立性质的社会团体不同,宗亲组织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整合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地方发展,其既具有传统性的文化功能,也有现代性的经济政治功能[12]。
然而,在宗亲联谊会运作的过程中,现代性功能与传统性功能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宗亲联谊会的主要工作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纪念祖先,然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宗亲联谊会的经济政治效益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延伸,一些以联谊会为主体成立的宗亲商会开始出现。宗亲联谊会虽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宗亲组织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型的社会组织,在联谊会内过度追求政治经济收益,会使得其传统性主旨受影响;当然,过度追求组织的传统性也会使其陷入僵化的状态,难以跟上当地现代性的发展步伐。
4.3 社会治理与政府管控的平衡
当前国家强调要发挥社会治理能动性,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动员群众上的优势。政府要简政放权,让社会来处理社会的事,打造“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宗亲组织在社会认同和社会动员上的优势,表明了其在社会治理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若与政府官方对接协调,在现代化建设、公共政策传达落实上也有很大潜力。
然而,“强国家”与“强社会”在当前仍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管控仍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于对传统宗族组织的消极性影响的担忧,政府对宗亲组织的态度虽然没有反对,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支持。虽然周氏宗亲联谊会在H县已经运营多年,但是当地民政部门仍然没有对其进行社会组织登记。当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较为薄弱,很难在放权与管控中做到平衡。宗亲组织不像官方组织那样拥有严密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制度,组织运营依赖于对宗亲文化的情感认同,工作人员及常任理事没有固定的薪资,甚至依赖于核心人员的资金支持。联谊会的核心成员年龄皆偏大,是对宗亲文化认同度极高的群体,组织的发展依赖于核心人员的领导力与实力。过于依赖“克里斯玛型”精英人物的领导,社会治理容易陷入人治的误区,因此,政府也需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控与指导,以便在社会性与国家性中找到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