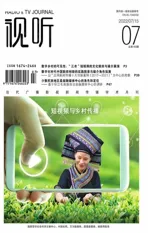激活·重塑·认同:家庭年代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2022-07-19郑文艺
郑文艺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的存续,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①。家庭年代剧通过重塑空间场景、历史重大事件、平民百姓生活方式等,聚焦于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维度,激活与唤醒受众的集体记忆,并将受众“带领”到过去的年代,充分调动受众的参与性,使其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记忆表达,以增强电视受众的情感认同。《人世间》《父母爱情》《金婚》《闯关东》等家庭年代剧通过真实还原一代人的现实生活,激活受众的集体记忆,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国家认同感,从而探讨集体记忆构建产生的现实意义。
一、激活与唤醒:记忆碎片的还原
“照片、报告文学、回忆录、电影被保存在客观化的过去的庞大数据库里。而进入现实回忆的道路之门并未因此而自动打开,因为还需要所谓的第二媒介,即那些可以再度激活所存储的记忆的媒介。”②如果说老照片、旧图像和文字信件等可以帮助受众储存记忆,那么电视剧作为大众媒介则可以激活和唤醒受众的集体记忆。
(一)营造:空间场域的“再现”
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一文中提到“名字”“土地”“劳作”“房子”“物件”“祠堂”“仪式”,“家庭记忆就好像植根于许多不同的土壤一样,是在家庭群体各个成员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③也就是说,家庭年代剧中出现的土地、房子、物件等符合时代特征的场景都可以作为承载记忆的历史媒介,激发受众的自主想象与情感投入。
家庭年代剧形成一系列直观的空间场所,从而激活了历史记忆。房子就代表着“家”,老房子能够瞬间将受众拉回过去。《人世间》中,周家老宅墙壁上的毛主席挂像、砌起来的火炕、贴满报纸挂满冰霜的木窗等室内布景很有20世纪70年代北方的感觉。《父母爱情》通过使用长镜头、全景镜头和移动镜头来展现炮校、岛屿、几位主人公房子的构建以及彼此之间的方位等,让受众感受到空间感以及整体风格。《闯关东》中多变的空间场景、丰富的人物身份、广阔的风物景观增强了电视剧的历史感。家是最小的社会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小的叙事单位。家庭年代剧十分注重对家庭的还原,无论是对人物的真实刻画,还是对空间场域的再现,都能唤醒受众对家的回忆与思念,直击其内心深处的灵魂。
家庭年代剧再现了过去极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空间场景,高度还原了时代的质感,营造出浓厚的时代氛围,勾勒和再现群众的记忆场景。家庭年代剧还激活老一辈受众的空间联想,使其回忆起自己曾经在这些地方的种种经历,使受众更能融入剧情以及剧作构建的空间场景之中,从而唤醒尘封已久的记忆。
(二)正视:历史瞬间的定格
每一个时代的人民心中都有其独特的记忆,重大历史事件可以唤醒存在人内心深处的模糊记忆,通过呈现出某一个事件的鲜明特点,即可勾连出浓厚的情感共鸣。集体虽然是看不见的物质实体,但却是无处不在的,对人的个体化、社会化产生着重要影响④。
要正视历史,客观地讲述过去。一方面,可以唤起老一辈人的青春记忆,更重要的是让年轻受众正确看待历史并且感同身受。年轻受众对于“建设兵团”“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市场经济改革”等可能只停留在书本上的大体认知。《人世间》中,“知青”岁月、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申奥成功等一件件国家大事都与个人的感触交织在了一起。在现在看来,剧中周秉义与百姓们的斗智斗勇,展现了利国利民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住房问题解决、改革开放等工作进程的推进与民生问题的解决,让受众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金婚》巧妙地运用了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客观地将三年灾害、大饥荒、改革开放等那个年代的重大事件,穿插在小人物佟志和文丽的婚姻生活中,与受众共同见证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的成长轨迹。
家庭年代剧对在改革开放、下海、恢复高考、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等国家重要发展时期做出的不同选择和决定的人们进行客观的描述,做到不偏颇、不片面,使得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看待过去。家庭年代剧也将老一辈的受众拉回过去,把家事与国事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折射出时代的风起云涌,掀开一代人的回忆。
二、重塑与缝合:记忆曲线的编织
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重塑。“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⑤家庭年代剧通过展现平民百姓的生活百态,对受众脑海中的记忆碎片进行视听方面的重塑,并缝合成一张受众都认可的记忆大网,将过去真实地展现在受众眼前,产生时空共情。
(一)以“时间推移”为主导,演绎时代变迁
家庭年代剧以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大事串联起来,以“时间推移”为主导,展现小人物在国家发展中的抉择与成长,编织成一张可堪回首的记忆之网,演绎时代变迁。对个体来说,别人需要保持对他们的鲜活记忆,否则个体就会忘记某些事实的许多细节⑥。《人世间》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从1968年到2016年东北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在通讯上经历了从写信、公共电话到现代化的手机的转变,在出行上经历了从自行车、火车到飞机的转变,在用水上经历了从提水桶排队接水到使用自来水的转变。该剧借助人物生活方式的改变重塑受众脑海中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并对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关键点进行深入的剖析。
群体的记忆需要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并且在个体记忆中体现自身⑦。从人物择偶观的改变来看,《父母爱情》中,从江德福头婚被父母包办婚姻,到通过媒人介绍与安杰相爱,再到儿女们的自由恋爱,剧中个体在择偶过程中逐渐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人物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紧密相关。家庭年代剧叙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几十年间的变化和家庭中几代人在不同的生活年代完成不同的人生梦想和时代使命,而且是对中国时代变迁的描摹。
(二)以“个体命运”为主体,映射国与家的交融
家庭年代剧撇开大人物、大主题的宏大叙事,通过平实叙事构建集体记忆,拉近了大众媒介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⑧
家庭年代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普通的个体,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感受平凡的事物,代表了过去那个年代整个群体的形象,展示出人民的朴素与真挚。同时,每个人物的人生轨迹都会在国家和个人生活交叉中被悄然改变,个人命运的沉浮都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人世间》围绕经历过下海、市场经济改革、住房改革等事件的不同人物进行讲述,将小人物与国家事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展现老一辈人的奋斗历程,描摹出一段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奋斗史。《闯关东》中,朱家命运的跌宕起伏总是与国家时局的命运根脉相连,透过“小家”的命运多舛,折射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国家民族的前途走向。剧中的人物关系并不是分散的,而是呈网状连接起来的。该剧以个人的命运反映家国历史,为受众展现了不一样的时代图景,促使受众形成总体集体记忆。
家庭年代剧在个体记忆和国家命运间架起了一座情感桥梁,实现“家国一体”的文化理念,也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将“小家”与“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微观个体与时代近距离接触。
三、情感与价值: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反过来也可以说,意义与经验决定了人们的认同⑨。家庭年代剧不仅要构建受众的集体记忆,使之产生情感共鸣,还要激发民众的深度思考,传递丰富的价值认同。
(一)平凡个体塑造自我的身份认同
认同有两重含义:“一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二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⑩若受众在观看影片时,与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或者人物的命运存在着某种相似性,那么受众可能就会产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从而产生共鸣。
1.主体地位中的自我认同
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奋斗历程,与剧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从而产生自我的价值认同。《人世间》中,周秉昆这个角色饱满立体,具有“多面性”。他是一个普通人,有着作为普通人的真善美。从干酱油厂工作到“下海”搞饭店,再到开教育书店以及出狱后做搬家生意,周秉昆体现出父辈人的付出与坚持。该剧通过塑造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人物形象,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交织缠绕,勾起受众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同时也使得受众深切领会到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人民的奋斗与付出是时代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该剧呈现出“小家”与“大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图景,赋予受众强烈的主体性。
2.人物关系中的情感认同
受众能够通过剧中的人物情感找到自我映射,从而唤起同理心,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金婚》中,佟志和文丽即将搬进两居室的新房子里,但是佟志在搬家前一晚失眠了。搬家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小屋见证了夫妇二人的新婚、生子、与邻居相处等点滴生活。受众大多经历过搬家,而《金婚》通过搬家唤醒受众对过去的回忆,从而产生对于家的情感认同。老一辈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是很多年轻人所向往的。《父母爱情》中,在江德福和安杰的爱情面前,“门不当户不对”的羁绊显得微不足道。他们相守共度了一生,成为婚姻楷模,将中国式的父母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家庭年代剧对于爱情的书写和刻画,使得年轻受众产生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同时也勾起老一辈受众自己的爱情回忆,从而对于婚姻产生情感上的认同。
(二)时代变迁建立个体的国家认同
家庭年代剧带领受众重温中国故事,在激活和重塑受众集体记忆的同时,引发受众强烈的家国情怀,从而凝聚国家认同。媒介记忆研究成果显示,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深刻影响着受众的家国意识⑪。
1.国家成就中的政治认同
家庭年代剧激活了受众的时代记忆,也在构建集体记忆的同时让年轻受众群体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和感受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唤醒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强化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人世间》以一群小人物的奋斗历程向受众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获得的跨越式发展,其中深圳特区的开放催生了一大批年轻而又多元的产业,骆士宾、水自流趁着改革的东风在深圳创业成功,并做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记忆可以作为一种粘合的力量,起到持续、团结的作用。”⑫家庭年代剧描绘了一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图景。看着新中国日益强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受众对于祖国的自豪感日益增加,促使其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策在其中的积极指导作用,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政治认同。
2.民族发展中的文化认同
“群体认同与个体记忆的互动传播则形成了文化的传承与精神的共鸣。”⑬家庭年代剧在重塑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深入挖掘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特质,激发文化自信,同时也勾勒了受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完成历史的承续。《人世间》光字片街道的名字分别由仁、义、礼、智、信组成,象征着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彰显出人与人之间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父母爱情》深刻传递了“知恩、感恩、报恩”等价值观,如江德福在退休后心里也一直记着老校长对自己的赏识与帮助,并与安杰一同看望老校长。重构过去强调的是集体精神的挖掘⑭。家庭年代剧通过讲述一个个时代故事,展现了民族文化对家庭文化的影响,将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时代精神和国家文化,使受众产生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
四、结语
家庭年代剧的叙事和传播兼顾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像符号,将平民视角下的个体记忆串联缝合,构建集体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受众早已不是荧屏前的旁观者,而是剧情中的参与者,仿佛与剧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年代,共同经历时代的变迁。新时代的家庭年代剧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历史与现实生活,将“小家”与“大家”连接起来,挖掘有时代内涵的典型人物与事件,创新创作方式,使受众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建构起时代的集体记忆,凝聚并强化受众对集体的价值认同。

注释:
①⑦⑧⑭[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40,71,93,59.
②③[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109.
④李保森.《国家相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J].电视研究,2018(03):47-49.
⑤[德]扬·阿斯曼.文化的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9.
⑥⑨[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180.
⑩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50-53.
⑪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
⑫大卫·格罗斯,和磊.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J].文化研究,2011(00):37-56.
⑬马东丽.文献类纪录片建构集体记忆的媒介功能探析[J].当代电视,2021(11):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