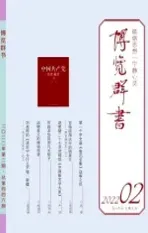《人生的容量》,死生由命和马克思那句话
2022-05-30赵勇
赵勇

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
2011年出版《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时,我没想到它会有些反响;更没想到的是,我在朋友圈里还落了个“会写散文”(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写)的名声。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甚至以刘勰的“情信而辞巧”为标题,写文章夸我,这既让我惭愧,也有些意外。想当年,我的博士论文成书时请他赐序,这个序是等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的。而这一次,他却速读速写,主动为之,莫非拙书真对他老人家有所触动?
我后来没有金盆洗手,而是继续写着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文字,很可能就与众师友的谬赞与鼓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许多时候是我确实想写。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人生经历既无高光时刻,也无华彩乐章,“旧”由我这样的人来“怀”,“就如同平胸的舞娘跳脱衣舞”,是很容易被人笑话的。但问题是,虽然寒酸,尽管平淡,却又总有一些瞬间或片断让我感到神奇或不可思议。它们在我的记忆深处哭着,笑着,叽叽喳喳着,仿佛是要破门而出,又仿佛是要让我另眼相待。实在嫌它们闹得慌时,我就只好把它们拽出来了。
于是有了上编内容——“私人生活”。
但这样一来也很危险。我的私人生活本就灰头土脸,如今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难堪自不必说,有时甚至还容易惹事生非。记得一位学生读过我的某篇文章之后很认真地劝我:这篇适合您80多岁以后发表,现在拿出来或恐他人说三道四。也许她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我能不能活到那个岁数呢?
壹
“人生的容量”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刘再华的说法,如今我把它用作这本书的书名,或许表达了我对死生由命、人生无常的感喟。79岁那年,童庆炳老师的生命突然终止在金山岭长城的台阶上,令人震惊;56岁那年,席扬先生一头栽倒在晨起锻炼的路途中,长眠不醒;51岁那年,刘再华同学与病魔搏斗几年之后驾鹤西去,不辞而别;26岁那年,我那个新婚不久的外甥突遇不测,一家人因此伤痛不已……而就在我写着这篇后记时,师母梁湘如女士刚好私信我,说梁归智老师已在问他的主治大夫,他是否还能活到这个月月底。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死神已在向他招手。可是4个月前,他还来我家里聊过啊。那个时候,他把酒话红楼,谈笑坐怡怡,全然不知自己身体中潜伏的杀手正准备向他发起攻击。梁老师生于1949年,如果能挺到月底,他就接近了自己的70岁生日。
因为震惊、悲痛、忧伤以及对生命的叹息,所以又有了下编内容——“秋叶静美”(取“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之意),那是长歌当哭的替代性表达。
当然,即便是长歌当哭,那里面也有我的私人生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绝望地想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语录,以此为我的假公济私,不得不写撑腰壮胆;而私人生活在长歌当哭中蜿蜒,它们固然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呈现机会,却也不可能不含着悲音,透着寒意,行行重行行,五里一徘徊了。结果,我的私人生活除了灰头土脸,还成了本雅明所谓的“悲苦剧”。
这个集子如此设计,与资深编辑向继东先生的约请有关。我与向先生相识于2017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随后,他约我加入“学术人生”丛书的写作阵营,我欣然从命。但这套丛书却因故流产了。因为这次交往,他知道我还有些散文家底,也希望我能把那些比较私人化的文字汇总起来,结集出版。我接受了他的美意,也决定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只是刚编了两辑内容,就已达到了他所说的字數规模,其他的文字也就只好弃之不用了。
收在这里的大部分篇什曾在《文艺争鸣》《山西文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新京报》《人民画报》《中国画报》等报刊上先期面世,但也有几篇并未正式发表,只是用我以前的博客现在的公众号推送过。没有发表的原因,一是我并没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二是觉得它们都是些练笔之作,还需要修改。但实际情况是,它们往往被新的写作迅速覆盖,待我想起来修订,已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一次因为成书,我又集中把它们顺了一遍,总算是可以定稿了。
感谢南京大学教授赵宪章老师为拙书作序。记得第一本散文集面世时,我曾奉上那册小书,请他指教。没承想,他不但读了我那堆粗服乱头的文字,而且还“到处逢人说项斯”,夸得我一鼓作气,整整高兴了三年五载。何以如此?盖因他之赞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也不得不兴奋得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这次我必须请他出山,赐序作文,为拙书增色。同时,我也决定,一俟该“犬子”呱呱坠地,我要一下子送他十本。
感谢为我提供珍贵照片的师友。为了把这本书打扮得好看些,我决定像上一本散文集那样,继续“有图有真相”。但我自己的收藏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便只好劳驾我的启蒙老师司玉莲、音乐老师王翠莲,知青丁大霞、作家聂尔、村里同学李翠林等,帮我找图。据说,当年我们村的供销社只进了三个“号志灯饭盒”,一个被我家买回,一个被女同学家请走,第三个下落不明。如今,我家这个已没了提手,女同学家那个却完好如初。莫非她像《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一样,悉心照看它,经常擦拭它,让它保持着革命本色?我从李翠林处得此信息,大喜过望,便派她把这盏“号志灯”请到庙里,在我的遥控下拍出了一张满意的照片。因此,我要特别谢谢她和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同学。
最后,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向继东先生为这些闲散文章提供集中亮相的机会,也感谢北京分社段洁总编辑和王苹编辑的辛苦付出。向先生有意与我继续合作,我也希望这只是合作的开始。
贰
这本书面世后,我开始使劲吆喝,这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其实我也不适)。一位网友在我的宣传文案下跟帖评论道:“一个大教授,为本小书居然都会这么卖力推销。出版社应该给老师发特别奖。”我只好借坡下驴,低头认罪。如今我要说明的是,书确实是小书,教授则不能说大;出版社当然不会给我发奖,但我的“卖力推销”却不能说与出版社无关。
如前所述,这本书是受资深编辑向继东先生之邀鼓捣出来的,那是2019年10月。大约一年之后,因泥牛入海无消息,我问向先生,方才知道书稿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分社。在我的过问下,分社领导段总高度重视,说很快进入相关流程。于是借书稿启动之机,我又对它做了一些增删(主要是删,向先生说字数多,篇幅长),找了一些图片,也请赵宪章老师赐来序文。而在2021年春夏时节,分社王苹编辑则请我看清样,选封面,并与我商量封面文案。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她说9月即可见书。
但9月没出来,接下来的几个月也动静全无。到年底时,我终于绷不住了,询问王编辑,她才告诉我:“因为咱们这本书会做成精装的,制作成本稍微有点高,所以高总说先暂缓出版哈。”高总是谁我没问,但我觉得“暂缓出版”并非什么好兆头。当然,出版社有它的考虑我也能理解,加上我出书的愿望并不迫切,也就索性听之任之,不管它了。
春节前后,向先生主动与我联系了。从他那里,我才弄清楚了事情原委。原来分社出书是单本核算,每本觉得能够赢利才会考虑出手。而据我猜测,我的书之所以按下暂停键,应该是出版社对它信心不足。向先生说,既如此,咱们不妨把书稿拿回总社,也省得给分社增加压力。但为了把印张降下来,他希望我再删书稿,最好能删到320页以内。而且,此前我签的是4000册起印的出版合同,如果我能同意再签一个补充协议,改成2000,书即可运作起来。
显然,分社的这一搁置,也让向先生失去了信心,但我却心有不甘。我说,当年我出散文集,起印好像是六千左右,后来也卖光了。我肯定缺少市场号召力,但销量也不至于那么差吧?
正是在这种七上八下的心境中,向先生向我介绍了接手我这本书的总社责编钱飞遥女史。我跟钱编辑说,遵向先生旨意,我得往下删一删篇幅。大致琢磨之后,上辑中《遥想当年读路遥》似可刪除,《过年散记》中写我外甥的那一节比较长,亦可拿掉。但实际上,我是不太想往下删的,原因说起来倒也特殊。当年我写《外甥多仿舅?》,也算是自曝家丑,我父亲不希望我拿出来,我也决定让它沉入遗忘的黑暗中。但此文写出3年后,没想到我这个年仅26岁的外甥突然亡故。我现在把它公之于众,其实也是纪念。
钱编辑说,是否作删减,何处作删减,待她读过书稿后再说。而阅读既罢,她也只是问我《北京有多远》能否删除,其他内容则应该全部保留,应收尽收。她对我说:“您写得很好,很真挚,没有虚情,我做编辑一看就知道了。大部分人写作都有点矫情。”
懂行,中国好编辑!
为了这位“懂行”(这是汪曾祺对编辑的赞语)的编辑,为了我这本基本未做删节的小集,我决定理直气壮地吆喝,明目张胆地宣传。同时,我还想告诉亲爱的读者,我那本《刘项原来不读书》也刚刚面世,要么您就两本书搭配着读?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或者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了窗前呐,咱们两个学《毛选》。老头子,哎!老婆子,哎!你看咱们学哪篇?”
这么一来,说不定您就能读出一种特殊的味道。如若不信,有诗为证:
人生有容量,昼短苦夜长。
刘项不读书,名高实秕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