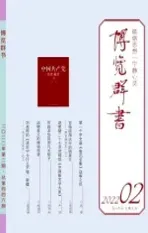古代,在黄河上游驻牧生息的他们
2022-05-30杜志强
杜志强
黄河上游地区,指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流域。黄河上游流经青、川、甘、宁、蒙、陕、晋七地,河道长3471.6公里,流域面积42.8万平方公里。在黄河的上、中、下游中,上游河道最长,流域最广,哺育之功亦最大。民谚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是仅就黄河的农业灌溉之功而言,如果从民族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则围绕着黄河的几大支流,如湟水、洮河、无定河、汾河、渭河等,与黄河干流一起,织成了一张哺育民族、滋养文化的大网,在华夏文明的浩瀚行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渭河平原(关中平原),扮演了文明根基的角色。
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民族概况
黄河上游地区是民族融合、发展的最天然的舞台和最热烈的熔炉,甚至可以说,凡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绝大多数都在这个区域生息、斗争过,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
先秦时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完善,因而,有些先民群体只能算是部族,如被舜迁往“三危”一带的“三苗”(“三危”大致在隴右范围内),周穆王西巡时会见的西王母部落,以及早期文献所记载的各部戎人、狄人部落等,他们分布在甘肃、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戎、狄还曾与周、秦、晋等国互有攻伐,深度地参与进先秦的历史中,但在秦统一前后,大多已经融入华族之中。
汉代以后,民族共同体发育完全,族属关系就显得更为清晰,一些重要民族如羌、氐、匈奴、乌孙、月氏等,都特色鲜明,纷纷登场。
羌族是自先秦以来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对黄河上游地区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民族。他们最早居住在河湟谷地,汉代以后逐渐向西北、东南迁徙,分布在甘肃全境以及关中地区,陇南、川西北一带尤为其聚居区。在中古历史中,羌族人民发起的斗争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东汉政府曾经一度因此而有弃凉州之议,边郡内徙亦屡见不鲜。
乌孙、月氏主要生活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带,匈奴强盛之后,他们或者被同化,或者迁至西域或河湟,对主流政治影响较小。匈奴是对汉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民族,按照王国维的观点,狄、匈奴来源于先秦时期的猃狁,历史悠久。
另外,生活于川陕甘交界的氐族,在汉代发展迅速。西汉设金城郡,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氐人的统治。东汉末,氐人已经遍布于陇右、关中一带,“其人半秦”,且“多勇憨”(《华阳国志·武都郡》)。三国时期,由于氐人众多、且处于川陕甘交界的地缘特点,因而氐人成为各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他们极为活跃,在隗嚣割据天水、马超转战陇上,以及曹魏、蜀汉争夺武都、天水、汉中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平衡力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力减退,周边各民族纷纷乘时而起。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建立的十六国政权,正体现出这些民族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其中羌、氐建立的“五凉”政权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河湟一带;鲜卑、氐人建立的“三秦”政权主要分布在关中、陇右、陕北,前秦还曾一度统一北方;鲜卑慕容部建立的“五燕”政权中,西燕定都关中,匈奴、羯族建立的“二赵”政权,虽然没有定都于黄河上游,但其攻伐征战无不以关中为目的。由此可见,这些民族力量的征伐,其核心着力点是关中地区;进而可以理推,关中一带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地区。围绕着渭河平原,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斗争、融合之潮风起云涌。
“十六国”之外,黄河上游还有一些范围更小的割据政权,如仇池、宕昌、邓至、枹罕、滇零等,以及由鲜卑慕容部发展而来的吐谷浑部,都有或长或短的割据时段,吐谷浑甚至国势雄厚,一直延续至唐代中期。
唐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的民族力量角逐,波澜壮阔,突厥、吐蕃、回鹘、党项、女真,无不实力强劲,深度走入中国历史。同时,一些存时较短的小部族,如沙陀、粟特、嗢末、龙家等,亦活跃于时代舞台。就黄河上游而言,主要是突厥、吐蕃、党项等族。
突厥征战的足迹则遍布黄河上游地区,在河西走廊、河套、山西一带,生息着大量的突厥人。隋末突厥国势最盛,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俯首称臣。唐太宗时,唐朝与突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征战,规模之大,堪比汉匈战争。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他们在攻灭吐谷浑后,国势强盛,成为唐政权的又一个强劲对手,安史之乱以后,整个河西、陇右地区都成为吐蕃的地盘。党项族源于河湟一带,又被称为“党项羌”,唐代中期,他们迁至陕甘宁地区,最后在灵武一带崛起为雄踞一方,与辽、宋鼎峙的政权。党项政权完全处于上游黄河的滋养之下。
元明清时期的黄河上游,主要是蒙古族、满族的活跃舞台。由于蒙古、满族居于全国的统治地位,所以,黄河上游地区有他们征战和驻屯的许多遗迹。其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凉州会谈”。1246年,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来凉州(今武威),与凉州的蒙古宗王阔端会谈,最终确定西藏纳入元朝版图,阔端授权萨班代理西藏事务。会谈结束了西藏社会持续四百余年的政治分裂,更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
这一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形成——回族。回族受中亚伊斯兰文化影响,在元代形成民族共同体。明朝廷规定,中亚、西亚各国商人、使臣只能经过河西走廊与明朝交往,于是,整个河西、宁夏、青海、陕西就成为允许回回人寄住、留居的主要地区,也就成了回族的聚居区。这个历史,大致奠定了今天回族的分布格局。最终,回族发展成为我国人口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
黄河上游地区古代民族的文化状况
早期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游牧特点,如逐水草迁徙,以穹庐为帐,以乳酪肉食为主,礼节与法制相对简单,政治上的军事部落制等;同时,他们天性勇敢,人习骑射,尚少壮、轻老弱,早期甚至多有收继婚制(妻后母)。就这些情形而言,确实要比中原汉民族的文化明显落后。落后的文化制度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能保证权力安全传递、进而导致其旋起旋灭的根本原因。
当然,落后的文化里也肯定有积极因素存在。比如他们的勇敢善战、人习骑射,这必然会影响到周边人民的生活习性。对此,班固曾有分析: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这是班固对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民风的分析。这里正是黄河上游地区,其中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属甘肃,为洮河、渭河、泾河流域;北地郡治府在庆阳,辖境包括宁夏南部,为马莲河流域;上郡即今陕北,属无定河流域;西河是由上郡分出来的,大致为今天的黄河中游。班固认为,六郡“迫近戎狄”,所以才形成“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的风气;汉匈战争中,“六郡良家子”威名赫赫,“名将多出焉”。
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周边各族都有着学习和借鉴的需求,他们需要中原的物产和技术。而中原政权出于大汉族立场,许多时候都不予应答或拒绝,即如马市一事,需要在多少次的请求和武力胁迫下才能同意,事实上,中原需要良马,民族政权需要中原物产,因而是双赢的事。此外,北方少数民族多能迅速吸纳汉文化,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比如羌族的早期人物无弋爰剑,被秦人虏为奴,在秦地,他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后来他逃回湟中,大大地改进了羌人的农业生产,使羌族较早地进入农耕社会。农业之外,他们对中原制度的学习更为典型。河西的几个民族政权,对于沟通西域和坚持中原制度,都非常积极。融合西域和中原音乐的大型乐舞《西凉乐》,就诞生于张轨的前凉政权;对佛经翻译产生深远影响的鸠摩罗什,就是后凉吕光从龟兹掳掠来的。而鲜卑的北魏政权,更是全面系统地、轰轰烈烈地推行着汉化政策,体现出何等宽广的胸襟和宏大的气魄。玄奘的西行求法,如果没有河西和西域政权的资助,仅靠满怀虔诚,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的西夏政权,在借鉴汉文化的同时,又创立文字,形成独立的文化制度。今存于张掖的西夏碑,就是西夏国古老文字的沧桑见证。而创立文字、建立自成体系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割据政权,史上并不多见,吐蕃、蒙古、满族,大致如此,但蒙古、满族都曾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政权,而吐蕃和西夏则仅仅割据一方,财力、物力尤其是人才基础都薄弱许多。由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表示赞赏。
黄河上游地区古代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原汉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最为醒目的就是大规模的惨烈战争。其实,战争仅仅是民族矛盾最集中、最激烈的体现方式,更多的情形应该是非战争的和平交流。每次某个民族的打马走过是交流,每次的交易是交流,每次的迁徙和驻牧,更是交流。遍布于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迁转之迹,以及各种遗迹、碑刻、文献等,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甘肃省博物馆藏一枚国宝级八思巴文虎头圆符牌(国内外仅两三枚),当时蒙古帝国横跨欧、亚,持此牌符,便可通行无阻并受礼遇。其遗留在甘肃,那说明持牌者行于甘肃,甚至很可能就卒于甘肃,这期间必然有民族交流存在。
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融合还对汉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汉代。汉武帝时,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形成压倒性优勢,而与之相对应的匈奴和羌族则反差明显。在这样的巨大反差,才使得汉民族的族群特点更为凸显,民族认同高度集中,进而产生“汉族”概念。如果没有周边民族的反衬,那又有什么必要来确立汉民族共同体呢?
民族间的物质交流也长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在海上丝路之前,陆上丝路一直就是中西交流的孔道,陆上丝路的黄金段则与黄河上游几乎完全对应。沿着丝路,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向中原政权贡献珍禽、异兽、异物,而且还传入了葡萄、苜蓿、玻璃、石榴、胡麻、胡豆(蚕豆)、大蒜、羌李,以及各种极有特色的乐器、乐舞。唐代时,周边民族的饮食、服饰风行一时,“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回鹘的紧身服是当时十足的流行风,与宽袍大袖的汉服反差明显。“元和妆梳君须记,髻堆面赭非华风”,元和年间女性妆扮明显不是“华风”,“赭面”(脸上涂有红色膏)是吐蕃习俗。长安城中的胡食亦极流行,烧饼、胡饼、葡萄酒,受到普遍欢迎。
马匹交易更值一提。汉武帝为获得高大神骏的汉血马而攻伐大宛,并作《天马歌》,可见中原政权对良马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汉武帝还任用善养马的匈奴人金日磾为马监,以振兴马政。吐谷浑、吐蕃、蒙古均善养马,河州、秦州、青唐以及蒙古,从来都是良马的故乡,其中蒙古马、六谷马、河曲马均极有名。著名的武威铜奔马,其原型很可能就是六谷马;而体格较小、耐力极强的蒙古马,则是成吉思汗征伐北半球的战略资源。唐代设陇右牧监,陇右遂成为军马的摇篮。明政府设立陕西巡茶御史,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设茶马司;清代在陕西设五位巡茶御史(西宁、洮州、河州、庄浪、甘州),专理茶马事务。可见,黄河上游从来都是国家战略资源——军马的来源地。
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在宗教、文学、习俗等方面,还在于民族精神的交流与融合上。中原地区固然文化昌盛,但也天然地需要周边民族强悍、英勇的血性。当中原丰厚的文化底子中融入了英勇、豪迈的血性时,中原文化便会勃发出灿烂辉煌的气象来。至今盛称的“盛唐气象”,其实就完全建立在“胡汉杂陈”精神底色之上的。唐代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胡汉杂陈的军事贵族集团,在其核心领导者身上,胡化特点更为明显。
以佛教流传而言,从敦煌以至关中的丝路沿线,密布着无数的佛教石窟,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石窟长廊。这些石窟中,由少数民族开凿的洞窟、绘制的壁画数量极多;元代时,藏传佛教甚至成为国教。这些都能反映出,在佛教东传的行程中,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的显著贡献。而每当有外来文化注入时,中国文化总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包容、消化,进而促使自身发生重大进步。佛教传入中国,正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促进。从这个角度来说,黄河上游的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小的促进之功。
黄河从青藏高原发源,融汇万流,左冲右突,历尽险阻,终于冲出群山,浩荡地奔向河套平原。然后在托克托掉头南下,劈山斩石地切割了晋陕高原。其广取博收、百折不回、一往无前的恢宏气度,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铸就了他们自强不息、蓬勃向上、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驻牧、生息在这片沃土上的各少数民族人们,如同黄河的各条支流,汇入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一同熔铸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时至今天,在国家“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政策下,我们回溯历史,理性评价各兄弟民族的历史与贡献,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论证和支持新时代的民族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挖掘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丰厚内涵。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