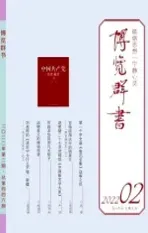从《书里书外》到作家写作的四大动机
2022-05-30党文亭
党文亭
赵勇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知名教授,出版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文学与时代的精神状况》《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等学术专著,但我看的第一本书却不是这其中的某本著作,而是他的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以下简称《书里书外》)。
记得是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漫游时发现的《书里书外》,许是书脊处富有诗意的书名吸引了我,便抽出书来先挑短的篇章浏览。《我的失语症》,有趣,文学教授竟曾苦恼过如何对外称呼自己的妻子;《给儿子的一封信》,真挚,字里行间流淌着父亲对儿子的深情;看过不少学生怀念老师的文章,但反过来的却很少见,《怀念张欣》既令人动容也让人唏嘘不已。三篇读毕,我觉得这是本值得借阅的散文集,于是便把《书里书外》从图书馆请回宿舍。待看完长文《一个人的阅读史》后,不禁感慨这岂止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它写的是一代人的阅读史和生命成长史。这样的好书有什么理由不购买收藏呢?所以“赵勇”这个名字于我而言首先是同散文集《书里书外》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第一次见到赵勇老师真人,我满脑子都是——《书里书外》的作者从书里走出来了。
《人生的容量》是赵勇教授时隔11年之久推出的第二本散文集,在谈论它的内容前,有必要先了解下赵勇教授为什么一边写论文,一边坚持散文创作。事实上,他在《书里书外》的“后记”里早已给出了答案:“散文其实是回忆之物,散文写作又是人到中年或老年的事情”,“我一下子就活到了可以写点散文的年龄,似乎也拥有了一点回忆的资格”,“我接通了自己的过去,我让自己沉浸在绵绵不绝的情绪记忆当中,因为回忆的幽光,我的身心也开始明亮起来。我意识到,我是在用这种写作为自己充电”。而从《人生的容量》的目录大略观之,会发现上编“私人生活”多是呈现作者过往的人生经历,下编“秋叶静美”则主要忆念已故去的师友和同学,由此证明了这些散文确是回忆之物。作者通过整理和书写私人的记忆,不断复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到哪里去”等命题,从而让自己活得更明白更踏实。
其次还应注意针对散文这一文体,赵勇曾强调过:
小说可以虚构,而散文不可以虚构,它需要字字句句落到实处。如果散文中有了虚构,它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赵勇:《〈我与地坛〉面面观》,《名作欣赏》2011年第22期。)也就是说,在散文不应虚构这点上,赵勇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因此,读者阅读《人生的容量》时对该书的真实性尽管可以放心。另外,真实也是作者本人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妨从《人生的容量》中搜罗一下别人对他的评价:“我喜欢赵勇什么呢?一直到写这篇序文时我才整明白,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真;如果用两个字,那就是‘纯真”;“或许是我的实诚——从小我就被人视为‘老实疙瘩——让他们意识到我是他们的同道”;“不加掩饰——这是童老师对我的评价”。所以,《人生的容量》的“真实”既是散文文体的要求,也是作者的本性使然。如此,讀者才有机会在这本散文集里看到作者小时候的一桩桩糗事:在“讲用”台上咬着半土半洋的口音说“我今年勃(8)岁了”,“自作聪明”地用旧钢笔调包供销社的新钢笔,被人高马大的女同桌欺负得哇哇大哭;看到作者暴露自己身体的创伤和心灵创伤:第一次去城里因意外烧伤腿部,第二次高考开考前遭不怀好意的同学报复,大学毕业分配时指标被他人顶替;看到作者揭开高校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和学术自由精神被扭曲的一角等。
“真实”是《人生的容量》的底色,与此同时,作者又很讲究散文的文学性。《故乡一望一心酸》里的“外甥多仿舅?”一节原本是作者写给自己的短文,因特殊原因才拿出来发表,但能看出即便是私底下写散文,作者也非常注重文章的结构安排。该短文选取的是过年期间甥舅闲聊的场景,但作者的思绪总是飘至六七年前,彼时外甥正上高中,三番两次有退学的念头,作者劝外甥坚持读完高中。往事的片段被不断穿插进外甥和舅舅们当下的对话中,读者也跟着在“当下”和“过去”之间来回跳跃,一面欣慰于作者的外甥终于长大成人,一面同情贫苦家庭出身的农村孩子成长之不易。如若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外甥的成长故事,则达不到这样强烈的阅读效果。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作者在“附记”里告诉读者“我这个外甥因不慎煤烟中毒,不治而亡”,读者再次重读这则短文又是另一番滋味,此时文章的结构或许已没那么重要了。《逝者魏填平》是整本散文集的最后一篇,它的主人公魏填平是作者任教晋东南师专时的同事,作者与他的关系算不上亲近,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他的老师宋谋瑒,就是《寂寞宋谋瑒》里的那个宋谋瑒。写自己熟悉的人不好写,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其实也不好写,很容易流于浮泛,但作者却把他不大熟悉的魏填平写到骨子里去了,让作为读者的我相信魏填平就是这样的人。这篇散文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比如魏填平请自己的老师吃饭过于寒酸让人感到不解,课堂上正讲述伤心家史时无缝衔接至“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操场上突然刮起的凉飕飕的秋风,魏填平病入膏肓时不愿同任何人说话的倔强行为,火化前被化成像国光苹果一样的脸等,而最最精彩的一处描写莫过于魏填平抽烟下棋的画面:
夏天时,他常穿极普通的的确良白衬衣,上面两个口袋各装一包大光牌香烟。不知不觉一包烟已经抽完,他下意识去口袋里摸索,发现已是空盒,就一把将它揉皱,扔掉,急忙去掏另一包。本来他刚抽完一支,却还是饿虎扑食一样把烟卷塞到嘴里,心急火燎地将它点着。第一口总是吸得很深,香烟立刻就下去了小半截。那口烟会在肚子里憋一会儿,然后他才依依不舍地让它徐徐而出。这时候,他的脑袋就锁在烟雾之中,如黄山景物。有时他会被烟呛得咳嗽几声,但咳嗽声又伴着他的嘲讽和笑骂,咳嗽似乎也就不再是咳嗽,而是成了胜券在握的得意,戏弄对手的享受。他咳嗽着,喃喃自语着,骂骂咧咧着,和着弥漫的烟雾,伴着铿锵有力的落子,构成了办公室的独特景观。他也完全沉醉在楚河汉界的世界中了。
其人如在目前,其声似在耳边。这段文字写活了魏填平的生存处境和性格特点,他穷困,他有股狠劲,他聪明,他无奈。直至散文的结尾,作者依旧保持着对这位前同事的距离,但读者又分明能感受到作者的伤感与寂寞:
办公室里依然有人下棋,那种落子时的巨大声响,敲击着90年代的剩余岁月,仿佛是对魏填平遗志的继承,也仿佛是对他未竟事业的延续。
在语言方面,《人生的容量》相比起《书里书外》有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使用方言的频率变高。作者成长于方言环境,身处其中很难对土里土气的方言投以青眼,小时候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普通话:
标准的吐字,悠扬的发音,仿佛仙乐敲击着耳膜,叮当作响。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种感觉就是“惊艳”。马四昌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喊他的名字是从来不带姓的。加上晋城话中没有前舌尖音,“四”便总是说成“柿”,“昌”又做了半儿化的扁平化处理。我们就这样四昌长四昌短地唤着他,早已唤得麻木了。女知青一张嘴,却一下子叫出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
不过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作为日常交流工具的普通话已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反倒是方言会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所以当读者看到《人生的容量》“上编”篇章里的晋城方言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细品它们的含义,甚至想象它们的读音。作者为什么愈来愈有意识地使用方言?我想方言不仅仅是方言,它关联着记忆中的故乡、家园、童年、亲人、食物,关联着底层、民间、地方和个体。所以《奶奶的记忆》和《姑姑老了》里的方言版或被方言化的顺口溜、笑话和儿歌才如此迷人,而即便我们大多数读者不懂晋城老土话,也能在作者营造的氛围中体味到方言的独特魅力。
《人生的容量》“下编”共有八篇缅怀逝者的文章,除上文分析过的《逝者魏填平》外,剩余七篇均是作者在逝者去世后不久完成的初稿(或定稿),最短的只有6天,最长的不超过3个月。以作者对他的老师和朋友们的感情,几天几个月根本不足以抚平内心的伤痛,但为什么要在痛未定之时写下寄托哀思的散文?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奥威尔认为作家身上存在四大写作动机,四大动机因人、因时而异:一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二是“审美热情”,三是“述史冲动”,四是“政治目的”。这里重点谈后两条写作动机。就“述史冲动”而言,我们会发现不仅是怀念师友的这些散文,作者在《人生的容量》整本散文集里都有记录和讲述历史面目与真相的自觉意识。笔者自认为对中国当代史有一定了解,但读《我的学校我的庙——70年代纪事》的“讲用”这一小节时发现全然不知它的意思,而更年轻的读者会不会已不清楚“大字报”和“知青”的含义?所以,仅从记录历史真实面目这点而言,《人生的容量》就有着宝贵的价值。当然,作者深知不可能呈现出全部的真实,他在《蓝田日暖玉生烟——忆念导师童庆炳先生》里写道:
我需要距离,因为距离不仅产生美,而且还能沉淀出真。我也需要寻找写作的契机,因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也许,只有在讲述故事的年代里,那些故事才能被我从容讲述。而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心情和笔法。我只能写出局部的真实,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
但即便现在只能写出局部的真实,作者说他还是想写要写,能写多少就先写多少,这和他期望将来可以从容地讲述全部历史真实的想法并不矛盾,毕竟我们现在身处于一个健忘且仓促的时代。
另一条写作动机是“政治目的”,奥威尔对此解释道:
这里的“政治”是最为广义的政治。渴望推动世界向某个方向发展,渴望改变别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同样,所有书都会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艺术应当与政治无关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我为什么写作》,乔治·奥威尔著,罗爽等译,《奥威尔散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版,P317)
作者悼念的诸位师友既是学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他们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在专业领域内无人不晓他们的大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但作者看到了他们精神上的孤独、沉重。正如他在《出来是完全正确的——忆席扬》里所写的:
读着席扬兄的这些文字,我感到一些安慰。肉体无法永恒,文字却可以不朽。而当那些文字中跳动着一个学人的灵魂时,它们更是有了生命的温度。后人见之,摩挲一番,注目沉思,精神便这样传承下去了。
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是少数的存在,作者不希望他们被湮没被遗忘,所以更要及时地写下忆念他们的文字,张扬他所钦佩的师友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批判精神,而将与《人生的容量》相遇的读者们读过这些散文后,对世界的看法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也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
《人生的容量》“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先生有意与我继续合作,我也希望这只是合作的开始”,希望在写作散文的黄金年龄,作者继续保持“许多时候是我確实想写”的旺盛状态,将“十年磨一剑”缩短为“五年磨一剑”或“三年磨一剑”,赶上甚至超越其学术专著的数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届博士。)